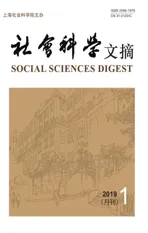政治献金与美国的选举政治
2019-11-17
著名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风靡寰球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在美国,20世纪并不是一个朝着社会正义大踏步前进的世纪。事实上,今天财富的不平等程度要比19世纪初还要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了所谓的“新镀金时代”,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不论是以收入水平还是财富多寡来衡量,美国的贫富悬殊都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许多学者认为,当前美国日益恶化的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对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物质福利进行调整实现缓解。但是,美国的公共政策却一直反其道而行之:最低工资标准长期停滞,实际购买力显著缩水,社会福利项目大幅削减,不断为富人减税。为什么以“民主”自我标榜的美国却不能实施使大多数人获益的公共政策呢?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美国政治结构中分权制衡和多重否决的制度导致了党派极化和政治僵局。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被“金主”和利益集团所绑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治选举的成本越来越高。2016年美国大选支出的竞选资金总和超过了80亿美元,选举成本之高刷新了历史纪录。在这种背景下,候选人自身根本无力负担天文数字的竞选支出,而不得不依赖于外围组织尤其是富豪和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来开展选举。在2012年大选中,奥巴马和罗姆尼的370万小额捐献者提供的资金总和不足159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的献金总和。从选举过程来看,利益集团尤其是商业组织和贸易协会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富豪和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巨额的政治献金,用于反对提高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反对公共财政投入到使普通公民受惠的项目上。有鉴于此,有学者指出,即使从最弱的意义上而言,美国政治完全沦为“金主政治”,“一人一票”的政治原则已经被“一元一票”所取代。
政治行动委员会与直接献金
政治行动委员会是利益集团的政治性组织。对于多数利益集团而言,介入选举活动的最佳方式是以“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向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在2015—2016年选举周期里,政治行动委员会(不包括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共接受了22亿美元的捐献,向候选人捐献了4.7亿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独立基金会”,这种政治行动委员会只能从企业、贸易协会和劳工组织等内部吸纳捐献,与捐献者之间存在附属关系或是与之保持密切联系。在2016年大选中,企业和贸易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超过了2500个,募集和支出分别达到5.65亿美元和5.34亿美元,而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只有289个,募集和支出的金额分别为3.42亿美元和3.32亿美元。另一种是“非附属委员会”,这种政治行动委员会面向社会公众募集竞选资金。除了意识形态或议题组织性质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外,国会议员和其他政治领袖均可成立所谓的“领袖政治行动委员会”募集个人和其他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用于支持其他候选人和政党。在选举中,领袖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如何支配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在2016年大选中,572个领袖政治行动委员会共支出了1.25亿美元。过去十年里,非附属性委员会数量迅速增长。在2015—2016年选举周期里,共有5455个非附属性委员会介入了竞选活动,而2010年时的数量仅有2122个。
政治行动委员会接受的捐献受到《联邦竞选法案》的严格限制,并且需要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自2000年开始,在那些十分活跃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中,对联邦候选人捐献最多的是美国房地产商协会。在2016年大选中,美国房地产商协会募集的捐献超过了1000万美元,并向候选人和其他委员会提供了524万美元的政治献金。在2016年大选中,政治行动委员会分别向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捐献了2.8亿美元和1.9亿美元。总体看来,商业和贸易协会组织的政治献金主要支持共和党,而劳工组织多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金主”和利益集团在选举中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资助候选人的能力。资助金额越多,对候选人的影响力就越大。资助的金额固然重要,资助的对象也同样重要。政治行动委员会在选举中倾向于支持谋求连任的在任者而非挑战者,尤其是政党领袖和重要委员会的主席。在2015—2016年选举周期的参议院议员选举中,包括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内的各种组织向现任议员平均捐献了236万美元,而向挑战者的平均捐献不足12万美元。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与“独立支出”
“金主”和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所谓的“独立支出”对政治选举结果施加影响。联邦选举委员会规定,个人、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和工会可以明确表达支持或反对某位候选人,只要捐献者不与候选人或政党委员会进行沟通且一致行动。在2015—2016年选举周期里,各类“独立支出”超过16亿美元,其中,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独立支出”了10亿美元,政党和个人的“独立支出”也分别达到了2.55亿美元和1.97亿美元。在2009—2010年选举周期里,81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共接受9278万美元捐献,支出了9094万美元。2012年选举周期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激增至1251个,接受和支出的竞选资金分别达到8.23亿美元和7.97亿美元。其中,接近60%的献金来自159位“金主”。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募集的超过10万美元的捐献中超过93%来自3318位“金主”,仅占美国人口的0.0011%。在2015—2016年选举周期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进一步增至2722个,接受和支出的竞选资金的规模更是刷新了历史纪录。对利益集团来说,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数百万美元,同时以“独立支出”的名义介入选举,可以节省许多冗长的环节,如进行咨询、雇佣律师、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为那些试图提供巨额献金干预选举进程的“金主”提供了一个合法而顺畅的渠道。在选举过程中,超级政治行动委员最主要的、最具有影响力的“独立支出”是电视广告,它们用于电视广告上的“独立支出”甚至超出了候选人自身。2016年大选中,利益集团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中贡献了54%的电视广告支出。在2016年国会选举中,绝大多数的选举广告都是由利益集团资助的。在一般情况下,捐献位于前列的“金主”往往会支持多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且同时向政党和候选人输送政治献金。如在2011—2012年选举周期里,金沙集团董事长谢尔登·阿德尔森和米里亚姆·阿德尔森夫妇共向八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献了4382万美元,并向政党委员会和候选人捐献了367万美元。在2016年大选中,阿德尔森夫妇又投入了超过2000万美元为特朗普助选。
政治非营利组织与“暗钱”
政治非营利组织即“501(c)组织”,是指根据《税收法》第501(c)款规定成立的享有税收豁免权的组织。这类组织不是政治性的,但是可以从事、开展非党派的选民登记和投票动员活动。政治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活动时隔很久才会对外公开,且没有公开其捐献来源的法律义务,可以使利益集团在不受公众关注的情况下影响政治。因此,它往往被称为“暗钱”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政治非营利性组织多是掩盖利益集团用金钱干预选举的“皮包公司”。它们多数只有少数的雇员,甚至是完全由志愿者组成。根据“响应政治中心”的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美国政治选举中“暗钱”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了11.5亿美元。社会福利组织和贸易协会组织是最为活跃的“暗钱”组织。在2015—2016年选举周期里,社会福利组织和贸易协会组织分别支出了1.45亿美元和3200万美元。在2012年时,社会福利组织的“暗钱”支出甚至一度达到了2.57亿美元。政治非营利组织之所以饱受批评,是因为很难追踪这些组织接受的献金总和及其是如何支出的。联邦竞选法律规定,政治非营利组织参与的某些政治行为不需要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只需要报告直接的政治行为即可),但是需要向国家税务局和劳工部门报告,然而,有的“暗钱”组织根本无视这些规定。政治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报告都是年度报告,报告中往往对支出含混其词,如多使用“媒体服务”或者“电话咨询项目”等模糊性表述,并且所谓的“教育性”和“组织建设”的支出也不需详细说明。与此同时,多数政治非营利组织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的金额远远低于真实数据。例如,“十字路口GPS”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它在2011—2012年选举周期里仅支出了7100万美元,但是据内部人士透露,实际上达到了3亿美元。政治非营利组织还经常利用联邦选举法律上的漏洞支付网络广告、邮寄广告,尤其是在广告制作和电视广告方面的大笔开销往往根本不会进行报告。
“527组织”和“竞选通讯”
利益集团不仅寻求避开捐款数额限制的方法,而且想方设法通过其他组织形式参与竞选活动。除了上述几种较为常见的形式之外,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527组织”和以“竞选通讯”的形式影响选举。“527组织”是指《税收法》第527款规定的享有税收豁免权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以影响联邦选举为主要目标,可以自由地募集选举资金,但是需要向国家税务局报告捐献来源和支出信息。在选举过程中,“527组织”主要通过选民动员和投放议题支持广告介入选举,不得明确呼吁公众选举或不选特定的候选人,不能在初选前30天或大选前60天进行广告宣传。2008年,“527组织”募集的捐献额度约为5亿美元,2014年超过了7亿美元。从最近几个选举周期来看,由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政治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和活跃程度的剧增,“527组织”的重要性已被大幅削弱,“吸金”能力有所下降。
利益集团影响选举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竞选通讯”的形式动员雇员或者成员。1971年《联邦竞选法案》及其修正案规定,企业和劳工组织可以向受到严格限制的个体就任何主题进行沟通,包括对选举表达支持或反对任何联邦候选人。这些沟通所产生的费用在每场选举中如超过2000美元就必须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推翻了对竞选通讯费用的限制,解除了此前对企业和工会组织花费自己的资金进行竞选通讯的禁令,导致利益集团联系组织成员或公司雇员的通讯费用支出不受限制。商业和工业性质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直接联系其雇员方面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在美国,年轻选民更易于接受来源可靠的出自私人部门的信息,而最可靠的来源就是雇主。在与选举相关的通讯发布之前,利益集团就已经与其成员之间建立起了密切联系,而不仅仅局限于讨论选举本身。在2012年的联邦选举中,约有2000万美元用于所谓的“竞选通讯”上,2016年时进一步增长至5600万美元。
结语:被金钱扭曲的美国政治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进入了所谓的“新镀金时代”。虽然美国工人的平均生产率翻了近一倍,但是薪资水平却陷入了长期停滞。社会流动性也越来越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及其后爆发的“占领华尔街”和“民主之春”等持续不断的抗争运动都清晰地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社会表达出失望和不满,社会不平等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美国富豪和利益集团通过提供政治献金,以多种形式影响和干预选举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向党派和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的绝大多数亿万富翁在向政党和候选人提供献金方面十分活跃;而占美国人口1%~2%的百万富翁群体在大选中同样活跃,平均捐献了4633美元,远远超过普通美国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政治献金的最明显的结果是让那些对富人友好的候选人当选,并在候选人赢得选举之后获得接近他们的渠道。政治献金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还体现在,那些知名度低的竞选者鲜有希望击败在任者,除非他们能够斥巨资大幅提高自身的知名度,或与选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那些关注度不高、选民投票率低的初选中,竞选的早期资金对雇佣工作人员、引起友好媒体关注、联系选民和动员支持者进行投票等方面更是非常关键。客观而言,金钱不是赢得选举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许多学者都发现,美国的选举制度中存在明显的“金钱预选”现象,即候选人必须首先募集到一定数量的竞选资金,以证明其有足够的能力开展选举。媒体对候选人筹集资金的报道有助于强化哪位候选人事实上有机会赢得选举的舆论认知。选举中必须筹集充足的资金已经成为一种“过滤器”,它将那些富豪无法接受的潜在候选人排除在外。“金主”通过控制候选人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着选举结果,进而影响公共政策。“金主”还可以通过政治献金塑造民意,这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对政治的认识和公共政策的选择。“金主”编织出的意见塑造网络与慈善基金会、大学、智库、政策咨询团体和蓝带委员会的紧密联系,这些机构的资助者和领导往往是富翁和行业精英,它们共同提出政策理念、发布报告和向国会提供证词。
在最近几次大选中,最大的“金主”是支持共和党的亿万富翁科赫兄弟,他们成立了一个由保守派亿万富翁组成的庞大网络,即“科赫网络”。在2012年大选中,“科赫网络”向共和党候选人捐献了4亿美元,并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再次支出了3亿美元。在2016年大选拉开帷幕之初,“科赫网络”计划投入9亿美元介入选举。“科赫网络”全部的预算支出十分庞大,以至于其在大选中的支出超过了共和党自身,这足以证明其对政治渗透之深。数据显示,共和党倍受“金主”和利益集团的青睐,但民主党也有自己的幕后“金主”。支持民主党的亿万富翁在很多议题,如女性、同性恋和平等对待非裔美国人等问题上秉持自由倾向,但是对消除高度经济不平等的公共政策问题态度冷漠,甚至与支持共和党的亿万富翁的立场十分相近。
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美国社会众多的利益集团可以保护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利免于多数人的威胁,起到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然而,在美国当前的选举政治中,判断候选人是否有望胜出的首要标准不是选票或者公众支持,而是金钱;这些金钱不是来自所有选民的公共资助,而是来自极少数人的私人献金。无论是民主党候选人还是共和党候选人都极度依赖“金主”和利益集团,尤其是商业贸易集团提供的巨额政治献金,故而在他们当选之后关心和维护的还是富人尤其是亿万富翁的特殊利益。由于富人尤其是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往往与普通民众存在截然不同的政策偏好,致使普通美国人的利益和诉求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与普通美国人相比,富人和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对政治尤其是对选举的资金投入,将经济优势转化成政治权力,利用政治权力维护经济利益,推动为富人减税的公共政策,阻止任何旨在削减经济不平等的公共财政支出或管制的努力。在这种背景下,政治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不平等,选举政治被金钱严重扭曲,最终形成了当今美国“不平等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