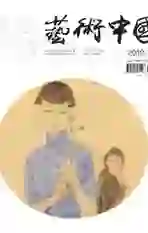消夏记趣
2019-11-16唐吟方
唐吟方
这些年每年都会收到友朋送我的自印本,多数是有关某家族的历史,老辈的书信集、纪念集、个人诗文集等等。这些单行本看起来是小众的读物,倘如从放宽历史的视野来考察,则是今后回望历史值得投去关注的文献,不仅因为书中贮藏的信息是公开出版物中不易见到的,历时既久,可能还是难得的珍本,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这样的印本,数量往往有限,加上流传过程中的损失,存世偏少,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我印象中上海的周退密先生以往每年都会印“诗历”,时间以年为限,期年印制一本,收录当年所作的诗词。像退老那样的做法,其实是以诗历作日记,要了解退老的交游情况,“诗历”显然是很重要的佐证。但话要说回来,有多少人能面见退老并获得这类自印本?
说起自印本,我知道的徐志摩最早的一本《志摩的诗》(线装本)是委托中华书局印行的自印本。吾乡的另一个前辈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也是个自行本,但他以“绿杨堂”的名义出面。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家们惯用手法,鲁迅也以“三闲书屋”之名自印过杂文集。而吴吉芳的《白屋吴生诗稿》则没有用任何名义,大概是自印本中最纯粹彻底的一种。在下的《雀巢语屑》最初的两个版本都是自印本,一种由友人富阳羊晓君印制;另一种由吾乡张建仑兄印制的,张本还配有插图。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吴战垒先生正是看到我的自印本,才约我在自印本的基础上扩充成书的。
友人卢为峰则收藏了为数不少上世纪50年代后的自印本古体诗词集。当时这类诗词集由于其内容太私人化,无法为出版社接受,然而这些集子在特定圈子里仍有交流传播的需要,大多数作者最后以自印的方法传世。如果要梳理20世纪古体诗词史,这些自印本则是不能轻视的文学遗产。据我所知道张伯驹和他朋友圈合作的掌故集《春游琐谈》最初也是以自印本的形式出现的,如今这已是读书界闻名遐迩的“名作”了。
暑天酷热,坦腹陋室,捡出几本旧书重读,一些人一些事忽忽浮上眼底,感慨不已,顺便在书边记下一点所感所思。
忆明珠《小天地庐题画》,自印本,无版权页
据编辑者杜海的跋文,大致知道,这是为忆明珠先生九十岁寿辰印的一本纪念集。忆先生对自己的题跋文字一向不在意,随作随弃,偏偏夫人蓝桂华非常珍惜这些零金碎玉,平日代为搜集抄录,才有了这本《题画》。忆先生晚年除了日记、书信,很少写文章,如果说有,大概就数题画诗了。诗人本色的他用短句记录他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或许与文艺无关,也或许有关,琐碎的和滋味寡淡的,都构成他生命最后的章节。我记得他晚年刻过一方闲章,叫“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尽管是闻一多的诗句,但仍然能嗅到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人生实苦”的况味,那里藏着他书香人家的底色和作为诗人深沉绵渺的哲思,以及走过风风雨雨的感叹。
题画印出来后,他曾寄过一本,上面照例用小字写上上款,钤上的却是他本名的印章。2019年3月中旬,我和朱永灵兄的书画展在南京博物院举办。金陵繁华依旧,忆先生却不在了,故地重游,令人倍感忧伤。
我们的展览2019年3月9日開展,当天下午,与吴东昆兄去黑龙江路汇林绿洲广林苑看望蓝桂花阿姨。忆老的公子赵文石正巧也在家。我们谈起忆老的日记,我问文石兄是否整理了。他告以已在整理。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把日记整理出版出来,这是忆老留给世人最后的文字帐,那里应该有我感兴趣的江苏作家群的交游信息。忆老经历过肚带营时期和汇林绿洲时期,前者是江苏省作协的宿舍,他的左邻右舍都是江苏有名的作家和诗人。蓝阿姨引我们去看忆老的书房,陈设一仍其旧,那张书桌上放了一本《圣经》,骨灰放在书架的中间,上面还放着忆老的彩色大照片。在我的请求下,蓝阿姨从书柜底层中取得几册忆老生前手写的文稿,摊开看,有书信稿、文录与自用印集,里面有修改的痕迹。熟悉的字迹、熟悉的语气。蓝阿姨说这是忆老生前删改过的稿本。
我们回到客厅,蓝阿姨说:以前你来我家总要吃一顿饭,今天的晚饭也在家里吃吧。是的,我往常来忆老家,总要吃一餐饭。今天的饭菜依然是蓝阿姨下厨做的。但我坐在餐桌边,有点神不守舍,时间带走了我们生命历程中很重要的一些人,如忆老,愔然。
临走前,蓝阿姨拿出《小天地庐题画》送给吴东昆,我也要了一本。
《来自田间——马士达太仓生活三十年追思纪念集》,邓石治编
此书是王亚东兄见赠的两种图书之一。
马士达先生生前,我与他薄有交往。20世纪90年代我发心要按地域写写四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篆刻家。当时了解一个印人的情况,除了收集报纸、展览等公开的信息,向知情人请教,最直接的就是登门拜访。某次到南京,由朱永灵兄陪同拜访过马先生,这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马先生给我的感觉真率朴实。把我们让进屋里后,落座泡茶,就拿出一大叠书法条幅给我们欣赏。他把条幅摊在床上,亲手一张一张翻给我们看,然后坐在床边的八仙桌上聊天。他抽烟我们喝茶。印象中他的行草形式上有点儿日本书法的意思,我好像表达了“这是篆刻家的字”的判断。从马先生的眼神看得出他对我的评价并不满意。
马士达是太仓人,求学于姑苏沙曼翁先生,因一艺之长,获选80年代初上海《书法》杂志全国篆刻评比一等奖,随后受尉天池先生的提携,以一个工人的身份登上大学讲堂,这在当时颇为罕见,属于因艺术而被社会见重的一例。他写过一本《篆刻直解》,从实践的出发谈篆刻,其中的见解,大概夹杂着他的创作心得与同时代师友交流所得的看法,可惜这本书的发行量大小,现在已见不到。
身为苏南人的马士达,篆刻用刀极其生辣,到后期甚至出现以生求生的现象。他本人篆刻创作风向上的转变,以我的理解,早期与苏南交游圈有关,交游圈的艺术趣味,直接决定他的艺术品味,故早期的篆刻趣味是江南的。到南师大任教后则受整个艺术界风气的影响,突出反映在对于刀法张力和印面视觉形式的追求。时代曾经非常眷顾他,但在一个风云激荡、观念横行的时代,一个艺术家拥有更大的舞台后,他的心理空间是否跟着壮大?就成了考验一个艺术家的心力是否稳定的标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背景下,大约不可能再产生马士达这样的人和艺术。
这本纪念集和所有同类性质的集子一样,有文献价值的文字太少。读这本集子感受到故乡人对他深深的牵挂,感人至深。在某种意义上,走出太仓的马士达,最后在精神上仍属于太仓。
《徐行恭致周退密翰札》,2010年午社刊行
午社是杭州几个青年画家组织的一个画人团体,他们组这个艺术团体,是受了民国时诸闻颖、张书旂、潘天寿等人“白社”的影响。后来团体成员的艺术趣向裂变,午社就蜕变成今天的“西湖画会”。西湖画会的核心人物有金心明、章耀、陈经、余久一、吴涧风、凌中翔六位。他们除了联合国内同好者连续举办带有文人倾向的画展、金石书画收藏展外,最值得称道的是以“西湖画社”画会名义印行的老辈书信集,可以看到这群画人的文化志趣,《徐行恭致周退密翰札》就是其中之一。
徐行恭担任过北洋政府财政部司长,后来受陈叔通之邀回杭州出任兴业银行行长。他虽然做过北洋政府的高官、银行家,却是做诗填词的行家里手,姜亮夫称其为“浙东名宿,一代詞宗”。
像徐行恭这样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满肚子的学问与掌故,一辈子除了填词和知友通信,不写正经文章。要了解那一代人的情况,书信是绕不过的文本。这本集子收录三十通书札,从1981年到1988 年,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八年,老先生们由于统战的关系,重新被启用,恢复政治待遇。读徐行恭的书信,从书信里能探知他们当时的生活、交游、海外关系以及延袭传统的老年娱乐。书信中既有徐以历史见证人对流行说法作出的纠正,也有友朋之间探讨印行个人诗集等琐事——书信文字记录了那个时代沪杭宁一带高龄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活与交流活动的片段,弥足珍贵。
这本薄薄的集子大概只是徐行恭晚年所写书信的绝少的一部分,却是考察那辈人生活不可忽略的文字。徐先生不是书家,笔迹自有特点,工谨稳厚,集子全彩印,印得朴素雅隽,溢漾着淡而弥浓的书香。
朱琪《朱琪论印文集》(初编)2009年梦石居自印本
朱琪是南京年轻的印学研究者,对“浙派”印人蒋仁有颇深的研究,写过蒋仁家世、生卒年、字号斋室名、交游考等系列文章,还对目前流传于世的某些蒋仁印章作过考辨,他的工作廓清了印学史上面目模糊的蒋仁。
关于浙派、蒋仁的艺术成就,印学史上已经有定论。蒋仁在晦显不明通过勾沉史料获得的印学史上是个小众人物,“浙派”中的两位先行者丁敬蒋仁都是平民,生活清贫,不过就是他们却一手造就了印学史上的一个高峰,他们的印风和印学观念影响历久弥远,差不多绵延了三个世纪。有关蒋仁的新文献还在发掘中,可以预料蒋仁研究随着零星文献的呈现,会走向深入,但不影响我们对蒋仁及其艺术的整体判断。不过朱琪的研究,显示在印学界“浙派”仍受关注,并持续有成果涌现。
朱琪的论印文集经打印装订成册,制作成本颇高,因为这重关系,这本集子的印量大概不会太多——我推测在十册之内,故愈加显得珍贵,何况还是作者的签名本。
集子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其一,封面书名集字取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摆印本《红楼梦》(程甲本);其二,书的扉页辑录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文字:“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订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其三,本集版权页上写明:欢迎有心人提供有关“西泠八家”相关图文资料,以供研究之用,征得足下同意引用后,著者将注明资料来源,以志鸣谢。其二、三文字除了示明作者的治学态度外,还希望与关心浙派的同好有交流,而其一仿宋体书名集自乾隆《红楼梦》本,说明作者是好古的雅士,大概还好研读古书。
《种瓜老人研究集》(邵川编),2001年种瓜轩自印本
种瓜老人邵子退,是林散之的总角之交。林散之成为研究对象后,邵子退跟着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当年新华社记者古平采访林散之,老人特意要古平到乌江去访问邵子退,邵是草圣的见证人,最能说清楚林散之的来历,而且珍藏着大量草圣的手稿、墨迹。老一辈的友谊延续到第三代,子退的文孙邵川前几年又借助丰富的家藏,做了一本迄今为至最翔实的《林散之年谱》。
今天我们说起林散之,无法不提邵子退。仿佛邵子退是林散之研究的一个章节,《种瓜老人研究集》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品读出它的味道来。
集子收录邵子退诗稿、草圣赠子退诗,尚有时贤题咏一部分。邵子退和林散之诗的价值,以谢冕的说法,证明了“布衣友情”的存在。一位是名重天下的草圣,另一位是啸傲于林泉的布衣,在世情淡薄的今日,林邵之交超越了世俗的意义,读他们的酬答唱和,感受到了文学史中那种令人一唱三叹的“交谊”。这本集子里的“时贤题咏”,我原以为只是当代古体诗词界应酬的一个范本,逐页读过后才知道作者里头隐藏着不少社会贤达——如张联芳、王瑜孙、唐大笠、周退密、王退斋、丁芒、吕学端、马祖熙、王钟琴、邓云乡、费在山、高锌等等,在白话文弥漫的现实世界里,还有一批究心于古诗词写作的诗人,要不是邵川的网罗,我们大概很难有机会看到他们的文字踪迹。这也许不是编者的初衷,但它确实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别样的阅读样本。
在我熟悉的友人中,有两位名人之后专注于先人事迹的研究,邵川是一个;另一个是南通的尤灿,今天尤无曲老人广为人知,与尤灿的努力推广分不开。
苏斌《听风楼文存》,2018年中国艺苑出版社
苏斌是个不折不扣的雅人,交往面之广,令我眼馋不已。他又善属文,文字淡雅从容,写的都是与自己有关的艺文日常,由读书、淘书、作文串连起来的书生活,书香绵绵。他的文字每隔几年就会结集一次,这一点颇有一些民国作家的风范。许多年前苏兄曾印过《听风楼散叶》,这次的《听风楼文存》仍是厚厚一本,收入书评、读书笔记、作家通信、日记等等。有彼此两个封面,一面由苏州作家王稼句题签;另一面题签出于拙手。目录也是两个。一个文,一个艺。艺文交融,在很大程度上映照出他读书的兴趣点。
我与苏斌只在一次偶尔机会中匆匆见过一面,交往大多数时候靠通信。他的公子非常优秀,留学归来在北京发展,苏斌有时也来北京小住。我之所以不敢见人,是海宁人的颜值担当,从民国开始一直到现在,都给那个“大闹一场,悄然离去”的徐志摩霸屏。像我这样的容颜,走出去很容易拉低海宁前贤辛苦积攒起来的颜值。体味先贤的成就,老老实实呆着,实是对前贤最好的礼敬。
我曾预言现在处在边缘的自印本,只要内容好看,将来一定会受读书界重视。苏斌的难得,是他只做少量(数百本)的自印本,而且目前他示人的都是自印本。借用某个经典语式来表达:做一本自印本容易,难的是半辈子或一辈子都在做自印本。这就构成了他与书的自有风景——一个写作者这样做,除了有自己的态度,多半珍惜自己的劳作,希望文字以原生态的面目呈现给读者。
人生漫漫路,冷暖只有自己知道,读书著书印书莫不如是。苏斌坚守自印本,我以为个性十足。他的“中国艺苑出版社”令我想起黄永玉在香港注册的出版社,只为方便出自己的书;另一个是周昌谷妹夫戏曲学家陈朗在台北注册的朗素园书局,也只为满足一个人的兴趣。苏斌的“中国艺苑出版社”显然和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
2019.6.26.北京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