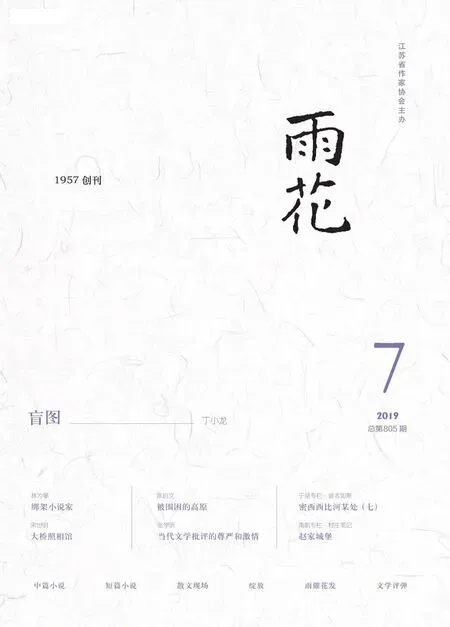让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2019-11-16安宁
安 宁
你要去哪儿?他一边拨打电话,一边飞快地问她。
我要去给女儿买一双运动鞋,明天一早她要跟爷爷奶奶飞老家。你呢?她盯着马上要跟人通话的他,有些不安地回道。
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没有选择电梯,而是避开文艺晚会审核会后混乱的人群,从四楼昏暗老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下去。
自从辞职离开这家演艺团体后,她已两年没有到过这里。一切看起来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每个排练厅里依然乱糟糟的,四周到处是散乱堆砌的舞台道具。一个石膏制作的裸体女人雕塑,倒立在墙角,将饱满却陈旧的小腹,不知所措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就在他们审核节目的过程中,不断有钢琴声,从天花板上雨水一样渗透下来。那琴声时断时续,每一次停下,她都以为会永久地不再响起,但隔上十几秒钟,琴声又犹豫试探着,继续滴滴答答地从四面八方流淌下来。以至于她总是走神,而恍惚的视线,又无一例外地落在他的右手上。那是两年前,她曾经亲吻过的手。
喂?喂?听到我声音了吗?可能我这里信号不好,在楼梯拐角走着,你稍等一下。
他的脸上,有些焦虑。她瞥见他看了她一眼,转而又朝窗户看去。窗户是洞开着的,其中一扇裂了长长的一道,那缝隙凛着一张脸,直通向锈迹斑斑的把手,又像一道闪电,面目模糊地指向外面虚空的天地。
他终究没有在那扇窗户旁边停下,又继续旋转着下楼。他的脚步依然是飞快的,像他说话的语速。两年未见,它们似乎更快了一些,以至于让她心慌,不由得也加快了步伐,紧跟着它们,有些晕眩地旋转而下。
下午几点见面?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一楼的大厅里阳光炫目,她看着门外耀眼的盛夏的阳光,忽然间有些紧张。
呃,现在是12 点钟,我一会儿就回家给女儿做饭,她妈妈出差了,然后三点我要送她去学舞蹈,那么四点?好,就这样。
他们在大厅的门口,一起停了下来。
我送你吧?他脸上写满了不知是歉疚还是期待的表情,她一时间有些判断不清。
不用,你去忙吧,我自己在门口打车就行。她慌乱地回他。
一个旧日的女同事,甩着钥匙链,颠着浑身的肥肉,快乐地朝他们走来。
嗨,走吧,跟我一起,我送你回去,正好顺道。女同事笑着向她邀请。
她忙忙地摆手,不用不用,我不回家,还有别的事要做,你先走吧,谢谢啊。
于是她和他站在门口,微笑着目送女同事离开。有那么一刻,她觉得他们好像一对送别客人的夫妇。这样一个突然闪现的想法让她忍不住想要笑起来。
他似乎敏感地捕捉到了她的笑。是这抹并没有流淌出来的笑意,让他恢复了昔日的霸气,于是他的语气里,就有了一丝不容分说的命令。
走吧,我送你。
她无法拒绝,也不想拒绝。
一脚踏出门,阳光便夹着让人头晕目眩的火星,重重地砸下来。她的脑子轰隆隆响着,头发也似乎嗞嗞拉拉地燃烧起来。不,是她整个的人,都被一团突然降落的火焰燃烧起来。这火焰让她想要快步逃掉。
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最高温度37度。但她怀疑预报天气的人为了安慰,撒了善意的谎言。从门口到停车场,不过短短的二百米,她觉得自己快要蒸发掉了。
这翻滚而至的热浪,让他们彼此没有话说。当然,她也找不到说话的机会。他不停地低头看着手机,听着因为一上午关机没有联系而爆满的一条又一条语音。那些语音,也是迫不及待的。
你在哪儿?怎么一上午都关机?有事找你!
那个项目千万别黄了,资金链快要断了!
老大被查了,我们的电影怕是开拍不了了!
她忽然替他着急,想着不如掉头离开算了,明明是十分钟的车程,她拦一辆出租就可以到的,为何还要麻烦他送?而且他们已经结束,两年不曾联系,这次偶然相逢,又能怎样?既然不能怎样,那么,这十分钟的陪伴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不是同事急需评委,又到处找不到人,她原本是不想来参加这次节目评审的。她当初从这家单位辞职后,就没有打算再回来。她对旧事、旧物或者旧地,向来不喜欢重提或者重游。旧爱也是。她并不觉得这是自己无情,相反,她无比珍爱所有人生经历,所以她将它们全部封存在心底,再不打扰,并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过往的尊重。
如果那天拒绝了同事,那她肯定见不到他。见不到他,也就不会这样头顶着一团火,急匆匆地走向停车场,只为了这一场相见,能够再延长短暂的十分钟。
他是被她的另外一个旧日同事邀请来当评委的。他当然也不知道会有她出现。所以当她跟前同事们逐一热情地打着招呼,忽然在人群里发现他的存在时,他们彼此都惊讶得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好。
你也来了?她脑子里一团混乱,停了足足有一分钟,才说出一句话来。
是啊,真没想到你也会来。隔着一个总想插话进来的女人,他笑望着她。他们谁都没有伸出手去握住对方,好像心照不宣,知道这样会打破美好的距离,让人生中的这一场意外相见,变得疏离。
为了评审公平,评委需要抽签选定座位顺序。重回旧地,又相逢旧人,她一时间有些紧张,胡乱抽了一个,打开,看到上面写着1 号。她听见他在旁边柔声问她,我是2 号,你呢?她竟然有些羞涩,好像初次与他亲吻,她闭着眼睛,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迎接他的深情。于是她一低头,什么也没有说,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他当然紧跟着走过来。坐定后,她听见他笑着说,今天是上天故意安排的吧?她也笑,或许是吧。
如果没有一上午的时间,坐在一起,用眼神或者低语交流对节目的看法,让这样的相见变得更温情一些,她还会在结束后,假装看手机,等他与人告别后一起下楼吗?而他又会不会在如此忙碌中,还要坚持送她?她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气冲荡着,思绪有些凝滞,直到他的车门打开,她坐进烤箱一样的前排座椅上时,想起他的那句话:今天是上天故意安排的吧?或许是吧,她在心里,再一次这样对自己说。
你说的商场怎么走?他一边将空调温度打到最低,一边问她。
她叹口气,你在这个城市待了十多年,还不知道路吗?
你知道,我很少逛商场的。
好吧。她打开手机导航。导航上显示只有十分钟的路途,如果不堵车的话。
她当然希望堵车。她觉得每一分每一秒似乎都变得无比珍贵,她几乎可以听得到秒针啪嗒啪嗒快速向前的声音。
这想象中的声音,像一双马不停蹄赶路的脚,将她吵得有些焦虑,于是她轻微抱怨他道,其实你真的不用送我的,这么近,我走着都可以过去。
我只是想和你说会儿话。他将再一次响起的手机轻轻划掉。
可是你那么忙。她的声音里,有一丝的悲伤,她一时间不知道这悲伤是源自自己,还是他。或许,跟他和她都没有关系。
堵车。车流像一条被烤焦的蛇,僵死在滚烫的马路上。
车里的温度,慢慢降了下来。她的心,也在这细细流淌的清凉里,如一片水中的茶叶,开始慢慢舒展。
这几天真热。她说。
是啊!我几乎不想出门。说完,他又有些不放心地,看了一眼空调是否已经调到最低。让人舒适的凉风,将车窗外炙烤着的一切,映衬得犹如一个虚幻的梦,明亮,耀眼,飘渺。
每年夏天,我母亲都要抱怨,生我的时候,她快要热死了。还好我那时没有记忆,我估计自己也是半死不活的状态。她说完忍不住笑起来。
他也笑,但很快止住了:你的生日,刚刚过去四天,对吧?
她吃惊,忽然想起来,你的生日,是不是也刚刚过去?
不,恰好今天,我们两个人的生日,相差四天。他的语气,依然是平静的。好像这是一个如此平凡的日子。
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伸出手去,握住了对方。
我们一起吃午饭吧,我请你。她带着过去他们相爱时的撒娇的口吻,对他说。
可是女儿一个人在家,这会儿,她怕是饿了……
他的女儿才刚刚9 岁,她知道这样有些自私,她也知道他很为难。但她还是试探着说道:要不,我们快一些吃,给她捎一份回去?或者,直接叫一份外卖?
他没有回应她的提议。她也马上否定了这样的想法。但她还是觉得遗憾,不知究竟是对自己还是对他忧伤地说道,可今天是如此特别的一个日子。
或者下午,你有时间吗?他犹豫着问她。
这次为难的成了她。下午我要陪女儿,她明天就要走了。说完这句,她不知为何,心里疼得厉害。那疼是从心口慢慢扩散开的,好像被什么给刺中了,有鲜红的血汩汩流淌而出。她觉得周身发冷,身体似乎沉入了一个无边的深潭,她很想抓住一些什么,可是四周全是无尽的空。
她在这冷嗖嗖席卷而来的空茫中,听见他说: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说会儿话吧。
如果不是再次相遇,她快要将那些与他相爱的细节给忘记了。世俗的生活总是那样强大,以至于她永远无法与其对抗,或者背道而驰。她想起来,他们约好分手的那天,也是七月,就像他们的第一次相识。
让我们回到各自的生活中去,以后不要联系。她拥抱着他,安静地说道。
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深深地吻她,似乎想要将整个的她都吸进他的身体里去。
之后她忙于生活,忘了许多的事情,却惟独记得这最后的吻。似乎,这个吻从未消失,一直在她的身体里,完好地珍藏。
她是怎么与他相遇的呢?她觉得这一点都不重要。甚至包括她为什么爱他,也无关紧要。她只是在行走的路上,恰好遇到了他。他们志趣相投,对舞台有着同样的痴迷,只不过她用剧本呈现,他用演出呈现。他们都有家庭,并各自为了家人承担着重负,但这也没有什么。那么什么才是她最为关心的?她想了许久这个问题。后来有一天,她在厨房里,忙着为上幼儿园的女儿做饭,她将鸡蛋打碎,放入葱花、火腿丁、胡萝卜丝,然后用力搅拌均匀,倒入平底锅。她看着鸡蛋在加热的油中慢慢蓬松,完美地打开,伸展,轻微地颤动,像一个女人性爱中轻柔的身体,直至最后,那些水一样稀薄的液体,变成柔软鲜嫩的金黄。然后她将鸡蛋盛入盘中,又取出面包片,夹一些进去,递给小鸟一样早已张开嘴巴的女儿。
她看着女儿幸福地咬下一口,而后立刻蹙眉,冲她嚷:妈妈,你又忘了放盐!
就是那个瞬间,她忽然明白了他在她心里的位置。是的,她爱他,他也爱她,那爱是生命中的盐。现在,盐没有了,可他们还是要继续行走下去。只是,不能同路。
此刻,她又遇到了这一粒晶莹剔透的盐,他在盛烈的阳光下,熠熠闪光。而她,则像一个孩子,忍不住想要靠近了,再重新品味一下那一粒盐的滋味。
他要带她去哪儿呢?她没有问,他也没有说。或许他们都不知道,只是任由车在车流中缓慢地向前移动。
手机导航还在导向她原本要去的商场。那机械化的直指终点的声音,似乎时刻都在提醒着她,这一场相遇,不过还有十几分钟,就要终结。她的身体因此有些紧绷,有那么一刻,她看着汽车向前滑动了一米,几乎想要跟他说一声再见,而后转身下车,一个人穿过太阳下的车流和人群,去往前方那片喧哗的属于她的日常生活。那里蒸腾着一种野蛮的力,她在那股强大的力中,独自行走了两年,没有欢欣,也无悲伤。她从不曾上岸,也不想上岸。
可是最终,她只是打开手机,将导航关闭,而后笑着问他,你这两年在忙些什么?
他凝神想了片刻,才缓慢说道,拍了一两个片子,都不如意,人一失落就容易迷信,于是找人卜了一卦,说我事业正在低谷,不宜开工,于是干脆休整半年,这段时间正集中看一些经典电影,算是给自己充电。你呢?
她看着窗外一个中年女人提着一大袋土豆和西红柿,飞快地穿过马路。那塑料袋很薄,她于是担心,它会忽然间撑破,或被烈日晒化,那些土豆和西红柿,便会瞬间冲破束缚,欢快地在大马路上撒欢。紧跟女人的,是一个头发稀疏、大腹便便的男人,他倒背着手,慢吞吞地穿过一辆又一辆车。经过他们车前时,男人突然好奇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好像她的脸上写着一个不可示人的秘密。她于是脸一阵红,低下头去,然后发现她的左手,正被他用力地握着。
她的脑子里飞快地回忆着最近两年自己的经历,似乎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一切都在琐碎的日常的河流上,泛着惨白浑浊的光。她甚至可以想象,在此后的很多年,她都将这样平淡无奇地度过,没有波澜,也无风暴,是一马平川的庸常人生。
她注视着马路右侧,一个在等公交的肥胖的女人,佝偻着腰的衰老男人,和举着房产广告牌眼神空洞无物的推销员,叹一口气,回道,能有什么变化?不外乎还是老样子,给人做嫁衣,为一个个上演的剧目奔波劳碌罢了。
他们谁都没有再说话。汽车不停排出的尾气,与无数行人呼出的废气,以及两边商店里空调抽出的热气,大大小小饭馆里涌出的油烟,缠绕着,蒸腾着,融混在一起,又经阳光的折射,散发出奇异的绚烂的色泽。
有那么一刻,她被这半空中升腾的虚幻的热力给吸引住了,她想象着自己也破窗而出,被太阳融化成它们中的一个分子,在热风中飞舞,旋转,上升,直至脱离世俗的虚空世界。
车流开始松动,马路变得开阔起来。他松开湿漉漉的手,转动方向盘,然后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她说: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可是,哪儿有安静的地方呢?她在心里回应他说。她知道他也是心底空茫,不知该将车开往何处。这个原本熟悉的城市,在他们的眼里,忽然间陌生起来,那些寂静的林荫小路,行人稀少的偏僻街巷,古老破败的城墙,似乎全都奇怪地消失在盛夏的暑气之中。于是,整个城市只剩下喧哗。到处都是拥挤吵嚷的人,到处都是劈面而来的高架桥、商场、饭店、银行、菜市场。他们的车,只能在这些夹缝中艰难地穿行。而且,它们永无休止,以一种无法逃脱的巨大的让人窒息的力,将他们紧紧地裹挟着,通往没有绝灭的空。
在终于穿过一条拥堵的十字路口后,他将车拐向一条植满粗壮法国梧桐的小路。她知道他们最多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短暂的时间,又能做什么呢?连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都觉得奢侈。她当然也不希望去咖啡馆,那里面对面说话的感觉让她觉得陌生,好像他们从未有过亲密的过去,又好像一切都已云淡风轻,彼此都可以相互忘记。她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在第一眼看到他的瞬间,她的心里轰然一声巨响,让她知道一切的放下都是自欺欺人。那么绕着整个城市的马路,一直将车这样开下去?听起来又有些悲伤,好像他们是被抛弃的无家可归的恋人,她与他只能在堵车的间隙,彼此握一下手。即便这样短暂的温情,也常常被各自手机里响起的铃声打断。
就在片刻之前,他接到女儿的电话。他将声音调到外放,她听到一个声音稚嫩的女孩在冲他撒娇:“爸爸,我做完了作业,有些饿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人家肚皮都贴到后背上去啦!”
他笑着安慰女儿,丫头,你先吃一些我早晨放到茶几上的水果和点心,爸爸一会儿忙完就回去了。
女儿再一次确认,不许骗我哦!
他笑出声来,傻瓜,怎么会?
她听了有些着急,真希望现在就放他回家。见他挂了电话,她握住他的右手,温柔地抚过每一个手指,而后深深地,将两只手扣合在一起。她最终什么话也没有说。说什么都是无用的,她想。她唯一期待的,是尽快地找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倚靠在他的怀里,细细碎碎地说一些什么。至于会不会有她怀念的亲吻,她还没有想过。
那条小路的两边,停满了车。他将车开得很慢,可依然没有等到有一辆车开走,空出车位。在快要驶到尽头时,一个肥胖的男人慢吞吞地走向他的奥迪,又费力地打开车门,将整个人硬挤了进去。她看到他的唇角上扬,溢出一抹微笑。
有位置了。他转头过来,笑看着她说。
那是一棵年月久远的粗壮槐树下的空位。台阶上歪歪斜斜地放了一排单车,其中一辆已经破旧,摇摇欲坠地倚靠在另外一辆车的上面。两个中学生模样的情侣,扫码开车,而后蹙眉,男孩冲着单车踢了一脚,女孩则低头认真地去挑选另外的一辆。胖男人一边将车慢慢地倒出,一边从车窗里伸出圆滚滚的脑袋来,好奇地盯着女孩,好像他跟她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女孩抬头看到胖子肥腻腻的脸,和明显带有窥视的视线,便悄悄附到男孩的耳边说了一句什么,男孩即刻抬起头来,朝着胖男人鄙夷地竖起中指。胖男人不但没有生气,反倒抖着一脸的赘肉,边将车转向正道,边嘿嘿笑了起来。
胖男人大约太专注于这件小小的日常趣事,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等待,所以差一点就跟他们的车撞在一起。他一声叹息,正要探出头去发作,一个协警过来,跨在一辆单车上,似笑非笑地盯着他们。这次胖男人老实了,老鼠一样灰溜溜地一踩油门,就跑得没了踪影。两个中学生终于各自选了一辆满意的单车,哼着歌,悠闲地并肩慢慢骑远。
年轻的情侣没有回头,她却觉得他们背上长了眼睛,只不过那视线被协警接替过去,不动声色地盯着车里的他们。她有些不安,似乎协警一眼看穿了他们,知道他们要在这里做一些什么,或者有做一些什么的打算,于是便依然双臂交叉在胸前,一言不发地紧盯着他们。
就在车已经进去半个身体,试图将另外半个也稳妥地安放进去与其他车排成整齐的一道线时,他忽然扭头看她一眼,说,我们走吧。
她点头,好。
于是车便飞快地冲了出去,又拐过路口,彻底地将协警甩在了后面。
她的心里空荡荡的,是用什么都填不满的空。那空越来越大,犹如一团薄雾,起初还是细长的一条,慵懒地环绕着她,后来便扩散开,将她与他,整个地包裹住。他们开着车,在这浓重的大雾中穿行,一直走,一直走,不知道这苍茫的道路,何时才能到尽头。
车拐过一条大道,又折进一条小巷,巷子很快到了尽头,一片亮光照射过来,她的眼睛有些刺痛,眼泪不知怎么就流了出来。
还是回家吧,女儿在等着你。她终于开口。
他没有回她。窗外的小饭馆里,一个穿白色工作服的服务生,正端出一盆洗菜的水,哗啦一声泼在白晃晃的阳光下。那水很快就蒸发掉了,地上只留下阴湿的一片痕迹,或许过不了多久,那印记也终将消失无痕。
这强大的世俗生活,重重地骄阳一样朝他们砸下来。如果车里没有空调清凉的抚慰,她还会跟着他,穿越大半个城市,只为寻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吗?而他呢?又会不会对这偶然的相逢,恋恋不舍,一定要在这火烤一样的正午,饭也不吃,只为跟她说一些什么?
我住的小区旁边,有一个无人打扰的小巷,我们去那里吧。说完这句,他硬朗的脸上,又泛起柔和的光。这光让她内心的躁动慢慢平复下去。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与他对视一眼,将内心浮起的温柔,融入那一抹明晰的光里。
她注意到窗外开始有细细的风,在闪烁的树叶间游走。风从一株干净挺拔的水杉树,跳跃到另外一棵阔大的法桐上,再到一小片闪亮的草丛中。最后,风落在一朵含苞待放的蜀葵上,并沿着柔软的花瓣,一缕一缕地,游进了花苞。她想象着风在花苞里亲吻着甜蜜的花蕊,并试图将花朵一瓣一瓣打开。那是恋人间的亲吻,湿润的,洁净的,温柔的。
因为风与花蕊的吻,她忽然就想起他们决定分开的那一天,也是这样的盛夏,午后两点,整个城市都陷入沉默无边的沉睡之中。
她说,再见。
他说,我爱你。
她说,我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
她最后一次拥抱他。微闭着双眼,而后仰起脸,慢慢地找寻着他滚烫的双唇。她听到他的呼吸,炽热的,急促的,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涌荡过来,并将她席卷。他们并未像过去那样,以惊涛骇浪般的激情,和一触即燃的热烈,迅速融化进彼此的身体。他只是微微地张开双唇,敏锐地捕捉到她的舌尖,而后像一缕轻风,一阵细雨,一抹晨雾,湿漉漉地将她浸润,抚慰,缠绕。他的吻,在她的唇边,只停留了很短,便悄无声息地消失掉了。但她却将它铭记在了心底,自此再也不曾忘记。
此刻,他载着她,开往某一条隐匿在喧哗中的小巷。她不知道他还会不会记得那一个淡若无痕的亲吻,又会不会像此刻的风一样,探入她的双唇,重新将她温柔地开启。她不再关心他要跟她说些什么,她只想要一个柔软的亲吻,那并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但她却可以获得他全部深沉的爱。
他的家位于这个城市靠南的一角,她曾许多次路过,却从未下车,沿着周围植满垂柳的小路,走上一次。甚至即便是透过车窗注视一眼,她也怕打扰到他。她只把这个名为“风尚”的小区,珍藏在心底,除非有人提及,她从不主动说出这个名字。
时间飞快地消逝,已经接近午后一点,尽管再拐过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就到了他居住的小区,但她心里还是着急,为正等他回去做饭的女儿。商业街的两边,是琳琅满目的店铺,暑气蒸腾中,到处都是晃动的人影。肉铺的老板正将一架冷冻的牛肉,咚一声扔到案板上去。饭馆里的伙计们,一边擦着额头的汗,一边小跑着给客人端盘送碗。理发店里的流行音乐,以将屋顶掀翻的架势,震耳欲聋地响着。几只鸽子站在一家福利彩票店的广告牌上,咕咕咕咕地叫着。火锅店里弥漫出辛辣的味道,刺激着路人的眼睛。风逡巡到路口,探头看一眼热气腾腾的人间世相,犹豫了片刻,终究没有进入,一转身,去了别处。
到处都是行人,他们的车只好走走停停,不过是几百米的道路,却似乎走了许久。以至于她几乎失去了耐心,想要开门下车,随便找个馆子,吃一碗热辣的牛肉拉面,便打车回到与他再无关系的日常生活。她的心里像这一条不长不短的商业街,处处都是拥堵,处处都有障碍。她侧头,看一眼他,见他脸上那抹明亮的光,正慢慢黯淡下去。
穿过商业街后左转,是一条小巷,大约三百米,便到了尽头。一墙之隔的小区里,六层楼上,挂着几件飘荡的衣服,一条酒红色的长裙,一件浅粉色的文胸,一条深蓝色的男士牛仔裤和一顶黑色的棒球帽。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探出头来,对着旁边一株高大的榆树,啪一声吐了一口痰。她不由得微微侧头,好像要躲开那一口痰。
巷子的两边,停满了私家车。只有靠墙的一个角落,一辆破旧桑塔纳的后面,可以让他们暂时地容一下身。
尽管开着空调,她还是看到他的鼻翼渗出细密的汗珠。她等他将车停稳,身体松弛,并朝椅背靠去。他转过头来,略微疲惫地注视着她,溢出一抹微笑。她也冲他微笑,并伸出右手。就在她的手指,轻轻触碰到他鼻尖的一颗汗珠时,他将她的右手深情地握住。
像许多次在梦里出现的那样,她微闭上双眼,热烈期待着他的双唇。此时的每分每秒,对于他们,都如此奢侈,她不想再虚伪地掩饰自己,她只想要他的亲吻,那可以一生铭记的亲吻。她愿深陷在那深沉犹如大海起伏的呼吸之中。
就在他们双唇热烈触碰在一起的瞬间,一阵砰砰砰敲击窗户的声音将他们惊醒。她与他几乎同时睁开眼睛,不安地朝窗外看去。那里正站着一个身体干瘪枯朽的带红袖章的男人,隔着玻璃,朝他们大喊:“快走,这里不能随便停车!”
几乎就在同时,他的手机也铃声大作。他低头看了一眼,犹豫片刻,终于接起。
宝贝,别急,爸爸知道你饿了,爸爸一定会回去的。呃,多久回去?
他停了几秒,朝她看过来。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将靠近他的身体坐正了,而后扭头,看向窗外。那里,一脸不耐烦的男人,正等着他们离去。
丫头,爸爸……这就回去,你耐心等着……
他说完这句,便匆匆挂断电话,发动引擎,并在男人的目送下,朝着喧嚣的大道行驶。
那里,正有无处可逃的烈日,像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落在沸腾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