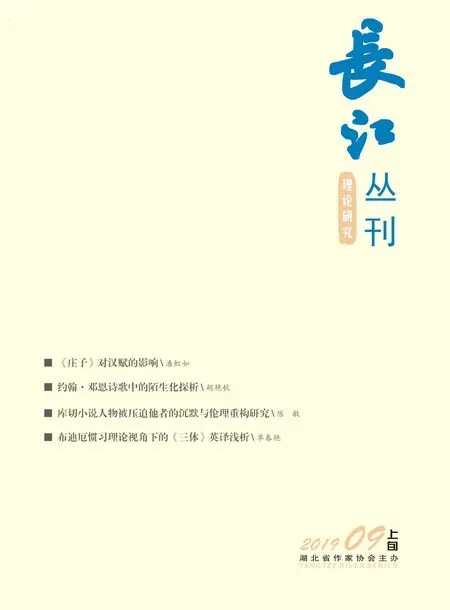论《启蒙辩证法》文化批判思想的三大理路
2019-11-15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 静/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化批判思想的主线是文化工业批判,而“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章则是《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启蒙的意义而言,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的概念”一章的最开头处已经指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本应让民众摆脱思想、政治上的控制与奴役,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充满着真实感与幸福感的个体。
人类尤其是欧洲近几百年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将这一群体带入一个真正的具有人性的、幸福的一种自由快乐的自主状态,反而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奴役的野蛮状态。他们看到了启蒙背后本应包含的个体自由、幸福、快乐的底色,然而现实的启蒙却走向了它的反面,走向野蛮、暴力。所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选择“连进步也不放过的批判思想”,去捍卫启蒙本应具有的人性、自由、自主的价值理念,以真启蒙的尺度标准批判反向化的启蒙。
一、文化商品化批判
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理论中就已经谈到“商品化”这一方面,“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平凡的商品背后是并不平凡的商品形式,这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商品除了劳动产品自身的物理性质之外,还具有一种精神属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商品拜物教作用下,就连这种精神性的东西也变成物的了。
文化工业下的文化商品具有标准化、商品化、单一化、机械化等性质,文化本不应该和工业混淆在一起,就比如手工艺劳动者是靠着自己的双手以及头脑思维来进行传统的手工艺品的制作,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制作出一件工艺品;现代机器的广泛使用,工厂已经可以批量生产这些手工艺品了,而且精确化的计算,每个产品几乎一模一样,可都是冷冰冰的,已经全然没有了人的温度,或者说艺术的温度,这样的产品怎么称之为艺术品?人是文化的核心,而工业的插手却让这些文化变成了不自由的仿造品。宣传广告则打着个性定制的旗号,对于不同阶级的消费者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着略有不同的产品,吸引着大众争相购买,以此展示自己的独一无二性。甚至连以利润为目的的广告都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文化,不经过广告宣传“洗礼”的产品,大多数人们都会持有一种质疑的态度,广告变成了商品本身。
“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人的个体的特性主要是指人的精神,消除的是精神所特有的个性,独特性,大众俨然变成了千人一面,成为了以“群”而称的,如同机械生产的商品一样,社会机器也在生产这样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是投资资本取得的成就,资本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主人,被深深地印在了在生产线上劳作的被剥夺者的心灵之中;无论制片人选择了什么样的情节,每部影片的内容不过如此”,大众的审美逐渐陷入一种贫困的状态,更确切一点说,这种审美贫困已经完全吞并了创新,生产者不需要生产那些新奇的玩意,因为他们已经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任何一种普通的商品,只要打上独一无二、专门定制的旗号就会引得大众争相购买。
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把赤裸裸的利润动机置于各种文化形式之上。自从这些文化形式初次开始作为商品成为它们的创作者在市场上谋生的手段的时候起,它们就已经或多或少地具有了这种性质。但那时候,它们对利润的追求只是间接的,仍保留着它们的自治本质。文化工业的新特点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把对于效用的精确彻底的计算直接地、不加掩饰的放在首位。”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艺术形式作为商品可以解决生计问题,而文化工业的出现,将这种交换形式变成了纯粹的商业贸易,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仅仅是为了售卖,给大众提供一种虚假的满足,以致丧失掉了人自身的现实感和自主批判性的东西。
二、文化技术化批判
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培根的这种认知为启蒙走向反面埋下了伏笔,自他以来,启蒙的时代所培养的理性精神逐渐缺失了一隅,仅剩工具理性或者说是技术理性片面的发展。启蒙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理性,理性思想冲破了封建愚昧的藩篱,大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没有旧式神话传说的时代。根据马克思的商品理论,一切劳动产品都可以作为商品,每一个被制作出来的劳动产品,只有出卖给消费者,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在这里,理性的工具性质体现的愈加明显,更进一步说,大众所在意和所想要的仅仅只是产品的有用性,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被视为纯粹客体的自然。
在20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科技、工业以其一丝不苟地标准化、批量化操纵着一切,使启蒙仅剩野蛮,工具理性一如法西斯战车一般浩浩荡荡地碾压所有:启蒙转向自身的反面,是神话时代的又一重现,不同之处在于,启蒙是“以内在精神的丧失换取外在的物质财富,以进步的名义要求个体与日俱增地服从权威”。
启蒙理性狭窄化为工具理性,或者说技术理性,带来的伤害包括“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技术合理性让启蒙变成了可控制的,起码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有利的,并为集权统治者的合法性制造了一种幻象,一种让大众不得反抗,甘心服从的幻象。随着技术合理性的增加,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统治者并不关心大众的精神世界,只需要满足大众的物质生活就够了。技术合理性控制下的统治是残缺的,片面的,所造就的社会用柏拉图的话说是“猪的城邦”,毕竟在这样的城邦里,对于统治者来说,一头猪有了自己的思想意识是极其可怕的,而在这样的统治下,人是不完美的,丧失了人之为人的自主性。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导言中谈到技术与政治,“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
三、文化去主体化
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应该是追求公平、自由、正义、真理等一切真善美的,而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下,文化的这些特性逐渐消失,开始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欺骗、控制无知的大众,在丧失自由的领域里享受着所谓的“自由”时间。《启蒙辩证法》中谈到了一则神话:海妖塞壬与船长奥德修斯。塞壬的歌声是美丽与危险的共在,船长奥德修斯让水手们用蜡塞住耳朵拼命划桨,而他则让别人把他绑在桅杆上,倾听塞壬的歌声,而不至于陷入死亡的深渊。按照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来说,主人奥德修斯虽然享受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但是却是用水手们的劳动实践换来的,而可悲的水手们只知道塞壬是可怕的危险的,却不知道她的歌声的美丽,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着奴役与欺骗。
文化工业的作用在于揭开了艺术的神秘面纱,让神话不再是神秘莫测的,或者说让艺术实现了平民化,水手们也可以绑在桅杆上倾听塞壬的歌声。但在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实现了同一性,并能够标准化、机械化、批量化生产这些“艺术商品”,供大众享受,使大众丧失自主独立判断的能力。就像卓别林主演的电影《大独裁者》所讽刺的那样,无论是理发匠还是独裁者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都利用了广播这一传播形式以蛊惑大众。快乐意味着什么,对文化工业控制下的大众,“快乐意味着什么都不要想,忘却一切忧伤”,这种快乐就像是一种迷魂阵或者说忘忧草,不是纯粹的真实的快乐,而是一种有目的取乐,在这种唐老鸭式的取乐包围中,大众丧失了反抗不合理统治的观念,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大众已经成为了娱乐至死之人。
霍耐特在《批判理论——从思想传统的中心到边缘》一文中表示“在‘启蒙辩证法’中,‘社会劳动’不再标志着解放实践的形式,而是标志着对象化思维的萌芽”,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劳动者本身却必须将劳动抽离出来,形成对立的主体,甚至是人自己的思想产物也不属于自己了。在文化工业中,大众已经不能称之为“理性人”,而是失去主体性变为消费文化工业的被动的不自由的客体。“就富于创造力的主观性来说,先验论所赞扬的是主体无意识地禁锢于自身之中。它的每一个客观的思想都使自己处于被驾驭的状态,就象一头在外壳里的披甲兽想要摆脱又摆脱不了;唯一的区别在于这种动物没有把它们的囚禁当作自由来夸耀”,这种无形的监禁是内在化的,“因此,将监禁重新解释为自由的兴趣,个人意识的范畴监禁重复每一个人的实际监禁”。
现实的大众是拥有认清这种囚禁状态的能力的,只不过囿于资本的利益诉求,一边享受着被监禁的现实生活,一边高唱自由之歌。他们认为“现实,一种被拔高为假想的自由主体的产物,将会证明自己是自由的”。
霍克海默说过“人类的未来取决于现存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当然包含来源于传统理论的要素和来源于目前正在普遍衰退的文化的要素”。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批判哲学与旧的批判理论相比,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现实,是站在社会总体运作的框架下进行的,其文化批判思想生成于启蒙倒退的历史语境,受到了前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以及研究者自身经历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些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其划时代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