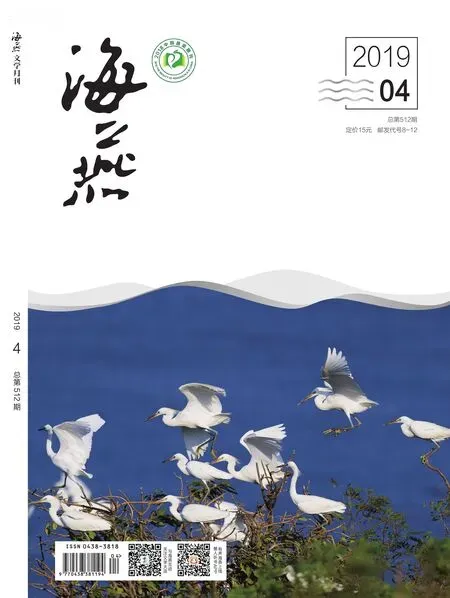文学的高地在乡村
2019-11-15林喦
□林喦
2019年1月20日,我和四位从事文学研究的同事到盘锦和盘锦的作家朋友一起参加关于“乡村文学”的小型研讨会。盘锦是我童年的成长域,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一直在这座曾经被称为“南大荒”的鱼米之乡长大。我所谓的“南大荒”并不是人们认知中因缺乏生活的物质需要的“南大荒”,盘锦,尤其是我童年生活的大洼县(现已改为大洼区),春季,稻秧千里平铺碧绿如野;秋季,稻穗风中摇曳一望金黄,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阡陌纵横、水系充盈,蜻蜓、青蛙、鱼儿为伴,满眼的田园景致中度过的。所以,那时的大洼县是被称为北方“鱼米之乡”。而所谓的“南大荒”,在我眼里是缺少历史和文化的“荒”。四十年过去了,盘锦再也不能称为“南大荒”了, 因为一代代盘锦人把盘锦打造成了有文化的场域。红海滩的红,美术馆的展、乡村民宿的新、盘锦大米的香,还有盘锦文学作家群体意识,都标着这座曾经被称为新兴工业城市的文化意蕴。
“乡村文学”研讨会从辽宁著名散文家王本道先生的散文创作研讨开始,并由此延展到关于“乡村文学”的文学现场讨论,我的同事尹晓丽老师发言中特别强调了王本道先生散文创作中“真”“正”“博”的三个特征;岳凯老师从王本道既为“仕”又为“士”的视角谈到了其散文的中国文人的文化气质问题;刘广远老师从“抒情传统”“叙事传统”“乡土传统”三个维度阐释了王本道先生散文的大散文观念;而宋扬老师从地域文化培育的角度解析了王本道散文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盘锦海河交汇形成独特的盐碱滩、芦苇荡、稻花香、石油场滋养了盘锦作家的创作,无论是散文家王充闾、王秀杰、王本道,刘长青、曲子清;诗人东白、阎墨林、宋晓杰、刘亚明、李凌、李箪、关洪禄、海默、赵小林;小说作家张艳荣;报告文学作家杨春风;他们都满怀真诚与激情地书写着这片属于他们的热土,讴歌着属于他们的时代,并形成了盘锦文学独特的乡村气息。
我认为,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不仅要在作家群和读者群里有地位有影响力,也要进入学界的视野,到被学界所梳理和研究,这标志着一个作家和其作品达到了一定的成熟性和稳定性,进而形成属于创作的个性化风格。学界的介入,不仅仅是一种认可,更是对作家,读者提供一个心灵的维度,一个通向超验世界的渠道,形成对作家创作的推动力。
我们在大洼区荣兴镇民宿进行“乡村文学”研讨。从我们参观荣兴博物馆、遇·稻咖啡屋开始,并在乡村民宿场域的座谈,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从百年前在海河交汇处的荣兴种植水稻开始,还是改革开放40年荣兴小镇的繁荣变化,从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乡民笑脸上,我们不仅能看到大家享受着生活幸福的喜悦,还能闻到满满的稻米香味。
无疑,乡村文化的气场是宏大的,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连绵不绝的强大气息支撑一代代生民的繁衍,无论城镇化的进程多么的快节奏,乡村气息渗透在生民的血液中,更渗透并溶解在人们的文化DNA中。所以,我们的文学创作离不开乡土、离不开乡情、离不开乡民、离不开乡愁,几位老师和在场的盘锦作家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畅谈了乡村对文学的影响,文学对乡村的表达。刘长青从中国乡土文学的传统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乡村文学创作,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40年乡土文学的发展,简单梳理了乡土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这方面也是给我们的作家提一个醒,文学创作离不开乡土、乡村。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作家也一样要接受这个时代所赋予的文学创作使命,我们常说,读懂中国的农村就是读懂中国。文学是农村的一种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深入到乡村,关注到农业、关心到农民,文学不仅有田园牧歌式想象,还要有根植于乡土、根植于农民、根植于农业的深刻思考。当人们喜悦于阅读宏大历史的故事,喜悦于关注现代化的都市,喜悦于品味家庭伦理的错综复杂,喜悦于相声二人转的媚俗,喜悦于想象戏说传奇、喜悦于觊觎后宫粉黛的时候,我们的作家更应该关注乡村,文学创作在乡村的历史中挖掘集体记忆是很好的题材选择,这样,会避免作家在创作中思维的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为,乡村是我们文学创作的高地。
我们的活动安排得很紧凑,大家围坐在一起,距离很近,无需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发言,这样的文学现场很温馨很亲切。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事实上,对于作家而言,所谓的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作家创作作品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在哪里发现,我觉得乡村地域是一个最好的内容发现现场。
这次我们参观的荣兴小镇民宿,是这座小镇的村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掘小镇历史的集体记忆,他们自建了反映水稻在这里种植的发展过程的“荣兴博物馆”,镇工委书记还给我们讲述了荣兴人正在做稻草秸秆编织草帽的文化创意。这种理念既是一种探寻,也是一种挖古,既是一种继承,又是一种文化创意。从民宿到博物馆,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得让乡民们与荣兴“遇到”,才有了与种植水稻的“遇稻”。这如同作家创作,因为每一位作家都生活在生活之中,周围的一切都是历史的悄然安排,不需要我们发明什么,而是需要我们真诚地用真心和慧眼发现什么。在你生活的属地,本身就存在着什么,无论是历史的记忆,还是你身临其境活生生的存在现场,你的发现都是你与这种历史记忆和存在现场的缘分,这些都在于发现。我觉得这是我们作家的一个使命和责任,创出作品是你发现的,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发现。
盘锦作家刘长青和刘亚明两位作家发言中谈到了以文学的视角来书写乡村振兴的话题,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义,我也觉得对于我们而言,乡村文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根脉文化。结合尹晓丽老师谈到的王本道散文创作“正”的特征,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认同乡村文化是重要的根脉文化以及王本道散文的“正”这一特征,都说明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对于个体作家而言是作家个体的自信,对于我们认同的根脉文化特征而言这是我们集体的文化自信,因为历史的“有”,才有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学创作的主题是人,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区域的文化名片,作家之所以成为文化名片,是因为作家通过作品反映了他所生活的区域文化。
作家的责任不仅是启迪当下,还要告诉未来。比如对于当下的80后、90后、甚至00后而言,他们对历史发展中的某些苦难的过去,都怀有一种超然的浪漫想象色彩,对苦难的思考从未有过,因为他们是改革开放40年来胜利成果的享受者,他们无法想象瘟疫、灾荒、饥饿、战争、社会动荡,他们没有经历社会之痛,甚至生活在五光十色的都市大众文化、快餐文化、网络文化的快节奏之中,人们已经忘却了历史之伤,因此,我们作家就要有责任还原历史,恢复记忆,修正想象。
我们要深信,因有乡村文化的根脉,有田园牧歌的生活,才有城市生命的存在与延续。我们更要相信,文学的高地在乡村。
(根据2019年1月20日“盘锦市乡村文学创作研讨会”作者本人现场主持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