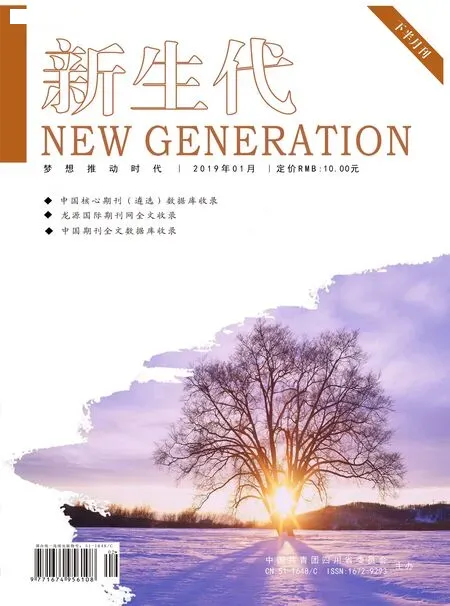浅析《萤火虫之墓》与《赤足小子》中的意象表达
2019-11-14张雨萌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张雨萌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序言
1945年之后,日本各行各业逐渐进入了恢复期,动漫行业也随之复苏,进而取得了飞速发展。在题材纷繁的日本动画中,二战题材始终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日本国宝级漫画大师手冢治虫创作的《铁臂阿童木》到2016年上映的颇具口碑的动画电影《这世界的角落》,随处可见战争对于日本动画的深远影响。
美国学者苏珊·j·纳皮尔在她的著作《ANIME》中曾写到:“在描写二战题材的日本动画电影中,最出名的两部要数《赤足小子》和《萤火虫之墓》了。这两部影片从片中主角的个人角度出发,以自传的形式为我们展现出那个集体主义语境下的日本记忆。”在这两部经典的日本动画电影中,战争的残酷和反战思想表露无遗,但更耐人寻味的,是一系列意象背后的文化根源与心理依据。本文将通过对比《赤足小子》和《萤火虫之墓》两部影片,浅析影片中诸多意象背后的含义。
一、影片的时代背景
战败后的日本,从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直到1970年代初,经历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等大型景气的日本,渐渐从战乱的废墟中恢复过来,国民生产总值也一度直逼美国。但进入八十年代,这种高速增长的模式有所减缓。1980年代中期,日本经历了所谓的“泡沫经济”时期,经济市场开始陷入低迷。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天皇制与家族制所代表的封建主义制度几近崩溃,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更加趋向于“自由”和“多元”。这种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动荡势必影响到文化的层面,《赤足小子》和《萤火虫之墓》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而产生的。
二、影片概述
《萤火虫之墓》在一片灰暗萧条的景象中,以男主角清太的一句自白“我死了”奠定了影片凄美悲情的打开方式。萤火虫若隐若现的光辉,仿佛清太奄奄一息的生命,清太的灵魂已从虚弱的肉体分离出来,随着地上的糖果罐子,终于与异世界的妹妹节子重聚。
相比于悲情凄美的《萤火虫之墓》,赤足小子的基调则要更加“励志”。影片开头就是一片翠绿色的麦子地与小元父亲充满男子气概的演说:“麦子啊,渡过严酷的严冬,不依不饶地在大地上发芽……”。本片主要从男主人公小元的视角,讲述了二战时期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在这次灾难中失去了父亲、姐姐、弟弟的小元与母亲和刚出生的妹妹相依为命的故事。在影片的结尾,小元与隆太看到土地上新长出的麦子芽,想起了父亲说的话,于是重新振作起来,决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三、“小元”与“清太”
《赤足小子》中的“小元”似乎一直“在阳光下奔跑”,在那个悲惨的时代,父亲的鼓励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小元的父亲是个坚定的“反战主义者”,痛恨战争与发起战争的日本政府,认为“政府”是在迫害人民。而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鲜明的反战思想也使得小元的内心没有太多反复与挣扎,这一点在小元哼唱反战歌曲这个情节中显现出来。因此,小元和母亲的那种在经历了核爆灾难后的悲伤与愤慨就显得格外纯粹,是一种“血与泪的控诉”。与此相比,《萤火虫之墓》对于主角清太的塑造就更为复杂。从影片中清太看到萤火虫联想到参观军事演习,并高唱军歌的情节可以看出清太原本对于战争的理解是较为正面的,但后面清太唱到一半的戛然而止,体现出了清太的挣扎与迷茫。在听到“大日本帝国战败”与父亲所在的舰队沉默的消息之后,清太更是陷入了混乱与绝望。节子的夭折无疑是压倒清太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清太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也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这种矛盾的扭曲,一方面增加了“清太”的角色维度,与旗帜鲜明的小元形成了强烈对比,在加深了影片悲情效果;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日本究竟是如何在“民众的拥护声”中将自己推向修罗场的,更能引发人们对于战争的思考。日本的这一系列“天灾”,又何尝不是“人祸”呢?
四、日本人的“依赖心理”
说起清太“孤独地死亡”这一情节,究其根源,则不得不提及日本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土居健郎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书中提及的“依赖心理”这一概念。汉语语境中的“依赖”不尽相同,这里的“依赖”指得是一种“相互容纳的,被动的爱”。简而言之,就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对于“被爱”的极度渴望。这种渴望是人类欲望深处的,本能的存在。土居认为,这种“依赖心理”存续与日本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是由于日本人已经把相互依存的人际关系贯穿到社会规范之中,所以在日本依赖心理得以发达。那么,接下来我就从“依赖心理”的概念出发,解析下面的诸多意象。
1、女性角色
在这两部影片中,“母亲”都是女性角色中的重要人物。土居认为,“依赖心理”是一种在婴儿时期形成的心理活动。当婴儿逐渐意识到自己与母亲各为一体,而感觉自己不能离开母亲的时候,“依赖”就产生了。不仅如此,“孤独感”也诞生于这一时期。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尼·克莱因在其著作《嫉羡与感恩》一书中曾经提到,“孤独感”来源于婴儿的一种无法被满足的渴求,当他发现自己对于“母亲”的渴求无法时时刻刻都被满足时,就会产生这样的心理活动。因而“母亲”这一意象本身,就带有着“依赖”的意味。而母亲角色的缺失(死亡),则代表了这种内心深处的渴望趋于终止,从而营造出一种深层次的孤独。
除此之外,女性角色通常也被认为是文化根源的象征。这一点在《萤火虫制之墓》中也有所参照,当清太带着节子到海边玩耍,海风拂面,清太想起了妈妈生前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传统女性形象,穿着粉红色的和服,轻轻举着粉红色的伞,一阵风吹过,伞被吹落在沙滩上。随风舞动的裙摆,尽显女性的柔弱温情,樱花一般,如同日本的文化情怀。而天真的节子与《赤足小子》里刚出生的友子,则代表了文化中最纯情文弱的部分。她们支撑起清太和小元的精神世界,是“幸福感”和“快乐”的源泉,并在灾难降临之后,给予他们生存的希望。
但是,战败后的日本,受到了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传统封建天皇制与家族制的禁锢被解除,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已经建立起了如同西方社会一样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思想的解放丝毫没有减弱人们相互依赖的心理,反而造成日本精神和日本社会的极度混乱。”而友子与节子的死去,恰恰体现出创作者对日本传统文化在这样极度混乱的社会情景之下能否存续的深深担忧。《萤火虫制之墓》中,节子在最后抱着清太,呼喊着“不要离开我……”,则也是传统文化的呼声。
2、父亲
“父亲”是两部影片中极为重要的意象。而在这两部影片中的父亲角色又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赤足小子》中小元的父亲是一个“有存在感”的父亲。在影片开头一直到影片中部,小元的父亲都占据了相当的戏份。而小元在父亲的鼓励和家人的陪伴下,他那见证了“惨绝人寰的灾难”的幼小心灵,并没有受到极大的扭曲与颠覆。甚至在母亲因目睹丈夫和儿女的死亡而陷入崩溃的时候,是小元将母亲从火场拖走,救下了母亲和尚在腹中的妹妹友子。小元脑海中,似乎始终回荡着父亲对自己的教导,模仿父亲的样子,学着如何成为一个男子汉。相较之下,《萤火虫之墓》中小元的父亲就是一个几近“虚无缥缈”的存在,苏珊·j·纳皮尔曾提到,“清太的父亲是海军军官,代表的是政府的一方”。而这种“缥缈”的感觉与二战时期政府“虚无缥缈”的存在感相一致。就像清太的父亲只存在于别人的话语中,相框里的照片中和清太的记忆中那样,“日本政府”也只存在于广播和火葬场周围。
更深层次去发掘“父亲”一词的含义,不禁会想到日本的“父权文化”。以天皇制和家族制为首的父权制度在日本战后分崩离析,开始进入“父权失坠”的状态。经历了这场浩劫的人们,终于认识到了以往所谓的传统“义理”已然腐朽破败,此时,人们强烈迫切地想要有所依靠的愿望收到了极大的挫败。年轻的一代开始不断地怀疑甚者抛弃以往父权文化语境下的许多观念。然而,从《赤足小子》的结尾我们不难看出,其实人们内心对于强大的父亲形象的指引和回归还是充满期待,希望能够重塑一个伟大的父亲形象。
3、“家”
“家”的意象在这两部影片中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萤火虫之墓》中,清太和节子在家被烧毁后一直试图建立并守护他们自己的“家”。无论这个家有多简陋,对他们来说,都如同之神天堂。节子死后,火化的那一段情节中,背景音乐的歌词则强调了“无处为家”的凄凉。也为清太的一蹶不振埋下伏笔。《赤足小子》中的小元之所以能够坚强的活下去,也是因为有家人的陪伴。这其中也体现出日本人内心深处对“家庭”深深的依赖。
4、“被害者形象”与“被害意识”
然而无论是怎样的主题,我们总是能在许多二战题材的影片中看到日本人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在控诉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之时,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过作为真正“受害者”的被侵略国国民的感受。究其根源,日本人之中强烈的被害意识也与“依赖心理”脱不开关系。
无论是战争中受害的民众,还是受伤的“日本大兵”,“被害者形象”甚至于影片各处,以至于有时我们会忘记这是在看一部“描写侵略国”的影片。土居健郎在“受迫害感”这一章节解释说,“受迫害感”起源于受干扰的意识,这种受干扰的意识正是“依赖心理”的体现。而“加害心理”则“是受害心理受干扰之翻版”,因此这种加害心理便很容易转换为受害心理而存续。因而“被害者形象”也是根植于日本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写照。
五、影片中的生命意象
《萤火虫之墓》中的萤火虫是贯穿整部影片的线索性的存在,也揭示了创作者想要在这部影片中索要表述的生命观——生命,美丽却又短暂。在赞叹生命美妙的同时,又强调了生命的脆弱易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正是明白了生命的脆弱与短暂,人们才能更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呼吁和平,感恩和平。
而《赤足小子》开篇那一片绿油油的麦子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子”这一意象背后,则体现出了与《萤火虫之墓》截然不同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观念。与之相似的,还有小元的头发。之后,小元的头发也全部都掉光了。不过幸运的是,小元并没有因此而死,在影片的最后,小元和弟弟隆太在一片土地上找到了新长出来的麦苗,小元的头发也长出来了。这种“生生不息”的思想观念,为当时处于社会“精神动荡”期的年轻人提供了方向,无论经历过怎样的动荡甚至是灾难,总有一天将会好起来的,就像麦子总有一天将会发芽。
六、结语
通过分析这两部优秀的动画影片中的意象,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文艺做作品与时代和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心理方面的紧密联系。艺术作品的内涵,与创作意象的选择和表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比较,可以在将来的艺术创作中有所渗透,从而增加艺术作品的表达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