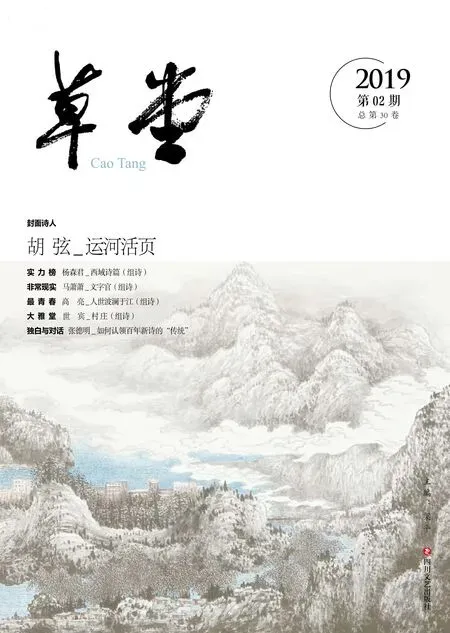如何认领百年新诗的“传统”
2019-11-14张德明
张德明
翻译家、诗人黄灿然在他著名的《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一文中,开章即曰:“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写作都处在两大传统(即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的阴影下。”这是对二十世纪汉语写作所承担的外在压力的确切言说,对于理解中国新诗的生成与发展而言,也是不乏启示意义的。黄灿然告诉我们,新诗时刻要面对的文学传统起码有两个,一个是作为中华灿烂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典文学传统,一个是来自异域的西方现代文学传统。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新诗的写作,都没有从这两大传统的“阴影”中完全摆脱出来。
不过,历经百年的新诗,尽管在担负着两大传统的沉重压力下一路风雨,踽踽而行,但毕竟向历史交出了一份并不让人失望的答卷。一百年来,运用现代汉语进行诗歌写作的诗人之中,能称得上佼佼者的还是不少的,而对百年新诗文本而言,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诗作也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这就引发了我们对另一问题的追问:抛开新诗面临的古典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不说,多方探求、艰难突围的百年新诗,是否也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特有“传统”呢?
何为“传统”?1979年出版的《辞海》如此解释,所谓传统是指:“从历史上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尚、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它通常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继承下来,其中最稳定的因素被固定化,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如民族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等。”这是从历史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层面对“传统”所做的界定,也与我们通常意义上对“传统”的理解相一致。而对“传统”所具深意阐释最为系统和透彻的,要数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了,他的《论传统》一著从多个维度对传统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剖解与阐释。在这部著作中,希尔斯指出:“传统——世世相传的事物——包括物质实体,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件的形象,也包括惯例和制度。它可以是建筑物、纪念碑、景物、雕塑、绘画、书籍、工具和机器。它涵括一个特定时期内某个社会所拥有的一切事物,而这一切在其拥有者发现它们之前已经存在。”在希尔斯看来,那种在人类社会中“世代相传”的“传统”,其实是包含着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很显然,我们要探讨的有关百年新诗的“传统”问题,属于希尔斯关于传统界定的精神属性的部分,是指中国新诗经过百年探索而积淀起来的某些艺术常规和美学惯例,这些艺术常规和美学惯例,得到了现代诗人的普遍认同和不断蹈袭,并将对未来的诗歌写作有着重要的导引与规训作用。从另外的角度看,如果说我们通常意义上言述的“传统”,例如“民族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等,是历经很长时间的历史而形成的,属于人类社会“大传统”的话,那么百年新诗假如说存在某种“传统”,也只能算“小传统”,是必须加以更深远的历史沉淀才能不断壮大,并最终融入强大的文化传统之中的。
百年新诗究竟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传统”呢?这个问题在诗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赞成者有之,反对的声音也存在。比如郑敏先生就认为:“我们今天的新诗的问题,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但还是半诗盲。因此,我一直认为新诗到现在没有自己的传统。”吴思敬先生的意见正好相反,他坚持认为新诗有了传统,并亲自撰文来呼吁。在《新诗已形成自己的传统》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在我看来,‘不定型’恰恰是新诗自身的传统。新诗取代旧诗,并非仅仅是一种新诗型取代了旧诗型,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自由的精神追求。新诗人也不是不要形式,只是不要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形式。他们是要根据自己表达的需要,为每一首诗创造一种最适宜的新的形式。”在这段话里,吴思敬不仅为新诗“不定型”的自由形式做了辩护,还把这种“不定型”与新诗体现着“对自由的精神追求”相关联,认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新诗的“传统”。我认为,吴思敬对新诗传统所持的观念,是更切合百年新诗的创作实际的。在我看来,百年新诗不仅形成了自身的传统,而且也借助这些传统塑造了自我的审美形象,构建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不断发展与更新的艺术生成机制。“传统”使新诗的历史地位得以奠立,“传统”又推动着新诗在新的时代境遇中不断前行。
既然承认百年中国新诗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传统,那么新诗的传统,又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呢?在我看来,百年新诗既已形成的诗学传统,至少包含了四个方面,即:现代性追求、个人化书写、自由性表达、中西方融合等,这四个方面规约着现代诗人的文学理解和创作实践,也形塑了百年新诗整体性的历史面目。下面对这四个方面分别详述之。
中国新诗是中国文学和文化追求现代化的产物,现代性追求也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中国新诗原发性的一种艺术诉求,也自然形成了百年新诗极为显在的精神内核。从文学语言的选择上看,中国新诗启用了现代汉语(白话)作为表意体系,这种语言形态来自人们日常口语的书面化赋型,从而与怀揣启蒙理想的新文化先驱者追求的“言文一致”表达理念一拍即合,构成了新诗现代性呈现的语言学表征。新诗发生之期,不少守成者曾讥讽白话诗人使用的语言乃“引车卖浆者”之语,透着粗俗肤浅的调子。殊不知,正因为现代白话与普通百姓的日常口语息息相关,因此保留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原生态的存在样貌,以现代白话作为基本的语言谱系的中国新诗,从而能更为真切地录述着现实生活的样貌,有效地复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影像,这种语言体系,自然就赋予了新诗在艺术表达上的现代性特征。在《谈新诗》一文中,胡适曾对自己创作的新诗《应该》自我夸耀说:“这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的。别的不消说,单说‘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得出的吗?”客观上说,按今天的审美标准来看,胡适的《应该》一诗并没有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不过他所指出的旧体诗无法把“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完美地表达出来,倒还是有几分道理的。相比旧体诗以精致的古典汉语书写而导致的诗歌与现实的隔绝而言,新诗创格以来一直持有的粗放的现代汉语表述,使得它能更完满地保留生活的原生形态,因而更能将现实生活的家长里短和百般情味有效传递出来。可以说,新诗以现代白话为基本的表达媒介,是与这种文体与生俱来并一以贯之的现代性诉求相合拍的。
对于百年新诗来说,使用现代汉语作为基本的表意工具,只是其现代性追求在书写路径上的呈现,而新诗现代性特征的体现,更深蕴于其直面现实人生和重视现代生命体验的精神境界之中。我们知道,在西方“现代性”话语的阐释历史里,波德莱尔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在创作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里,较早对“现代性”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精妙的诠释。波德莱尔在观摩了自己朋友、法国画家贡斯当丹•居伊的绘画创作后,这样写道:“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观念。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如果取消它,你们势必要跌入一种抽象的、不可确定的美的虚无之中,这种美就像原罪之前的唯一的女人的那种美一样……一句话,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这段话具有多重意蕴。一方面,它强调了现代性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所谓“过渡、短暂、偶然”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现实生活的基本属性,但这些转瞬即逝的现实之中,自然也包含着某种永恒的东西,需要艺术家仔细发现和用心抽取出来。另一方面,现代性有可能成为艺术形成某种传统并得以“永恒”的重要标志。过去的艺术之所以流传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的传统,就因为它记录了过去时代的“现代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仪式、眼神和微笑”。因此,真正的艺术家都必须把握这种“现代性”,“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对于我们理解百年新诗现代性追求的特征和意义来说,是不乏启示作用的。一定意义上,中国诗歌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就是中国诗人在创作取材上从书斋生活向现实生活的转轨,相比充满“陈词滥调”(胡适语)、形同僵死美人的晚清诗歌,早期白话诗之所以更具鲜活灵动的风姿,就在于它对现代世界的直面和对现实生活的直写,就在于它对诗人个体真实的心灵影踪的真实记录和描画。而这种直面现实人生和重视现代生命体验的书写策略,无意中又暗合了波德莱尔“现代性”观念的思想逻辑,百年新诗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并不断前行,或许是与它遵循的这种现代性逻辑分不开的。
百年新诗艺术传统的第二个层面即为“个人化书写”。不少人认为,“个人化写作”主要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中发生的,恰如王家新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那句诗所昭示的,“个人化写作”成了1990年代先锋诗歌的重要诗学标签。王光明还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个人化写作”理解为,“不过是拒绝普遍性定义的写作实践,是相对于国家化、集体化、思潮化的更重视个体感受力和想象力的话语实践。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对意识形态化的‘重大题材’和时代共同主题的疏离,突出了诗歌艺术的具体承担方式”(《在非诗的年代展开诗歌:论90年代的中国诗歌》),强调了“个人化写作”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历史关联。不过在我看来,所谓“个人化”旨在强调个人现代体验的独特性以及个人内在确立的主体性,因此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百年新诗审美个性的凸显,百年新诗艺术品质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不同时代、不同个体从各自不同的路径上所开启的“个人化写作”。从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到胡适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中国诗歌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就是现代人寻求用现代语言表达现代自我的过程,就是现代主体逐步树立并不断壮大的过程。百年新诗史上,视域宽广、情感深沉的艾青诗歌代表了新诗的一种“个人化写作”,语意含混、情绪复杂的穆旦诗歌也代表了新诗的一种“个人化写作”,兼容着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和个人意识的北岛诗歌,也属于新诗的一种“个人化写作”。完全可以说,百年新诗中凡是具有审美独特性的优秀诗歌,都是不容忽视的“个人化写作”,中国新诗的历史谱系,正是由这些各具特色的“个人化写作”合力构建而成的。
百年新诗艺术传统的第三个层面即“自由性表达”。新诗有一个别名叫“自由诗”,自在书写,自由表达,俨然成了这种文体的基本属性,自由性表达也应视作百年新诗不容忽视的传统。新诗从一诞生,“自由”就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而被诗人们反复加以指认。在《谈新诗》里,胡适将中国新诗的发生视作“诗体大解放”,并将这种“解放”所赋予的写作权利概括为:“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适的这段概括无疑是凸显了新诗创作“自由”本性的具体表述。当时,与胡适观念一致的诗人也不在少数,俞平伯就说:“我对于作诗的第一个信念是‘自由’。”陆志韦也声明:“我的作诗,不是职业,乃是极自由的工作。非但古人不能压制我,时人也不能威吓我。”废名的表述最直接:“新诗应该是自由诗。”不言而喻,“自由”成为初期白话诗人共同的创作信条,也逐渐演化为百年来所有诗人都在默默遵循的基本写作原则。尽管新诗的“自由性表达”也造成了这种文体始终缺乏固定形式的问题,从而招致了很多人的诟病,不过“不定型”并不代表新诗没有自己的形式约束,诚如郭沫若所说:“好些人认为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便是最无成绩的张本,我却不便同意。我要说的一句诡辞: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倒正是新诗一个很大的成就。”“不定型正是新诗的一种新型。”在我看来,新诗之所以“不定型”,之所以以“不定型”为“新型”,正是为了保障其开放书写、自由表达等诗学理想的完满实现,这正如吴思敬所说:“自由诗的自由,体现了开放,体现了包容,体现了对创新精神的永恒的鼓励。”
在创作资源的汲取和容纳上,百年新诗的开放与包容也是同样值得称道的。中西融合的资源意识,给新诗的发展与创新带来了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 这种“中西融合”的理念,也构成了百年新诗的重要传统。事实上,古典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学传统,一方面构成了中国新诗“影响的焦虑”之源,是现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始终摆脱不了的两大阴影,另一方面又成了现代诗人必须反复摹习的文学对象,它们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前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回首中国新诗的百年历程,不难发现,不少诗人创作的优秀诗作,都程度不同地刻印着古典文学或者西方文学的精神烙印,都与诗人巧妙地“化古”与“化欧”的艺术匠心有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人的诗歌创作,既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启迪,又受到晚唐温庭筠、李商隐诗风的影响。艾青的诗歌既有波德莱尔、凡尔哈伦、聂鲁达等诗人的影子,也将中国古典文学的感时忧国等文化传统加以弘扬和发挥。穆旦将中国古典诗歌的精致传统与艾略特、奥登等西方诗人的现代主义技法糅合起来,形成其意蕴繁复、语言凝练的诗歌形态。五六十年代台湾诗坛涌现了余光中、洛夫、痖弦、郑愁予等诸多优秀诗人,他们在融汇古典与西方上做出了许多探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新诗的繁荣和发展,顺应了特定时代开放、多元的历史潮流,在这个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下,继承古典,学习西方,也构成了许多诗人增强自身修养、提升诗歌技艺的有效途径,从而催生了大量艺术质量优异的诗歌文本。诗评家唐晓渡曾说:“借鉴古典,正如借鉴外国,对以自由、开放为本性的新诗及其发展来说,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句话从新诗发展的资源汲取来看,无疑是极为精辟的,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点明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新诗蓬勃发展的深层原因。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艾略特精妙地指出:“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而诗人从事诗歌创作的“经验”,并不仅仅是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与思考,对自我的内省与认知,还包括对先行者的学习与借鉴,包括对文学传统的有意识承继。实际上,越是具有历史意识的诗人,越是懂得传统的重要意义,他们无时无刻不尊重传统,并始终希望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实现对传统的弘扬与超越。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解和认识百年新诗的美学传统,对于当代诗人诗学观念的升华与创作水平的提升,无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