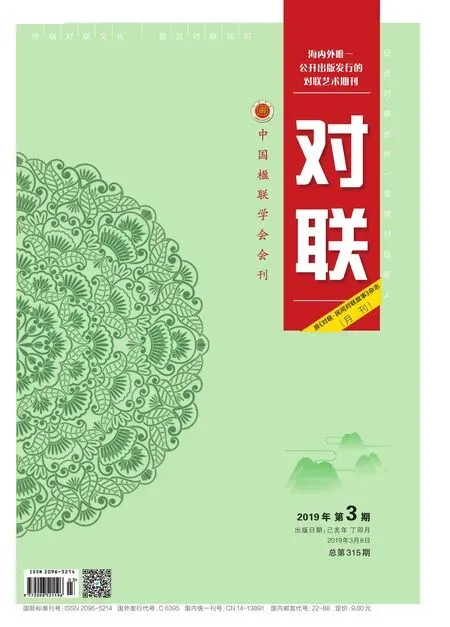辞赋的起源
2019-11-13李牧童
|李牧童
关于辞赋的起源问题,自古及今,众说纷纭,撮其要而言之,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诗源说”,即认为诗是赋的源头。
而对于“诗”之含义,又有分歧,其一侧重于诗之“三百”,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言:“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主要是从赋对诗的社会功用之承续的角度来谈的。其二则侧重于诗之“六义”,如左思首倡此说,在其《三都赋》中说:“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后来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诠赋时继承了这种取向并重申之,同时提出了“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的精辟见解,不仅指出了赋对于诗的传承关系,也揭示了楚辞对于赋之作用与影响。后人因此又提出了一种起源说,叫“楚骚说”。但大体而言,楚骚说并没有完全否定诗对于辞赋之影响。而楚辞今亦多被归为先秦诗歌类,故若将诗之内涵从原来“诗三百”的狭义,扩充为涵括古代押韵祝辞(包括楚辞)等在内的广义之诗,那么以上的各种分歧,自可兼容了。学者许结即持论,定为“广义诗源说”。第二种观点是“纵横说”,即认为辞赋本于纵横家的言辞。
此说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为章太炎,他在《国故论衡》中明确说道:“纵横者,赋之本。古者诵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纟由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禅》《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也。”章太炎在这番言论中,将纵横家对赋的影响作了相关的阐述。第三种观点为“隐语说”。隐语又称廋辞,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谜语。“
隐语说”认为辞赋的起源受到了隐语的很大影响,甚至于赋就是源自隐语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历史上首个以赋命名的文学作品——荀子的《赋篇》,即多用隐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荀结隐语,事数自环”,“荀卿《蚕》赋,已兆其体”等句,已经认识到隐语和辞赋的关系。等到王闿运论赋,则更是直接将隐语和赋等同而论之,他在《论诗文体式答陈复心问》一文中说道:“赋者,诗之一体,即今谜也。亦隐语而使人自悟,故以谕谏。夫圣人非不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伤相继,政俗无裨,故不为也。庄论不如隐言,故荀卿、宋玉赋因作矣。汉代大盛,则有相如、平子之流以讽其君。太冲、安仁发摅学识,用兼诗书,其文烂焉。要本隐以之显,故托体于物,而贵清明也。”关于辞赋的起源,尚有其他诸说从略。社会本是复杂而多元化的,任何一种文体的兴起、昌盛以及衰落,应该说都是社会诸般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分析辞赋起源时,总括前人之说,提出了“综合说”,或者称“多源说”。清人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有一番话尤为精辟:“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章学诚对于辞赋兴起之因缘讲述得比较到位,既认识到了诗骚肇其端的作用,也看到了战国时诸子百家之文对于辞赋产生的影响。后来的姚华在其《弗堂类稿》中论及赋之源流时,从古诗之六义出发,再讲到荀卿演赋,楚辞递兴,赋也日益成蔚然之气象,进而指出“骚者诗之变,而辞赋之祖也。于是赋有三本:其一承诗,其次拟荀,其次宗楚。”学者马积高在此“三本”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三本的说法,将辞赋大体分为三大类,每类的源头都各有所本:一类是从楚歌或者说民间歌辞演变而来,叫骚体赋,比如屈原的《离骚》;一类是从战国诸子的问答体以及纵横家之文辞演变而来,可以称为文体赋,比如宋玉的《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之赋;还有一类,则是从诗三百演变而来的,不妨称为诗体赋,比如屈原的《天问》、荀况的《赋篇》、扬雄的《逐贫赋》和赵壹的《穷鸟赋》等。
当然,诗体赋其实并不应仅仅限于四言,五、七言诗兴起之后,赋体中亦往往有相应之体出现,如骆宾王擅长五言诗与七言歌行,其赋作《荡子从军赋》,通篇五十多句,除了“抗左贤而列阵,屯右校以疏营”“既拔距而从军,亦扬麾而挑战”“终取俊而先鸣,岂论功而后殿”“花有情而独笑,鸟无事而恒啼。见空陌之草积,知暗牖之尘栖”等十来句为六言之外,其他基本上皆为五、七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