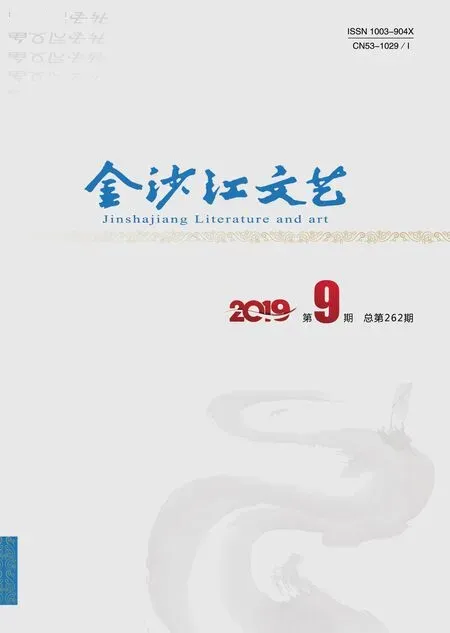注入时代意蕴 记录文学成长
——评杨荣昌《攒动的群山》
2019-11-13杨继渊
◎杨继渊
伴随新时期历史前进的步伐,楚雄文学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与时代一同成长。新时期以来的40年,楚雄文学创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到目前为止,楚雄本土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1 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184 人,楚雄州作协会员586 人,形成了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网络文学门类齐全的楚雄作家群,成为当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楚雄师范学院的青年批评家杨荣昌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民族文学的研究与评论,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关注前沿文学动态并作出及时的理论反应的同时,他聚六年之力,对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进行爬梳剔抉,精研成章,推出了大气、厚重的《攒动的群山——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论稿》(以下简称论稿),这既是他对自身学术领地的新开拓,又填补了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研究的空白,同时是对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生动记录。
一、溯源探流,理清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脉络
楚雄新时期文学诞生于2.8 万平方公里的楚雄彝州大地。楚雄,地处滇中高原腹地,山灵水旺,气势雄伟; 磅礴乌蒙虎踞东方,巍峨哀牢龙盘东南,百草岭鹤立西北,金沙江滚滚东流,礼社江欢腾南去。上苍孕育生灵于三山二水间,2.3 亿年禄丰恐龙活动于此,170 万年元谋猿人生活于斯。这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彝族十月太阳历、十八月历发现于此,以2.3 亿年前的禄丰恐龙化石、800 万年前的禄丰腊玛古猿化石、170 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化石的发现而闻名于世。这里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具有丰富的民间史诗传统。以《查姆》《梅葛》为代表的彝族创世史诗,是研究彝族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和民俗的重要资料。叙事长诗《赛玻嫫》,抒情长诗《彝族哭嫁歌》,彝族民间故事《罗牧阿智的故事》和《沙则的故事》等,构成了楚雄古代文学主流,对后来楚雄现当代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楚雄的少数民族肩负着本民族的历史责任,他们用汉语言文学表达民族思维,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民族性。反映在创作中,已构成一种文化存在价值和独特的艺术特色品质。杨荣昌在长期的阅读、研究中发现,楚雄新时期的文学与各个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流尽管有交融、有互补,但更多的是坚守自己的美学立场,彰显自己的艺术个性,坚持民族性和地域性,向文坛昭示自己独立存在价值。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楚雄文学自 “五四”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新革命,其对楚雄新时期文学影响至深,如文学现实主义根基的固化,文学时代性的强化,文学写实格调的定型,作家使命感、忧患感的加深,创作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密切等问题,杨荣昌能够把楚雄新时期文学纳入到时代发展变化之中,与远古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相连通,赋予了新时期楚雄文学以深广的历史维度,凸显出楚雄新时期文学所彰显的民族精神,这就使点与面、今与古、民族与世界有了较为妥当的联系。
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是构建地域文学的基本框架。《论稿》在进行空间维度考察的同时,以时间维度的发展作为叙述的脉络,对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作了系统梳理与全面扫描,全景展现楚雄文学发展面貌,具有传统编年体史书的特色。全书所述上起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金沙江文艺》创刊,下迄2018年,且依年份的变化而自然延伸,以时代的更替构成不同的段落,叙述清楚明晰,方便查阅与寻实。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首先借助了大量的史料,对之进行认真地辨伪存真,剔析梳理; 同时又对许多方志、相关作家的研究成果进行广泛阅读,细致考辨,使对各个时期的记述更为丰富、翔实,勾勒出楚雄新时期文学40年来的演进与嬗变的全貌,呈现出兴旺繁荣发展的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态势。
楚雄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杨荣昌以批判的思维审视研究对象,辩证地书写,更倾心于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文本的生命力; 诗性地言说,渗透史论结合的传统。研究触角伸向丰富的文本内核,勾勒出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生命轨迹。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时间跨度为40年,杨荣昌以乡土文学始终贯穿全过程为中心,遵循史学、文学、美学等逻辑结构,精准地把握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代表作家作品,选取展示不同时期出现的文学现象、代表作家及创作实绩,从地缘文化学角度勾勒主客体、文化构成、审美心理结构等基本特征,理性概括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将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和特殊文学生态相结合,进行具体阐释和理论探究,对楚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稿》主要对作家作者的生平、文学活动与创作实践等进行裁录,同时对影响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较大的文学组织、文学活动、文学奖励制度等史料给予适度收入,这样的处理是很可取的。作家作者是一个动态的存在,一方面,他们始终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作家作者间又相互产生着影响,并影响着特定的文化环境。只有把视野放宽,才能进一步增强所述对象的历史感与客观性。
《论稿》既弥补了有关楚雄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的不足,又拓展了楚雄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空间和领域。文学研究在对具体的或类别的文学个案和现象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后,就需要并呼唤着更深入而阔大的史家写作,这昭示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要求研究者的思路拥有史家的眼光与气魄; 另一方面,指研究成果需从历史的意义中走向现实和向未来敞开。阅读这部《论稿》后我们会发现,有关楚雄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已进入文学史写作的新阶段。杨荣昌的《论稿》出版之前,已先后出版了左玉堂、芮增瑞、杨继中编著的《楚雄彝族文学简史》(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版),芮增瑞先生编著的《彝族当代文学》(云南民族出版 社,2002年12月版) 等专著,为建立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研究的体系奠定了一些资料和理论基础。历经6年的挖掘、梳理并进行理论概括,杨荣昌写出了系统、丰富、翔实的专著,它既填补了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研究的空白,又以新颖而独到的理论视角和文学史家的气魄,构建了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研究体系,从而把楚雄新时期文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和进程。
二、史论结合,展现楚雄新时期文学的本体形态、人文关怀、价值体系和审美风格
《论稿》虽说具有史的特点和意义,但它的写作体例区别于一般的文学史,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严格说来,在体例、结构和方法上都很严谨,材料也非常丰富。它采用的是一种以 “史” 带“论” 的方式,史论结合,知人论世,人品和文品并论,开创了一个文学史写作的新方法,也提供了很多新的信息。它着眼于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意义结构和问题框架,而不是简单的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演变。作者首先确立了对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总评价,准确地说是作者自己的楚雄文学新时期文学发展观。他认为楚雄新时期文学是以乡土文学贯穿全过程为中心,从而形成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融会发展的特征。在叙述上,采取以叙述为主,以史带论,史论结合,辅以作品评析和作家论述,勾勒出40年的新时期文学发展轨迹。在时间性上,把楚雄新时期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筚路蓝缕的开创期 (1978年—1984年)、承前启后的发展期 (1985年—1999年) 和走向文学自觉的成熟期(2000年以来)。上部为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史述,叙述《金沙江文艺》的创办、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实施 “八三四”计划、文学社团组织,组织化的文学生产、文学组织、文学活动、文学奖励、文学奖励制度,包括重要作家的文学创作和作品发表、出版情况、兼及介绍在20 世纪80、90年代活跃但2000年以来逐渐淡出文学视野的作家; 下部是楚雄新时期作家创作论,介绍2000年以来仍活跃于文坛的楚雄作家群。
楚雄老中青作家创作贯穿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40年,因此杨荣昌对其论述的重点放在下部,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创作述评、竞相争艳的楚雄文苑两章,以60 余个楚雄作家为案例,具体、全面地勾勒出新时期楚雄文学发展的整体风貌,以其丰富的资料性,不可辩驳的理论气势和细密而严谨的思维方式全面而真实地评述了竞相争艳、果实累累的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成就。当他的大部分论述文章几年前在《中国艺术报》《中国民族报》《云南政协报》《雨花·中国作家研究》《边疆文学·文艺评论》《文学界》上发表时,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过较大反响,因为它体现出一个真诚而执着的青年学者所具有的无畏勇气和坚守科学真理的学术精神。现在,他又把它们置于《论稿》的重要位置,在写作体例上起到 “导论” 或 “总论” 的作用,实际上更隐含着一种潜在的深刻意义,重现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真实面目。
蒋寅先生曾说:“历代的文学研究,由于在文献上发掘不够充分,提出的问题和结论都比较肤浅,许多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和文学史人物都缺乏扎实的研究多方面成就,并未受到关注”。这种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杨荣昌却很好地避免了这一些弱点。他不畏艰苦,爬梳剔抉,细大不拒,广泛参阅了多种文献、传记资料、地方志、诗文别集,使得《论稿》文史互证,尽显文坛多姿多彩的人生风景,使得本来枯燥无味的一部文学史变得有血有肉。正是这种扎实细致的考证,引领读者逐渐步入风云多变的历史情境之中,更加深切地理解楚雄新时期文学思想和创作,从而避免了空疏枯燥的学术流弊。作者在《后记》中说,为了研究楚雄新时期文学,参阅了大量的理论书籍和评论文章。尤其是《楚雄彝族文学简史》《彝族当代文学》《楚雄彝族自治州文艺评论家协会文艺评论选》等书籍,以及马荣春、马旷源、李俊、张永权、张昆华、张承源等作家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写作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他的研究时间长、用力勤、资料占有多、成果也最为丰富,在史料与观点上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个性,既接受了老一代学者的扎实与厚重,又吸收了青年一代学者身上的新颖与方法更新,从而结出丰硕的研究果实,已引起研究界的关注与探讨。因为他的努力与成就,使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成为研究楚雄地方文学的重镇和中心。
三、纵横对比,阐述楚雄新时期文学在中国文学大格局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地域文学的差异
近年来,文学界愈发关注各种文学史的重写及新研究领域的开辟。通史、断代史、分体史、学术史、名家名作个体研究史以及诸如抗战文学、民俗文学等专题研究史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显示了盛世文学发展的辉煌实绩与良好趋势。而地域文化研究自上世纪末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关于几大地域文化版块如河洛、荆楚、齐鲁、巴蜀、岭南等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作为地域文化研究重要内容的地域文学研究,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睿智目光,湖南、黑龙江、河南、山东等省级文学史研究著作的出版可谓 “引领风气之先”。杨荣昌的《论稿》凝聚着作者苦苦思索并尝试系统化理论构建的努力与心血,饱含着作者对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真挚深情。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由此看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楚雄这个局部地区发展的缩影,看到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典型性和特殊性,看到楚雄地域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具体的操作,还是学理的深入探讨,它对研究楚雄地域文学都有着深刻的导航意义和参考价值,值得学术界重视。
作者以自己独立的文学观确立了评价、认识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点和价值度。他认为 “民族性” “地域性” 和 “时代性” 是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创作所显示出的精神特征和审美意蕴。“民族性” 是当代中国与世界历史潮流的核心,也是楚雄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核心。中国现当代文学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以 “人的解放”和 “民族的解放” 作为思想背景,并内化为文学的创作主题,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也就成为它所追求的双重目标,生长于多民族生活背景下的楚雄新时期文学进一步强化了它的 “民族性” 这一主题。当然,也是楚雄彝族主体背景下多民族生活本身对文学的呼告与召唤。《论稿》把 “民族意识” 作为理论基点,同时又强调了楚雄新时期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找到了楚雄新时期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关节点,也理所当然地使楚雄新时期文学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和世界新时期文学联成一体,因为它们都凸显出鲜明的民族意识。杨荣昌的楚雄新时期文学观,站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学发展主潮流的高度,力求对楚雄新时期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评论、戏剧的整体关照,发现其中的交融、呼应以及个性。
《论稿》中,杨荣昌从不同角度系统地阐释了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轨迹、主要理念、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贡献,对作家的评论注重知人论世,对作品的评论兼顾审美和历史的标准,又参以文化的民族视角,见解独到而又切中肯綮,可以称之为楚雄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硕果、里程牌。作者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思想缜密、充满理性,他始终坚持正确的学术思想,尊重文学规律,潜心研究,求真务实,因此《论稿》可视为我国地域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必将在地域文学史研究领域产生积极影响。作者认为,“楚雄作家要关注民族性,认真分析楚雄民族文化资源的特点及共性,选准切入点,尝试写作民族化的题材。重点探究民俗、民族文化后面所蕴涵的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切忌走平面化、猎奇化展览民俗文化的路子; 不拘泥于现成材料,创造性地应用民族文化资源,凸显作家主体性地位。如果楚雄作家能在历史文化和乡土两个维度上奋力开掘,楚雄文学必将大有可观。” 在地域文学理论探索上,显示了一种开阔的视野和执著的追求,为我们建构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版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思路。
《论稿》在方法上也很有独特之处,从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上,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横向的比较与纵向的联系中,去思考问题。酝酿思路,框定格局,进行写作。从世界文学主潮流中汲取营养,同时也能立足中华美学精神,构建楚雄新时期本土文学话语体系,它涉及到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作为单个问题出现,而是从时代演变中引伸下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空间,就成为一个世界的地平线。有学者认为,现代文学研究者与当代的评论家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他的历史感,前者看问题的思考视角总包涵着一种历史眼光和深度,这使得现代文学研究总渗透着浓厚的学院气氛。应该说,杨荣昌的研究方法也浸润着丰富的历史底蕴,这既是一种学术眼光,更是一种学术精神的彰显,对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研究的深化与体系建构,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多年来,杨荣昌以 “写一部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史” 为宏愿,孜孜不倦地从事楚雄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工作,新见迭出,佳作不断。这部耗时6年完成的著作,脉络清晰,完整地梳理了楚雄州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学发展史,在对楚雄文学40年历程的回顾与叙述中,呈现了几代作家执着奋进的心路求索历程,让新时期的楚雄文学及楚雄作家群得到了呈现。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雁岭文心》丛书主编曹晓宏教授在《地域文学研究的系统化与深化》一文中认为,《论稿》的出版,“让四十年的楚雄新时期文学终于有一个相对周全的学术呈现,让闪光的文学精神穿过历史的积云,绽放其锋芒。同时,也寓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那种甘于寂寞、勇于挑战的学术理想,在被滔滔名利裹挟、层层体制压抑的学术情境之下,依然存活并焕发光彩。” 诚哉斯言,期望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