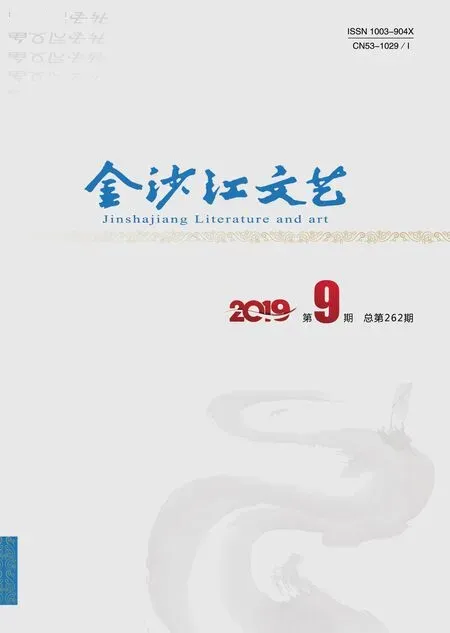大江行吟
——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移民搬迁采风笔记
2019-11-13赵春银
◎赵春银
从龙街渡出发
从龙街渡出发,顺江而下,我们就走进了乌东德大水爬升的地方。
攀枝花谢了又开,老酸角树叶归去了又来,渡口礁石的创伤还在,红军标语的光芒还在。
钻天坡的牛羊从白云中走进天堂,放牧的彝女用金沙江作长长金线,缝补时光。
古驿道在落水洞啃穿了山岩,一队马帮从我们眼前穿越,消失在历史的山岚。马蹄踏碎晨昏,清脆的铃声被古老的榕树收容。那时的黑者村们、万德勒村们,远在天涯。
五月,山枯水瘦。
岁月雕刻的皱纹,铺展在江岩的两岸。从大江涮净的山脉肋骨上,你可以清晰读懂地老天荒; 在江流婉转的迷蒙天际里,你能够依稀印记水远山长。
峰回水转,睡美人迎面横陈,浴足江水,双乳高峙,哺育苍天,也哺育了大地先人。在美人峰下,我们永远都是孩子。
从龙街渡出发,顺江而下。落水洞、金砖岩、观音山、白马口……一个一个优美的传说欲说还休。
我们将收集一村又一村古老的记忆,以及一丛又一丛劲草一样浓密生长的乡愁。不让他们沉睡水底,我们将和彝族同胞、傈僳同胞们一起,合力将他们搬向新家福地,蓬勃生长。
大江两岸,回望故乡。搬迁绝不是水涨船高,而是由闭塞落后的末梢,一步踏进现代化的天堂。
在天空行走的黑者村
晒黑的山崖石峰早已困顿,惯看的大江已成老旧风景。桃花汛年年如约而至,而每一朵野花都会按时刷新春天。
多年来,黑者村已经融进了黄白的土壤,黄白皮肤、黄白楼房、黄白篱笆、黄白的村巷。
路在楼顶,黑者村是行走在天空的村庄。家家门不设防,夜不闭户。谁说了人心不古,请到黑者村找回你的天良。
巷口的酸角花又开了,手掌上的血泡又开了。楼顶的黄土瘦了又肥,田野的庄稼黄了又青。清亮的汗水滋养着黄白的土地,黑者村,守着孤独的大江,和打盹的远峰,缩在世界的角落,把又苦又涩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黄白的土掌房顶,老阿妈在对江祈祷,搬迁临近,她坚信自己的灵魂终将被观音山收纳,皈依圣洁的莲台。
一抔乡愁,在一位老叔的楼顶散发,比云淡,比风轻; 比山重,比水长。现在,村后山顶的苦水箐、以都拉村,随着扶贫规划,即将人去村空,孤独的黑者村也将在水电移民的号角中迁往新天地,许多村民的思念早已远游,向往那神奇的新生。
世界给你关上了一扇窗,就必然为你打开一扇门,这个道理我懂; 沧海可以成为桑田,桑田也可以更有价值地成为沧海,这个道理我也懂。我只能用酒泡淡与生俱来的乡愁,让江风吹散我难以下咽的忧伤。
为了远方的召唤,干杯,为了祖国的发展,干杯,即将到来的永别,干杯!
聆听以进嘎
一登岸就是古木阴凉,一转弯就是金色沙滩。
老榕树坐拥巨石,从容向天,巨掌四顾,荫庇八方; 攀枝花树如巨龙探海,枝叶温柔舒展,抚摸一江粼粼波光; 劲草高过人头,抢滩登陆,齿叶剑指四方。在以进嘎的古木荫里,我愿意是一枚圆润卵石,永享清凉。在以进嘎彝族古歌声中,我找到了先祖征服自然的力量,以及洪荒万古的悲壮。
笛声清越,豪迈张狂,一进入歌的世界,舞的海洋,老阿妈小婶子以及大叔小哥们,全都放下了故土难离的惆怅,沉浸于干干净净的欢欣。让患得患失的我们顿悟:欢乐可以如此的真实而简单。
攀枝花完成了表演,凤凰花又登场,凤凰花卸妆了,还会有满山的索玛花向我们走来。现在,一树树鲜艳的火炬点亮了古老的村庄,一个个工作队员穿越了一扇扇安土重迁的心墙。
必须对移民满怀大山一样的敬畏,对保守老人们具备大江一样包容的心肠。新居需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
唯有老阿妈的诉说让我们抓狂:十围老榕树是我的硬伤,为了祖国的富强,我只能选择慢慢疗养。神啊,我请求你予我几秒的神奇的力量,瞬间恢复老人满脸的荣光。
江边篝火红
沙滩是沉睡的波浪,卵石是流浪者筑梦的故乡。劲草收藏好强劲的能量,退守山脚,背后的黑者村花香夜暖。
江石被阳光翻晒出赭红的心情,江风翻越重峦叠嶂,在薄暮送来亘古苍凉。江面悦动着天之湛蓝,金沙一般悄悄闪耀起漫天星光。
赤脚亲吻江沙的绵软,忧虑在夏至的暮色里走散,江风正用清凉的手掌,抚慰疲惫的心房。
一堆篝火就是一个重生的太阳。黑暗中虫甲蚂蚁在尽情吐露心事,火之舞消融了彼此的陌生和彷徨。火光映红的笑脸,全部跑进童年,回到先祖的梦幻故乡。
火的热力送来烧烤的芳香,火的飞腾让我们张开兴奋的翅膀。今夜,心不设防。不管是鳏夫与村长,不管是美女与丑男。我们饱受掩藏之苦,我们需要还原一个清澈轻盈的自己,抖落一身的沧桑。
在江边的篝火旁,河滩地醉了,黑者村醉了,文友们醉了。变成蜻蜓,变成蝴蝶,甚至是雄鹰,在金沙江河谷惬意飞翔。
迈道中年,我们极少这样举止不端。金沙江,请接受一群诗人在你的怀抱里慢慢变老,请容许我们像无名的小兽在你的沙滩上写下笨拙的诗行。
在清醒的陶醉中,人人皆回归真我,欢声笑语里,敦厚安然,心底敞亮。
今夜篝火红,我们都变成了浴火重生的凤凰。包括那个使尽招数的村长,包括那个最最顽固的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