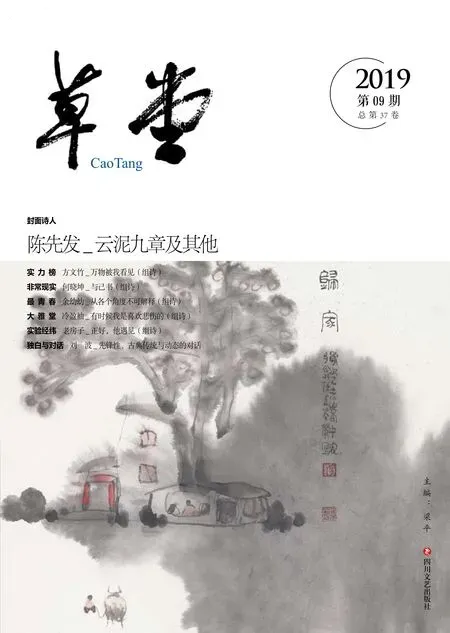未知的旅途、中年困境、写碑之心以及救赎的可能
2019-11-13卢山
卢 山
诗人陈先发早前在凤凰读书上有一篇题为《困境与特例》的文章,阐述了自己对诗歌写作与诗歌写作的现实语境的一些思考,他说“诗,本质上只是对‘我在这里’这四个字的展开、追索而已”。
陈先发道出了写作的终极秘密。我思故我在。古往今来多少作家试图用肉体凡胎推动西西弗斯的石头,用一支笔撬开写作和生活的嘴巴,从那些幽深的黑暗源泉中寻找栖居的家园和存在的意义。写作终究是为了解决个人存在的问题,是一次伟大的自我完成和自我救赎。我之前曾读过陈先发的诗集《写碑之心》,受益于他精准的语言天赋和化古为今的杰出能力;同时,我也感慨于今天的诗人如何在未知的旅途中发现诗意,在旷野的野蛮和荒芜的困境中,保存自己的“写碑之心”?
孤寂的诗学与“我拥有石榴趋向浑圆时的寂静”
博尔赫斯说一个诗人要在诗歌中留下他自己的形象。陈先发的诗有一种孤绝、冷静、克制的学者气质,善于透过庸常的生活表象直达诗歌的精神腹地。他是一个不断向内挖掘的诗人,将所见所未见之事物纳入自己的阐述体系,不断开掘寻找诗歌之道、解开世界之魅,构建具有自我辨识度的诗歌世界。
《云泥九章》和《知不死记九章》显示出一种孤寂的气质。当然,从诗歌的题目上来看,我们会联想到诗人屈原的名作《九章》,诗歌里都交织着辗转反侧、冥思叩问、虚实转换的情感和场景;我不知道陈先发是否有意在向屈原致敬,或者向着这种伟大的文学传统靠近;但是,至少从这组诗歌里,我们能感受和发现陈先发的诗歌抱负和理想,对于生死的思考、对于存在和虚无的追问等。云和泥,天上人间,阳春白雪,高蹈,游离,存在与虚无,大和小的对峙,我想到了这些词语和组合。
这是一组“在路上”的心灵冥思之作。“在路上”是伟大的文学母题,召唤着诗人进入它幽深的腹地。陈先发在乘坐高铁时所遇到的时空变化、场景错叠,激发了这些诗歌的触发器。“几个小时的旅途。我反复/沉浸在这两个突发的/令人着魔的问题之中”,他试图在这次旅途里寻找到某种意义上的救赎。
“铁轨切入的荒芜/有未知之物在熟透/两侧黑洞洞的窗口空着/又像是还未空掉,只是/一种空,在那里凝神远眺”。通读这组诗歌,他笔下的“未知之物”,不就是“那种空无”吗,也不就是那只在《闷棍记》里“都已不知所终/又仿佛仍悬在那里”的“闷棍”?无限意义上的广阔的存在和生长的空间,他试图去揭示意义在空无中的野蛮生长。他深究事物的内涵与外延,探索事物的内部和外部如何做到统一性?于是沿途的那些事物进入了他的思想国:“蓊郁之林中那些枯树呢/人群里一心退却/已近隐形的那些人呢”“而人群,像一块铁幕堵住我的嘴/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当由自然场景进入社会化的世界,诗人面临的困境到来了。“一种空,在那里凝神远眺//在‘空’之前冠之以一种/还是一次?这想法折磨着我”。“一种”和“一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中代表着不同的丰富性和唯一性。“一个空/我们曾是,是,并永远/将是,盛开的:/这空,这/无人的玫瑰”(《赞美诗》),诗人保罗·策兰从苦涩的杏仁中只能看见空无,而空无之中的存在是什么?我相信陈先发从空无之中看到了伟大的风暴和力量。
他从大地升起的一片虚无中,寻找到了强悍的力量。一个诗人如何做到与虚无之间的和谐相处?向虚无借一盏灯,汲取一汪泉水,开出一朵绚烂的花瓣。无论是写作的虚无还是中年的游离,都在这次特别的旅途中,随着铁轨的延伸而抵达了中年的词根。他度过这片虚无可能只需要一只黑鸟,一棵桦树,是的,旷野上的一棵桦树拯救了他。
他在诗歌里进行一系列的叩问:“以枯为美的,那些树呢/弃我而行又永不止息的那些人呢”“黑鸟取走的,在门背后会丧失吗”“旷野有赤子吗”“会有一股稀有的蛮力/把我们吞入曾经的那个壳中吗”……这次旅途让他陷入某种在场的冥思,进入了海德格尔似的黑森林中进行诗歌和肉身的存在之思。我想此时的诗人不就是从黑森林里飞出来的一只他笔下的“黑鸟”吗?“塔身巍峨,塔尖难解/黑鸟飞去像塔基忽然溢出了一部分”,黑鸟揭示表象的存在,而他在寻找和追问时间背后的那些存在之物,那些诗歌所无法捕捉和阐释的存在。而现实是某种无奈:“我只剩这黑鸟在手,寥寥几笔建成此塔又在/条缕状喷射的夕光中奇异地让它坍塌了大半。”
当然这其中也描述了某些温暖的片段。石榴树、小狗、旧诊所,“暮光为几处垃圾堆镀上了金边”,而此时“我拥有石榴趋向浑圆时的寂静”。深陷中年危机里的人,我们如何拥有这种“石榴趋向浑圆时的寂静”?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自在和辽阔!
火车因为故障停靠的小站,显现出某种神性的所在,“渗着血迹的白衬衫在绳子上已经干透”。我忽然想起了诗人米沃什的那首著名的诗歌《礼物》中“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所呈现的安然和美好。接着他描写了旷野里那些“赤子”:“瞧瞧晨光中绿蜻蜓/灰椋鸟/溪头忘饮的老牯牛/嵌入石灰岩化石的尾羽龙”都是“这些云中/和泥中的眼睛”。云泥在此出现了,这万千世界存在之物无不在云和泥的辩证法里面了。但是我们却在不断的社会化和现代化中丧失自己的“赤子”部分。陈先发在发问“会有一股稀有的蛮力/把我们吞入曾经的那个壳中吗”?我们还能回到出发的那个地方吗?未来仍是虚无缥缈的,未知的事物野蛮生长,如同诗人的命运,“B 地依然不可知、不可测、不可控”。
时空变幻,云泥交织,他甚至由此进入了某种对往事生活瞬间和片段的回忆。这时候月亮下的父亲出现了。“是逝者伴随我们完成从/A地到B地的徒然迁徙/父亲高挂于途中任何一处”,生与死不也是“云泥”的一部分吗?陈先发在《困境与特例》里写道,“我父亲要在我身上永远地活下去,就必须在我不断到来的回忆中一次次死去。而他每一次死亡的镜像,都并非简单的复制,因为对应了诗的创造,这镜像自身也成为一种创造。诗,在对遗忘的抵制与再造中到来,是对‘现实存在物中不可救药的不完美’(普鲁斯特语)的一种语言学的补偿。”云和泥是多么的悲怆!
这组诗中展示的旅途最后以父亲的出现而结束,实现了生与死的循环往复,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救赎——“干干净净的风吹着/我们从它的空心一次次由云入泥”。死,这个时候成为一种必须解决的命题:“我置身于死者之中/死得越久、剩得越少的死者/让我心安”(《马鬃岭宿酒记》),“曾无息而共饮的死者围着我”。生命和诗进入一种可怕、孤独的空无中的静寂,这是死亡的悖论,也是命运的可能。当然,诗人给我们保留了一个温暖的结尾“我们因为爱这些叶子而获得解放”(《观银杏记》),诗人获得了某种完成仪式之后的解脱和寂静。
“写作,就是去肯定有着诱惑力威胁的孤独,就是投身于时间不在场的冒险中去。”(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诗人以智识来引导幻想,对现实和逻辑常识秩序及情感常规秩序的颠覆,对语言的律动力量的操作,让诗歌呈现犹疑、尖锐和迷茫的特性。它清澈的叙事与高贵的抒情无不显示出生命天宇的澄澈与清晰,显示出生命理性的高贵与深广。
在路上的困境和冲突以及诗歌晦涩性的问题
旅途中的“困境”和“冲突”无处不在,无论是自我内部的审思叩问还是外力的重叠碰撞,都创造了写作的广阔腹地和某种可能性。陈先发自己坦言,“哪个时代的人能逃脱掉这种质疑与冲突、矛盾与变形呢?我相信,在所有时代生性多敏的诗人身上,这种撕裂都会有,而且会有许多歇斯底里的时刻”。当下的社会转型期的进程中呈现的病症,以及诗人写作之路上的身体分泌的虚无和疼痛,无不都是一个“在路上”面临的困境。陈先发显然在这组诗里注意到了这种隐性的冲突,无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文字的触须都触及了自我以及社会的一些病症和痛点。
评论家敬文东说陈先发的诗歌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刺痛”,我认为这是一种读书人的内心的悲怆和理想的表征。“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者眼中的桦树。/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丹青见》)向死而生,以死为美,多么伟大的救赎!从词语里奔突而出的力量,再现了诗歌理想的可能。我想起诗人保罗·策兰笔下的那棵白杨树 :“你们高高的白杨——大地的人类!” “我看见了你,姐姐,站在那光芒之中。”
“远方……和闷棍,都已不知所终/又仿佛仍悬在那里”(《闷棍记》)。似乎一个艺术家对他所处的时代来说永远是一个境外流浪者,如波德莱尔所谓的“微服私访的王子”。似乎所有真正的诗人都是自己时代的“波西米亚人”,没有尽头的漫游成为其生存方式。诗人在他存在的时代只能是一个路上的漫游者。他在不断地承受生命的履痕和疲倦,并采撷甜美之蜜奉献人间。他把自己在漫游时所经历的焦灼和孤寂,通过歌唱的方式表达出来。
当然这一组诗歌存在着晦涩性的难以进入的难度。晦涩是诗歌现代性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方法。陈先发这样的诗写,无疑是有难度的诗写。 他说:“我一直主张在词语的组合上,保持充分的弹性,以便在一首诗内部形成尽量多的空白,为那些不能显形为词汇的语言留置更多的呼吸空间。这几乎是在说:空白,其实是一种最重要的语言。”他通过词语的交织、变形制造了诗歌的“空白”。诗歌语言是一种建立在记号基础上的情感语言。正如诗题,这组诗可以说是冥想的盛宴,存在着某种“创造性的晦涩”和“多义性的象征”,它不断逼仄着读者的想象空间,激发着其跳跃性思维,没有诗歌阅读理论基础的读者是很难获得其解读的密匙。
布罗茨基反对把诗歌变成娱乐和读物,“语言的堕落导致人类的堕落”,真正的诗人要保持对语言的敬畏和敏感。“晦涩难解让他着迷的程度,恰与让他困惑的程度相当。这诗歌的词语魔力与神秘性发挥着不容抗拒的作用……”(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通常这类诗歌并不被人理解,因为按照艾略特的话来说,它并不包含“让读者的习惯得以满足的”意义。然而真正的艺术都是向心而生、向死而生的,它甚至从一出生就开始拒绝大众,因为他是面向历史和未来的写作,也是面向存在和时间的写作,“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它毋宁是一种纯洁的写作”(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
云和泥的辩证法无处不在,正所谓“但有危险的地方,也有拯救生长”(荷尔德林),困境在突显的同时也会出现特例和意外,诗歌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面对当下的写作环境,陈先发显然是充满自信的,应“当速朽登高一呼”。“是的,诗歌可以从一片垃圾上发现它的时代”(《困境与特例》),而正如评论家胡亮所言:“他必将同时在两种考量——美学的考量、历史的考量——中求得胜算,成为一个精致而显赫的罕见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