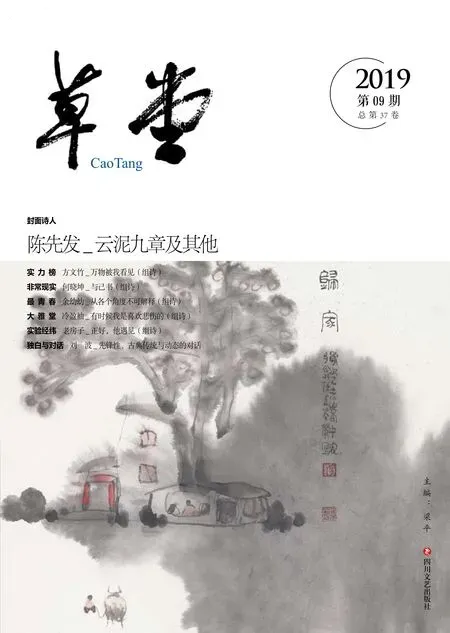先锋性、古典传统与动态的对话
2019-11-13刘波
刘 波
进入新世纪以来,先锋诗歌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说法,很少有人质疑这一命名的合理性。之所以谓之先锋,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于诗歌中所潜隐的现代性与异质的反叛精神,它与盛行的主流诗歌审美拉开了距离,以更具前瞻性和创造性的书写建构先锋的诗歌美学。诗人们也确实在以自己的实践靠近这样的先锋,但他们普遍强调的是其反叛精神,一味地注重消解、破坏与颠覆,而缺少必要的守护,这样的先锋性就显得平面化。这也是新世纪诗歌在先锋性上弱化的原因,整体上缺乏一种冒险的气质,诗人们也很难把握好探索的尺度,这种理解和体悟无法在更深的层面上确立起先锋的谱系。
也许正因为先锋诗人所面临的困境是普遍的、整体的,新世纪先锋诗歌的生产机制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1980年代带有浪漫主义抒情色彩的先锋转向了更为节制、内敛的叙事性先锋,这一转向是先锋诗人由主情型向主智型写作演变的见证。然而,在先锋诗歌试图接续上1990年代的话语策略时,受消费主义的影响,观念化写作盛行,先锋诗歌的格调愈发显得凡俗平庸,如同诗人朵渔所感慨的,“写小诗让人发愁。”当大面积的“小诗”充斥诗坛,先锋何去何从?先锋如何与时代、现实和传统对话?先锋诗人在普遍的症候性书写中能否重新召唤新的诗歌精神?这些追问可能是历史延续性的表征,它需要打破固有的认知,再度找回丢失的先锋诗歌的主体性。
[先锋的困境及其拓展空间]
如何认识先锋,对于诗人来说,仍然是个内部问题。一直以来,我们过多地强调了先锋这个词,以致将其等同于现代性、反叛和极端的冒险。这在一个需要打开视野的特殊历史时段具有它的效力和影响,但是当过去的先锋也成为当下的主流时,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界定先锋的属性?针对新世纪以来的现代诗,似乎都可以称为先锋诗歌,对此并没有多少人去质疑,先锋诗歌这一概念本身究竟包涵了什么样的对诗之创造的主体性认同?什么样的诗歌不是先锋诗歌?我们能否承认自己写的诗是不先锋的?先锋诗歌是否对自身的美学也构成了一种遮蔽和掠夺?这些疑虑在很多诗人那里其实被当作了“伪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的写作被排斥在先锋的范畴之外,一旦哪个诗人被认为是非先锋的,也基本上就相当于取消了他的现代诗人资格。“即便‘先锋’这杆旗被当代艺术擎着已成破竹之势,它也难逃桑塔格所讲的‘必成商业文化、广告文化一个分支’的魔咒。已极少有人敢承认我是旧的,我不能。”(陈先发:《黑池坝笔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88页)诗人们如此看重身份上的“先锋”这个修饰语,原因何在?“现在诗歌界很少有不以‘先锋’自居的”,先锋首先就体现为一种反叛,因此,“诗歌‘先锋’所需的才智成本十分低微。”(陈超:《“先锋流行诗”的写作误区》,《山花》2008年第10期)皆因先锋意味着不落伍和前沿性。在相信历史的线性发展逻辑这一“正确”的观念下,只有先锋才是诗人的护身符。正因为先锋如此泛滥,关于先锋的标准没有统一和明确的界定,于是,所有的现代诗都可以称为是先锋诗歌。
评论家耿占春在谈论雷双的绘画时曾说过,如今,“所谓先锋也早已成为俗套”(耿占春:《可见性的秘密或反对俗套——关于雷双的画》,《艺术广角》2017年第2期)。诗歌界的先锋估计也和艺术界一样,“先锋”这个词本身就变得滥俗,不是说它让我们丧失了信任感,而是在面对浩如烟海的作品时,我们可能也不知道“何谓先锋”了。当然,这个命题可能没有真相,而先锋到底何在?“先锋无罪,罪在对先锋的误解和利用,罪在诗人的短视、狭隘与偏见。”(朵渔:《先锋就是冒险》,《诗歌现场》2008年春季号)朵渔的解释可谓一针见血。那么这个时候,先锋就不能再用来作为衡量诗歌的标准,而要看它是否成为诗人们在写作上的精神自觉。先锋作为一种意识的存在,它并没有退潮,只是在另一种向度上转化成了诗人们的美学气质,也就是说,它不再需要刻意标榜,而是内化成了某种诗歌精神。
在我们看来,先锋只是“保守”时代的产物,它必须要打破某种范例和规则,很大程度上是从形式入手的,这就是先锋诗歌一直未曾摆脱“形式先锋”的缘故。新世纪以来,很多人也在反省诗歌的先锋:什么样的诗是先锋诗?先锋不仅有形式的先锋性,而且更多的是精神和思想的先锋性。现在看来,先锋应体现为一种综合气质。“先锋性不是一个流派的写作倾向和风格,而是一种写作精神。它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人的。”先锋作为个人化创造,依据的是想象力和独特的语言禀赋,诗人需要在这一秩序内部完成对个人趣味的召唤。先锋性意味着某种反叛的力量,其创新建基于消解的功能。余怒对先锋的理解,乃出于诗人的直觉,他甚至将自己的理解转化成了公共的经验认知,先锋摆脱了单一的修辞表述,而进入了相对复杂的接受语境中,“它的内涵是叛逆、创新和超前,意味着对权威的怀疑、对旧事物的扬弃、对循规蹈矩的不满和创造的激情。”(余怒:《诗观十六条》,《湍流》2012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如果这些都可以纳入先锋的定义,似乎还是显得有些绝对,尤其是面对当下特殊的环境,简单的反叛,并不足以构成诗人们对先锋的日常实践。就像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先锋是趋于激进的,既不包容,也非认同,在“革命”的激励下,一切发声都会显得昂扬和与众不同,这只是理解了先锋的一部分内涵,而另一部分则有违先锋的本质。现在出现的两极分化是,一方面将先锋简单化,只要是反叛的、激进的就认定为先锋;另一方面是将先锋神秘化,这很容易陷入怪力乱神和装神弄鬼。我们很难看到一种更为理性的先锋认知和行动。
与其将先锋简单化或神秘化,不如真正去理解尤奈斯库的那句真言:“先锋就是自由。”一切与自由相悖的写作,都与先锋无关。这种自由是内心的自由,而不是伪装的表象自由。现在先锋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不是诗人们缺少先锋的精神,而是将先锋当作了幌子,从而导致符号化和观念化了,先锋就此成为诗人们的脸谱或面具,这是先锋异化之后的美学灾难。一旦先锋沦为姿态性的表演,就很难保证诗人的写作是纯粹的,而且会越来越趋于狭隘。“有效的先锋诗写作,既不指望得到主流文化的理解和撑持,也不会靠仅仅与此对抗来获具单薄的寄生性‘意义’,它的话语场和魅力来源要广泛得多。”(陈超:《“先锋流行诗”的写作误区》,《山花》2008年第10期)先锋的延展性源于诗人的宽广视野和相对节制的写作,过于放纵的情感表达,要么是回到浪漫主义的抒情,要么仅是一时情绪的宣泄,很难保持一种恒定的美学。从近些年诗歌趋于功利化的现实来看,先锋其实是被好些诗人所征用的“工具”,我以为同质化写作会倒逼先锋“自行革命”,但有的诗人选择维持现状,反而让那些自我复制拉低了先锋自身的诉求,同时也逐渐消磨了诗人的主体创造精神,变成了追逐当下名利的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先锋如果缺少了主体意识,诗人就很容易陷入虚空状态。无论是针对现实的发声,还是面对历史和自我的经验转化,总是显得过于平面化和碎片化,这种整体性的症候式书写,一度成为诗坛的常态。先锋诗歌趋于平庸化,不完全是时代和环境所致,症结还是出在诗人自身。“先锋诗歌是那些始终重视和保持纯粹的精神价值关怀的诗人的写作,也可以说是始终树立了‘理想主义精神’的诗歌。”(周瓒:《当代中国先锋诗歌论纲》,《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周瓒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指出了当下先锋诗歌的困境——诗人们的写作不再纯粹。当然,我并不否定在一些诗人身上还存有理想主义精神,否则,诗歌写作的难以为继就真正成了危机。但是这种理想主义精神遭遇了更多的诱惑和束缚,诗人们在价值观上的倒退与不确定,在反思和批判精神上的自我阉割,过于注重现世名利回报在写作上的欲望投射,在风格选择上的狼奔豕突,几乎全方位地消解了先锋所建构的美学可能性。个体的差异性被取消,写作难免导向同一种思维模式,从形式到内容,都可能“巧合般”地重复。“一首诗所宣告的独特性不进入任何可能存在的利润计算。”([法]阿兰·巴丢:《语言,思想,诗歌》,伊索尔译,《诗刊》2014年8月号下半月刊)阿兰·巴丢的这句话虽然稍显复杂,但的确形象,真正道出了先锋诗歌复杂的内部光晕,它只存在于无功利的创造。针对先锋诗歌的困境,我们也不可能预设一个绝对标准,其动态的变化顺应着诗歌所要求的方式与规则,它可能进入到新的美学共同体中,也可能原地踏步,这取决于诗人怎样对待与先锋有关联的诸多探索。
这一矛盾的显现,其实指涉了先锋诗歌向何处去的命题。如何打破先锋的困境,并重新获得其美学上的合法性,这是先锋诗人在反叛中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也即先锋除了一味地向前,它还有没有可能回到历史的现场,在源头上寻找新的突围契机。“如果只是求新求变不求常,一味移步换形,居无定所,则必然导致典律的涣散与边界的模糊,使现代汉诗的诗性与诗质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那又谈何经典与传统呢?”(沈奇:《从“先锋”到“常态”——先锋诗歌20年之反思与前瞻》,《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先锋的恒定性似乎是一个悖论,它不符合自身所具有的天然的内在对抗性,因为它打破的就是某种“确定”状态。从不确定到确定,从流动到恒定,从激进到幽暗性,这充满挑战的审美转折,开启的可能是先锋诗歌得以拓展的另一个维度,那就是它曾经反对并与之决裂的传统。这一传统不仅有西方现代诗歌的传统,同样也有汉语诗歌自身的古典传统,还有其自身形成的百年小传统。
[动态性:先锋如何对接传统]
在“五四”文学的现场,古典传统很大程度上充当的是一个靶子的角色。当新文学的旗手们策略性地选择诗歌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文体时,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自己所反对的不仅仅是语言,而是代表着一种制度的美学。当古典诗歌美学遭遇了大变局的时代,它对于新诗人来说是一种腐朽美学的退隐,但其内部所蕴藏的诗学体量并没有随之转化为可资重新利用的资源。被抛弃的后果,一方面是与现代的断裂,另一方面,诗人们在利用了古典诗学作为“批判的武器”之后,又在不久之后重新回到了古典,这一策略所显现出的矛盾乃至悖论,需要诗人们来解决,也需要他们来领受这一代价。
很多“五四”新诗人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反叛与颠覆,并非无意识的,他们这种策略性的抵制只是出于那个特殊时代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一真相对于诗歌现代性的提升不无作用,但其所导致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现代性被认为是按照线性时间发展逻辑来进行历史定位的,它不可能回到古典这一“保守”的美学模式中。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很多诗人一直对古典诗歌持有“偏见”,想当然地认为它有违现代性的本质,并不兼容于先锋的想象力和趣味。而还有些清醒的诗人意识到,现代诗无法割断古典诗歌传统,甚至认为古典诗歌传统也属于现代诗传承资源的一部分。李金发、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废名、朱湘、林庚等现代诗人都曾在短暂的反叛之后迅速回到古典,而当代很多重要的诗人,也都对古典与现代的融合抱着相当高的期望。包括郑敏在内的一些主张现代派的诗人,都在新世纪之交对现代与古典传统的关系问题进行过反思。“传统是一种不断生长的秩序。”(郑敏:《新诗与传统》,《思维·文化·诗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尤其是在1980年代的诗歌现场,先锋成为诗人们向现代致敬的标杆,但仍然有一批诗人选择回到古典去寻求资源,像江河、杨炼、张枣、钟鸣、石光华、宋渠、宋炜等,在一种历史主义的建构中找到了现代诗的孕育空间,这种实践已经打破了现代与古典不相融的 “神话”,而长久以来的“被压抑的古典”似乎已经成了诗人们根深蒂固的看法,很难大面积地改变二者隔膜的局面。在这条路上探索更深的诗人,他们选择返身回来,在现代与古典交叉的十字路口重新规划先锋的路径。“我是觉得‘先锋’不是只有朝前这一个方向,先锋也可以迈过现代性,迈过浪漫主义,回到古典主义的源头上去寻找新的资源和出路。”(夜鱼、朵渔、育邦、江雪:《先锋的误区与我们的方向》,《长江丛刊》2018年11月号上旬刊)朵渔的反思,我相信也会让很多诗人产生共鸣,而如何实践,则成了又一个难题。当向古典学习仅仅只是成为口号时,重返传统显出了一种精神传承上的艰难。尤其是对于以反叛精神自居的先锋诗人来说,向传统的回归,几乎等同于对创造性的放弃。
有些诗人拒绝古典诗歌传统,他们的气质更多地偏向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现代汉语的外延大于古代汉语。古代汉语活在现代汉语中,而不是相反。现代诗歌之于古代诗歌并不是一个强大帝国衰落后遗留下来的没落王孙。古代诗歌之于现代诗歌不过是它值得荣耀的发端。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史学观。西方汉语家们总是乐于赞同前者,而我们又总是乐于赞同汉学家。这是双重的被动、误解和屈辱。”(韩东:《关于诗歌的十条格言或语录》,《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韩东的言说和思考看似辩证地道出了现代诗与古典诗歌在语言上的分歧,其实他对现代的辩护里暗含着对古典的“吞噬”,也即是说,古典的终结预示着现代性的到来,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如果我们无原则地扭结二者之间的关系,会显得过于牵强。可在很多诗人的潜意识里,断然无法割裂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比如西川,他作为一个在先锋的角色上没有什么争议的诗人,曾在很多访谈与文章中谈到自己对于传统的看法。“自中国新诗发轫至今,传统对于新诗写作的意义一直处于悬空状态。如果我们承认传统对新诗写作是一个坐标,那么,没能使之放射出它本可以放射出的光芒,其责任既在诗人,也在学者。”(西川:《抹不去的焦虑》,《大河拐大弯—— 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西川有着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角色,他理应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他的反思不仅针对所有诗人,也针对他自己:传统的意义之所以被悬置,不在于传统自身的问题,而在于作为主体的诗人是否有转化传统的能力。
今天的先锋诗人之所以对传统既爱又恨,原因在于他们知道古典传统的庞杂与丰富,但是以他们的功力又很难深入到传统中去,因为无法建基于对传统的充分了解,现代性的转化就是一句空话。这也是西川所说的传统的意义被悬置的原因。传统在现代诗写作中要被激活出新质,这对于不少诗人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所以他们对传统的重返是很谨慎的。一方面,因无法把握二者融合的度,知难而退;另一方面,传统也是检验新诗现代性的一个参照,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可以重新理解新诗的生产机制。于坚致力于从传统中获取现代诗“生长的力量”,他认为,“用意境、意象来说现代诗太小,白话诗的语言是比古典诗歌的语言更丰富、更深入细节、更具体的语言。”(于坚:《棕皮手记:诗如何在》,《诗歌之舌的硬与软》,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页)最终还是语言本身被置于这场比较中,现代诗的优势或许正在于语言的自由度,它的创造性变换有自身更大的回旋空间。于坚的想法和实践也是很多先锋诗人试图去回应的方向,但他们往往在两者的融合点上对接不上,其症结在于既没有准确地定位先锋,也无法真正触及古典传统在时间上的内在延续性。
——这也许是很多先锋诗人面临的困 境:先锋如何对接传统,这一问题被悬置了几十年,一直贯穿于先锋诗歌的演变过程,即便有诗人零星地探讨过,最后也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有的诗人意识到这样的难度,于是干脆选择放弃。实际上,在很多年轻的先锋诗人那里,其写作的方法论和美学观“总是倾心于西方诗质一源,而疏略了古典汉语诗质一源”(沈奇:《语言、心境、价值坐标及其他——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散议》,《南方文坛》2012年第6期),这是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所遭遇的极端现实。我们看到更多诗人是倾向于学习西方现代诗一脉,这不仅契合于现代美学,更是特殊时代的现代诗人们与古典传统渐行渐远的原因。诗人们以个人日常经验对接现代汉语本身时,某种诗意的生成就决定了共鸣的产生。“诗人在诗歌里运用‘西方’语言资源的能力,也就是一种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也就是一种写作能力。”(陈东东:《回顾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诗探索》2000年第1-2辑)征用西方资源,对于先锋诗人来说并非绝对化,他们的选择是基于对现代性的广泛认同,这也是一条通向先锋的路径。针对选择西方还是古典传统的命题,我们还是可以将其转化为“化欧”还是“化古”的问题,这对应的现代与古典的镜像,是一种“分叉的想象”的美学折射,已经内化为当下不少先锋诗人的写作参照。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冷霜的判断可能更具说服力,“‘传统’远非一个自明性的概念,而是一个现代性的认识装置。”(冷霜:《新诗史与作为一种认为装置的“传统”》,《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他将传统当作一个动态的概念,这样对于同样动态的现代性来说,它就是一种需要我们不断去认知的经验,而没有固定的含义。
我们再回到先锋与传统的关系上来,这二者架构起来的也正是一个现代性认识装置,其内在的关联性需要现代作为介质来搭建起互动的可能。它们各自所承担的功能,对于这种互动是一个有效的发现甚至是发明。“先锋性在颠覆旧有的文学秩序上功不可没,但同时也会造成失衡,即割裂与传统的联系。”(张曙光:《先锋诗歌的悖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4期)
张曙光指出了二者不平衡时的现状,但真正的先锋可以唤醒并激活传统,它们之间也有着相互对话的可能,关键在于我们怎样来平衡“词与物”和“诗与思”之间的张力。
[潜在对话的可能性]
在先锋的困境与古典传统所遭遇的尴尬之间,是否有一条衔接之道通达二者互动的可能?对于这条线索的寻找,其实还在于先锋诗人如何处理主体性问题。既然先锋处于变化之中,古典传统同样也不可能固守于一个既定的秩序,“传统与现代永远在建构中,二者的博弈推动着审美文化的嬗变。” (李永东:《传统的征用、转化与慢的艺术》,《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11期)这样的观点同构于艾略特所认同的“重新调整”,在相互的移动变化中寻找那个自然契合的点。对话的可能性正是基于这个交叉之点的重合,在诗人那里,它们不会是完全孤立的两极,彼此的参照都可能映射出话语实践中相互感应的轨迹。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新以二者的融合切入到先锋意识与古典传统的双重线索,寻求和描述一种新的变量。在此,我们需要参照一些有实践经验的诗人的看法,他们也许更能在具体写作的层面上重构一种价值观。“创新的对象是传统,一切创新都是对传统的创新,即对传统有所扬弃,有所继承,并在传统基础上大胆谨慎地为传统注入新的内容。”这是几乎所有认识到传统之道的诗人共同的愿景,他们的实践也应围绕这一命题展开,但事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传统的创新有可能突变成现代性的终结,也有可能陷入新的复古,这也是很多诗人所担心的问题。那么,当我们重新回到先锋的立场,以保证现代性的增殖时,空间虽然拓展了,“而先锋派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极端性和破坏性,他们可以不遗余力地求新而不惜打破创新与传统间的平衡, 造成与传统的断裂。” (张曙光 :《先锋诗歌的悖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4期)这正是先锋派的极端性所带来的后果,但并不完全代表他们的初衷。无意的反叛造成的断裂,是对古典传统在长久脱离现代语境后的不信任,如何打破这一固有印象,对新与旧的理解就成了一个需要突破的观念认知。传统所代表的陈旧与保守被普遍接受,而江弱水先生也提出了“古典诗的现代性”,并做了充分论证。古典传统的现代性问题,也许是我们再次切入先锋与传统对峙的一个认识装置。
有诗人和学者曾不止一次道出“传统需要被重新发明”的观点,对于“传统”这一问题,吴晓东说:“其实,实体化的传统并不存在,所谓‘传统’,正是被现代性呼唤出来的东西。没有现代性,也就没有传统。”(吴晓东:《“想象的共同体”与中国语境》,《文学的诗性之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以重构的现代性激活出传统的潜在能量,这还是印证了前述的传统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念。既然是动态的,它会随着认知的变化而不断延伸,以适应新的时代审美机制。那么,传统和现代生活的对接,也有可能达成另一个策略性的诠释格局。就像诗人所认识到的,“传统可以帮助我们再一次想象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西川:《传统在此时此刻》,《大河拐大弯—— 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西川将古典传统放在了一个更大的生活序列中,这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里来延展传统的丰富性。传统进入先锋的范畴,不仅仅只是时间问题,它也是一个转化的空间问题。“过去的传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我们生活与创造的标准,而是出发和创新过程中不断对话的资源。”(王光明:《传统:标准还是资源》,《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这些观点一再强调的是传统作为精神源点的重要性,它对现代构成的不一定是“影响的焦虑”,而很可能作为镜像映照出现代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如果说传统是现代性主体的一个参照,王家新的这句诗更能表明参照的特定位置,“都说诗人们带来了雨,/但最好的诗从来都不是诗人们写的。”(王家新《在威海》),雨是诗人们和“最好的诗”之间的一个参照,但诗人们从现实性上是带不来雨的,它是王家新所虚构的一个诡秘的幻象。传统是否是被诗人们虚构或发明出来的呢?“为了反对而发明一个传统,这也正是新先锋派的一个使命。”(桑克:《当代诗歌的先锋性:从肆无忌惮的破坏到惊心动魄的细致》,《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4期)桑克出于某种先锋派更深层次的考虑,推导出传统的被发明,这其实和很多诗人与学者的想法殊途同归。现代内部的微妙与敏感能否对接传统强大的主体意志?这不是一个小与大的对比问题,而是美学价值观和属性问题。
先锋对传统的敌视并不是对反叛性的刻意强化,因为传统是一个在时间流逝中趋于中和的概念,它将更多的资源积淀归拢到平和且坚实的点上,不是轻易能被先锋颠覆和取代的。因此,桑克所言的先锋的使命是为了反对而发明一个传统,也只是站在先锋角度而言,他并未意识到没落的传统也可能会有强大的再生性。这不是理论辨析可以被验证的事实,传统的再生性是在诗人的写作实践中被滋养出来的一种气质,它有时候会疏离自身,甚至与时代拉开距离,以形成必要的“历史感”。“我取西方诗歌的观念和技术,再注入中国古代的诗歌精神,踉踉跄跄地向着诗坛走去。”(罗振亚、雷平阳:《寻找宁静的力量》,《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这种简单的言说里包含着诗人朴素的方法论,写作主题与精神的契合度,也对应了他们在认知接受和经验转化上的戏剧性策略,其修辞同样被叠合在形象的建构中。传统与生活之间的体认,需要现代诗以自身来观照,这对于诗人也会是一种诱惑,像胡弦的诗,智慧、典雅和现代性并存,但在这些风格融合的背后仍然有着先锋的底色。“雨滴已无踪迹,乱石横空。/晨雾中,有人能看见满山人影,我看见的/却是大大小小的竹子在走动。/据说此地宜仙人居,但劈竹时听见的/分明是人的惨叫声。/竹根里的脸,没有刀子取不出;/竹凳吱嘎作响,你体内又出现了新的裂缝。/——唯此竹筏,能把空心扎成一排,/产生的浮力有顺从之美。/闹市间,算命的瞎子摇动签筒,一根根/竹条攒动,是天下人的命在发出回声”(胡弦《仙居观竹》)。这种大气的修辞里肯定暗含了古典的修养,它不用我们在诗中刻意寻找,一种精神气质渗透在字里行间,是古典传统所留下的影子,再多的诠解都无法真正探索到内部的独特性,这是传统形塑现代并构成新的方向的价值所在。
先锋和传统是现代审美的一体两面,我且这么认为,先锋的极端性有没有可能会激发出传统的内部所隐含的生活美学?从当下先锋诗人们的创作来看,也并非没有这种可能。“事实上,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美学立场,诗歌始终是心灵、精神和语言的艺术,如果说先锋意味着自由、反抗和创新的话,传统的本意则是忠实于心灵。当姿态和观念脱离了心灵,变成姿态崇拜和观念崇拜时,无论什么样的姿态和观念,都会变得和先锋诗人所反对的一切庞然大物一样面目可憎。” (沈浩波:《下半身诗歌运动与中国诗歌的互联网时代》,《星星·诗歌理论》2017年7月号中旬刊)沈浩波在先锋的意义上强调心灵的力量,而心灵的力量也可能是某种传统在当下写作中的投射。殊途同归需要的是调和,而没有戴望舒当年评价林庚“拿着白话写着古诗”(戴望舒:《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新诗》第1卷第2期,1936年11月)那么简单,那仅仅只是语言表层的技艺转换,并未在心灵革命的境界提升上完成使命。先锋和传统之间看似可以相互转化,但在历史的轮回上,它并不依照时间的循环,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或下降的过程,它指向的是精神的终极。在此层面上,我认同臧棣的判断,“今天我们称之为先锋的东西,或者今天我们称之为现代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终将是传统的。” (臧棣:《诗道鳟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从终极意义上看,传统是所有美学意识形态的最后归宿,先锋也无法自外于这个规则。先锋和古典传统之间的求同存异,只有以现代性作为中介,它们之间的对话才成为可能。
相比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新世纪诗歌的先锋性正趋于日常,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型,在于诗歌由特殊时代的使命意识回归到了一种文学层面的修辞技艺。那种承担着时代的精神救赎的写作理念,逐渐让位于向文学本体的回归,这也是先锋在姿态性上很快被识破并由此转化成了一种道义的原因。传统也就是这道义的一个维度,先锋的动态演变正是伴随着传统的复兴,其整体意指着差异中的同构性,这既对先锋诗人是一种考验,同时也挑战着传统能否再次融入现代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