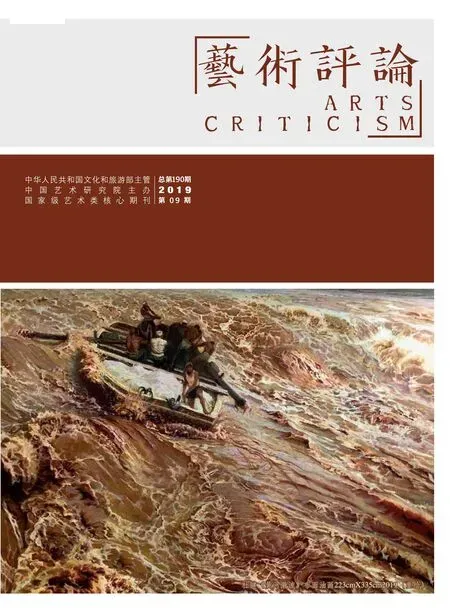古画鉴定漫谈
2019-11-13
经过对古代绘画鉴定鉴赏问题的长期关注,笔者发现它并不是一个领域的孤立问题。就中国画而言,往往涉及绘画创作、史论研究、鉴定鉴赏、考古发掘等诸多领域。如果这些领域没有交流,没有互动,成果不能共享,对其中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但现实的教育分科细密,相互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隐形的厚墙”在阻隔彼此。这就导致了这样的局面:画家缺少史论素养;理论家脱离实际手眼训练,专注于文献梳理和概念思辨;鉴定家深居固守,成果不能为他人共享;考古人员没有审美训练,对于美学和美术知之甚少。
对院校内专业学习中国绘画的学生而言,对于一张古代绘画的真假好坏应该有所认知。所谓“取法乎上”,“上品”所包含的应该首先是“真”,其次是“好”。而对于把古画作为范本来教学的教师而言,真假好坏的差异更需辨明,若搞不清楚可能真会“误人子弟”。对进行理论研究、架构学术体系的史论家们而言,可能其立论的基础正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某个成说,但若不加分析鉴别便将其沿用为自己的佐证,或仅仅因为自己闭门造车,没有及时了解鉴定界的最新成果,不了解鉴定界最新的研究已发现该作品为伪作,以至于产生讹误,那更是令人遗憾的事情。而鉴定界本身又如何?因为中国古代书画临仿、造假的历史由来已久,大量古代绘画的遗存问题本来就难以厘清。古代绘画作品是通过各种渠道而留存下来的。百年来,大量古代绘画作品是从宫廷或从巨商大贾等私人藏家手上辗转流散出来的,如今又纷纷进入各博物馆、公私藏家之手,导致现在难以通过古画的来源辨其真假。加之前代鉴定家囿于学养、眼界以及其他客观条件所限,所做出的结论未必可靠,但其后辈又往往承袭、延续他的说法。再者学术壁垒森严,公开、客观的争论并不是非常通畅。这些最终都造成对古代绘画作品这一丰厚遗产系统的正本清源工作一时难以全面展开。另外,鉴定界本身具有一种神秘性,在外人看来,鉴定家们的研究似乎基本不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但我们也确实很难看到鉴定家在学院里开设课程;史论家和鉴定家之间的互动、交流也远非常态。还有另一个与鉴定发生密切关系的重要领域就是考古。考古界通过发掘、考证而发现新的证据,并由此而引发出的新的假设和推断、论证,完全有可能给古代绘画鉴定提出新的思路和依据。
另一方面,在现实当中,一些专家学者深入严谨的研究成果不能为更广大人群所共享,令人难免感到遗憾。尤其是鉴定界,一代一代鉴定家殚精竭虑积累的学术成果,实在应该被画家、理论家乃至广大观众所关注和接纳。鉴定鉴赏不应成为鉴定家的专属,它应该是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学人所应该具备的人文修养。对于丰厚的中国古代绘画遗存,真正走进去,看一看其中的风景,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一笔一墨的审美感悟来领略中国画的奥妙,乃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熨贴的心灵守护。
中国画讲究“远观其势,近观其质”,这句话对于鉴定而言,千真万确。一画呈前,首先从置陈布势、音容笑貌来感知其时代气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如鉴赏汉代的器物,是不是有两千年历史的积淀,这需要在大量观摩原作基础上的心领神会。一幅真迹,真气弥漫,会穿透历史风尘,顽强地表现出神采神韵,以使有经验的观者意会心受;伪作,尽管往往也是根据文献记载的特征来制作,细节都不差,但貌合神离的乖谬往往会在一刹那间流露出来。当年张大千仿制石涛,据说可以乱真,但今天我们把两者的印刷品摆在一起看,还是真伪判然。原因就是作伪者有的是机心,从下笔之时,已然与自然相悖。
以此来看传世名作《太宗步辇图》,笔者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太宗步辇图》经过广泛的印刷传播,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唐代阎立本“真迹”。观画者基本是一眼望去,将熟悉的色泽、熟悉的构图、熟悉的形象和脑子里面的某个概念对应起来,便认为那就是一张阎立本真迹,不需怀疑,也不容怀疑。但问题就在这里。观者远观其势之后,没有近观其质,或者根本无从把握画面上说明问题的那些“质”。这就需要一个基本的入门门径。
我们面对一张古代绘画,要鉴定其真伪,大体需要从几方面入手。
首先是传统文献的梳理。比如,有关这幅画,有没有权威著录,所见实物和著录是否应和,历代关于此作有否品评等等。这是老一辈学人常用的方法。它的应用前提是这幅作品基本没有什么可资参照的对象,只能根据文献记载来判别它的年代和风格。因此,据此作出的鉴定结论也往往会囿于鉴定家的眼力和学养而出现问题。因为历史上流传的假画,大体也是根据古代著录中的描述而制作的,所以眼前实物不等于著录中的原物。就《太宗步辇图》(以下简称《步辇图》)而言,如果对于“辇”这一古代器物不熟悉,不知道其实不会出现女子抬辇这样的事,那就容易先入为主地接受画中的事实,对于这一重大疑点就会轻易放过。
其次,相比文献梳理,更重要的是面对作品,从具体的绘画风格和技法表现入手来仔细考究真伪。这是最切实的也是最可靠的绘画鉴定方法。它的难点,就在于鉴定者本人的学问不仅仅是从纸上得来,还需要他本人有相当的绘画或者鉴藏实践体验。近代以来,重要的鉴定家几乎都是书画家兼收藏家。书画实践可以洞悉笔墨的微妙法门,从一笔一墨中寻找真伪优劣的蛛丝马迹;收藏又可以让眼界大开,在作品之间的比对、互证中接近客观事实。就《步辇图》而言,我们需要的是仔细观察每一张脸,判断其五官的画法是否是唐代风格。这就涉及到参照的问题。标准的唐代绘画在哪里?因为年代久远,保留在公私藏家手上甚或是博物馆内的唐代绘画已经几乎绝迹,偶有吉光片羽,已然被奉若拱璧。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历代帝王图》是鉴定界意见比较一致的唐代阎立本真迹,是可以在鉴定中比对参照的一个标准件。《历代帝王图》保留了阎立本绘画的讯息,也保留了唐代人物画的时代风貌,并让我们领略了唐代一流大画家的水准。以此比较《步辇图》就会发现后者的许多不足之处。比如红衣虬髯站立者的右耳,画者似乎不知道耳朵的结构,完全画错了;一把胡须,也是画得杂乱没有章法。现在若有这两幅画下真迹一等的高清印刷品,将它们放在一起,高下立判。如果说《步辇图》是唐代一流大画家的手笔,似难以令今人服膺。另外就是围在太宗周围的宫廷侍女,她们的五官小眉小眼,纤纤略显病态,这更像是明清之际仕女画的典型风格。而再看一看西安附近唐代公主、太子墓出土的唐代壁画中的侍女形象,一般都是蛾眉大眼、圆面高髻、衣纹整肃、身形挺拔,凛然有盛唐气象。唐代公主、太子墓中壁画,一般不可能是出自民间画工之手,一定是宫廷一流画家的亲笔,也许其中就有阎立本或者与阎立本水准相当的画工的真迹。这些保留在墓葬、寺观甚至棺椁线刻中的古代绘画遗存,正好可以补充唐代以前卷轴绘画不足的情形,为今天的鉴定工作提供第一手的可资借鉴的参照。
鉴定还有一些辅助手段也非常重要,比如历代递藏印鉴、题跋、纸绢老旧破损程度、装裱手法等等。在书画本身孤证难明的前提下,这些辅助材料有时候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的情况也非常复杂。一些有名的鉴定者自己也曾制作假画。比如董其昌就曾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而苦心孤诣地制作假画,在他的某些题跋中,我们可以体会他当时的运思和心态。后来许多人因为迷信董其昌,就把他鉴定过的古画一股脑儿地接受下来,以讹传讹至于今日,需要今天的鉴定家拨云见日、去伪存真。纸绢虽然是一个参考因素,但因为保存条件的不同,同一年代的纸绢,可能出现相当不一样的老旧程度。此外还有造假者专门做旧、人为破损以障人耳目的做法,更增加了鉴定的复杂程度。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画数量不胜枚举。对待这一笔遗产,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既不能依靠主观意志妄断真假,也不能固步自封,躺在前辈的结论中不思进取。其实,今天的影像、交通、资讯、学术方法包括科技手段空前发达,正是在鉴定古画这一传统领域中大有可为的时机。当代海上画坛名宿陈佩秋先生就说过:我们并不是比前辈更聪明更有学养,只是比他们见识到更多的古画,有机会把这些古画放在一起仔细比对,才有了超越他们的可能。老先生毕生从事中国画创作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绘画实践体验;近几年,他又专注于古代绘画的鉴定鉴赏,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成果公布于众。陈先生的见解和实践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和指引,促使我们不断加强学习和体悟,对于鉴定这一本来神秘杳远的领域能渐窥堂奥,并体认到其中甘苦和它对于绘画创作、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作为一个后辈学人,也欣喜于能够有吸纳前辈学术成果的精华和利用时代发展所提供的一切便利条件,从而有理由做出新的不负时代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