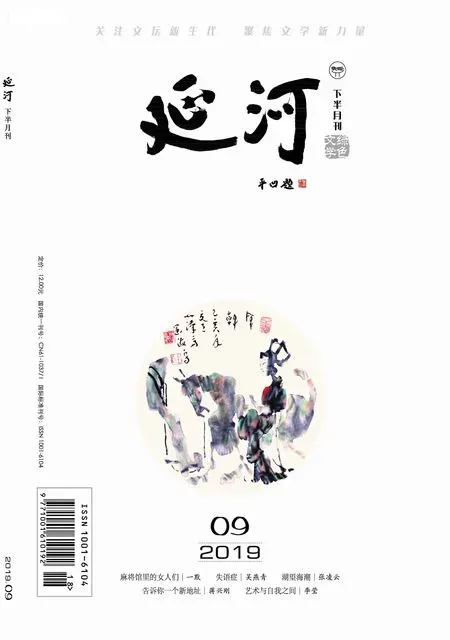缝补与完整(评论)—谈吴燕青的诗
2019-11-12张丹
张 丹
吴燕青的诗中频频提到一个词汇:缝补。缝补意味着先前存在着一个完整。缝补的动作意味着,想要回到完整如初。什么样的完整如初呢——这是吴燕青的另一些诗中所呈现的世界。这种呈现,经由两种路径:一是破碎与孤独之现代生存体验;一是在诗中想要重新通过回忆去构建故乡与童年的生存。后者的动因,实际上已经蕴含在前者之中,两者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正如我们不能全无暗影就去认出光线,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存在一种纠织的不透明性。因此对生存和诗的问题下科学的结论和剖析在现时代是可疑的。也因此反过来我们得以理解为何很多现代哲学家皆要借助于诗去阐发自己的思。那么这时,诗的这种不透明性和其思的准确性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一个值得我们去关心的问题。我们从《回到缝补之前》这首诗去切进诗的问题。
题目已经预先地指出一种价值的偏向:回到缝补以前。即不需要缝补的时候。全诗动用了十三对词,这十三对词皆处于文化或词义上的二元对立之中。每对名词,皆由动词缝补联结,因而处在了某种意义的沟通和交流当中。其关系是:由前一个词语的所指,对后一个词语的所指进行缝补的工作。我们看看用于缝补的词语:破碎、痛苦、贫穷、太阳、海水、战火、阴暗、饥饿、哭泣、离别、一片秋天的落叶、雾霾、死亡的一秒。这些词语准确地指向了人类生存的现状。现代人首先必须面对的便是过往一切经验的破碎,人与他人关系的破碎,人和世界关系的破碎,人的自我的破碎。痛苦、贫穷、战火、阴暗、饥饿、哭泣、别离,则是永远伴随着人生命的极为萧瑟的处境。这里出现了四个自然的意象:太阳、海水、一片秋天的落叶、雾霾。我们可以注意到雾霾乃是典型的现代自然图景,可知这首诗里的自然意象指向的就不是纯粹的自然和季候了,而是掺入了现代生存体验的自然,也可窥得诗人的用意之精微。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破碎之中还含有某种颠倒。这种颠倒即表现在太阳、大海和它们缝补的对象上。太阳与海水分别缝补的是月亮和雨滴,在我们的意识之中,月亮似乎才常常是缺失的状态,颗颗雨滴才是跟分离更为切近的意象。但这种颠倒事实上并不是什么非常难于理解的事情:一方面,自然与生命体验在在现代世界中失去了过去所能取得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相较于太阳与大海颇具男性雄浑气质的文化意指,月亮和雨滴作为自然意象更偏向于女性柔软、易于接纳的一面。
现在我们来看被缝补的对象:完整、快乐、富裕、月亮、雨滴、和平、光明、温饱、微笑、相聚、一片森林的绿、一场雪的白、漫长的一生。前面我们说,在经验破碎之前,人是有对完整性的体验的。快乐、富裕、和平、光明、温饱、微笑、相聚则是人生在世想要求取之物。无论何时,人们在世界上聚集,皆为着同样的目标:幸福。然而,何以如今,诗人想要倚靠与之相反的事物去缝补呢?正如加缪所言:没有想写幸福手册的人,是无法发觉荒谬的。追寻幸福快乐,必然体验到荒谬。词语的对立,事实上指向了这种悖谬,即缝补并非为了单向度地回到被缝补的事物,而是要回到对立的事物在缝补之前的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缝补之词和被缝补之词实际上本来在意义上是不可分离和分割的,两者互相遮蔽着又凭借对方得以敞现,因而并没有所谓的补完工作。这首诗真正的意图开始呈现——“让一切回到缝补之前”。如何回去呢?与追求幸福相联系的一个行为乃是爱。但现代之爱其弱点在于其完全指向了一种封闭的心理体验,但实际上爱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起落,而应当是一件社会性的工作。“让你回到离开我之前/腾空一个草原的位置/给我们早经枯萎的爱”。爱,并非是因为另一主体的离开而导致枯萎,而是因为主体与主体间失去了沟通和交流,致使爱的消亡。爱需要流动和生长(腾空一个草原的位置,正是由于诗人已经意识到爱何以枯萎),这恰恰是现代世界封闭的自我和物化的人与人之关系所不能给予的。
在这组诗中,《可能》《降》《埋头吃饭》《快乐多么稀少》《暮归》等皆是对此种存在状态的表现。而吴燕青诗歌的另一主题也源此顺利地敞现,即试图构建其所知的同一性的生存:童年与故乡的生存。诗人已经敏感地认识到世界的破碎,现代之爱的不可能,便十分自然地借由诗走上归家之路,这条路径是通过回忆与慨叹来被发现的。《小麻雀》《万物退到无可退之处》《花事,白菜或故园》等诗便相互关联地在进行着这种当下现实与家园的缘构。以《小麻雀》为例。
《小麻雀》是典型的还乡之旅。诗人率先制造了一个空无的背景:雪把世界下白了/茫茫的/让万物显得/不可捉摸。这种空无,适宜于存在之涌现。故乡与麻雀显现了,对诗人来说是回到故乡,对麻雀来说,却是客居之地。而麻雀却是在诗人故乡的长期生存者,而诗人回到的故乡,却已经不是她那个故乡。这个故乡“童年捉迷藏的墙角/芦苇摇摆 杂草肆长/每一块古砖都有坍塌的笑/都彷佛藏着雪花和焰火”,芦苇和杂草,坍塌的古砖意味着故居的衰芜,甚至麻雀在此的居所也道出这种情形。这个故乡提供出了那个故乡的线索,故乡因而也就在在与不在之间了。在这样在与不在之间,回乡的诗人与客居的麻雀,看似有某种状态上对立,实际上是可以相互依偎与沟通的存在者。这首诗因而也就在白茫空无的背景中,涌现存在的踪迹。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正是这种矛盾性,这种矛盾性直接指示了吴燕青诗歌的现代性。不管世界如何走向了虚无,人总是免不了多少有求取意义的冲动,对诗和诗人来说,这尤其难于回避。诗人孜孜不倦地在童年中去追问这一命题,或者说正是由于现实的虚无致使文学意义上的家显得重要了。
我们通过理解吴燕青的两首诗,看出了她的诗歌的现代命题。但我们在一开始所关心的两个问题(缝补与完整),依然由于其不透明性而在诗人的诗中悬而未决。这种居间状态反而并不是暧昧的,恰好道出了真理的场所。正如我们在《小麻雀》中分析的那样,故乡之所以成为故乡,就因其实际上在在而不在之间。诗人孜孜不倦的指出缝补的悖谬与家园的线索,沿着这一线索的不断建构却未见在其诗艺上显得同质反复,反而不断交织互文,也因而有了一种主题不断强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