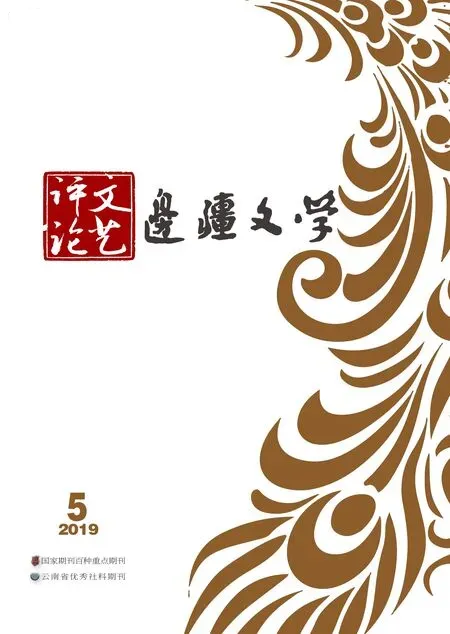优秀的动物小说,是人类与动物的心灵对话
——沈石溪访谈录
2019-11-12沈石溪李秀儿
沈石溪 李秀儿
受访者:沈石溪,原名沈一鸣,1952年10月生于上海亭子间,祖籍浙江慈溪,汉族。1968年初中毕业赴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插队落户。1975年应征入伍。沈石溪从1980年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最擅长动物小说。被称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代表作品有:《猎狐》《第七条猎狗》《再被狐狸骗一次》《狼王梦》《白象家族》《斑羚飞渡》《最后一头战象》《一只猎雕的遭遇》《和乌鸦做邻居》《野犬女皇》《鸟奴》《混血豺王》《雪豹悲歌》等。
访问者:李秀儿,女,满族,1978年12月出生于黑龙江佳木斯,现为上海师大人文传播学院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曾多年担任电视新闻主播。在《中国作家》《散文》《少年文艺》《文艺报》《文学自由谈》《文学报》《边疆文学·文艺评论》《滇池》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有多篇作品入选各种选本或获奖,小说《晚秋》获2017年度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第一名。已出版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花山村的红五星》等8部作品。
李秀儿(以下简称李):很高兴在上海见到沈老师。我知道沈老师早在十六七年前就离开云南,回到上海,但是您创作的起点在云南,生活的根一直深扎在云南,几乎所有的动物小说,也一直以云南为背景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称沈老师为云南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中的一员,并且是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读者最多的领军者,沈老师您不会介意吧?
沈石溪(以下简称沈):说我是云南儿童文学作家,我当然不会介意。我的创作,从云南出发,以云南为根,以云南为荣,也以自己是云南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中一员感到自豪。但说我是其中的领军者、是影响和成绩最大者,这不仅不妥,也不是事实。我从吴然先生、隆中先生那里知道,你也是云南儿童文学队伍后来者之一,而且现在来到上海,既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也做儿童文学博士专业研究,对你这样的后起之秀,我们充满期待。你肯定知道,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以来,云南在各个时期,儿童文学都有她的标志性人物,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像为延安儿童编写教材读本的刘御、写战斗诗篇也写儿童歌谣的柯仲平,延安时期就已成名;刘琦、马瑞麟、普飞,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作品就引人注目;再后来的乔传藻、吴然、辛勤、钟宽洪、康复昆、杨美清等,以及更后来的吴天、湘女、汤萍、余雷等等……可以说云南儿童文学源远流长,其来有自。我只是其中以动物小说为专攻,得到较多读者认可的一只“太阳鸟”,仅此而已。
李:沈老师谦虚。报告一下沈老师,我正在以云南儿童文学为例,尝试探寻研究和描述生态儿童文学在中国生长发育的轨迹和特征。在我看来,将云南作为生态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样本,是因为其具备较为特殊的研究价值。她不仅仅在地理意义上是中国生态儿童文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和人文多重意义上,也有着鲜明特殊的印记。其中印记之一,就是云南被习惯性称为“动物王国”。以沈老师您为代表的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从一开始就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书写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联系——诸如自然生态、边地民族、森林动物、异域风情等题材路径,为其“标签化”的独特个性,由此产生了陌生化的审美效应,并取得了成功。动物小说是最受当代少儿读者欢迎的文学样式,也是生态儿童文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想知道,沈老师您是怎样开始动物小说书写的?
沈:从1980年4月在北京《儿童文学》杂志发表第一篇动物小说《象群迁移的时候》算起,我从事动物小说创作,迄今已有四十个年头了。回想起这篇小说的创作,我就会想起更早的一段青春时光:我初中毕业那年,正赶上上山下乡大潮,对上海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时空概念的我,居然报名去到了云南西双版纳一个名叫曼广弄的傣家村寨插队落户。当时我只有十六岁,对世界充满幻想,也充满好奇心。我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蛮荒的西南边陲,竹楼、火塘、木鼓、芒锣、长刀、筒裙……看什么都觉得新奇,最让我惊讶的是,来到寨子第一天,就看见有人竟然骑着大象上山拉木料!
因为大象,我认识了一名驯象师,他叫巴松波依,是曼掌寨手艺最高的老象奴,养了一辈子大象,据说能听得懂大象的语言,能和象对话,再桀骜不驯的野象,经他的手调教,也会变成听话的家象。当时我太崇拜他了!很想拜巴松波依为师,学习养象技能。我就千方百计和巴松波依套近乎,傣家人喜饮酒,我就隔三岔五弄壶包谷酒送他喝,很快,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我与巴松波依这段友谊持续了六年,直到1975年我参军离开曼广弄寨。
数年后,我已是西双版纳军分区一名新闻干事,有一次我正在中越边境采写战地新闻,突然接到过去同寨插队的一位同学的电话,说曼掌寨老象奴巴松波依去世了。老人家重病期间曾多次提到我,还委托这位同学给我写信,说是要谢谢我曾多次送他酒喝。
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一幕幕我与老象奴在一起生活、劳动和喝酒的情景。虽已阴阳两隔,但老象奴的音容笑貌却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我想,他养了一辈子大象,死后应当还和大象有点瓜葛,人生才算画上圆满的结局。我觉得被他放跑的那头大象应当从密林深处跑回寨子,在老象奴的坟墓前哀嚎三声,以示祭奠。想着想着,就根据老象奴的经历想出一篇小说来,取名《象群迁移的时候》。这是我第一篇动物小说,也是第一篇写象的小说。
稿子写好后,投寄北京《儿童文学》,半个月就有了回音,编辑来信大大称赞了一番,鼓励我继续写这类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动物小说。
于是,我又根据巴松波依给我讲过的战象的故事,写了《最后一头战象》。
这就是我从事动物小说写作最真实的起点和源头。
李:原来如此!在《象群迁移的时候》和《最后一头战象》里,我都找到了沈老师您说的巴松波依老人的影子——《象群迁移的时候》故事里面,他是那个曾经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拯救过幼象,让幼象放归森林的傣族老爷爷巴松;《最后一头战象》故事里面,他是与小象嘎羧从相遇到一同成长、变老的傣族少年波农丁。您把巴松波依老人的名字拆开,刚好分配到这两部小说的主角身上,而且两部作品都描写了人与动物之间那种亲密无间命运相通的特殊关系,尽管打上了当时特定时空条件下意识形态的鲜明印记,但是仍然是难得的反思人与自然、战争与和平关系的重要作品。我注意到,《最后一头战象》不仅一直是入选国家教科书的经典作品,最近还被改编成了人偶舞台剧在国家大剧院多次公演,这种殊荣,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中,好像并不多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沈老师的动物小说经受了时间和读者双重考验,穿越时空,经久不衰,成为经典,起点很高!
沈:时间和读者,确实是文学作品接受考验、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两个指标。我只能说我很幸运,《最后一头战象》被改编成国家大剧院公演的木偶舞台剧,使我早年动物小说获得了当下认可,得到了综合艺术样式对我旧作的当代表达,也可以说是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这部剧作的导演何念认为:“我们不一定要引进国外的舞台剧,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土壤。整个创作力求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让中国传奇故事走向国际,带给社会更多启示。”我到现场看了公演,感到确实很震撼。因为在小说原作里,我开口比较窄,主题很小,比较单纯,但大型木偶剧《最后一头战象》已经发挥了很多,是一种二度创作,实际上是一个很新的作品。这头象让我很震撼,那么大的木偶,我想都不敢想,那么大的木偶能够在舞台上演,而且神态、动作基本上都能还原、再现大象的灵性,非常了不起。导演的团队将这个中国故事所要升华的国际表达,就是要反思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烘托出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的主题思想。从主题内容到表现形式,都赋予了原作更加深刻的思想性、更加鲜明的当代性,更加好玩的观赏性,可以说,现代高科技和当代审美的完美结合,为作品披上了一件华丽炫目的锦绣外衣。作为原作者,我也从中受到启发:面对当今时代的儿童文学创作,作家必须具备更大格局,更宽视野,更富于表现力的艺术手段,才能满足当下少儿读者(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当下儿童文学在读者审美需求与创作者之间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巨大矛盾。任何抱着陈腐经验老化知识一层不变抱残守缺的写作者,都很可能被时代的审美浪潮所淘汰。我自己就时时感受着这种危机。
李:我们还是回到从前。我注意到,沈老师动物小说创作发表时间很早,为什么差不多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才广受读者欢迎,市场追捧?
沈:我喜欢动物,喜欢动物小说写作,恐怕是国内这个领域最早的拓荒者之一,我几十年下来,一直在动物小说这块方寸之地上辛勤耕耘。对中国动物小说发展,也算体会深刻。
从进入这个领域开始,我从没奢望过我的动物小说能畅销。我很明白,如果把整个文学比喻成一条江河,儿童文学只是壮阔江河旁的一条小溪流;如果把整个文学比喻成一座百花园,儿童文学只是姹紫嫣红百花丛中的一块小苗圃;如果把整个文学比喻成万家灯火,儿童文学只是璀璨星光下的一盏小桔灯。那时节,整个图书市场儿童读物只占百分之十左右,且以教材教辅为主,儿童文学在儿童读物里又仅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就这么一点可怜的份额,引进版的外国儿童文学又占据了半壁江山,原创儿童文学的存在空间狭小逼仄可想而知。而动物小说又是整个儿童文学一个并不起眼的分支,一棵树上的一条枝桠而已。长久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主打品种是童话和少年小说,还有儿童诗和儿童散文,动物小说实在是微不足道,有它不多,无它不少,写的人屈指可数,市场无人问津,读者寥寥无几。我从事动物小说创作前将近三十年,就处于这样一个写作和出版环境。既没有催稿像催命一样的编辑,也没有热烈期待我新书的读者。好在我从小就缺乏雄心壮志,安贫乐道,特别容易满足,有点小成绩,有个小庆幸,幸福指数就直线飙升,暗自感恩命运之神的眷顾。就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我过得懒散而率性,寂寞而平静,想写就写一点,不想写就一点不写,不紧不慢去写,平均一年写一本书,新书首印一万册就很开心了,一年半载后能加印五千八千册,高兴得就像一锄头挖出了金元宝。如果能得个文学奖什么的,领到几千元奖金,全家过节般热闹,必定去大排档嘬一顿,以示隆重庆贺。
我完全没想到,忽然有一天,这一切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2008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我的“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第一辑六本。刚开始我对出版这套书并不特别看好,我以为也像过去几十年间我出版的作品一样,首印个一万册,最多一年半载后加印个八千册,卖完也就完了,无声无息,自生自灭。谁也没想到,品藏书系一投放市场,竟然迅速热销,当年就重印两次,翻过年又连续不断重印。一炮打响,出版社领导、编辑和营销都倍受鼓舞,再接再历,以平均一年半推出四本一辑的速度,连续出版我的动物小说。截至2018年,“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共出版七辑三十二册。国内出版界有个不成文的标准,一本书年销量能达到八万册就算畅销书了。以这个标准衡量,品藏书系几乎每一本都是畅销书。尤其是长篇动物小说《狼王梦》,2009年出版,单本累计印数已达六百三十万册。十年间整套品藏书系总销量超过三千五百万册。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计,儿童文学作家市场占有率,我由十年前排名第四十七跃升至前三名。
国内出版人说,这十年,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十年”。这十年,具体到对我来说,实实在在是我生命中的黄金收获期。感觉就像天上掉馅饼,这块香喷喷甜蜜蜜的馅饼,刚好就砸在我头上。我至今都有点回不过神来,怎么稀里糊涂就变成畅销书作家了。
李:这就是厚积薄发的创作规律吧。很难想象,如何没有沈老师前面将近三十年动物小说创作的积淀,没有那些既有趣又厚重的数十部作品垫底,这个黄金馅饼恐怕也不是什么人都那么容易被砸着的。说到您动物小说的走红,有人认为,您主要是写了鲜为人知的猛兽,让城市孩子感到震惊,所以受到特别欢迎,是这样的吗?
沈:还真有一位老朋友曾经开玩笑对我说:你的动物小说之所以畅销,是因为你喜欢写大型的或凶猛的动物,老虎、狮子、大象、野牛、野马、豺狗、野狼、豹子、狗熊、野猪、老鹰、金雕、巨蜥、鳄鱼,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家伙,动物威猛,帮你逢山开路,过河搭桥,无人能挡,所以就在图书市场越卖越好了。
我觉得有点冤枉。是的,我写了许多豺狼虎豹、象熊鹰雕这样凶猛的动物,但我也写过野兔、山羊、黑天鹅、白天鹅、金丝猴这样可爱的动物,还重彩浓墨描写过热带雨林里娇小玲珑的太阳鸟。我并不偏爱某一类动物。我深知,地球出现生命已有十几亿年,生命发展遵循这样一条规律:汰劣留良,适者生存。从这个角度说,凡存活至今的物种,都有独特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技能,都有克敌制胜的高超本领和顽强拼搏的非凡勇气,都是生存竞争的胜利者,也是生命进化的佼佼者,值得我们珍惜、敬畏,也值得我们去书写、赞美。
人不分高低贵贱,动物也不分高低贵贱。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种动物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
但老朋友“动物威猛”这句话,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动物的确威猛。老虎的威严让人心惊胆寒,猎豹的速度让人自愧弗如,大象的力气让人望尘莫及。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多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傣族的图腾是白象,彝族的图腾是雄鹰,哈尼族的图腾是山豹,蒙古族的图腾是骏马,景颇族的图腾是野牛。世界上还有许多民族有狼图腾、熊图腾、雕图腾、龙图腾、鲨鱼图腾和虎鲸图腾等等。如果将全世界各个民族图腾崇拜汇总起来,就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动物园。人类崇拜动物,模仿动物,才创造出灿烂文明。譬如模仿青蛙游泳的姿势,学会了蛙泳;模仿动物的鳞甲,盖起了屋顶的瓦楞;模仿鱼类的形体造出船只,并模仿鱼鳍摆动制造出船桨;模仿蜻蜓发明了直升机;模仿甲虫发明了坦克;根据野猪鼻子测毒的奇特本领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防毒面具;根据蝴蝶色彩伪装的原理发明了迷彩服;模仿海豚发明了潜水艇并利用海豚的“回声定位”发明了声呐系统;利用乌贼和章鱼喷射墨汁的原理制造出烟幕弹;利用蛙跳的原理设计了蛤蟆夯;研究萤火虫发明了冷光技术;根据响尾蛇的颊窝热感应原理,发明了跟踪追击的响尾蛇导弹……等等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动物的生存能力也非人类所能企及。无论高山雪域、戈壁荒漠,还是寸草不生的生命禁区,人活不下去的地方,却往往是动物的生活乐园。举个极端例子,太空应该说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生命禁区了,真空、低温、辐射和微流星,让任何生命都无法在太空生存,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一种小小的水熊虫,被宇航员带到太空后,却能在生命禁区顽强生存下来,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动物威猛,绝非浪得虚名。
我就是喜欢动物,对动物着迷,才几十年在动物小说这块方寸之地上辛勤耕耘。我创作动物小说的宗旨就是:破译动物世界的生存密码,展现五彩缤纷的生命奇观。
感谢美丽、威猛、充满灵性的动物,给了我无穷的创作素材和创作灵感。
李:破译生存密码,展现生命奇观——沈老师创作动物小说的宗旨,确实贯穿于几十年创作过程中。我更愿意把沈老师动物小说纳入到生态文学范畴,看作是云南生态儿童文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我看来,肇始于新时期之初的云南生态儿童文学,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着眼于生态环境的外部描摹赞美到关注于生态危机的内部矛盾揭示,从文学主题的浅表粗鄙到关照现实的深刻丰赡,从文学样式的简单粗放到艺术呈现的丰富多彩的流变过程。
就以曾经在儿童文学中居于主流的少年小说为例,曾几何时,云南儿童文学对少年形象塑造,惯常在与人斗或与自然斗的矛盾冲突中锤炼而得。即便到了新时期,云南作家仍然习惯于利用边地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作为创作素材,并将其视作儿童文学取得成功的一条捷径。很多描写勇敢机智少年形象的小说,较多地以狩猎、拓荒、冒险为场景,显示出少年临危不惧、勤劳勇敢、敢于胜利的精神品质。其中那些《猎虎》《抓猴》《捕蛇》等狩猎珍稀动物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合时宜。
沈:如你所说,云南儿童文学的生态书写,确实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不自觉也好,盲目也罢,但这不能怪罪于云南儿童文学作家。这个过程,整个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也可以说整个中国作家都经历过。环境意识、生态意识,是在整个社会进入到改革开放,走过很长一段弯路之后,经历了先发展先破坏后治理后保护的这个痛苦过程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才认识到的。绿水青山确实是金山银山,但人们是先看到山上的金银,山肚子里的金银,山被扒皮了,掏空了,河流被污染了,甚至断流了,既不青也不绿了,才想起来这个道理。积重难返,却又不得不返。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揭示,也是跟社会发展轨迹基本同步的。作家也不可能先知先觉。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具有先知的、能够对社会做出预警的、能写出真正的预言似作品的作家,少之又少。
但是也必须看到,云南儿童文学在生态书写方面,比较明显地领先于中国西部甚至国内很多地区,这是事实。森林散文、生态散文、动物小说、大自然童话和寓言……这些文体,在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中,都有与之对应的比较成熟的作家。这并不是说云南儿童文学作家有什么特别的理性,也不是有特别强大明晰的理论支撑,而是靠生长于“魅力丰富神奇”的云南大地的儿童文学作家所特有的朴素的直觉和生活经验。我记得当时云南儿童文学作家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乔传藻、吴然和我,以及不多的评论家,都对这个命名做过阐释。太阳鸟体型娇小,喜好光明,亲近自然,是一种不起眼却生命力旺盛的鸟类种群。云南森林散文作家乔传藻以太阳鸟为名写过散文名篇,我也以太阳鸟为原型写过小说。我们意识到了云南儿童文学在创作题材方面的某些得天独厚,与当时云南出现的红土诗歌、边地小说等标签化的文学现象一道,儿童文学也试图在区域性、地域性、神秘性、独占性等方面,力图有自己的解释,有自己的特质,有自己的地盘,从而向京津沪那些文学高地进军。当时云南儿童文学整体性地取得了一些突破,以至于被外界同行认为是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上“崛起的新山脉”,这道山脉中,就有生态书写的最初的表现和印记。这些经验,放到今天生态儿童文学审美尺度下来重新打量,到底哪些经验站得住,哪些需要甄别臧否?这是需要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看待的问题,也是你们做理论清理和思考的需要辩证研究的课题。
李:沈老师您离开云南这块创作热土,迄今已有十六七年时间。一直以来,您以云南为背景的动物小说,有效地成为了孩子们走近自然、观察动物、认识世界、思索人生的一个重要窗口。云南以及云南土地上那些存在或不存在的动物,跟您的创作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沈:熟悉我的作品的读者都知道,我所书写的动物小说的背景、故事、人物、动物和植物以及情绪和细节,都依然来自云南。我虚构了诸如滇西北“日曲卡雪山”等等比较典型的动物生存环境,尽可能让笔下的动物与这些环境构成一种现实或历史的真实存在关系。这样才有一个真实可信的动物表演舞台,也才有我施展文字拳脚的空间。我以自己十八年的亲身经历以及多年来案头的查阅考据,熟悉这些地方的今天、昨天和前天,熟悉这些地方现在还存活着哪些野生动物,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哪些野生动物,它们消失的原因是什么,消失的大致时间是何时,等等。云南事实上成为了我创作的精神家园和灵感来源,我这一生,只能用自己的全部作品,来反复书写云南、拥抱云南、依恋云南,我书写云南土地上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传奇故事,借此表达我的生态追求和理想、生态忧伤和愤怒、生态愿景和梦幻。也借此来回报我对云南一辈子的感恩之情。
李:学界对动物小说从定义上细分,大致有三种,拟人动物小说、类人动物小说、逼真动物小说。沈老师您自己觉得,这些动物小说的不同类型,都有涉及吗?最成功的集中在哪一类?
沈:动物小说的分类有很多种。如你所说,拟人动物小说、类人动物小说、逼真动物小说——以此作为三分法,基本能够概括现有动物小说的类型。
动物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说古已有之,但是以动物为主角,以刻画动物形象为主要内容、写出有血有肉动物形象的真正意义上的动物小说,通常认为是由加拿大作家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开始的。19世纪末期,西顿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创作了《狼王洛波》《乌利——一只黄狗的故事》《银斑——一只乌鸦的故事》《塔克拉山的熊王》等一系列动物小说,由此开启了现代意义的动物小说书写,他也因此被誉为“动物小说之父”。我拜读过西顿的全部作品,也仔细琢磨过他创作中的一些特点。比如,他的小说,坚持真实客观这个大的原则,真实客观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已经接近于动物学的严格规定。哪些地方出现哪些动物,这些动物与哪些动物是共生关系,动物的生存繁衍是如何进行的,群居动物内部都有哪些制度和法则,诸如此类的内容描写,西顿都有实证的依据才会写进作品中。也就是说,他所写动物,绝不开“黄腔”,他既不拟人化,也不类人化,不让动物开口说话,也不让动物按人的思维方式思考,没有人的感情方式介入作品情节和细节,而是严格按照动物生存的本来属性去照相式的还原描写,所以说他的动物小说是真实客观的,是经得起动物学家对其“复盘”分析的。我对西顿动物小说表示由衷的敬意,对他的某些艺术处理方式表示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是,我进入动物小说领域,有我自己的分析研判和路径选择。我不可能选择零度写作,做不到西顿那样的客观冷静。因为我虽然有比较漫长的、比较接近野生动物的人生经历,但我远不是真正意义的动物学家。我坚持认为,照相似地纯客观记录和还原动物生活的形态,并不是以语言为介质的文学的长项。人们完全可以去观赏那些逼真还原的电视纪录片,而不必看你费了很大劲也未必真能还原的语言文字作品。所以,我写作动物小说,有意于突破前人设置的某些藩篱,既着眼于动物的自然属性,更把力气花在挖掘动物社会鲜为人知的行为规则,塑造动物本体形象上来,我认为只要故事情节和动物行为基本真实,个别动物的心理感受和思维稍稍逸出物种的局限,无伤大雅。关键是得到读者的接受和认可。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变的,动物小说也不例外,没必要画地为牢,束缚自己的手脚。我想也是,童话倾向的动物小说或许还是有益的变异,会导致一种新的文学品种呢。至于说到我的动物小说在分类中哪一类比较成功,这是见仁见智的话题。如果从读者欢迎以及获奖的角度说,我的《狼王梦》《红奶羊》《混血豺王》等作品,发行数量较大,获奖次数较多,规格较高。这类作品,恰好就是你们对动物小说进行分类所认为的类人动物小说。
李:学界认为,国内外动物小说,大致经历了从以人为中心到以动物为中心,从对动物的尊重到以动物为师的变化过程。从拜读沈老师您的动物小说,我发现您始终关注着人类与动物、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浓厚的生态意识,其所塑造的动物形象身上也有着明显的生态学诉求。其主要表现为:以热爱敬畏生命为本的生命意识、以动物权利为本的平权意识、以自然规律为本的生态意识。您通过作品中塑造的不同动物形象,通过描写人类对动物界食物链的破坏,揭示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揭示人类对于动物的迫害,唤醒人们对于“动物解放”“动物权利”和“遵循自然”的认识,让人们主动意识到“动物保护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牵动每一个人的神经,直逼每一个人的心灵,是建立生态道德不可或缺的一环。”沈老师您的认识和实践,对动物小说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请结合您的创作变化过程,谈谈您的体会?
沈:笼统地说,动物小说经历了从以人为中心到以动物为中心,从对动物的尊重到以动物为师的变化过程,这大致是不错的。但是也要看到这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甚至还是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当强调了“以动物为中心”的生态主义,一些作品在描写人与动物关系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往往愤世嫉俗,咒骂人类的贪婪无耻,以动物的保护神自居,以揭露人类身上的丑陋为己任,所以很多作品,包括许多很有影响的经典动物小说,都带有暴唳之气,嘲讽人类,挖苦人类,鞭笞人类,把人类社会当作黑暗的地狱,把大自然动物世界当作光明的天堂。看起来就像挥舞斧头的战将,不由分说一路砍将过去,要为可怜的动物们杀开一条血路。文风当然非常犀利,对肆意破坏环境屠杀野生动物致使生态日益恶化的人类来说,不啻是一剂警醒的猛药。但杀鬼的战将,自己的面目也难免狰狞。读这类作品,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在我看来,是缺乏宁静美,少了一点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
我更欣赏东方民族的智慧,平和豁达,从容儒雅,不走极端。我更钦佩这样的动物小说,中庸宁静,慈悲为怀,大爱无言,大爱无疆,既关爱动物,也关爱人类,既欣赏野生动物身上的自然美和野性美,也欣赏人类社会的人文美和人性美。动物很美丽,人类也美丽。对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灵,都投以温柔眼光,都施以爱的抚慰,采取理解包容的态度。少一些人与动物的激烈对抗,少一些善与恶、美与仇、爱与恨的激烈对抗,少一些血淋淋的暴力场面,因为人与动物不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两极,而是理应相濡以沫共生共荣的和谐生态圈。
世界原本就不应该有这么多喧嚣、杀戮和仇恨。世界原本就应该宁静、平和充满爱的阳光。每一种生命,包括人类,包括美丽的野生动物,都应该有尊严地在我们这颗蔚蓝色星球继续生存下去。
这就需要对话。以对话代替战争,以和平代替杀戮,以平等代替歧视,以温柔代替粗暴,以尊重代替仇恨。通过对话建立大自然新秩序:人与动物和谐共存。
优秀动物小说,就是人类与动物的心灵对话。
李:说得太好了!优秀动物小说是人类与动物的心灵对话!但是我也看到,也许是动物小说市场蛋糕越来越大,受利益驱使,一些动物小说写作者,在作品中出现了人性极度扭曲、兽性极度夸大的情形,特别不适合少年儿童读者阅读欣赏。对此,沈老师您怎么看?
沈:这是动物小说繁荣背后的一些乱象。确实,有少数动物小说创作的后起之秀,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好吸引读者眼球,把缺口和准星瞄准人性与兽性冲突这个靶心。人性与兽性,是人类进化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是社会文明进程永恒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动物小说,围绕人性与兽性,是一种很讨巧的做法,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和无限广阔的外延。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因为描写兽性容易使作品出彩,有些作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渲染兽性,进而赏玩兽性,给作品涂抹太浓的血腥气和太恐怖的暴力色彩。从本质上说,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是闪耀人性光辉的文学,是传播正能量的文学。任何描写兽性,无论是描写人身上的兽性,还是描写动物身上的兽性,只能是必要的衬托和对照,用兽性来衬托人性,用黑暗来对照光明,人性永远是第一位的,光明永远是第一位的。我赞赏很多作家围绕人性与兽性来结构故事从事动物小说创作,我自己很多作品其实也着眼于人性与兽性这个主题,但我还是想说,在描写人性与兽性冲突时,注意分寸,讲究适度,轻微摩擦,合理冲撞,才能永久让自己的作品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中国动物小说创作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瑕不掩瑜,发展和繁荣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问题是第二位的。相信有志于动物小说创作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能在前进道路上克难攻坚,写出更多的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李:谢谢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