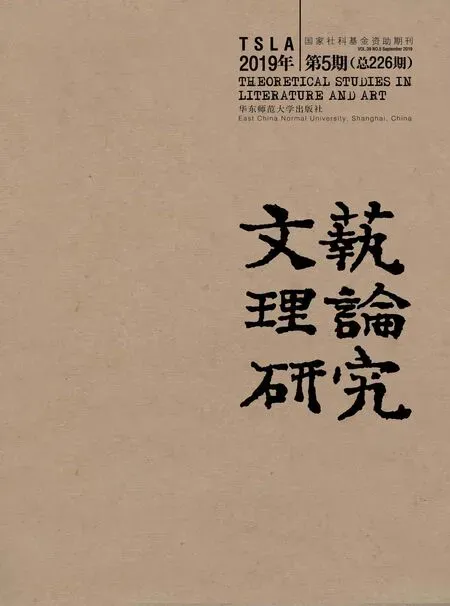清代“唐宋诗之争”二元对立的消解及自反性特征
2019-11-12唐芸芸
唐芸芸
明代复古派恪守“第一义”的汉魏五古、盛唐七古及近体为学习典范,定义自己为其继承者,从而进入文学史传统;而清人进入文学史传统的焦虑,便集中表现为如何介入“唐宋诗之争”。
明代影响最大的复古主张,是典型的二元对立思路。以近体诗为例,他们是以“宗盛唐诗”为一元,“宗中唐至宋元等盛唐以外的诗”为另一元。所以,我们自然会认为从批判、扬弃明代诗学入手的清代诗学,也持续了二元对立的思路。更何况,从字面上看,清代“唐宋诗之争”似乎是唐诗派、宋诗派争胜的文学现象,至多还有一个折衷派进行调和。由于“学术研究的惯性”,很多研究者对“唐宋诗之争”习惯优先使用“唐”“宋”二元对立,用“宗唐”“宗宋”来划分清代诗学阵营。而论争中常见的正与变、格调与性灵、拟议与变化、个性与传统等数对概念,似乎也相应呈现出二元对立、一元中心的状态。果真如此,那么参与“唐宋诗之争”者当持论守成,门户清晰,紧紧围绕或唐或宋进行论辩,可预知应该是以某一派的胜利,即成为诗坛主流而结束。但事实上,这个论争并不似看上去那么主张分明,派别清晰,而是复杂纷呈。
一、 从学术研究中反观问题
大部分研究者用“宗唐”“宗宋”来区分清人的诗学主张。另有一派,居于折衷的立场,就是所谓“唐宋兼宗”者,这一派还有很多别名,如“融通唐宋”“唐宋兼采”“唐宋互参”等。于是,清代关于“唐宋诗之争”的问题,基本上被划归为三个阵营。大致而言,一般是明显对宋诗持反对态度的,划入“宗唐”派;对宋诗极力支持的,划入“宗宋”派;对宋诗持同情态度,但也存有赞赏唐诗言论的,划入“唐宋兼宗”派。如此,“唐宋诗之争”的问题似乎呈现出清晰的面貌。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对向来被划归为“宗宋”一派的厉鹗的几篇研究:
张兵、王小恒在《厉鹗与浙派诗学思想体系的重建》一文中,认为厉鹗以其特有的人格精神和有力的诗学实践,结合浙派诸先辈的诗学主张,通过“因”“变”“创”的努力,构建了以宗宋为前提、重学为途径、追求诗歌“清寒”为最高境界的三位一体的完整的浙派诗学理论体,是“宏通的宗唐宗宋观”。
在王英志先生主编的《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一书的对应章节中则认为厉鹗是“取法乎宋”:“厉鹗生活在宋诗地位不断攀升的时代,但他从未明显地在理论上称扬宋诗或为宋诗辩护正名,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极力赞誉或标榜某个宋代诗人,这固然与当时‘唐宋诗之争’趋于缓和的外部环境及他对‘唐宋诗之争’的反思有关,但也可以看出他对宋诗保持的理性平和的态度。”“与其说厉鹗宗宋,毋宁说厉鹗取法于宋更为恰当。”(王英志301)
夏飘飘《“唐宋互参论”辨——厉鹗“宗唐说”献疑》则认为:“面对唐诗,清代宗宋派诗人厉鹗表现出不否定、不忽视的态度,并且他看待诗歌发展的具体问题时,曾有‘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物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不少研究者由这些诗论得出厉鹗诗学观乃‘宏通的宗唐宗宋观’‘兼采互参’的结论。其实,这些个别涉及唐诗的诗论并不足以作为他宗唐的证据,厉鹗作为一个宗宋者并不意味着他不能认同唐诗自有的精华,面对唐诗,厉鹗采取认可的态度也有其背后的原因,他的基本态度是: 以较为公允的态度看待唐诗,不否定唐诗,甚至有时承认唐诗的可取之处,但这并不等同于主唐、宗唐,也尚未达到所谓的‘唐宋互参’的地步。在清代唐、宋之争的诗潮中,厉鹗始终是个坚定的宗宋派。”
上引论者对厉鹗诗学的认知,并不是停留于表面的口号,也不偏于理论主张和诗歌实践的某一方面,而是深入到厉鹗诗学的核心,讨论不可谓不精深,却又为何会出现这种越辨越不明的情况呢?我们发现,三篇如此细致讨论厉鹗诗学的文章,似乎都有一个最终目的,便是必须将厉鹗在“唐宋诗之争”中标举的大旗描绘清楚: 或是“唐宋兼宗”,或是“法宋”,或是“坚定的宗宋派”。那么,“宗宋”与“法宋”的界限是什么?究竟怎样才算“宗宋”,怎样才算“宗唐”?“认同唐诗自有的精华”“承认唐诗的可取之处”,与“主唐、宗唐”的区别该如何判别?抛开论者对相关材料的取舍和解读的出入,我们应该从根源上进行反思: 判定厉鹗的阵营,究竟是不是研究的最终目标?进一步地,这些用以归纳并引起争论的研究术语,是否真的可靠、有理、有效?
在“宗唐”“宗宋”“唐宋兼宗”这几个研究术语中,“宗唐”似乎是最清楚的,研究者将明确反对宋诗的诗学家,归入“宗唐”派,看似应该没有问题。但我们深入到诗学实际中会发现,同样是“宗唐”,云间派、二冯、康熙、毛奇龄、沈德潜等,在真实动机和具体主张上,都有很大区别;而他们对待宋元诗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宗唐”这个概念的内涵实则相当丰富。“宗唐”的“唐”,有盛唐、中晚唐之分,或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商隐之别,甚至杜甫本身就有盛唐和中唐的不同。这不仅仅是审美理想或取法策略的区别,而是清人对唐诗审美价值判断的问题。同理,“宗宋”的“宋”也有不同的指向,如苏陆、苏黄、杨万里等,即使同样推崇黄庭坚,也可能角度不同,反映出不同的理论观念。
“宗宋”比“宗唐”复杂得多。因为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关键,并不是争论宋诗比唐诗好,还是唐诗比宋诗好,唐诗的经典地位是不容动摇的。大家争论的,是从什么方面把握宋诗的审美特征,并对其在诗史上的地位进行判断。实际上我们找不到一个所谓“宗宋”的诗人对待唐诗,有如一个所谓“宗唐”诗人批判宋诗一样犀利的文字。所谓“宗宋”者,自有一个对唐诗的态度。即使没有对唐诗作整体评价或者深入思考,也并不能说明其对唐诗价值的漠视。如果说只要对宋诗表示同情,就可以明确归入“宗宋”一派,那对唐诗为何又要求必须作出全面的审视和整体的判断呢?可见,“宗唐”“宗宋”作为分类的术语,在标准上本就不平衡,把论争参与者分成“宗唐”“宗宋”对立的两派,是不公允的。
那么所谓折衷的“唐宋兼宗”,大致就是“宗唐”和“宗宋”均不偏废,其可追问之处便更多。如所谓“宗宋”诗人对唐诗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才会被纳入“兼宗”?对宋诗价值报以肯定的诗人,他们有的试图寻找宋诗在唐诗中的源流,有的试图最后回归唐诗,有的试图寻找唐宋诗共同的源头,这究竟该归入“宗宋”还是“唐宋兼宗”?进一步地,“唐宋兼宗”,究竟是站在“唐”的基础上,以“宋”就“唐”,还是站在“宋”的基础上,以“唐”就“宋”?抑或是在“唐”“宋”之间寻求一种同源?或者是各取所需,形成自己面貌?如翁方纲,实际上是一个寻求唐宋同源的诗学家,却因为他对学问的推崇,而被很多研究者归入“宗宋”一派。这样看来,“唐宋兼宗”也是内涵不清。
我们如若采用“宗唐”“宗宋”“唐宋兼宗”的术语,还会掩盖清人和明前后七子的根本区别: 如果用“宗唐”描述清人主张,就容易被划入“宗盛唐”的七子遗风;那么,与“宗唐”并置的“宗宋”,也将被误会为只是置换了取法对象而已。如此讨论,清人对明人诗学便是继承为多,其拨乱反正的价值则将被淹没不计。
可见,在当前研究中用“宗唐”“宗宋”“唐宋兼宗”来划分清代参与“唐宋诗之争”的诗学主张及诗学家,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性质、时间断限、论辩的内核等有充分的认识,扩大研究视野、转换研究思路,充分发掘其复杂性,而不是急于建立简单化系统化的阵营分布图。
在讨论中,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 即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明确。这本应是个在研究之前就该确定的基础工作,在学界也没有引起过多的讨论。因为研究者几乎默认,只要是对唐诗、宋诗持有明显主张的,包括清代后期的宋诗派、同光体等,似乎自然而然地被划归其中,甚至还延续到近代。那么,“唐宋诗之争”就成了一个没有结束的论争,因为今人也可以持续发表或唐或宋的言论。而同时,似乎所有人均可以参与,因为只要对诗歌具备一般鉴赏判断能力的人,均可以表达出或唐或宋的主张。如此,“唐宋诗之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意义,究竟体现在何处?进而我们追问,清人是否真的抱着如此热情投入一场没有结束的论争?
二、 作为实际内核的传统诗学核心概念与唐、宋二元对立的消解
清初钱谦益等提倡宋诗,诗坛掀起一阵学宋风潮,但成效不大。叶燮对此进行反思:
有人曰诗必学汉魏,学盛唐,彼亦曰学汉魏,学盛唐,从而然之,而学汉魏与盛唐所以然之故,彼不能知不能言也;即能效而言之,而终不能知也。又有人曰诗当学晚唐,学宋、学元,彼亦曰学晚唐,学宋、学元,又从而然之,而置汉魏与盛唐所以然之故,彼又终不能知也。(叶燮154)
“人云亦云”存在于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创作实况中。这也导致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或局限于表面的创作实际,持分唐界宋的观念。叶燮总结这种“人云亦云”的现象,都是无“识”的表现,当识古来作者“何所兴感、触发而为诗”(叶燮153)。以这样的思路进行下去,“唐宋诗之争”必然是与非唐即宋的格调选择愈趋愈远。若研究者继续人云亦云,分唐界宋,也将落入无“识”的境地。所谓古来作者“何所兴感、触发而为诗”,即透露出清代“唐宋诗之争”要解决的,不仅是“学谁”的问题,更是“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
接续明代的清代,虽然认识到明人“门户之见、摹拟之风、应酬习气”(蒋寅76—91)导致了诗歌传统的衰落,但这几个方面多属于诗歌创作的外部因素,是可以或者比较容易规避的。清人要延续诗歌传统,必须解决内部因素的问题。途径有二: 一是在创作上另立标杆,如此可以成果立见,但是在反驳或扬弃明代诗学的力度,以及长期创作的稳定性上,均显不足。故而需配以另一个重要途径,即诗学理论的支撑。清人对明代诗学密切关注,不仅仅是新朝对旧朝“以史为鉴”的总结,而且是因为文学史传统被明代大肆洗刷斧藻,特别是明代复古派将宋诗划出文学史,导致了断层,却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文学史的接续问题,这让文化精神更趋近于宋诗的清人或多或少感到一股焦虑。清人需要厘清被明人带偏了的诗学传统。
明复古派由一句“宋无诗”,便抹杀了宋诗的价值,典型的如李梦阳《缶音序》:
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杂错,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物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今人有作性气诗,辄自贤于“穿花蛱蝶”“点水蜻蜓”等句;此何异痴人前说梦也。即以理言,则所谓“深深”“款款”者何物邪?《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又何说也?(李梦阳,卷52447)
材料中明确说明了唐诗具备而宋诗缺乏的因素: 高者可以被管弦;其声悠扬,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香色流动;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其气柔厚;感触突发;言切而不迫;流动情思;不直作理语,而理在其中;“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批判宋人对“法”的过分讲求等。归结起来,正是“性情”“学问”“赋”“比兴”“切实”“兴致”“辨体”等,这些都是传统诗学核心概念。那么,清人如果要解决“宋诗是否可以进入文学史,以什么方式进入文学史”的问题,便需要对这些因素一一进行考辨。考辨的方向有二,一是宋诗是否真如李梦阳等所说言,缺乏这些因素?二是这些因素,是否足以构成进入文学史的全部判断标准?
因为明人只是从理论上下了“宋人主理不主调”的论断,并没有对宋诗史进行过如唐诗般细致深入的反观和思考。所以第一个方向的考查,是清人易于着手之处。从钱谦益提倡苏轼、陆游,到吴之振的苏轼、黄庭坚,到王士禛的黄庭坚,到翁方纲的黄庭坚,这其间对宋诗审美特征的考量,是一个非常细致甚至反复的过程。唐诗在这个过程中,是作为参考存在的。而这个参考,究竟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取决于诗学家对于“变”的认知。很明显,清人对唐诗、宋诗的关注,入手点及用力程度很不相同。对于清人来说,前人留下的宋诗研究文献,存有大量的研究空白。而唐诗,则是一个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问题。
宋诗审美特征的最终确立,关捩在于上述归结的核心诗学概念,再加上以此推导出的“温柔敦厚”“正与变”“拟议与变化”等。唐诗经过明代的选择、阐释、经典化后,已然失却原来面目。而要破除这些魔咒,比直接回到唐诗传统更重要的,是解决明人学盛唐而不得的症结在何处。于是对这些诗学概念的论辩便构成了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实际内核。我们对这些核心概念作清晰的阐释,便能够重新确立唐诗、宋诗文学史地位与价值,也能够完成对唐宋诗关系乃至整个诗史的重新建构。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学唐还是学宋的师古主张。
关于李梦阳等归结出的这些因素,是否足以构成进入文学史的全部判断标准,清人对此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认为明人极端复古,以及后来公安、竟陵派的修正失败,症结在于明人没有从“诗之本”入手,这是明代诗歌创作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传统诗学最核心的概念。所以,无论是钱谦益、陈子龙,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是从“诗之本”入手的,并且越分越细,越论越深。魏裔介将“诗之道”概括为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典范的“道德”,以陶渊明、阮籍为典范的“气节”,以杜甫为典范的“经济”,并言“三者之外,无诗矣”(魏裔介33—34)。即使学古,也是先重视古人的精神内核:“学少陵者,学其气之混茫、辞之雄博,非学其痛哭流涕也;学渊明者,学其自靖之志,寄托之苦,非学其耕田饮酒也。”(34)直到乾嘉时期的翁方纲,还在谈论“言有物”的问题,将体现其诗学主张的诗歌选本命名为“志言集”,并最终将忠孝与学问成功纳入“性情”,完成对“性情之正”的讨论。所以,讨论“诗有本”的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清人对诗歌的人生意义进行重新认知的问题。
可见,清代“唐宋诗之争”,包含了诗歌本质、诗歌批评原则、诗歌审美特征等重要理论问题。从讨论宋诗的价值,深入到讨论“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拟议与变化”“学问”“赋比兴”等传统诗学核心概念,才是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实际内核。清人对这些传统诗学概念的考量不是单独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关注其历史演变,以及各个诗学概念之间的关联,如辨体论人是否肢解了“诗有本”的整体统一性,这又与“正变”观念的认知有关;又如“温柔敦厚”究竟是更强调其呈现“性情之正”,还是更强调其表达方式“赋比兴”;“铺陈排比”究竟是“连城璧”还是“碔砆”等等。清人由此解决“宋无诗”的问题,解决“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的问题,解决“变”的价值,即唐宋诗关系的问题,最终解决“诗必盛唐”的问题。我们对“唐宋诗之争”实际内核的揭示,足以消除其字面所误导的唐、宋二元对立的表面印象。
在对传统诗学概念的整合中,绝大部分清人并不是将唐诗、宋诗作为独立的诗歌创作成就来看待的,而一直关注的是唐宋诗之间的关系。从钱谦益主张苏轼、陆游,便是与中唐白居易一派有着密切关联;黄宗羲主张似唐诗的宋诗;吴之振在《宋诗钞》的序言中对明李蓘、曹学佺选宋诗“取其离远于宋而近附乎唐者”深表不满,认为“以此义选宋诗,其所谓唐终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诗则已亡矣”。(《宋诗钞》3—4)由前期的“似”或“不似”,进而为叶燮的“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叶燮15—16),又为王士禛的从整体风格入手,跳出唐宋诗窠臼,再为翁方纲的以“肌理”“正面铺写”接续从杜甫到苏黄的文学史,这其中隐含着唐诗到宋诗的“变”是如何呈现,且是否可以接受的问题。即使是反对宋诗者,也是因为宋诗学唐而不得,无法延续唐诗的精神。如果我们若仍然以“宗唐”“宗宋”“唐宋兼宗”来分别清人的诗学主张,将清人分列为二元对立或三足鼎立的阵营,便是辜负了清人由对诗学深层问题探讨而反思建构整个诗史的使命感和热情,低估了其价值。
所以,清代“唐宋诗之争”的终极目的,不是唐、宋二选一作为师古对象,或者惟务折衷的问题,而是清人对整个诗史进行重新整合的过程,是一个重写诗史的工作。各种诗体在唐代即已臻成熟,宋人便已不可能在文本世界再作创新。而由于明人对诗学的断层处理,诗学发展到清代,自然需要作整体性回顾,如此才能继续推进在创作上的主张。在清人对传统诗学核心概念的探讨中,“唐”与“宋”的分别已经被逐渐弱化了,更遑论成为二元对立的结构。整个“唐宋诗之争”中蕴含的,竟是大量消解这个论辩的因素。
我们还可以从学理上分析唐、宋的对立结构关系。
明代复古派对诗史的二元对立判断,有一个前提,即双方建立在同一个理论基础上,以符合/不符合这个理论基础,构成对立的双方。以近体诗为例,其理论基础便是“从第一义入手”,宗“第一义”的盛唐诗为一元,而宗中唐以后至宋元诗,由于不属于“第一义”,被置于“宗盛唐”的对立面,为后人师古不可取的部分。且正是由于明复古派明确坚持“从第一义入手”这个理论基础,才呈现“宗盛唐”一元中心的局面。
明人对第一义的盛唐诗的学习,集中表现为“格调”,这是坚持审美理想与师法策略合一的思路,后人师古成果高下立见,但同时也容易落入机械摹仿。清人的批判,究竟是要置换审美理想,还是改变师法策略?审美理想和师法策略究竟是合一还是脱离?其思路大致有三:
第一,同意从第一义入手,也同意盛唐诗为第一义,但批判明七子从格调学盛唐。如王士禛,认为盛唐诗的价值并不体现在格调上,认为唐诗被明人以“格调”大量摹拟后,面目全非,已不是真唐诗,所以需要找到诗道“第一义”的其他表现,摆脱明人对“格调”的过分推崇;
第二,同意审美理想与师法策略合一,但批判明七子以盛唐诗作为第一义。典型者,莫过于翁方纲。他坚持从第一义入手,只不过他的第一义,不再是盛唐,而是杜甫;
第三,直接针对或者弱化“从第一义入手”的论调。这有两种走向: 一是主张“转益多师”,这是清代很多诗学家,特别是倡宋诗者如钱谦益选取的角度,这为中晚唐诗、宋诗等进入人们视野提供了可能。二是主张“先河后海”,即从规范性强的对象开始学习,最后再学第一义,这是师法策略和审美理想脱离的主张。主张晚唐如冯舒、冯班者也属于此类,研究者是这么描述的:“其实杜甫方是二冯心目中之最高审美典范,只因老杜诗歌已臻及化境,故难能以寻常之典范学习之也。因而二冯效王荆公之言,认为‘学杜当自义山入’。”
可见,与明代复古派诗学二元对立不同,理论基础有交叉的“宗唐”“宗宋”,并不能构成二元对立结构。
进一步分析,“唐宋诗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或可置换成关于“审美理想和师法策略”的争论。即可以分为“从第一义入手”“转益多师”“先河后海”;即从“第一义”的判定来说,又可以分为“风貌”(如格调)“审美特征”(如神韵),还有创作的统一性(如肌理)等等。这些分辨均不与所谓“宗唐”“宗宋”两派重合对应。
“唐宋诗之争”还可以置换成对宋诗“变”的价值的论争。其中对“变”的价值持否定判断的论调,不仅存在于将宋诗划出文学史的派别,还存在于以宋诗似唐而支持宋诗的主张中。那么,所谓“宗宋”的派别,竟同时包含对“变”的价值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可见,即对“变”的价值或肯定或否定的对立双方,也不与所谓“宗唐”“宗宋”两派重合对应。所以常见的如将黄宗羲作为浙派起源的观点可能需要重新考量。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 清代“唐宋诗之争”,并不是唐诗与宋诗之争,而是传统诗学核心概念之争。理论是诗歌创作主张的基础,看似相近的或唐或宋的创作口号,有可能产生于不同的理论观念。即使在对具体理论概念的讨论中,清人也一直在试图冲破明代诗学二元对立的格局。如翁方纲对性情与卷轴的结合,方东树的创新与典雅的结合等。清人实则消除了明代诗学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理论视野变得广阔并清晰。清代诗学追求的,是对被明人玩坏了的整个诗学史的重新梳理。这种考量,从清人进入文学史之初就开始了,最终实现了对明代诗学的整体性颠覆。坚守二元对立的思路——无论自觉与否——透露出在我们的诗学研究中,只关注创作主张或口号,却忽视了思路形成的历史及逻辑过程的缺陷。
三、 “唐宋诗之争”的自反性特征
清人究竟如何解决或结束清代“唐宋诗之争”?其方向主要有三:
第一是在唐宋诗之外,寻找其他源头,如上追到《诗三百》,直接回到传统诗学的本原,与“诗有本”的政教思想相呼应。虽然这仍不过是置换了一个取法对象,但是,变唐诗、宋诗二者为一,也达到了师古上取消唐诗、宋诗非此即彼的对立,还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很多追随者的人云亦云、只重“声色”的肤廓理解。但是,《诗三百》属于四言诗时代,三言、五言、六言、七言,虽有呈现,却并不成熟,仅仅主张取法《诗三百》,其实越过了辨体、“变”“温柔敦厚”“性情”“学问”“赋比兴”等一系列理论概念。如果只是在创作的取法上直接回到传统诗歌的源头,而不对诗学的演变进行反思,特别是对经历了明人或强化或偏移的诗学阐释进行反思,那么对当下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指导的作用则会流于空泛,其价值只能限于置换摹拟对象。故而类似的主张,并没有最终消解“唐宋诗之争”。这也体现了清人对理论探索的深刻性。


无论是探索唐宋诗的延续性,还是从外部消除唐宋诗对立的可能,都可见清人试图将唐诗、宋诗乃至整个诗史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具有“变而不失其正”的特征。正是这个方向,恰恰消解了“唐宋诗之争”存在的合理性。名之为“唐宋诗之争”,却随着讨论的深入,理论的指向越来越明确地表现为消除或唐、或宋对面而立的合理性,消除论争的必要性。这昭示了清代“唐宋诗之争”具备明显的自反性特征。
余 论

与经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畋域清晰、持论分明不同,作为清代文学文化三大论争之一的“唐宋诗之争”,并非一场界限清晰、有强烈门户意识甚至流派意识的诗学论争。用“唐宋诗之争”来命名,更多地指向其呈现出的诗学旨趣。但作为研究者来说,不能只停留在诗学旨趣的表象上,而应该多方面深入地思考其关涉到的诸多理论问题。我们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不再以“阵营”来陈述清代“唐宋诗之争”,而是以诗学核心概念的逻辑进程来陈述。要构建“唐宋诗之争”的脉络,自然是以时间为线索,但是这个时间,如果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就很容易走进分唐界宋的泥沼。清人进入及最后走出“唐宋诗之争”,都是因为对这些诗学核心概念的发现、解决、弱化,或者转移。这个过程基本上仍然是以时代为序,也符合逻辑进程的体现,但构成时代的,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具体的诗学概念。
清代“唐宋诗之争”并不存在唐、宋二元对立,又具有自反性特征,其理论论述中存在无数消解、变化的可能,使得这个论题变得复杂而有趣。以衣衫为喻,清代“唐宋诗之争”呈现出来的色泽和风采,粗看去或唐、或宋、或唐宋均沾,但若将褶皱一一平整铺开,便是一幅色彩层次丰富、韵味隽永,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品。这件精品,用来比对明代诗学,乃至放置于整个中国诗学中,也是光彩耀人,熠熠生辉。
注释[Notes]
① 这其中还包括论者观点变化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几乎发生在绝大部分诗学家身上,宋琬、汪琬、王士禛、厉鹗、翁方纲等皆如此。
② 张兵 王小恒:“厉鹗与浙派诗学思想体系的重建”,《文学遗产》1(2007):80—89。
③ 夏飘飘:“‘唐宋互参论’辨——厉鹗‘宗唐说’献疑”,《浙江学刊》4(2014):96—101。
④ 唐芸芸:“文学史视域中的翁方纲宋诗学”,《文艺理论研究》5(2015):158—66,转185。
⑤ 这里面还需要与诗“无分唐宋”的概念进行区别。所谓“唐宋兼宗”,无论人们是持赞赏还是疏离的态度,视野都集中在唐诗和宋诗上。而“无分唐宋”,已经将眼光超越了唐诗和宋诗,是对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进行观照,一般是从承认“变”的价值入手的。
⑥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诗坛上确乎存在明确的分唐界宋的情况,如“凡声调字句之近乎唐者,一切屏弃而不为,务趋于奥僻,以险怪相尚;目为生新,自负得宋人之髓”(叶燮:《原诗笺注》,蒋寅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41页)者。但一种文学现象,当有主张者,有追随者,只是将眼光置于奥僻、险怪等声色上的显然是随流者。对“唐宋诗之争”真正有影响的诗学家,尤其是木铎起而千里应的诗坛领袖,如钱谦益、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袁枚等,都不是简单持“非唐即宋”的诗学观念。我们讨论的自然是这些对诗学发展及诗歌创作走向有重要影响的主张者。
⑦ 唐芸芸:“翁方纲对‘吟咏性情’命题的回归与修正”,《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017):38—45。
⑧ 蒋寅:“王渔洋‘神韵’的审美内涵及艺术精神”,《中国社会科学》3(2012):129—48。
⑨ 唐芸芸:“翁方纲核心诗学概念关系辨析及价值定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018):46—52。
⑩ 廖宏昌:“二冯诗学的折中思维与审美理想典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05):38—43。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蒋寅: 《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Jiang, Yin.A
History
of
the
Qing
Poetics
. Vol.1.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2.]李梦阳: 《空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年。
[Li, Mengyang.Collection
of
Kongtong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 Vol.1262.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of Taiwan, 1986.]王英志编: 《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Wang, Yingzhi, ed.A
History
of
the
Contestation
between
the
Tang
and
the
Song
Poetryin
the
Qing
Dynasty
.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魏裔介: 《魏裔介诗论》,《清诗话三编》第一册,张寅彭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Wei, Yijie.Wei
Yijie
’s
Remarks
on
Poetry
.Poetry
Commentariesfrom
the
Qing
Dynasty
. Vol.1. Ed. Zhang Yinpe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4.]吴之振 吕留良 吴自牧选,管庭芬 蒋光煦补: 《宋诗钞》。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
[Wu, Zhizhen, Lü Liuliang, Wu Zimu, Guan Tingfen, and Jiang Guangxü, eds.The
Anthology
of
the
Song
Poetry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叶燮: 《原诗笺注》,蒋寅笺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Ye, Xie.Annotated
Origin of Poetry. Ed. Jiang Yi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