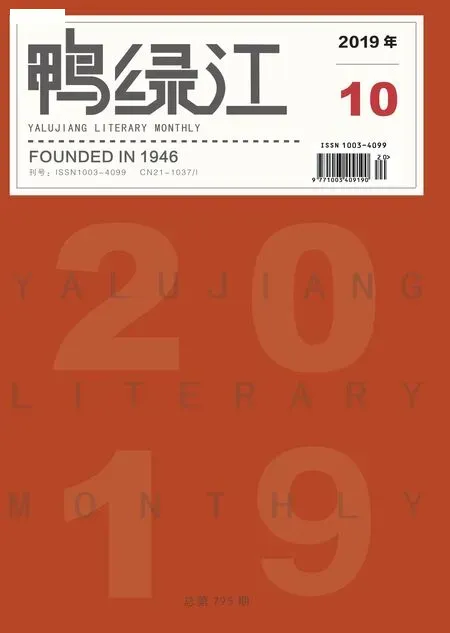浅析《哈姆莱特》和“俄狄浦斯情结”在《夜宴》中的改写
2019-11-12周珊伊
周珊伊
“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夜宴》是对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莱特》的跨文化、跨媒体改编,在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和整体基调上基本沿用了戏剧原有的设定,并且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再创作。其戏剧改写基于对哈姆莱特“俄狄浦斯情结”的阐发而生成,为我们重新鉴赏文本提供了新的视点。
一、哈姆莱特“俄狄浦斯情结”解读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为哈姆莱特人物形象之解读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向,尤其是对于哈姆莱特为父报仇的行为多次延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弗洛伊德认为哈姆莱特复仇行为中产生的延宕并非是由于其性格的柔弱,他向亡父起誓为其复仇时的坚定以及其在复仇行动展开后的勇敢、机警显示了其绝不是行动上的弱者。弗洛伊德认为哈姆莱特为父报仇之行为的延宕可以解读为哈姆莱特作为男性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母亲乔德鲁特具有着不正常的依恋和占有欲,而其叔父克劳狄斯的弑兄行为正好满足了哈姆莱特潜意识中想要取代父亲独占母亲的心理。
弗洛伊德在《释梦》中指出:“哈姆莱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只除开向他父亲娶了他母亲、那个实现了他童年欲望的人复仇。于是驱使他进行复仇的憎恨为内心的自责所代替,而出于良心上的不安,他感到自己实际上不比杀父娶母的凶手高明。”实际上意在指出哈姆莱特复仇行为的延宕是出于对其自身对母亲不正常的独占欲而造成的,他在复仇行为中产生的犹豫是因为恐惧对克劳狄斯的复仇导致的直面自己内心对母亲的不正常依恋。这种解读遭受了多种的争议,但是不失为解读哈姆莱特复仇中延宕行为的一种合理角度。
二、《夜宴》对《哈姆莱特》“俄狄浦斯情结”之改写
1.“弑父娶母”情结之合理性的赋予
《夜宴》中人物关系的置换赋予了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合理性,“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弑父娶母”得以从潜意识中浮出。婉后身为太子无鸾的初恋情人却被无鸾的父亲强占为继后,成为了无鸾名义上的“母亲”。这种身份的置换赋予了“子”对“母”的爱恋以合理性,尽管继母与继子的身份仍然受到伦理道德的谴责,但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反而能够得到接受者的理解。无鸾与哈姆莱特的复仇具有相似性,无鸾对厉帝复仇除了其杀害了无鸾的父亲,更包括了其对于婉后——“母亲”的觊觎和强占。而无鸾面对厉帝的刺杀与暗算却迟迟不展开复仇行为一定程度上同哈姆莱特的延宕具有相似的理由——恐惧承认自己对“母亲”的欲望。尤其在其复仇成功后自身的恐惧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时,无鸾的复仇行为陷入了极端的犹豫和忧郁,这与弗洛伊德对哈姆莱特复仇的延宕原因的阐释高度契合。
2.人物形象之改写对弗洛伊德妇女观的颠覆
《夜宴》人物改写的颠覆性在两组女性形象的对比中得到了体现。《哈姆莱特》中,对乔德鲁特的形象塑造使其陷于一种丧失话语权的地位,她的行动、言语皆显示出女性由于其所属的从属的社会地位而产生的柔弱。她对于人物之间暗流涌动的冲突一无所知,最终无知地饮下毒酒死去,显示了女性在男性中心意识下备受摆布的悲剧命运。而《夜宴》中的婉后却具有着鲜明的主体意志与强烈的个人欲望,她运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在波诡云谲的斗争中斡旋稳占上风,巧妙而不动声色地保护着自己的爱人无鸾。在认识到只有权力能够让她和爱人的命运不再受到他人的摆布后,她对于权力的欲望和贪婪比戏剧中的男性角色更甚。婉后的形象是对于原文本中娇柔的女性形象的颠覆,显示了女性主体对于男权中心意识的冲击与反抗。
而奥菲利亚同乔德鲁特具有相似性,身为匍匐于男权的统御下的柔弱者,她的温顺、天真使她注定无法成为哈姆莱特复仇之路的同路人,并最终在不自觉中受利用成为了国王和父兄试探哈姆莱特的工具。她为爱情所致的疯癫固然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但是这种牺牲植根于其感性中心的人格,是不自觉的牺牲。《夜宴》中青女的人物形象更为丰富饱满,而且更加具有明确的女性意识,她的纯净和痴情与婉后的贪婪和恶毒、对爱情的忠贞和无畏强权与朝臣的懦弱和自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她强烈的人性的光辉的感染下,厉帝被权力和私欲扭曲的心灵也重拾愧疚。影片聚集的阴谋和冲突带给观众紧张的刺激的同时,为这小女子坚如磐石的真情而具有了道德上的升华,她的死亡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非在无知觉的状态下由他人造成的悲剧。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暗含着女性对男性的“阳具崇拜”,而《夜宴》对于《哈姆莱特》中女性角色的失语和其在戏剧冲突中的边缘地位的改写所体现的鲜明的女性意识正是戏剧再创作的颠覆性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