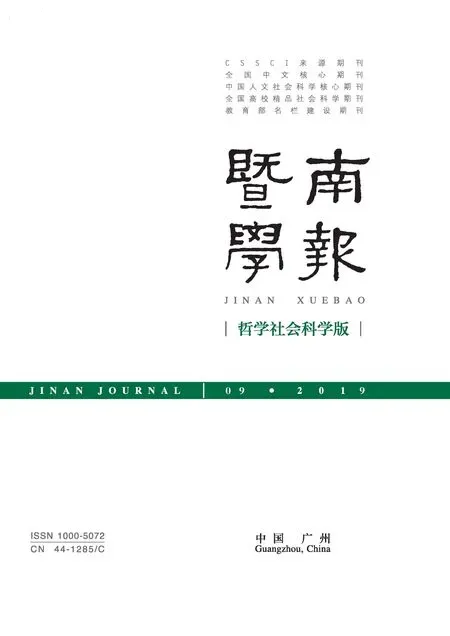《山海经》永生审美意象研究
2019-11-08罗筠筠李洁琼
罗筠筠, 李洁琼
引 言
《山海经》是中国早期文明保留最为完整的古籍之一。书中除了丰富的神话、民俗、历史、地理等信息外,还蕴含着独特的原始美学思想,其中关于“永生”的美学意象具有清晰的脉络和鲜明的特色。
目前,针对《山海经》永生审美意象的研究相对空白,但已有学者做出了相关的先驱性探索,如周腊生1986年发表于《江汉论坛》的《中国上古神话审美意识的三个特点》分析了中国上古神话特点的同时略有论及此类审美意识;涂晓燕2007年发表于《东南文化》的《原始思维对〈山海经〉长生思想的肯定》从思维的角度列举了《山海经》中否定死亡的几种方式;林静、贤娟于2012年发表于贵州师范学报的《〈山海经〉生死意象的审美浅析》尝试从美学的角度对《山海经》的生死观进行分析,并将这些生死观的美学表达分为“永生”和“变形”两种;赵悦、孙惠2017年发表于《兰州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山海经〉中的死亡变形神话类型》将《山海经》中的死亡变形神话分为图腾型变形、类比想象型变形、情感型变形、接触型变形四种;徐美琪2018年发表于《绥化学院学报》的《〈山海经〉中的不死神话与死亡认知》以神话和认知的角度来论述《山海经》中的此类问题。这些研究中,存在一些对此类主题内容的分类过于粗浅,不清晰、不系统,甚至不恰当的问题。其次,这些研究对《山海经》中涉及“永生”这一命题的原始资料考察和挖掘尚不够全面充分,对书中明确记载或历代重要注本中提及,但后代流传不广的某些资料未给予关注。此外,现有的研究中,针对《山海经》中此类主题产生的原因和根源性研究较少涉及,从审美意象角度展开的研究也并未深入。

一、《山海经》中永生审美意象的呈现形式
“永生”维度下的审美是美学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类美学形态。关于灵魂不灭的观念自古就有,并且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早期文化中都普遍可见。这种灵魂不灭的信念并非只是 “虚无”的抽象存在,先民们幻想出与长生不死相关的各种形象,让灵魂永生的信念贯穿渗透到具体的形象中,创造出了最初、最原始的“永生”美学意象。《山海经》中的永生意象十分丰富,无论是较系统的《山经》部分或较零散的《海经》部分都频繁出现关于“永生”的内容,涉及这一主题的美学意象在该书中主要以四种形式呈现:“不死”“延寿”“复生”和“化生”。
(一)“不死”美学意象
实现“永生”最直接、最彻底的方式就是“不死”,它将死亡从生命历程中直接删除,对“死”这一必然结果做出颠覆性的否定。《山海经》中以“不死”形态呈现的意象大概有以下几类:
1.不死之地
《山海经·大荒南经》曰:“有不死之国
,阿姓,甘木是食。”《大荒西经》载有传说中黄帝居住的“轩辕国”,并说这里“不寿者乃八百岁”。《海内北经》提到了历代求仙的圣地“蓬莱山”。这些都是让人长生不死之地。原始先民们认为在围绕着日常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现实世界之外,必有超乎现实的不死世界存在。这种带有原始审美意象的“不死之地”并不像文明时代宗教系统中的往生世界或天堂那样,人在现世无法到达,而是与现实并行存在的区域,它们虽在未知的远方,但人们相信在现实世界中经过努力是可以抵达的,并非虚无缥缈的存在。《史记·封禅书》就有这样的记载: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
,而黄金银为宫阙
。未至,望之如云
;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
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不得,还至沙丘崩。文中记载了秦始皇屡次寻找神山以求不死之药未果,并且从首句便可知,秦始皇虽是统一六国的始皇帝,但绝非寻山求药的始皇帝,对于不死之地的执着,“世主莫不甘心”。对比《山海经》中的“轩辕之国”“蓬莱山”,《封禅书》关于这些神山的描述更加具体生动——“黄金银为宫阙”“其物禽兽尽白”“望之如云”,并且有了明确的方位——“勃海中”。源自《山海经》中原初的“不死之地”在汉代的《史记》中发展成为美轮美奂的仙境,成为人们在现实中无限憧憬的圣地。
2.不死之人
《山海经》记载了两种不死之人:
不死民
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一曰在穿匈国东。(《山海经·海外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
。(《山海经·大荒西经》)前一处叙述不死之人“为人黑色”的特征和所居住的位置;后一处也具体描述了不死之人“三面一臂”的外貌特征并说明他们是颛顼的后人。可以看到,不死之人不只一种,而且在不同的地域出现,这让当时的人们更坚信其真实性:通过相信和自己同样属性的生命体可以不死,在内心点燃了自身也可以不死的期望;自我认知范围内无法确定、无法实现的“不死”,借由陌生的、未充分认知的他者的“不死”得到了确认。
3.不死之物
有不死之人、不死之地,必有不死之物与之共存。《山海经》借由对不死之物的描述,将这种“不死”的意象更加具体化、合理化、扩大化、系统化,让其他生灵甚至无生命体也以“不死”的方式具备了“永生”的属性,让人对“不死”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更广阔的幻想空间。关于“不死之物”,在《山海经》中分两类:第一类是使人长生不死之物;第二类是自身不死之物。
(1)使人长生不死之物
《山海经》中明确地记载了“不死山”和“不死树”:
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
。(《山海经·海内经》)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
,凤皇、鸾鸟皆戴瞂,又有离朱、木禾、柏树、甘水、圣木、曼兑。(《山海经·海内西经》)除了此两处,《山海经》另有两处涉及“不死树”和“不死泉”,一是晋代郭璞注《山海经·大荒南经》“不死之国”处云:“甘木即不死树,食之不老。”二是郭璞注《山海经·海外南经》“不死民”处云:“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此外,《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 “灵寿”也属于“不死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
,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按照民间传说和一些古籍记载,“灵寿”是生长在昆仑山及其附近地区的神树,人吃了它的果实可长生不死。历代注解《山海经》此处时均认为“灵寿”应是“椐树”。相传古代老人常用“椐树”的树枝做拐杖,一方面因为其天然的造型十分适合做拐杖,无须过多地加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相信其枝干和果实一样具有使人长生不死的神力。除了非人为因素而自然存在的山、树、泉等具有不死的神力外,还有通过巫术对抗死亡时使用的“不死药”有此效力: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
以距之。(《山海经·海内西经》)《山海经》中能让人不死的神物可以是自然生长物,也可以是人为创造物。在先民的观念中,“不死”可以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同时,“不死”的权力也可以掌握在某些地位特殊的、有神性的人手中。根据《山海经》记叙,这种权利往往掌握在 “帝”手中。带有巫术性质的活动是上古原始文化的主要载体,巫术活动不是用来简单满足人的某一个具体的需要,而更多的是人与神的对话,达成这一沟通的媒介便是“巫”。这样神圣而重要的职务自然不是一般人可担任,“巫”在当时的地位极高,很多专家认为,“巫”就是原始社会部族的领导者。而彰显他们威力的一种有效,甚至是必要的手段,便是操“不死药”,有起死回生的法术。《大荒南经》中便有这样的记载:

帝药
、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2)自身不死之物
先民们坚信,“不死”不仅可以发生在人和神身上,同时也适用于其他的物种。《山海经》中的“不死”并非只是 “神”或有神性的人的特权,而是宇宙万物都会发生的现象:

冬夏不死
。(《山海经·海内经》)第一段记载了一种像羊但无口、“不可杀”的神兽。第二段中,不死发生在植物身上,后稷埋葬之地生长出来的草,不像自然界中寻常的草木一样会枯荣凋零,而是“冬夏不死”。
“不死”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普遍信念,“不死”的意象也是使以族群为存在单元的原始社会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因素,更是先民与永生的宇宙万物链接、沟通的方式。虽然这些能让人实现不死和自身不死的神物在《山海经》中只有只字片语,但内容多样、结构系统,从“不死之地”、“不死之人”、“不死之物”几个层面立体地勾勒出了上古社会人们所希冀的永生乐园,让人读来惊奇感叹,心生向往。
(二)“延寿”美学意象
除了“不死”之物,《山海经》还记载了通过乘坐神兽“乘黄”和“吉量”来突破死亡、增加寿命的内容:
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被发。有乘黄
,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
。(《山海经·海外西经》)犬封国曰犬戎国,……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
,乘之寿千岁
。(《山海经·海内北经》)“乘黄”在其他古籍中也有记载:《周书·王会》曰“白民乘黄”,《淮南子·览冥训》记为“飞黄”,《汉书·礼乐志》云“黄帝乘之(乘黄)而仙”,唐代诗人韩愈《符读书城南》云“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后演变出现代汉语中“飞黄腾达”一词。 “飞黄腾达”代表财富、地位大幅度提升之意正是源于“飞黄”初始的“延寿”,指向“永生”的含义。另一个神兽“吉量”的神话还可见于《淮南子》《史记》清马骕《绎史》等,传说当年商纣王拘禁周文王,太公与散宜生以重金求世间珍稀之物献于纣王,以求赦免其君,求得之物最重要的一样便是“吉量”(文马),纣王大悦,赦免了周文王。
“乘黄”与“吉量”的形象类似神话中神仙的坐骑,这些神或仙的神力与他们乘坐的神兽具备使人长生不死的功能有直接关系,甚至可能是必然关系,而人和神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寿命的长短或寿命是否有限。中国很多古籍中都有长寿、延寿的记载,《庄子·逍遥游》云“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楚辞·天问》也有“延年不死,寿何所止”一问。人对寿命的增加有着无限的热忱,因为寿命的长度是衡量生命最直接的标准。通过让人的寿命得以延长而建构出的“延寿”型永生审美意象,虽不如“不死”意象那样彻底有力,但“延寿”同样是人们对抗死亡、寻求“永生”的重要方式之一,达千岁之寿和人真实的寿命相比,以及当时人们对数量的认知程度来看,已是个接近无穷大的寿命概念。
(三)“复生”美学意象
除了“不死”和“延寿”外,“死而复生”也是通往“永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1.刑天与夏耕
《山海经》中流传最广的“死而复生”神话当属“刑天舞干戚”:
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
在《山海经》中还有一处“夏耕之尸”与刑天的形象类似: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山海经·大荒西经》)
断首并不能让刑天和夏耕真正死亡,一个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抗争,一个依旧手操戈盾,尽忠职守,只要与人世间尚有一息链接,便还要倾尽全力延续自己的生命,用残缺的躯体、以“死”的形态来完成“生”的宿命。这种“死而复生”的意象,给人一种强烈、悲壮的美感。

《山海经》中“死而复生”的美学意象除了和英雄主义的形象相关,还有出于先民们单纯地坚信有机的生命可以在死后重获生命而产生的美好希冀:


3.鯥
关于“鯥”,《山海经》这样描述它的“复生”:
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夏生
,食之无肿疾。(《山海经·南山经》)现代人眼中“冬死夏生”应是动物冬眠的自然现象,但先民们却用“死”和“生”的概念来理解,因为在他们眼中,死亡是像人睡眠或暂时昏厥一样,会再醒来,他们的观念中并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他们认为或者说更愿意选择相信:“死”并非生命的终点,而只是生命历程中的一种暂时状态,“生”才是生命的常态。屈原《楚辞》就用瑰丽的言辞表达了这种通过“灵魂”往返重获生命的观念,在《招魂》和《大招》篇中不断重复“魂兮归来”“魂乎归来”的召唤,欲求召回逝者的灵魂,达到“穷身永乐,年寿延只”的目的。这种将生命看作是灵魂在躯体中往返的过程的观念在《列子》中也有论述,《列子·天瑞》云:“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死亡是“精神离形,各归其真”的观点。
“复生”通过让已死亡的有机生命体重获生命的途径实现,是针对个体的生理存活迹象会消失,物质的躯体会消亡而幻想出来的抗拒死亡的方式,其形成的观念基础是,以灵魂为核心的生命不会因为躯体的死去而真正死亡,而只是在有形的躯体中进行“来”和“去”的往返而已。正如《庄子》所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四)“化生”美学意象
与“不死”和“死而复生”相比,“化生”的美学意象展现出先民在更广、更深的程度上对生命限制的突破:生命不是简单地延续或重复,而是产生了质的变化,以另外一种形态的生命体存在,并且往往是对前一种生命形态的升华。“化生”赋予了生命无限的可能,让人的想象力在更广袤的空间驰骋。
《山海经》中记载了多个 “化生”的神话形象:
1.精卫
精卫填海是中国广为人知的神话故事,《山海经》中这样记载:
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
被大海夺去生命的女娃化作精卫鸟,飞到西山衔来石木,填埋东海。浩荡的大海和渺小的飞鸟,无边无垠的海水和鸟喙中的微小颗粒之间构成了天壤的悬殊,它们之间的角逐早已注定以悲剧结局,而这种绝望的抗争却能让人的心灵为之颤抖,萌生敬佩与怜惜之情,让微渺的个体生命在浩瀚的宇宙间闪耀出光芒。注定的悲剧、绝望的抗争、微渺的个体却铸就了一个顽强抗争、义无反顾、永存希望的美学意象。
2.夸父
与“精卫”渺小和无望的形象不同,“夸父”的形象力量感十足,强大而坚毅,展现出了人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和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山海经·海外北经》)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山海经·大荒北经》)

夸父的手杖化为邓林(即桃林),象征着夸父精神的延续。桃林让人联想到的是一幅果实累累、枝叶繁盛的景象,桃树在中国文化中向来有宜子孙、繁衍生息之意,如《诗经》中的桃树“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现代汉语用“桃李”来比喻教师 “树人”所得的硕果。以“邓林”作为夸父之杖的化生物,寓喻着夸父这种敢与日竞走,突破自我极限、牺牲自我、征服自然的精神将如桃林般绵延不尽、世代相袭。
3.大禹
“大禹治水”传说中的“禹”,据《山海经》载,由“鲧”化生而来: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
。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一心要治理洪水、消除人间灾难的鲧,因为没有等待天帝命令,私自窃取“息壤”,被帝下令杀死。传说鲧死后其志不灭,身体三年不腐,剖开腹部生出了“禹”,也有学者认为“腹生”即“复生”,“禹”乃是“鲧”的化身。夸父逐日以失败告终,鲧治水本来也是失败的结局,并且因“不待帝命”而惨遭杀戮,但“化生”后的故事却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演绎:“鲧”通过另一个更强大的生命体“禹”来完成遗志,并铸就出一位治水定九州、贤能有德的伟大君王形象。中国很多地区,尤其黄河流域,民间至今仍保留祭拜大禹的习俗,禹有时甚至被作为同创造人类的始祖神女娲、伏羲同样重要的神祇来祭拜。
4.枫木
《山海经》中蚩尤所弃桎梏化枫木的记载,也是一个“化生”意味浓厚的神话:
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
。(《山海经·大荒南经》)中国部分苗族神话说中,枫叶的红色是蚩尤鲜血所染,苗民的始祖是由枫树而化,这与《山海经》所载枫树由蚩尤的枷锁化生的记载相印证。苗族先民们将枫木看作是万物的始祖,很多苗族地区至今仍保留枫木崇拜的习俗:迁居时先栽种枫树,意为向祖先询问,遵循祖先的昭示行事,树活居,树死离;建房时以枫木作为房屋中柱,因为枫木生人,可繁衍子孙、兴旺人丁。苗族流传下来的古歌《枫木歌》便反映了这一观念,歌词译为现代汉文大意如下:
世间万物多,来源是一个。要晓得清楚,来唱枫木歌。
枫木生榜留,才有你和我。要晓得典故,来唱枫木歌。
回头看太初,悠悠最远古,……
汉民族尊炎黄为祖先,苗民族则尊蚩尤为祖先,蚩尤的“灵魂”在枫树的意象中留存下来,得以永生。《山海经》中化生而来的“枫”所蕴含的意象与《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的悲凉意境或唐诗“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秋意美景截然不同,它承载着祖先崇拜、生育崇拜的信仰,是一种蕴含生命循环变化、氏族神图腾的特殊原始美学意象。
5.其他(神十人、鱼妇、瑶草、大鹗与鵕鸟)
除了上述几个流传较广、影响颇深的“化生”意象外,《山海经》中其他几处“化生”形象虽不广为人知,却饶有意味,如女娲之肠化生的“神十人”:
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
,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在蛇化为鱼之际与鱼合体化生的“鱼妇”:
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山海经·大荒西经》)帝女之尸化生的“瑶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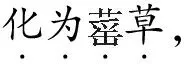



“化生”的美学观念自先秦起就广为流传,《列子·周穆王》载老聃曰:“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列子·天瑞》有“天地含精,万物化生”一说。《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种指向“永生”的“化生”美学意象与道家的“气论”“阴阳说”“五行说”“天人合一论”等有着密切联系,与宇宙万物的本源相通,是中国古典美学所特有的形态。《山海经》中的化生形象充分地呈现了这一原始、古朴的审美意象。
《山海经》中出现的“永生”美学意象,其形式构思独特、内容瑰异绝妙、层次丰富多变,贯穿于整部典籍的各个篇章,是古今文学、艺术创作的滥觞所在,也是当代人解读《山海经》这部经典古籍的美学意义和思想价值的一个关键点。从中国美学史角度来看,《山海经》中以“不死”“延寿”“复生”“化生”四种方式构建的“永生”美学意象体系,是历代中国文化艺术中“永生”主题的母体和原型。
二、永生美学意象产生的根源
“生”字最早见于殷商卜辞,本义为草木从土里生长出来,上面部分是冒出地面的草木,下面部分是大地、土壤,到周代始有“生命”之义, “生”字的字源演变图示如下 :

甲骨文金文小篆楷体
《周易·系辞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间最伟大的法则,而“死”是与“生”相对的存在,是人面对“生”时最大的疑惑和难题,也是人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永生的追求和向往,是人们抗拒死亡、回答“死”这一难题时衍生出的对“生”之信念的坚定认同和对“生”之永恒性的美好希冀。
《山海经》中“不死”“延寿”“复生”“化生”这四种永生意象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是特定历史阶段下人们的认知模式、审美需求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是人最原初、最本能的情感对象化和艺术化后的结果。总的来说,《山海经》中的永生美学意象的产生由三方面的因素造成:第一,原始思维对“生”“死”的认知逻辑;第二,初民对人自身价值的认同;第三,人超越时空限制的本能渴望。
(一)原始思维对“生”“死”的认知逻辑
先民对于死亡的认识与现代人不相同,对他们来说,客观存在的躯体生命迹象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他们把死亡和梦境看作是独立于人躯体生命活动之外的另一种生命力在进行活动,这另一种生命力就是初民观念中的“灵魂”。原始人坚信“灵魂”的存在,并将其移植、泛化到其他一切客观事物身上。早在十七世纪,西方学术界在研究原始人的思维时就提出了著名的“万物有灵论”,又名“泛灵论”(animism),即认为天下万物皆有灵魂或精神,并且会控制或影响其他自然现象。继“万物有灵论”之后,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提出“互渗律” 来解释原始先民的思维方式: “以物力说的观点看来,存在物和现象的出现,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发生,也是在一定的神秘性质的条件下由一个存在物或客体传给另一个的神秘作用的结果。它们取决于被原始人以最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想象的‘互渗’:如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用,等等。”他认为原始人的思维“首先是和主要是服从于‘互渗律’”。
在先民的眼中,客观上的死亡,并不妨碍主观上的永生。早期的先民认知生死,乃至认知万物的方式都和现代人大相径庭,他们以“万物有灵”的思维模式来认知世界,对客观的生命终止持否认、回避、解脱的态度,以抵消对外界不可控的恐惧,给自己认知范围以外的现象以合理化解释。对事物因果性关系的构建,在泛灵论的框架下,以“互渗”的方式进行,于是他们将死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某些主观因素,而非客观规律。由此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人可以“永生”,生命可以无限延长的原始逻辑,这一逻辑十分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发展。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也持同样的观点:“原始民族认为生命是不朽且可以无限延长的。死亡的观念只有在稍后才被勉强接受。”
先民对死的认知与后人截然不同,他们并不认为死亡是所有生命必须承受的一部分,也不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点,他们笃定:人是可以长生不死的,不死的生命以及使人实现不死的事物真实地存在着,试图将“死亡”这一现象直接理想化地从生命历程中抹去,对其进行直接或间接性的否定。《山海经》将这种对永生的笃定与当时人们日常熟知的事物和生活相联系,构建出这样的信念:世上一定有“不死国”“不死树”“不死民”存在;“延寿”,甚至是无限的寿命是人和其他自然物存在的常态;“死而复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实现,那只不过是灵魂在躯体中的去和来而已;“化生”是同一个灵魂通过不同的存在物转换生命体在现实中的存在形式。先民们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对实际生活所见所闻之事物进行加工创造,在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永生的具象显现,从物到人,从植物到动物,从日月星辰到山川河流,无一不蕴含这种原始的、永生的审美意象,这是当时环境下人特殊的认知逻辑所决定的。这种逻辑认为“死亡”是一种意外,是生命暂时的形态,甚至认为“死”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生”的不同形态,“永生”才是自然之道。
(二)初民对人自身价值的认同
黑格尔说:“古人在创作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氛围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是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为认识的对象。”初民时代的现实生活是时刻被死亡威胁着的,相对于现代人拥有的人身安全、物质保障、医疗技术等多方面的现实条件,原始先民在现实中面对死亡时显得更加渺小、无力,这就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内心世界来给予他们精神的支持。“永生”是先民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渴望,是其内心精神生活中最核心的价值观支点。《山海经·海外南经》开卷便云:
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
,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
。在天地六合之间,日月星辰运转、四时更替变化的无限时空中,“生之道”普通人无法理解,只有圣人能懂,“死”就更无从谈起。“生”与“死”,是生命的两端,先民们在对待“生”的问题上神秘感和崇敬感居多,对于“死”则带着深深的恐惧并试图逃避。《山海经》中呈现出的永生美学意象以坚决的态度否定着死亡的普遍必然性和必然性,同时对“永生”进行了强有力的肯定。人生活在自然当中,大自然提供了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感恩于自然的恩赐;另一方面,大自然始终凌驾于人类之上,变幻莫测、难于掌控,自然赋予万物生命的同时也主宰、限制着生命的种种可能性。人要在浩瀚乾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把握自己的命运,必要以一种形式来达到和生生不息、永无休止的宇宙平行共存的状态,以此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而不被自然的永恒和无垠所吞噬,即便这种状态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庄子·大宗师》就提出了通过“外天下”“外物”“外生”而达到“朝彻”“独见”“无古今”的境界,从而实现“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的永生状态。
“永生”意象除了受“原逻辑”生死观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这一审美取向是先民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同方式。尽管它们看似诡异、神秘、夸张,甚至怪诞,但却是蒙昧时期先民观念世界的真实反映,折射出先民强大的生命信念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人文意识的最初觉醒标志。“不死国”、“不死民”、“寿命无限”、“死而复生”、“死而化生”,这些决不是孩童般幼稚、天真的幻想,而是先民历经了大自然的种种严峻考验和人世间的万般磨难后,对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进行深刻反思而形成的意识观念凝聚。换言之,基于“永生”观念创造出的美学意象是原始思维与具体的现实形象相结合的文化产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理性思维对感性认知的加工结果,构成了前文明时代人类文化传播和存在的重要艺术形态。
(三)人超越时空限制的本能渴望
《山海经》所记叙的内容除了神秘美好外,也反映出先民生存环境的恶劣,各种灾难疾苦随处可见:
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
从首始。(《山海经·海内北经》)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颙,其鸣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
。(《山海经·南山经》)又西三百里,曰阳山,……其中多化蛇,其状如人面而豺身,……见则其邑大水
。(《山海经·中山经》)又北二百里,曰狱法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见则天下大风
。(《山海经·北山经》)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见则其邑有譌火
。(《山海经·西山经》)又南三百八十里,曰余峨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菟而鸟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见则螽蝗为败
。(《山海经·东山经》)
大兵
。(《山海经·西山经》)南次二山之首曰柜山,……有兽焉,其状如豚,有距……见则其县多土功
。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见则其县多放士
。(《山海经·南山经》)食人猛兽、天灾人祸,在《山海经》中不胜枚举,人的个体生命在当时的环境下何其脆弱?大自然一方面是人赖以生存的保障,另一方面也限制着人的种种自由,最根本、最核心的限制就是对“生”的限制。生命的有限性、人能力的有限性让人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恐惧。先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与“死”十分困扰,不明其理,处于一种模糊的混沌状态;另一方面在冥冥中知道死亡的必然性,以各种方式不断回避、对抗着死亡。对永生的种种描述都发生在远方的异人、异物身上,因为人们即需要将内心深处对永生的信念用物质世界熟知的形象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从而更加笃定;同时,又巧妙地将这些形象异化,并置于遥远的、未知的、现实中未曾抵达过的空间范围,这样一来,永生的信念才不会幻灭,它的存在才更加合理,从而对观念世界中的“永生”做出更有力的支持。简言之,这种永生的意象超越了自然对生命的限制,超越了世界的表象存在。
“超越”一词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带有高远、高超的、形而上的含义,如:“休动之人,志慕超越
。”“思致超越
学而不倦。”“神思超越
,下笔殊有气也。”中国古人常将“超越”与“思”、“志”这类主观活动连用,更加偏重于“超越”在精神范围内的实现。《山海经》中的诸多永生意象,归结来看都带有“精神超越”的意味,即这些永生的意象试图透过错综复杂的外在表象,达到事物的核心本质。这种意识形态并非完全与人的基本经验相悖,并非出于无知或无望,相反,它是人们希望挣脱经验世界中具象事物的沉重束缚,所积极寻求的一种雄心勃勃的形而上的超越。正如《庄子·大宗师》云:“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认为“真人”不眷恋“生”,也不惧怕“死”,只是潇洒地“来”和“去”而已。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对永生的追求于先民而言无比重要,如果残酷的现实无法被超越,那么天地再广阔也只是一具牢笼。并且这种超越的渴求不仅对原始先民十分重要,对进入文明时代、经过社会化洗礼的人来说,也必不可少,是人类藏于内心最真实、最本质的精神需求。宇宙的浩瀚无垠给人带来的渺小感和人征服自然过程中形成的强大自我认同感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矛盾,对抗这种矛盾需要不断地超越,这些超越的方式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进行突破。所以,在空间层次上,《山海经》在四海之内、山川纵横的范围之外还有“海外”,比辽阔的“海外”更遥远、更宽广的还有无垠的“大荒”,形成一种无限延伸、没有边界的无限空间感;在时间层次上,《山海经》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各类永生意象,使时间延长至无限,对时间的有限性加以最彻底的超越和突破。在超越有限生命的过程中,人敞开了生命全部的可能性,摆脱了现实无情的束缚,人的个体生命得以无限延展,达到了一种自由的审美存在。
超越时空限制的渴望不是上古时代所特有,但上古社会人对超越的渴望却往往借助具象来完成。形象思维在先民的思维方式构成中占据主要比例,其思考都是借助具体的物像来完成的,他们超越时空的方式往往就是构建富有意蕴的神话,且这类神话又大多是对事物形貌,即视觉可感知的内容进行描述来达成的。具体从《山海经》来看,这些神话情节性缺失、完整性不够,更多的是塑造出诸多带有神性的意象。这些“永生”的意象使时间和空间具备了无限性,这种无限性或体现为最大限度的突破延伸(“不死”和“延寿”),或体现为无尽的循环变化(“复生”和“化生”),从而构建出一个永生的审美意象体系。
结 语
《尸子》曰:“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中国古先哲很早就具备了以空间和时间的系统宏观角度来认知世界、反观人生的思维模式。《山海经》正是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产生并流传至今的一部重要古籍,其中构建的“永生”美学意象系统而丰富,展现了中华民族早期的独特审美形态。对时空有限性的超越、对永生的向往不单单是蒙昧时代先民审美心理需求的体现,更是古往今来人们不曾停止的现实追求和精神向往。“永生”意象不仅在《山海经》中十分重要,在中国原始时代的文化构建中也十分重要,并且始终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之中。《山海经》中以“不死”、“延寿”、“复生”和“化生”为模式构建的“永生”意象体系,在当代、在多学科领域以及世界文化范围内都具有独特的借鉴和发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