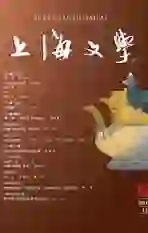批评的分歧抑或重叠的共识
2019-11-05马兵
马兵
当人们使用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时,往往会失察新世纪到目前已经与“新时期”有差不多的时长了。如果说,文学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遽然转型构成当代文学史的表述焦点之一,那么历经近二十年的新世纪文学似乎依然无法被纳入史的叙述秩序,而成为一种无限向未来延伸的正在进行的文學样态,这其中除了国人所谓隔代治史的积习外,大约也与阿甘本所感慨的作为同代人的那种悖论感有关,“我们的时代——即当下——不仅仅是最遥远的: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抵达我们”,换句话说,“就像准时赴一场必然会错过的约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讨论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差异与共识,当然也应该采用阿甘本式的那种站位,即“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裸体》第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共识也好,差异也好,其实既与文学演进嬗变的累积有关,也与作即刻式的悬置理解有关——近来,不少讨论这个话题的会议和论坛似乎在给外界塑造一个强烈的印象,即共识破裂是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现象,或至少是新世纪文学批评的重要表征。有批评家不无讥诮地说,如果说近来的文学批评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批评的共识已经破产了!有意味的是,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声音也不时地冒出,那就是当下实质性的文学争鸣屈指可数,而作家和批评家那种内嵌紧张对立、又彼此互援共生的关系也杳不可寻,批评的同质化几乎无处不在,差异被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貌似共识”取代。那么,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到底是一个差异大于共识,还是共识大于歧异,抑或二者不分轩轾呢?
一
让我们先回到新世纪文学的起点阶段。2001年3月,《上海文学》刊发了李静对李陀的访谈《漫说“纯文学”》,李陀在言谈间对笼罩于新时期之上、作为一个主能指而被人熟知的“纯文学”这一概念做了梳理与反思,其核心观点是,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语境中,坚持对“文学性”的标榜而给相对异质性的文学样态提供了充分保护的“纯文学”,因为“没有和90年代急遽变化的社会找到一种更适应的关系”,当其美学上的积极功能耗尽之后,便开始变成作家们拒绝干预生活、卸脱公共关怀的遁词。李陀尤其对1990年代流行的“个人化”和“私人化”写作进行了质疑,认为奉“纯文学”之名的个体性写作,势必将“与老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事情”排除在外,从而让写作成为不负载任何思想和政治热情的轻盈之物。李陀的这个访谈迅即引起热议,不单因为其提出的问题,还在于其本人在1980年代恰恰正是他力图反驳的“纯文学”概念的坚定护卫者。
今天重新来看李陀在新世纪初的发言,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其一是李陀此文引发的争议日后不断发酵,成为串联新世纪文学观念歧异与共识的一个重要样本,如2005年,《上海文学》接续这个话题,发起对“文学自主性”的讨论;同样是2005年,吴亮在网上对李陀观点提出抗议和质疑,李陀答复,形成一场网络之争;2018年,借长篇小说《无名指》的出版,李陀再次捍卫“思想,是时代写作的最高境界”的观点,并以“回到19世纪”对现代主义的文学观予以全面清理。其二,李陀的观点其实隐含着文学界自198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观念最大的分歧,甚至可以说是“元分歧”,因此,李陀的发声以及他与吴亮等的歧异,不但是作为过来人个体层面的碰撞,还意味着当下的文学实践与新时期不同的文学观念之间深切的互动关系,而且新世纪其他一些重要的文学论争事实上也是这一话题的重演。
李陀对文学的期待体现于他对文学因应时代的批判性、反抗性和思想性的看重,尤其是“今天的文学艺术怎么才能和今天的现实生活发生连结”——在他看来,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要考虑到“写作是对社会的一种承担”。如果对比李陀1980年代对先锋文学的鼓吹和对激进语言实践的赏识,确实让人觉得恍如隔世,但正像贺桂梅所观察的,“两个李陀”的巨大反差,“并不是一种投机主义的取巧,而是基于自我反思与自我否定而对新的时代和现实做出的批判性回应。因此,值得尊重的,正是他在痛苦的自我撕裂中顽强地探寻介入现实路径的自我批判勇气”(贺桂梅:《两个李陀:当代文学的自我批判与超越》,《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换言之,有一点可以说李陀是没有变的,即他一直秉有作为时代文学批评“立法者”的意识自觉。
吴亮对李陀的发声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首先他表明自己对文学没有期盼,也不应有期盼;而后又以私人写作为例,指出私人写作并非人们想当然的“逃避时代或自我幽闭”,对这种写作观念的排斥极有可能是“自诩公共性优先”的道德说辞,而且这一说辞失察了私人化写作携带着巨大的社会潜能,也失察了“非政治化”恰恰是政治化的重要表征。可见,吴亮没有否定文学应有的“社会批判性”,但文学的批判并不一定表现为李陀所理解的那种对时代的介入和强攻的勇气。当作家选择不去批判时,重要的不是声讨和质疑,而是考虑其何以作此选择的历史情境和情由。在吴亮看来,只有一种文学是可以被攻击的,那就是“缺乏才华”的文学,作为一个真正有同情心的文学批评者,要尊重文学的原生、偶然、充满变数和它之所以为文学的“特殊的精神迷惘”(吴亮:《吴亮致李陀》,见《雪崩何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对于他们曾并肩为之鼓吹的1980年代的“纯文学”,吴、李二人其实有着高度的共识,即他们都很珍视“纯文学”曾经起到的拒绝僵化的总体性和教条指令、恢复文学语言与形式自足的审美维度的历史功用,但是对于文学如何在新世纪实现其思想性,以及如何看待新世纪文学的写作资源上,二人又截然不同,约略可以看出新启蒙阵营分化后历史的不同投影:李陀对文学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吁求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政治标准”“艺术标准”的评价优先性的持续摆荡,而吴亮对各种文学写作观念的包容和理解也像是人文主义思潮大讨论中王蒙“躲避崇高”论调的回声。当然,作为卓有影响的批评家,二人绝非要依附于某一个庞大的批评诠释传统,不过二人共识之下的分歧确实指向了那个看似解决、实际悬而未决的话题,也即文学的社会功能性与审美自足性的二元论。而且更为复杂的状况是,即便批评者言明自己坚持二元论的某一立场,他其实也未放弃对另一元的考量,只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对某一元的诉求被集中释放,而仿佛成了对另一元的排他理解。就像“纯文学”在1980年代那样,“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反抗,但就理论来讲,它遮蔽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李陀在其时回应吴亮的最后一帖中,曾以韩少功的《暗示》为例,指出《暗示》是“对文学如何保持批判性所做的最重要的实验”,但是绝大多数的批评却将小说的意义集中于“文体意义”,所点出的也正是这么一个症结。
不妨再来看一个文学论争的例子。2004年围绕“底层写作”不断发酵的争鸣被视为是新世纪文学诸多话题中唯一真正进入社会公共舆论空间的一个,从《天涯》杂志率先开辟“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到后来《上海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等刊物陸续跟进,“底层写作”一时间成为最热门的文学话题,由其引发的文学评价的尺度以及相关的写作伦理的讨论到今天也还未完全终结。“底层写作”争鸣的聚焦,在我看来,主要是两点:其一,对“底层写作”这一现象的评价应该基于美学还是道德的立场;其二,对经历了“私人写作”风潮的作家而言,关注底层苦难是否是彰显其公共关怀的唯一方式。
批评家李云雷是“底层文学”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他曾如此概括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这个概括很全面,既强调了“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力,又着意提及不排斥艺术的“创新与探索”。然而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底层”这一内植道义立场的词汇事实上已经遮蔽了其审美的维度,而询唤着批评界和读者对其作道德批判式的解读。包括李云雷在内,不少批评家都认为底层写作是“摆脱纯文学的迷思”和反思“文学当下困境的一个契机”——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对“纯文学”的质疑。
当然,也不乏质疑底层写作的声音。2006年9月上海市作协组织了由王纪人、郜元宝、杨扬、王宏图等数位批评家参与的“社会正义与文学批评”座谈会,与会者对底层写作审美匮乏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驳,认为“底层”是一种被构想的文学形态,是狭隘陈旧的文学观念的借尸还魂,是新世纪里打着关怀旗号的媚俗文学。郜元宝在发言中如是说到:“文学的好坏,并不决定于作家写了什么;文学的好坏,还是要看作家在关心和描写人的感情和灵魂的真与深时所达到的程度。与其说一些学者‘发现了‘底层,不如说他们帮助我‘发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原来有多么的陈旧。”而王宏图的发言谈到:“在文学创作中是思想领先还是文学领先,对于文学而言,是一个已经被重复无数次的问题,我觉得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文学的华彩来自于恰到好处的呈现,而不是人为的拔高和紧跟形势。”
从这些援引可见,围绕底层写作的争执,几乎是吴亮和李陀论战的一个聚焦个案的翻版。李陀和李云雷对批判性的强调,吴亮和郜元宝所谈到的批评界“姿态前卫与观念滞后”的问题,这些确实是“已经被重复无数次的问题”,而它们之所以被重复,正来自于其自身的二元以及那悬而未决的因人而定的评判标准。因此,所谓新世纪文学批评共识破裂的说法如何炫目并不打紧,重要的是要明白这种破裂的前提与因由,以及被破裂所掩盖的某种共识。
二
十年前的十月,中国首次作为主宾国参与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作协组织了一个由一百多位知名作家组成的庞大访问团。也正是在这次书展活动上,老作家王蒙在发言时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这个说法在国内引发巨大的争议。半个月后,由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总部主办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其中的圆桌会议上,围绕如何评价当下的中国文学,陈晓明以阎连科、贾平凹、刘震云和莫言等为例,力挺新世纪中国文学,与参会的肖鹰以及因为“垃圾说”而陷入舆论热点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形成鲜明的观点对立。之后,以陈晓明、王蒙、吴义勤等为代表的“唱盛派”和以肖鹰、王彬彬、林贤治等为代表的“唱衰派”又各自撰文,并引起或同气相求或拍案而起的各路文字参与,《羊城晚报》还为此组织专版,陈晓明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林贤治则抛出了“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的说法,显现出巨大的分歧。这场争论的核心,其实质与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相关:其一,当代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文学能否经典化以及如何经典化;其二,评判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应着眼于不同于西方文学的异质性,并返回到中国本位的立场。与前述的“审美性”和“政治性”的纷争类似,新世纪各种争鸣性的文学话题也都与这两个问题相关,比如最显而易见的,每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文学大奖的评奖都会引发“唱盛”或“唱衰”的和声。
先来看第一个经典化的问题。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学界对经典的建构主义的讨论成果足够丰富,虽然依然有布鲁姆这样坚称经典一定显现着某种永恒的“正典”光辉的本质经典论者,更多的学者则试图在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既认同经典筛选中存在着通约性的价值参照,也反对将经典作固化凝滞的理解。但回到中国文学的语境中,事情又变得相对复杂起来,从事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学者一直试图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做一种仪式化的正名,甚至表现为一种“正典化”的焦虑,就像学界那个著名的关于学科鄙视链的调侃说法——治古典文学的瞧不起治现代文学的,而治现代文学的瞧不起治当代文学的——其背后恰恰体现的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已然经典化且历史化的文学秩序给予当代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文学的压力。陈晓明在做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表述之后不久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时,特意强调“这一说法是有时间范畴的,所说的是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并不是要与鲁迅、沈从文所在时代的中国文学高度相比较”,其言下之意维系的依旧是当代文学要弱于现代文学的等级评价,事实上与反对他的林贤治和顾彬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像林贤治的观点就是:“一百年来,鲁迅的《阿Q正传》仍然是中国小说的高峰,至今无人逾越;曹禺的《雷雨》《日出》仍是中国戏剧的最高峰,至今无人逾越;散文方面,有多少作家超越了周氏兄弟?就说诗歌,抗战时期的艾青,1940年代的穆旦,我们超越了?”这似乎印证了斯蒂文·托托西在《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中谈及经典时的观点,他认为经典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作家在批评系统中的地位。就此而言,“鲁郭茅巴老曹”所代表的现代文学的等级秩序虽然受到诸如“重排座次”之类的挑战,但对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的当代文学依然是巨大的笼罩和模范的参照。
也有批评家指出新世纪文学应自信地展开其典律确认的过程,因为经典的评价总是被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而且是同代人借此来实施文化权力、构建文化身份的重要途经。比如,吴义勤就认为,强调新世纪文学的经典化,不是一定要评多少个具体作品、作家,而是“要启动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种文学选本与文学评奖,虽然聚讼纷纭,但是正像赵家璧当年促成《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一样,其努力是要留下同代人对自己时代作品的见证,为后世积累经典品评的“初级样本”。这让我们想起佛克马说的:“确立经典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更令人兴奋的是观察不同社会文化下不同的经典之间的差别,并对这种差别给与解释。”
“唱盛”派与“唱衰”派分歧的真正意义或正在于此:“唱盛”派认为新世纪文学所承纳的时代关切和文化现实有着不容替代的意义,对文学经典进行周期性地建构理所应当;“唱衰”派则以鲁迅、沈从文等的文学高标予以质疑,即便莫言凭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了经典化最大的象征资本,也无法平息他们的质疑。对于当代文学中的历史意识和审美自觉如何内化为文本形式,两派给出的侧重不同的评判,其实正显现了作为一种物理时间上后发的文学样态必然遭受的现代性困境,即一些经典论者谈及的“彼时”对“此时”先验的领先,从这个层面上说,新世纪文学中一些代表性的写作现象,如网络文学的正名、青年写作价值的确认、重建写作的“历史感”等也不过是这一问题的缩影。
第二个是本土立场的问题。顾彬的“垃圾”说尽管有标题党之嫌,但他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说自己对当下中国文学一些现象的不满是因为他坚持“世界文学”的标准。陈晓明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圆桌会议上则针对性地表示:“在世界现代性的文化谱系中,中国的文化/审美现代性,是要重新或者单独给予定位的,这个定位谁来完成,只有中国学者自己来完成,我们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是对历史不负责。”又说:“我强调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式,不是要抛开西方现有理论知识及其美学标准另搞一套,而是在现有的我们吸收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他在举例证明新世纪文学的经典性时,也特别突出了“汉语小说”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进入乡土中国本真文化与人性深处”等的能力。肖鹰不同意陈晓明的发言,他认为:“‘對中国文学六十年的定位只有中国自己的学者才能完成,恰恰是违背了我们达成的共识,我觉得对中国文学六十年的定位应该在中西学者和中西文学的对话中才能完成。”(《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文学圆桌会纪要》,《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
批评界对于陈晓明的质疑还在于,作为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陈晓明一直以善于运用西方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的理论资源著称,他对中国立场的标举似在否定自己此前的批评站位。陈晓明对此的回应是,中国当代文学有其经验的特殊性,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语境下,如果忽视这种特殊性,就“无法给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准则”,中国当下文学也就永远是“欠发达”的。张清华也撰文指出:“用‘中国故事承载的‘中国经验的讲述,是‘中国作家对于世界的独一无二的讲述。”与之相呼应,从2014年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张江接连发文,认为理论批评界多年的“强制阐释”导致了理论的滥用和误用,“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反序的认识路径”造成大量对文本的削足适履式的解读,因此,批评家应“辨识历史,把握实证,寻求共识,为当代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改变过去曾经有过的盲目依从和追随,推动中国自己的理论健康壮大”。从陈晓明到张江,对坚持“中国立场”的共识,既是对二十年前中国文学资源取径中西的问题与批评界“失语”话题讨论的接续,也显现了新时代民族复兴背景下本土理论批评的自觉,显现出在中国故事和中国叙事日益成为重要文学构成的当下批评家构建新的批评话语的迫切,而且在新世纪叙事文学最有分量的那些作品中,本土的历史风物、传统的叙事智慧、当下中国人的经验在在可见,这也理所当然地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
不过,当过于强调民族本位的理论建设和以本质主义的方式看待自身的特殊经验时,也可能会让中国文学面临“成为西方知识体制内组成部分的另类复制”,从而再次“东方化”的风险,只有“把自身与他人都视为多性,共同作为历史的主体,才能开展出一个不被西方垄断以及开放与共享的普遍性场域”(于治中:《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读书》2007年第4期)。就像法国的批评家帕斯卡尔·卡萨瓦诺在她著名的《文学世界共和国》中谈到的,远离强势文化中心的作家并不必然是外在于“世界文学”的,文学有其自然的评判、接受和传播逻辑,正是这种文学逻辑可以让文学拥有不同于政治标记的领土和疆界——这也应该是文学批评者应有的一种共识吧。
三
在今天翻看任何一本文学刊物都会发现,“90后”作家的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更年轻的新世纪一代也正跃跃欲试。不知不觉间,以“80后”为代表的所谓“青春写作”已经成为一个有些蒙尘的历史概念,不过对新世纪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忘记2006年白烨与韩寒那场略显夸张的网络骂战。回头来看这场口水之争,有两点是当事双方所始料未及的:其一,韩寒、郭敬明等偶像式的写作路径并未成为后续青年写作的主流,大量后来成长为中坚的青年写作者还是与前辈一样,基本依靠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文学批评、作协组织构成的文学场域培育生长,文坛对于他们并非“祭坛”;其二,被韩寒所不屑的代际概念依然被广为使用,而且成为区分群体最方便也最策略化的一种分类标准,何况白、韩之争本身即隐含着一种代际的隔膜,尽管白烨本人是资深的批评家中较早关注到“80后”创作现象的一员,但他与“80后”写作现象的对话关系鲜明呈现出一位前辈对后辈的瞩望和告诫姿态,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厕身于“80后”的写作立场。
2012年,《当代作家评论》刊出青年批评家金理对导师陈思和的访谈《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其中陈思和谈到:“因为审美方式和文学取向都不同,即使是很优秀的批评家,他也没有办法去阐释一个在方式和审美取向上不相同的对象。”金理则表示:“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应该关心同样年轻的新秀作家,……批评的审美标准到了一个该更新的时候了;再沿用‘中年作家的规范可能会对新出现的审美精神、表达时代生活的新方式和感受产生遮蔽。”这个促成以金理为代表的“80后”批评家崛起的访谈当然与白、韩的骂战无关,但不妨看作是对六年前事件的一个针对性的回应,由此又可引申出一个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当代文学的分歧、共识与代际的关系。
事实上,就当代文学而言,批评家的代际命名其实早于作家的代际划分。“50后”的批评家在回顾1980年代创作与批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黄金岁月时,经常会提到两个会议:1984年12月的杭州会议和1986年5月的海南会议。前者作为“寻根文学”的策源已被写入文学史,后者即由广东社科院文学所、暨南大学中文系、海南大学中文系和当时的海南行政区文联等联合发起的“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会议聚集了吴亮、许子东、陈思和、王晓明、李洁非、张凌、南帆、蔡翔、周政保、林建法等一批被称为“第五代批评家”的其时批评界的新锐。会议前后,谢昌秉、陈骏涛分别发表了《第五代批评家》《翱翔吧,“第五代批评家”!》等文,充分肯定了这代批评家在“重写文学史”、“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方法多样化”、“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批评中的双向同构”等话题上敏锐的问题意识。当然,这个有点借鉴导演代际区分的“第五代批评家”的概念并没有流行下来,也没有后来代际的承续,但是它在彼时被郑重提出还是体现出了命名者的苦心——将新文学发轫阶段的“五四”一辈作为第一代,“第五代”自然便是一个“被纳入到新文学批评谱系中的概念,也隐含着一种预设的文学史立场”,鲜明体现了其时创作与批评的同频共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以“60后”为主的批评家与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与新生代小说家的互动,进入新世纪后,“60后”、“70后”的批评家与“70后”写作者的互动,以及近些年成长起来的“80后”批评家与他们同龄人和更年轻一代的写作者的互动关系。
批评界代际逻辑的凸显,既带来不同代际关于文学理解的代沟,呈现——有時甚至是人为制造了文学观的分化和断裂,也在代际内部强化并塑造出一种“模糊的”共识。代际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审美经验的共同体。齐格蒙特·鲍曼在《共同体》一书中谈到社会系统中的后来者需要一个全新的共同体来界定自己,以“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但是鲍曼也提醒,要注意共同体的两难处境,即“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的保护,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所谓的“失去自由”在代际批评分化的框架里,其表现就是批评者的个性让位于一种均质的整体理解,而这种批评的反馈到了被评论的同代作家那里,又会带来更强大的形塑力,进一步巩固代际间的审美区隔,造成同质化写作现象的加剧。
若要避免这种后果的出现,需要批评界达成两点共识:其一,应在代际内部坚持“和而不同”的批评立场,置身于一个美学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放弃个体审美建构的能力,就像鲍曼指出的,一个能够给人们带来支援和信任的共同体,它的成员必然是具有独立个性的、千差万别的人,而不是“像我一样的其他人”;其二,必须有跨代际的对话、交流、碰撞与分享,每一个批评共同体既要有批评范式转换的自省,也要具备跨代际的知识迁移能力,以及对于非同代人批评对象的祛除“成见”的初心,以守卫最基本的批评伦理。近年来,活跃的“70后”和“80后”批评家在坚持为同代人发声的同时,表现出了各各不同的批评个性以及不同师承带来的知识结构和谱系的差异,以致争论频出,尤其是涉及具体文本解读时经常会有巨大的歧异,这看似分歧的加剧,其实质反而与前述的共识相关。
另外,《做同代人的批评家》的访谈中,陈思和在追溯1980年代的批评轨迹时着意提到了吴亮的《论圈子文学和圈子批评家》。吴亮的这篇文章敏锐洞察到不同场域批评的文学观念差异的问题,后来被反复探讨的北京中心与外省写作、庙堂与民间、学院与作协系统批评的差异都可以这篇文章作为一个起点。时至今日,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与作协体制内批评的三分天下,自然也带来批评视角与方法的差异,虽然从事媒体批评与作协体制批评的批评家大多也经受了完整的学院训练,但站位与介入现场的情由还是决定了三者各有侧重。当然,无论何种立场,就像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的,作为一个批评家,“必须在更宽阔的背景下来观察自己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检视自己的生活”,这也应成为批评的共识。
综上言之,笔者以为,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界围绕各种话题和作品的争论与分歧,有时体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基于某种共识的“互斥”,会促使我们想起罗尔斯提出的著名的“重叠共识”理论——文学批评当然无法与政治正义层面的“重叠共识”相提并论,但不妨从中取得一些借鉴。在罗尔斯看来,“重叠共识”是当今社会人们在多元理解上达成一致、协调彼此行动、稳固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的观念保障,它包含几个不同层次:“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以合理的态度彼此相待;基于不同价值的人们从各自角度出发或通过采纳彼此视角而支持共同的规范;以及目前持有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们,努力寻求未来的彼此理解乃至‘视域融合。”(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因此,在我看来,新世纪最有意义的文学论争并非那些逞口舌之快甚至有杀伐之气的意气之争,也非以一己审美障目而对其他文学样态视若无物的傲慢批评。要而言之,清明理性的文学理解,包容和规范地对待歧异,以及致力于新世纪汉语文学内在品质的提升应该是批评界“重叠共识”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