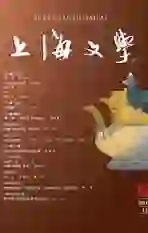半醉半醒度余生
2019-11-05刘湘如
刘湘如
又是清明时节,香港、台湾和上海的亲人们,齐聚苏州东山陵园,祭拜一位老人。此刻,我的心头总是牵扯起绵绵的思绪。那个傍晚,那个永远的记忆中的时刻,仿佛就在眼前。我们在上海只有四十多平方米的蜗居,他和他的小床只能蜷缩在昏暗的一角,老人独自靠在他窄小的床边,他木讷地去床头找他的金丝边眼镜,伸出的手几次缩了回来,他想上卫生间,我扶着他的身体时有一种特别沉重的感觉,他已经无法挪动脚步了,其实,这一切细节后来都被认为是某些征兆……
老人就在那天晚上去了医院,不久就走了。此刻我只能看到那个晚上我的一段微博截屏。上面写着:老岳父一生信奉基督,虔善正直处世,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我给他写的挽联是:历百年风雨虔诚为怀晋见耶稣别人世,经两纪尘寰耿直待人侍奉上帝入天堂。横批是:归天神前安乐永恒。
人生一切总是在失去之后感到愧悔和珍贵,被我一直亲切地喊为“老爸”的岳父,虽以高寿去见一生信奉的上帝,但他留给我的记忆却在时间推移中越加清晰,斑斑往事如茧丝般缠绕在我的心头。他临走前的一段时间常要我为他找黄仲则的诗词,“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用是书生……”他低声咏哦。我知道他在怀念旧事和先走的岳母了。老人一生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早年毕业于外国人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一副潇洒的旧上海滩上流人物派头,他与毕业于震旦大学的岳母大人结合时,照片曾登在上海的《申报》上,报界名人赵超构、香港船王包玉刚、书画名家费新我等人,都和他常有来往。一次我见到费新我为他特制的私人印章,工整而精细。我说这很难得,他却拿出自己刚写的一首诗让我看:“时违渐觉襟怀尽,老旧惟怜故旧情。南飞豪情今犹在,半醉半醒度余生。”我忽而感到他们那一代人,那些无法复制的往事,那些磕磕碰碰,那些过往的云烟,像斑斓飞絮一样充塞着今天的喧嚣,让我的思想穿越到历史的深处。
约莫七八十年之前,在大上海最繁华的外滩码头地段,矗立着一座巍峨的大厦,直到今天这座大厦仍然以绅士的风度屹立在外滩的一角,当年,骄傲地坐镇这座大厦的,就是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
那时候,我的岳父杨翼民先生就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岳父一生秉性善良忠厚,为人正派无私,尽管精通业务,还兼管着公司财务,却从不沾钱,一切大事都让董事长操控,公司职员甚至笑他是个老实的挂牌经理。可世事颠倒真情在,没想到这些却在后来帮了他的忙,上海解放后董事长卷款外逃,党和政府经过对他的多次审查,终于洗出他的清白,最后给他定了个资方代理人,让他依然上班、工作、生活。为了感谢政府,他还主动上交在旧公司拥有的一套私人洋房,受到政府的表彰。他继续在岗位上分管业务工作……
老人一生本该有着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他常常骄傲地对人说,他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他的四个女儿。他在孩子面前俨然是天下最好的慈父。记得当年我娶了他的三女儿时,他曾对我说,我的最好的女儿给你娶走了,你一定要好好待她。其实他的每个女儿各自优秀,我何尝不知道老人的心思。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生了一场大病,老爸从香港到合肥来看我,他扶着我走过合肥的长江路,我说我们乘车吧,他说你别怕累,人就是慢慢走过来的。我尊敬地看著老爸,他这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我产生了许多的联想。那天回来后,老爸拿出他在香港的一首诗:“玉树临风一君子,世途汹涌滑浪人。银河已裂心未裂,击节声传万卷书。玉郎挥袖飞云彩,据案抒怀不老情……”他的诗尚未念完,我便感叹说:“老爸!圣贤书立风骨,胸襟广浩瀚,视野阔天边。老爸奇人也!”他听了我的赞叹笑得很开心,像个孩子一般,我从他的笑容里仿佛读懂了人生的一切!
1993年,当我在香港礼芳街葵福大厦十六层楼上,小心翼翼地叩开那扇沉重的钢门时,我的眼前倏然一亮:啊,岳父还是那个满目笑容和蔼可亲的岳父!那时候老人已经去香港定居,依然是那个精神矍铄声音宏亮的老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人饱经沧桑的程度可以想见。那时他已经是七十八岁高龄,但在他的身上,几乎找不见一点点历史颓废的影子。他甚至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我这一生走遍世界,过过‘天堂一样的生活,也受过‘监狱一般的煎熬,这几年刚过上……”他的目光忽然昏暗,似有老泪落下。我知道他最悲痛的事不是他的坎坷,而是不久前才失去相伴半世纪的老伴——我的岳母。
岳母的逝世几乎使岳父的世界倾刻崩溃,自此,他天天找黄仲则的诗词。那个善写哀怨凄楚情思咏叹的诗人陪伴他度过无数个寂寞的晨昏。但他很快就挺过来了。在香港,他像许多香港老人那样一个人生活,一个人上街买菜,乘电梯回到高高的楼屋上,烧饭、扫地、抹桌,忙得井井有条,万般繁华的世界几乎与他绝缘,他需要的只是自我安慰。那时香港政府对老人还算爱护,他能每月领到固定的养老金,还能领到几百元的水果费。他和所有老人一样进公园免费,乘地铁半价,到银行不要排队,等等,老人就有一种“人间尚存暖意”的感觉了。在我们住处附近的马会诊所,我亲眼见到一些颇富人情味的镜头:医院用专车去把几位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接来看病,看完后又派专车把他们送回去,那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残疾老人。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世的真情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地域和制度……岳父在香港过着一种清淡如水的生活,他极少交际,也极少赴宴,大部分时间守着那套清冷的老屋,我常想似这般还不如回大陆度日呢!老人说他的两个女儿还在这里,他不能离开她们,其实岳父的心结还是在逝世于香港的岳母身上。他是个寡言的人,有时儿女们好不容易聚到一起谈谈,他总是坐那里听着,有时虽也插上些话,总是平淡的家常,设若有某个儿女与他辩论点什么,他就一笑了之,不置可否了。尽管在港的女儿女婿们对他百般孝顺,人人争着接他同住,但他还是执拗地守着自己的“家”,叨叨地念着黄仲则的“半醉半醒度余生”……
那年八月,我们全家自香港乘船回上海,临行时岳父送我们到他的门口,我因头天晚上睡眠不实,提着大包走路时有些踉跄,岳父像年轻人那样过来搀着我的胳膊说:“当心点!出门千万叫个的士,不要省钱乘地铁啦!千万千万……”只是些平常话,但我听起来语重心长。他见我们安然坐上的士,才慢慢转回身,走进电梯……一忽儿工夫,从的士上回转头来,我见到葵福大厦那高耸的楼层,十六层上那盏灯又亮了……
岳父有着渊博的知识与非凡的经历,他因一口流利的外语一生与国际经营相连,但临老时却茕茕孑立身无分文,命运之神跟他开了很多玩笑,历史转折使他低沉过又让他高昂地站立了起来,他个人的生命之舟在历史大潮中颠簸了近百年,少年从老家宁波闯荡上海,再从上海到了香港,最后叶落归根于上海,他为自己画了个巨大的圆圈。他的经历就是历史的注脚和记录。“老了,晚了,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他晚年时常对我说,“人生不要把什么看得太重,世间其实很简单……”他这样说着,体验他的自我安慰和安逸的老人生活。
时间若是可以微微停留,我多么想留住那些与老爸相处的日日月月,那些日常的浮华与沧桑。我想看着老爸以悠然自信自强和尊严的姿态,绅士般漫步在香港九龙大街,或者上海南京路,或者合肥长江路,那种无可替代的优雅和高贵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