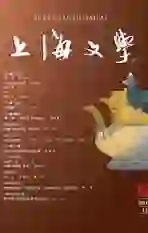他不会再到我们这里来
2019-11-05陈晓兰
陈晓兰
2008年4月24日,贾植芳先生生命垂危,得知这一消息,我立刻赶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看了他最后一眼:他弱小的身躯静静地躺在床上,氧气罩几乎遮盖了他的整个脸庞,床头柜上的仪器屏幕显示着心脏跳动的曲线。一颗强大的心脏已经衰竭,那根起伏微弱的波浪线很快会变成一条直线,接着便迅速消失,闪烁的黑屏,宣告死亡,任你们活着的人高声呼喊、哭泣,他的灵魂已经离开此岸。据说,在灵魂离开肉身的霎时间,处于阴阳交界中的灵魂隐隐约约地会听见人间尘世的呼喊,并同时看见一片天光,他已不再有痛感,他已感觉不到肉身的存在。我那时想到了天使。有天使会待在病房的角落吗?如果在的话,他会超然地看着医生徒劳地奔忙、亲人痛苦地呼喊吗?他会对他说“我是来带你回家的”吗?我下意识地看看病房的角落,我想,天使在的话,会看见这些无助的人,而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抬头看看输液架上挂着的药瓶,液体通过输液管静静地流向他的血管。那输液架让我感到它就像一个十字架。它让我想起了十字架,想起了十字架上的受难者,想起了这个即将离开我们的顽强的老人说过的话:“我曾经理智地、自觉地为了某种人生信仰而去选择巨大的苦难”,“知识分子就像耶稣一样,总是要一代一代背上十字架的。”
医生还在尽最后的义务,亲友们在等待奇迹的发生。我走出病房,大脑一片空白,泪水像溪流一样流个不断。我不知道那泪水从何而来,我无法将它关闭。我分不清是在为自己、为大家,还是在为那个受尽磨难的人,为他所遭受的一切磨难而流泪。耳边回响着他曾经说过的话:一个上过战场、坐过监牢的人,是不惧怕死亡甚至随时准备迎接死亡的。战场和监牢,使人认识一切。而认识了一切,就获得了自由。现在,他真的自由了。
师友们静候在病房外。
夜幕降临了。医生宣告了最后的时刻。虽然大家已经有所准备,但一时还是反应不过来,紧接着便是一片慌乱,慌乱之后则是一片空白。
晚上,在医院太平间的一间小屋里,陈思和老师主持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之后,一个陌生人将那个瘦小的身躯放进旁边冷冻箱的一个抽屉里,迅速关上,将扑面而来的冷气锁住。我的心一阵紧缩。一个人的生命就真的完结了。桂芙大姐心痛地呻吟着。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她的呻吟。她真的失去她的姑父了。我们再也看不见他笑,听不见他讲故事了。复旦校园里再也不会有他拄着拐杖散步的身影。复旦九舍再也不会那么热闹了。过去几十年来,因贾先生而去复旦九舍的人,没有再去的理由了。
贾先生去世后,在一次媒体采访中,陈思和老师说:随着贾植芳先生和“七月派”作家们的先后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如果这个“时代”,指的是先生们所经历的那个内忧外患、充满苦难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给他们留下的磨难和痛苦的记忆,真希望这个时代真的结束,永远结束。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人生选择以及他们为之所付出的沉重、惨烈的代价,无疑包含着悲剧的崇高,令人敬仰,但同时也令人恐惧。但愿历史不再重演,以免不能经受试炼和考验的人经受试炼和考验。突然明白,“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意味: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一些人,失去了这些曾经为了美好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信仰理智地、自觉地去选择巨大苦难的人们。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脊梁、社会的良心,他们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是,现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他们不会再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却要到他们那里去。
1990年,贾植芳先生在《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一文中这样总结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在那个战乱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我没有做一个坐在书斋里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学者,过比较平静、安稳的生活,而且我也不屑于在祖国烽火连天中做这样的学者,更没有做发战争财的商人,虽然我是商人家庭出身,但我又没有找一个安定的职业,只为个人的生计操劳,而是把有机会到手的工作当作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脱离历史的苦难,走向新生应尽的历史责任来从事。我这种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我这种不合时俗的生活态度,使我在动荡的时代里,东奔西走,在生活中遭到打击,遇到挫折,使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坎坷和灾难。①
在1941年的《沉闷期的断想》中他如此说:
书这东西是可以增进世界的发育,但也可以消没著书人的生命。……一个年轻轻的有血有骨头的人就躲进书斋,以著书立说为事,总是可怕的事。而且是一种无聊。安德列夫说,“垂死的人想活在著作上,是太可悲的事”。这位被谥为“一个受伤的知识阶级”的话,确实是可以思议的。②
他更看重的是“文字以外的力量”:
一生能为人类写一卷书,是高尚的德行,但这写必建筑在坚固正直的人生基础上。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文字还不够是一种真正的手段,用来报复自己所切恨与憎恶的。③
对他而言,人生永远是第一义的,文学则是第二义的。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蕴含丰富的书。他不愿做一个安坐于书斋写文章的书生,即使写作,也要做一个来去自由的作家,而这写作也必然要有益于社会人生。他的文学创作,对于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他的翻译工作,他复出后对于学科建设、新生代青年人的培养,都是他人生信条的实践。他自称是“社会中人”,被称为“书斋外的学者”。
作为“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现代知识分子,贾植芳从“五四新文化”中汲取了人生而平等、自由、尊严的精神营养,同时,其思想和文化性格的形成又深受“红色”的1930年代的深刻影响。如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许多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憎恶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自觉地担负起社会责任,献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这些也成为他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和理想灯塔,召唤他走出荆棘之地。他的充满苦难坎坷的一生,证明了坚守这种人生准则和理想的艰难与危險。
1935年,賈植芳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抗议国民党政权与日方的妥协而被北平警察局逮捕入狱,由他的伯父疏通关系保释出狱后于1936年6月逃亡日本,如他自己所说,开始了流亡加留学的生涯。他不听经商的伯父希望他学医和学商的规劝,而是选择社会科,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并通过覃子豪、李春潮参加留日中国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开始了与“左翼”文学运动的联系。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便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抗战,于1938年随留日学生训练班到汉口,他被分配到山西中条山前线做日文翻译,授上尉军衔,同时受胡风委托为在抗日根据地具有很高威信的《七月》杂志写战地通讯,报道抗日前线士兵与群众的抗日消息。1939年,他拒绝到国民党的干训团接受提拔前的训练,离开了军队,辗转到了西安,回到大部分沦陷的山西探亲,旋即又离开家乡,前往重庆,因路费被偷,返回宜川县秋林镇,此地当时是山西省府和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阎锡山想留他在自己的部队做教官,给中将军衔,月饷一百八十大洋,这促使他迅速离开此地,因为他先前正是为了不做官才离开国民党军队的。他穿越宜川到洛川的黄土高原,经西安到重庆,由同学介绍,到国民党的军报《扫荡报》当编辑,但很快他又不得不离开重庆,再次踏上了漂泊者的路。
他在1940年1月27日和3月7日致胡风的信可以解释他离开重庆的原因:
重庆的气候恶劣、空气坏,过得很窒气,在垃圾堆一样的工作上,活得寡而无味。④
我已决心脱离报社,来重庆五月,呼着极不自由的空气。⑤
1940年4月,他离开重庆到了西安,他在信中写到:
人的灵魂由愤怒变得粗暴,觉得生活的本质,就真如尼采所云,分别善恶,而用力量去征服恶。⑥
……找得一个机会的职业,又像爬在云泥里。⑦
他决定再次回到前线,于是又一次离开西安,一路北上到宜川,因为这里更靠近前线,他第二次来到秋林镇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但是很快就因为赤色嫌疑而辞职,他再次回到西安。“皖南事变”后,文化人有的做了国民党政权的文化帮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则抗议国民党的暴行而离开重庆,胡风辗转香港到桂林,贾植芳在西安与小商贩混在一起做小买卖糊口。1943年,他在西安街头看到工兵部队招考日文翻译,便通过应聘到驻扎在陕西省朝邑县的国民党工兵第三团任职,不久被怀疑为共产党,面临被活埋的判决,于是再次踏上逃亡的路途。1944年,他因参加抗日策反活动,被徐州日伪警察特高科逮捕关押三个月,日本投降后被释放。1946年他辗转到上海,1947年9月,因共产党的地下报纸《学生新报》之约撰写了《给战斗者》一文,又应复旦学生的小报《文学窗》之约发表《暴徒万岁》,被国民党特务以煽动学潮罪抓捕,关押半年多,直到1948年春被保释出狱。
《人的证据》记录了这次被捕和受审的经历,揭露国民党中统局特务们(有些还是臭名昭著、令人闻风丧胆的76号的小角色)对于共党嫌疑犯的身体和精神虐待,亲眼见证了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所遭受的酷刑,这些不是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景象,而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和他的狱友们的身上的事实,这让他对于国民党政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可惊的愚昧无知,用脚后跟思想,穷凶极恶以敲诈发财,在别人的痛苦中找欢乐以外,却并没有任何什么信心和它自己那一套的政治认识,所以没有什么政治责任心,全是混饭吃的东西,譬如这中统局,是国民党的心脏地带,但是你看看他们的行事,不就是说明这国民党不仅没有一个政党的作风,简直不能说是一个政党,没有一般政党的资格,只是一伙图财害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匪帮!⑧
贾植芳的人生选择和他的遭遇,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憎恶、抵抗国民党政权而倾向“左翼”、认同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人生选择做了生动的解释。就贾植芳而言,他完全可以像他的大哥贾芝那样循规蹈矩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或者继承伯父的产业成为一个买办,或者留在日本以逃避中国的灾难,或者利用自己的留日学生身份和日语技能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混得一官半职……他有很多安全的、合乎常情的选择,但是,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关头,面对强大的政治高压,他都做了完全相反的选择,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改造社会的行动中去。他为这种违背世俗而合乎理性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0年代初,当他论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时说:“我出身地主,我伯父是买办。我要是不出来读书,我就是黄世仁。后来我做的事,也不非要说是背叛了原来的阶级,也不是什么赎罪,只是想,活着就是要像个人的样。”⑨原来,活得像个人的样,是极为不易且须付出代价的。
1950年代初,当胡风被公开批判,接着便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首魁”时,贾植芳本可以利用他的哥哥贾芝的关系躲过劫难,但是,他却在那个濒临深渊的时刻为这个“国家的敌人”辩护。被捕当天,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和上海高教局领导询问他“胡风搞的什么阴谋”,他大为光火地说:“胡风按正常组织手续向中央提意见,又不是在马路上散传单,怎么是阴谋?”当领导问他与胡风是何关系时,他更为光火:“我们是写文章的朋友,我们旧社会里患过难,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个关系。”⑩他一直认为: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说真话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不卖友求荣,不过是最基本的做人道理,这还需要选择吗?然而,他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丧失自由二十五年,十一年的监禁和十四年的监外劳教。他入狱时四十岁,解除劳教时六十五岁。
1981年,时隔二十六年后,贾植芳和任敏去探望住在上海龙华精神病院的胡风(他已患严重的心因性精神分裂症)。四个老人劫后重逢。胡风不停地流泪,梅志不停地擦拭泪水……
直到我们离去时,他呆呆地望着门口我们的身影,兀自流泪不止。我们也不能自持了,我们夫妇泪流满面地离开了这个变相的监狱——精神病院。是的,时隔二十六年之后,我们终于又相见了,我们的泪水里,有着欢欣的激动,而在他的这种激越的感情里,还包含着对因他的名字而遭株连的许许多多朋友和青年的歉愧之情。但是人们是不会怪罪他的,因为这是历史的恶作剧,咎不在他。
这之后,我每次因事进京,或路过北京,总要抽空去看望他。
1990年10月,贾植芳应邀赴日本,在他留学的母校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做了“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的演讲:
我和胡风先生通过这场灾难的考验和磨难,反而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理解和友情。胡风先生逝世五年了,但我们夫妇和他的遗孀梅志夫人和孩子们,仍一如既往地亲切地来往着。经过生死大难的苦难考验的友谊,就是永恒的友谊,真正的友谊。
据梅志回忆,1990年代,北京上海等城市人们看望老人有时会送燕窝,“正宗雪窝,天然补品”,是名贵而稀罕的礼品,价格不菲,大约百元以上,即使获得这样的补品,也舍不得自己享用而是再转送其他需要蛋白质和维生素的老人。1996年贾植芳赴京开作代会,亲自带来一大盒燕窝送给梅志。梅志检查自己的存货,发现好几盒燕窝都是他送的。
贾植芳与胡风的患难友谊,他对于胡风的忠诚,不仅仅是对于传统伦理道德诸如不卖友求荣、对朋友有情有义的坚守,更重要的是对于胡风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的操守和风骨的支持。从贾先生与我们的交谈和他自己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对于胡风的高度评价:
我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利己主义、虚伪、圆滑等庸俗的市侩习气的东西,或盛气凌人、自认为高人一等的那些官僚化文化人的恶劣行为。他是个讲信义、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继承了鲁迅的精神,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他是对人民革命的文化事业忠诚无畏的革命作家。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个正直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同时又是青年人赤诚的朋友。他对新文艺运动的贡献与对文学青年的扶植、关怀、帮助,于我个人的有限的经历,都是一个证明者。
在贾先生的心目中,胡风是一个敢于说真话,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主义激情的知识分子。他在险恶的政治文化环境里坚持自己的工作岗位,编杂志,以作品思想和艺术质量为取稿标准,而不以作者的名位为准,他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作家和詩人。因此,贾先生对于胡风无怨无悔的友谊,实际上是他对于知识分子理想和人格的忠诚与捍卫。
早在1949年,贾先生蛰居青岛时,偶然在街头发现了英国学者爱德华·奥布莱恩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一书,他花了一个月的工夫翻译这部著作,他在译者序言《旧时代的回忆与告别》中如此评价尼采:
尼采他起码要我们没有虚伪地做一个真人,坚持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他的生涯和悲剧却值得作为我们知识人的一个警惕性的训诫和启示。我们要深刻地认识所谓“孤独之伟大”(易卜生语)的危害意义,那是新时代知识人的最大精神危机或堕落。……这本书使我沉思再沉思——知识人的命运问题。在“不是跌倒,就是站起来”的新的时代中,知识人精神上没有战斗和战斗不够的结果,在不是堕落(无耻和反动)就是疯狂(超越现实的孤傲和自满)的历史旋律中,这真是一种空前的战栗和激动。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孤独和孤傲不是伟大而是疯狂,这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根本之所在。胡风以及贾植芳,的确不是孤独者,共同的政治使命和价值观把他们连接成一个社会群体和精神共同体,险恶的环境和自觉担负的政治使命使他们自觉追求这种知识人的社会联合和精神归属,正是这种联合使得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极为显著。
1994年,贾先生在一次答《上海社会科学报》记者的采访时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归与超越: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坚持自己的理想不容易,在现实面前碰壁,就要另找出路。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就是1920年代北大新潮社的那帮人,搞学生运动出身,后来大多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这些人镇压“一二·九”运动。一代闹一代,自我否定,走向自己的反面。为什么?因为他只有走向自己的反面,才能得到功名富贵,如果要照直走下去,死路一条。因此,知识分子的“回归”就成了一种非常有意味的现象:一些人最初是反封建,最后却走到了反面。年轻时是洋务派,老了是“义和团”,“扶清灭洋”。比如郭沫若,早先写《女神》,讲个人主义,反叛得不得了,最后却转回来,拥护一些原来他自己批判过的东西。
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悲剧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的坎坷的一生本身就是这种民族性和悲剧性的体现,而他对于历史的回忆也从未离开过这个命题。
1941年他在《沉闷时期的断想》中说:“一个人不仅要温习过去生命里的欢乐,更应该温习过去的痛苦,后者对于‘人的生长上,极为重要。……能和世界一齐痛苦的人,是最伟大的人。这痛苦包涵了创造和斗争意义。”从贾先生晚年所写的一系列回忆性文字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贾先生所坚守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这些回忆大多是对于他的老友们的人生经历和精神品格的描绘,如早年负笈欧陆、才华横溢的范希衡,在长期不堪其苦的逆境中苦心劳志,尽十年之功翻译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赞扬范先生忠于所业,死而后已,“极左”的阴霾无以窒息其精神的高洁和灵魂的高贵。还有那个气呼呼地跑到贾先生家里讨论自己作文的学生施东昌,因受株连而遭受磨难,忍受精神和肉体的疼痛,成为美的探求者。他为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所遭受的磨难和英年早逝感到彻骨的痛苦和无尽的悲哀。这个总是开朗幽默、坚韧顽强的老人,总是以黑色幽默的口吻回忆自己的不幸,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为了这些知识人的遭遇而潸然泪下,被他们知难而进的坚韧品格所鼓舞:
他们的可贵之处是在季节转换、深陷绝境之后,并未沉湎于消沉麻木与怨尤逃避的无为或无所不为的历史泥泞之中,而是仍然以昂奋之姿,肩负起历史与时代所赋予的重任,忧国忧民,埋首工作,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为了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蹒跚前进,发挥自己的余光与余热。
1987年的一则日记中,记载了他阅读《中外名人座右铭》一书的摘录:
在绝望的坚壁前正是希望的火花闪烁的地方,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你才发现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价值,明了了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从世上得到了什么,而是体味到了什么,这里才有诗,有哲学。
他将这段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这些话正好说明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因此,这个饱经忧患,数次被暴力剥夺自由、被推到死亡边缘的人,却总是给人以温暖、激励,因此,他并不孤独。
他在《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的自序中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科学与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虽然生性喜交朋友,但绝不滥交。我交友是有选择的,有原则的。古人评价文人用“道德文章”这样的标准,我认为用于现在,也不失其原则的真理性,虽然,随时世变迁,“道德”与“文章”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认为,人品是第一位的,才学是第二位的。我交友,首先看他的人品,做人道德,其次看他的才学和能力。
贾先生在复旦九舍的家,向所有来访者敞开。这里总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国内外知名与不知名的学者,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进校时间不同的校友,文化界的工作者,以及从他的山西老家来的乡亲。起初,我感到迷惑:一个经历了如此磨难的人,为什么还对于人世如此信赖,如此热情好客?人們为什么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看望一个毫无权势、一无所有的耄耋老人?渐渐地我明白,人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看这个为了人生信仰和友谊付出过巨大代价的人。看看他,与他聊天,从他这里获得某种精神的安慰。我相信,当一个偶遇挫折或孤独忧郁的人,来到这个饱经忧患却依然心胸豁达的老人面前,在他的寒舍里听他风趣的谈笑,自己遇到的那一点挫折和困难实在算不得什么,自己的苦闷和焦虑也就显得可笑、浅薄而释然了。来到这里的人,坐在他那个拥挤不堪的房间里,与他和其他不期而遇的来访者漫无边际的谈话本身就是目的。在这里相遇的人之间,淡忘了高低贵贱、成功失败、年老年轻的等级界限,彼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共通感就是对于人的一种理想和境界的敬仰,对于人本身的尊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平等、关爱、同情和理解。虽然贾先生离开人世已约十年,但是,他从来未被遗忘。
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谁记住一切,谁就感到沉重。”的确,贾植芳这个名字,所承载的历史的重担,远远超出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①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第5页。
②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创作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第102页。
③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创作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第103页。
④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第16页。
⑤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第17页。
⑥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第18页。
⑦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第19页。
⑧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创作卷,第232页。
⑨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理论卷,第366页。
⑩ 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第93页。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创作卷,第365页。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第14页。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第6页。
贾植芳:《狱里狱外》,第117页。
贾植芳:《狱里狱外》,第26页。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理论卷,第366页。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创作卷,第104页。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第137页。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第416页。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