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交流三昧
2019-11-01赵康
赵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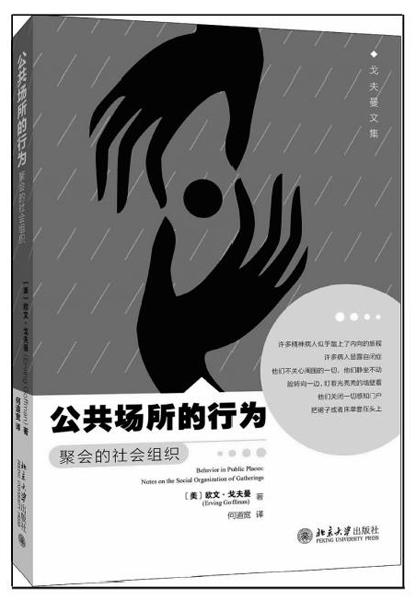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公共场所的行为——聚会的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公共场所的行为》)一书由何道宽先生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中,戈夫曼研究了社交场合中的行为规则。他指出,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存在着一整套情境性礼仪作为交往的规范。这些规则仪礼框定了交往参与者的小圈子、小社会,规则指引着行动者的社交行为,也划定了社交的边界。边界之内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超出边界之外的行为则被群体所排斥,相关的行动者也就无法享受群体圈子的归属感。戈夫曼看到,对违规的最严厉惩罚就是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的医生通常是通过病人的“不适合情境行为”对病人进行诊断的。精神病学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不当行为人,而戈夫曼研究的重点在于情境背后的社会规则。在戈夫曼之前,社会学研究尤为关注社会骚乱、集体恐慌等集体行为,忽略了对一般性社会交往的考察。受到精神病学研究的启发,戈夫曼对公共场所中的“不当的行为”进行了观察。戈夫曼认为这样的考察有助于社会学去探究日常交往的模式与结构,这将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戈夫曼从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家公立精神病医院和设得兰岛的参与式观察中获得了一手资料,并以中产阶层的礼仪手册为研究文献进行了深人的文本分析。通过对比精神病院和一般公共场所的社交行为,戈夫曼总结出了公共场所交往行为的三个主要特征:交互性、情境性和规范性。
一、交互性
戈夫曼所说的交互性(mutuali-ty)与库利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传统颇为一致,社会交往中的交互性体现在个人理解与接受他人的态度上。按照戈夫曼的划分,公共场所的行为可以分为两大类:无焦点互动和有焦点互动。有无焦点的区分是根据社会场合交流的松紧度划分的,匆匆一瞥、擦肩而过等比较松散的互动是无焦点的,而围绕某个问题、某个人进行的紧密互动则是有焦点的。面晤、邂逅等面对面的有焦点互动具有显而易见的交互性,这是传统社会学考察的范围。戈夫曼对无焦点互动的考察突破了传统社会的框架,扩展了交互性的社会学内涵。
只要进人公共场合,我们就很容易进人无焦点的互动。无焦点互动的涉人在人的体态习语方面体现最明显。个人进入公共场所时可能并不会与他人进行言语交流,但却无法不进行体态交流。在无焦点互动中,人人都会通过体态习语与他人进行交流,仪态举止就是交互性在公共场合的体现。与米德区分有意义体态和无意义体态不同,戈夫曼眼中的体态并没有“无意义”的类型,因为“习语对行为者和目击者都唤起相同的意义,行为者用它是因为它对目击者有意义”。行为者对目击者意义的考虑,是一种不自觉的交互性关照,这拓宽了交互性理论的延展度。
戈夫曼对意义的定义也更加宽泛,他认为有意义的持续交流并不是典型的社会互动,很多时候行为人只是为了保持一种印象,不自觉地进入了一种自发性的涉人。自发性涉人、自我专注的活动以及礼貌性忽视在戈夫曼的理论框架中都具有交互性的特征。自发性涉人背后有一种基于印象管理的交互性在起作用,这类活动在米德的理论中并不被社会学范畴所含纳。自我指向的人体活动,如剔牙齿、修指甲、打瞌睡等并不会指向他人,所以也不在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社会互动框架之内。戈夫曼认为公共场所赋予互动以一定的情境,在情境之内“自涉人”的行为也具有潜在的交互性,这对米德和韦伯的理论构想是一种突破。
礼节性忽视也体现了一种交互性的张力。礼节性忽视介于盯着人看和视而不见之间,既给在场者以充分的注意又不过度关注对方。礼貌性忽视只是传达自己注意到了对方的存在,而自身的注意力却保持交互性弹力,随时可以撤回自己这里。另外,防涉人、开小差、出神、告别等行为在戈夫曼的整合之下,也具有理论弹性。这些不具备交互性的活动作为交互性的理论参照,实现了戈夫曼理论建构的闭环。戈夫曼将社会互动的交互性扩展到了无典型社会学意义的层面,这种扩展为传播学的介人提供了理论切口。
二、情境性
戈夫曼将公共场合的互动行为放到了社会情境(social institution)之中进行考察,“合乎情境的活动”是其主要考察对象。戈夫曼将情境界定为“人们聚集时总体的空间环境”(P20),凡是能够进入这一空间的人员都是情境中的一员。所谓合乎情境指的是置身于情境的涉人其中,而不是在情境中活动。置身于情境(within the situation)和在情境中(in situation)的区别在于,前者所体现的社会学主张声明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情境不再像“在情境中”一样作为背景而存在,而是作为参与社会互动的主要社会学元素而得到彰显。
戈夫曼描述了不同的社会情境:家庭情境、俱乐部情境、阶级情境、民族情境、文化情境、地域情境等。戈夫曼认为,个人对情境的归属,超越了家庭、文化、阶层等社会学要素。以文化情境为例,戈夫曼列举了不同文化与同一文化不同时间的差异对于理解社会互动的影响。戈夫曼提到美国观众到剧场看戏必须保持对演出的关注,而很多东方国家的观众在观看演出时则可以遁出、飘移。如果只是从文化比较的视角去分析的话,就不能区分“哪一部分差异反映的是表达涉人习语的差异,哪一部分差异反映的是涉人本身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文化对待演出的态度有很大一部分是行动者表达涉人的一种体态习语的差别,并不能算作参与互动本身的差异。东方观众以松散的形式观看演出,同样是在剧场这种社会情境中进行互动,只不过他们互动的形式并不是以美国观众熟悉的体态习语进行的而已。戈夫曼绕过了传统社会学要素的干扰,从情境的一般性特征出发来认识人际互动。这样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互动的内涵,毕竟很多互动与规则是不同文化群体通用的。
戈夫曼的情境社会学认为,参与社会互动就是进人一种社会情境。情境语言与情境习语构成了一整套情境性礼仪。情境性礼仪是社会互动的基本工具,对这套工具的運用无时无刻不在彰显情境本身的在场。在戈夫曼看来,退出社会互动就是退出社会情境。不管是从社会共同体和社会机构中脱节,还是对社会关系的疏离,其实都是对社会情境的疏离。这一点在戈夫曼对精神病人的观察中尤为明显,戈夫曼认为如果考虑情境因素的话,很多稀奇古怪的行为就比较好理解。很多精神病人并不是真的“有病”,他们只是没有满足一种情境性要求。表现情境性失当行为,不能说明行为人就是病态的。所谓的精神病人犯的不过是一种情境性错误,这并不足以支撑精神病学的病理性诊断。戈夫曼的情境社会学对传统精神病学的理论观点和传统社会学的区块分割式构架同时提出了挑战。戈夫曼抽象出情境这一概念,避免了传统社会学对个人、群体、文化、阶层等粗线条的划分方式,为重新整合社会互动提供了理论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