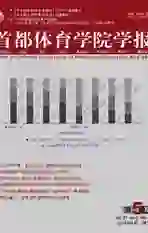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角分析乡村仪式性体育的变迁:湖南郴州“汝城香火龙”活动研究
2019-10-18邱海洪胡建忠
邱海洪 胡建忠
摘 要: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视角,以湖南郴州的“汝城香火龙”活动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野调查法、文献研究法等,梳理乡村仪式性体育活动的产生与延续、断裂与沉寂、恢复与重构。探讨“国家—社会”关系演进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仪式性体育的变化。分析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前,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国家源于社会”角度来看,乡村仪式性体育虽能产生与延续,但缺乏动力;在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国家脱离、驾驭社会”角度来看,乡村仪式性体育在国家控制下被动中断和沉寂;改革开放后,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国家与社会融合角度来看,乡村仪式性体育在得到国家政策扶持的基础上得以恢复与重构。
关键词:“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仪式性体育;乡村;汝城“香火龙”
中图分类号:G 80-054 学科代码:040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taking “Rucheng Incense Dragon” activities in Chenzhou of Hun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ergence and continuation, rupture and silence,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ritual sports activiti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on rural ritual spor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was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that “the state originates from the society”. Although rural ritual sports can be produced and continued, they lack motiv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was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that “the state detaches from and dominates the society”. Rural ritual sports were passively interrupted and sil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tate polic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tate and society showed an integrative relationship, where rural ritual sports can be restored and re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policy support.
Keywords: theory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ritual sports; rural area; rucheng “incense dragon”
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可归结为:国家源于社会理论;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理论;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国家回归社会理论[1]。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学界围绕“社会先于国家”“国家高于社会”和“国家与社会之间分立与相互制衡”等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2]。有学者依据已有相关理论对中国不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特别是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3]。也有学者认为,国家权力在乡村行使过程中也遭遇到农民的抵抗[4]。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在具体的“过程—事件”场景中对其进行考量与把握[5]。国家通过“借用”民间仪式使国家力量、符号在社会中得以存在,并对社会实现间接塑造[6],而民间仪式的重新崛起,又使其与国家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谋[7]。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接纳和社会对国家的反饰,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饰[8]。
在体育学研究领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体育,而应将其纳入民族国家的范畴,视其为以民族国家的文化为源、传统为根、民族精神为魂的一种直接的身体表达[9]。学者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中,不再执著于民族传统体育本身的功能、价值的分析,开始关注民族传统体育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李志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抢花炮”的几度“沉浮”折射出乡村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的密切关联,反映了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间的互动关系[10]。万义等认为,乡村女性体育参与行为的形成是由地方政府对话语权的掌握、对女性体育参与意识的“误识”及二者间恰当地契合而产生的[11]。汪流等通过回顾中国老年体育中的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活动互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给予社会力量以有效的激励,来实现国家与社会对老年体育的“双轮驱动”[12]。杨海晨等通过对一项仪式性体育(即“演武活动”)的历史性、过程性的诠释,缩影式地呈现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路径及发展趋势[13]。
综上所述,学界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研究及在此视角下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拓宽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进路。同时,笔者认为,目前在体育学研究领域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角下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此外,在讨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式微、中断、复兴时,对国家权力影响的分析存有“过度解读”现象。湖南汝城的“香火龙”是一种乡村仪式性体育,其蕴含了地缘、社会结构等诸多要素,紧密联系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场景的变迁。“国家—社会”关系的演进对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香火龙”又是如何顺应这种变迁?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是本研究的主旨所在,并借此阐释民族传统体育如何存在于国家体制中。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研究法
首先,在湖南郴州市汝城县档案馆查阅了《汝城县志》,找到了对汝城“香火龙”的记载;在县文化馆查阅了汝城“香火龙”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书,以及国家有关部委、各级政府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汝城“香火龙”的政策文件;在此基础上,基本收集到了汝城“香火龙”的历史起源与发展的资料。其次,课题组在田野调查对象、龙灯理事会等的帮助下收集到了与汝城“香火龙”相关的族谱、传承谱系等第一手资料。最后,中国知网、学校图书馆及汝城图书馆查阅了民族学、体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相关专著和期刊,收集了有关仪式体育、乡村体育的相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和整理。
1.2 田野调查法
课题组自2013年12月开始,在近5年的时间里,对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香火龙”进行了累计90多天的田野调查。课题组全程参与了汝城县多个村的“香火龙”活动(每年各村的“香火龙”活动不是同一天开展)。其中,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的田野调查,主要通过走访汝城县文体广电局、文化馆、三拱门范家、广安所李家,初步了解了“香火龙”活动开展的形式及特点,基本掌握了“香火龙”活动的概况。2015年正月初四,笔者再次前往三拱门范家,参与式观察“香火龙”的扎制与活动的组织过程。在此期间,笔者访谈了龙灯理事会成员、扎龙人、村民共40余人,拍摄了近500张照片和“扎龙”视频,并撰写了田野调查报告。2016年2月19日,笔者在金山村全程参与观察叶氏“不夜天香火龙”。本次调查访谈了金山村支书YSL,“扎龙”艺人YLZ及龙灯理事会成员、村民50余人,拍摄了整个“香火龙”活动的视频。2016年8月、12月及2017年正月,笔者在金山村、广安所、周家村进行“香火龙”调查,深入到村民家中进行深度访谈,收集到了广安所李氏“香火龙”活动的录像和文字资料,对“香火龙”活动的文化形态变迁有了大致的了解。通过以上调查掌握了以下情况:1)“汝城香火龙”活动的整个过程;2)“汝城香火龙”活动有关的文字、图片、录像资料;3)确定了深入调查的具体村落和访谈对象,并建立了田野调查点和确定了调查对象;4)“汝城香火龙”活动的文化变迁与国家话语体系的关联。
2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国家源于社会”视角下,“汝城香火龙”活动的起源及延续
目前,关于“汝城香火龙”活动的起源的研究中,较多地来源于口传故事和民间傳说,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本文主要从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出发,不对事件的时间、地点、参与对象及具体过程等方面进行严密的考证和准确的描述。根据汝城县文化馆提供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对象的口述,笔者认为“汝城香火龙”活动最早起源于治理洪涝灾害。据传说,在唐朝弘道元年,今汝城县连年遭遇洪涝灾害,洪水淹没了村庄和田里的庄稼,后村民“以火龙降水患”。村民用当地常见的干稻草编成数条稻草龙,将其在汹涌的洪水中焚烧,洪水终于退去,村民恢复了正常生活。此后,该地区村民逐渐形成以村落宗族为单位,在元宵节期间举行“香火龙”活动,用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且村民将“龙”雕刻在庙宇、祠堂的横木梁上。汝城至今仍存留有多处古时修建的龙王庙、龙王殿、龙母宫。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时期,人们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普遍存在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来抵御自然灾害的心理,汝城县村民便是通过“香火龙”活动来表达对自然灾害的抵抗。
新中国成立前,汝城地区长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乡村社会是在非制度性“精英”(即地方士绅、宗族头领)的主导下,自主地决定本地事务,处于一种自治或半自治的状态;而此时的“香火龙”活动的组织基础是“宗族”,“族田”和“小农经济”是“香火龙”活动存在的经济基础,其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等在历史传承中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香火龙”活动是以村为单位组织开展的,龙灯理事会是其组织机构。龙灯理事会负责“香火龙”活动的各项事宜,包括确定活动时间、活动分工、筹集资金、设计行进路线等。“香火龙”活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村内“公产”收入和村民的“乐捐”;行进路线仅限于本村范围,在途经本村异姓祠堂时要事先知会,得到对方同意后方可通过。在很长一段时间,“汝城香火龙”活动没有超出村的界限。各村的龙灯理事会都配有一套完整的乐器设备,设有负责“鼓乐”和“扎龙”的人员。“香火龙”的舞动动作、鼓乐、扎龙技艺在村内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
3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视角下,“汝城香火龙”活动的断裂与沉寂
3.1 “香火龙”活动组织机构的瓦解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步体现,耕者有其田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出台、农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14]。另一方面,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推行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一系列新制定的土地改革政策等使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社会生活中。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1年11月18日汝城县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汝城县开始了第3次土地改革,“香火龙”活动的主要经济来源——“族产”(宗族土地)也纳入土地改革的范畴,土地改革使得“香火龙”活动的主要经济基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人民公社时期,当时的金山大队(今金山村)隶属于土桥公社,下辖卢氏(上巷、下巷、界下、陈家)、叶氏(上叶家一队、二队,砖屋、象形湾、汉头、汉下)、李氏(井头一队、二队,田心一队、二队)共计14个生产队。当时的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单位,所有的村民都被纳为生产队“社员”。村民以生产队为单位,由生产队长组织生产劳动。在这一时期,村民只有一个身份,即“公社社员”[15],这一身份弱化了村民对宗族和龙灯理事会的认同,至此,发端于宗族的“香火龙”活动组织机构——“龙灯理事会”便不复存在。
3.2 “香火龙”活动的群众基础的自我封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49年开始,汝城县乡村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建构起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从而使汝城县迅速与县外进行文化对接,“汝城香火龙”村落宗族活动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下趋于衰落。人民公社时期,叶氏宗祠是金山大队第二生产队的队部,这座祠堂的墙壁上至今还保留有人民公社时期特有的印记,例如社员评比栏详细记有该生产队社员的工分、出勤、投肥情况,但在当时的祠堂中已经完全找不到任何与“香火龙”有关的记录。同时也由于当时物质相对匮乏,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香火龙”活动显然已失去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的支撑;但是,村民对举办“香火龙”活动的热情却没有消退,这也成为了“香火龙”活动在改革开放后恢复的群众基础。
4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国家与社会融合的视角下,“汝城香火龙”活动的恢复与重构
4.1 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资源”
将民间仪式性活动纳入“国家事件”,在当前具有积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地方政府通过打造地方民俗体育文化品牌和搭建国家治理现代化平台,将“汝城香火龙”纳入到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规划中。
4.1.1 打造地方民俗体育文化品牌
民俗体育文化品牌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民俗体育文化品牌建设对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提升、助推作用。民俗体育文化在地方政府的宣传推广下,以体育赛事、节庆体育的形式打造成地方文化品牌,比如,某市的国际风筝节、某市的傣族泼水节、某市的彝族火把节、某市的那达慕等。2006年“汝城香火龙”活动进入湖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汝城香火龙”活动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汝城县政府对“香火龙”活动的发展制定了规划、政策和措施,开展了一系列的发掘、整理与推广工作。汝城县政府在地方经济、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的政府工作报告、地方年鉴中均将汝城“香火龙”纳入发展规划。汝城县委宣传部通过其官方、新闻媒体及“香火龙”电视专题片,对“香火龙”活动进行了大力宣传和推广。汝城县文化馆多次组织文艺干部收集和整理有关“香火龙”的发展脉络、传统技艺、组织机构、艺术造型、传承谱系、文化内涵及鼓乐等资料。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背景下,汝城县级政府要重视文化建设。首先,《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应通过对其辖区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恢复、重构、转化创新,并以此争取文化建设项目与资金。其次,汝城县提出的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把旅游產业作为全县经济龙头产业,元宵节期间的“香火龙”活动成为当地旅游部门主推的亮点活动。一方面,“香火龙”活动成为了汝城县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香火龙”活动无疑能成为带动地方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4.1.2 搭建国家现代化治理平台
在汝城“香火龙”活动的研究个案中,国家文化符号对乡村仪式性体育的“形塑”十分明显,活动现场的牌匾、对联及各种横幅、标语中“华夏”“中华”“国泰民安”等话语的使用已经超越了乡村社会中地方文化的原始含义,社会在与国家疏离的场景中又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汝城县政府每年在元宵节都会“接龙”,下拨“香火龙”活动专项经费,并要求“香火龙”的点火仪式需在县政府指定地点举行。汝城县县委会参与“香火龙”的点火仪式。
汝城县政府在节日活动、重要庆典中设置“香火龙”表演,最直接的作用是其可以营造祥和、热闹的节日气氛。“香火龙”固有的“喜庆祥和”“平安吉祥”的象征意义被突显出来。民间仪式性体育活动进入“国家事件”,多数是受到某种征召。“香火龙”活动被征召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社会价值,也意味着“香火龙”活动的合法性得到确认。汝城县政府对“香火龙”活动的组织从根本上赋予了“香火龙”活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香火龙”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政策支持下赋予其合法性及汝城县政府的支持密切相关。
4.2 多元主体参与助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在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项目越能够得到国家政策的助推,就越容易发展[5]。“汝城香火龙”活动主要通过学术界、地方政府、新闻媒体来实现其传承发展。之所以进行这3方面的讨论,主要基于:学者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研究者,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评价的话语权;地方政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担当着“检阅者”角色,而新闻媒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展示的“窗口”。
4.2.1 学者的助推
学者指的是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汝城香火龙”活动的助推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受汝城县政府邀请,专程为“汝城香火龙”活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做指导;受汝城县政府的委托,为汝城县撰写村志;学者对“汝城香火龙”活动进行的研究。无论是哪种助推方式,他们要通过调研、撰写论文或著作、发表评论对“汝城香火龙”活动进行宣传和推介,由“不为人知”变为“广而告之”。笔者从广安所龙灯理事会成员LCL的访谈中得知,2007年,“汝城香火龙”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汝城县政府十分重视此次申报,邀请了一些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学者到汝城县进行申报指导。汝城“香火龙”申遗视频中就加入了当时被邀请的一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从事民俗学、文化遗产学等方面研究的研究员的点评。
从口述者LCL的访谈可知,汝城县村民对学者的到访非常重视,学者对“香火龙”活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起到了助推作用。在“香火龙”活动的传承与发展中,学者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构、知识再生产的主体之一。他们通过课题研究、学术讨论等形式,引发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15]。学者的“在场”,不仅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间接通过学者“生产”了知识。学者的“参与”本身也成为扩大“香火龙”社会影响的方式。
4.2.2 地方政府行政人员的参与
“汝城香火龙”活动传承了几百年,主要是以乡村内部宗族为单位组织开展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外村及同村异性人员是不参与的,偶尔会有村外的政界人士参与,但这些人都是出自同村。他们主要以宗亲的身份参与,这种参与形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香火龙”出龙仪式前的致辞环节中,以往是龙灯理事会理事长通报“香火龙”活动情况及宗族内的一些事务。当前,在该环节会邀请汝城县政府出席致辞,并已成为“香火龙”活动的“标配”,而且出席人员的级别成为了“香火龙”活动规格的一个象征。龙灯理事会在邀请政府出席致辞方面主要有2个渠道:一是龙灯理事会通过上报“香火龙”活动计划,由县文体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及镇政府指派;二是通过龙灯理事会、村两委邀请上级部门。一般而言,后者出席“香火龙”活动的被邀上级部门的级别通常高于前者。“香火龙”活动的出龙仪式致辞通常也是对“香火龙”活动意义的阐释,包括汝城“香火龙”活动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并对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有促进作用,这对“香火龙”活动的传承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4.2.3 新闻媒体的宣传
汝城县土桥镇金山村2016年和2017年连续2年分别由村里的2个姓氏家族举行“香火龙”活动。2次“香火龙”活动均在新闻媒体进行了全程报道。笔者访谈金山村YSL得知,2016年和2017年的“香火龙”活动通过省级、县级、市级电视台进行了全程转播,并且2017年的“香火龙”活动还推送到手机APP进行直播和在市、县旅游局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了推送。在调研过程中,笔者获悉,“香火龙”活动存在一些禁忌,例如女性不参与舞龙等。而在电视台转播的“香火龙”活动的“点火”环节,有2名女性记者参与了“舞龙头”,但龙灯理事会成员等均未提出异议,都对“香火龙”的诸多禁忌进行了“选择性”忽略。笔者认为,这是乡村民俗体育文化在新闻媒体宣传时的一种自我“调适”。而访谈对象金山村的YSL对电视台对“香火龙”的全程报道一事倍感自豪,他认为“香火龙”活动的电视转播能让更多的人观看到这一乡村仪式性体育活动,还为观众提供了可以随时点播的活动现场视频,更对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2次“香火龙”活动组织者对电视台全程转播的感受可见,“香火龙”活动虽然还是以乡村中的宗族为单位组织开展,但“香火龙”活动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村。新闻媒体的宣传也将对“香火龙”活动的文化品牌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5 结束语
乡村仪式性体育的变迁折射出“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乡村仪式性体育活动在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表现也不同。在新中国成立前,乡村仪式性体育活动主要以一种“自发”的状态延续,但由于乡村宗族的有限力量,“香火龙”活动的开展在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在规模上局限于村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乡村文化空间进行重构,仪式性体育活动被迫断裂与自我封存。“汝城香火龙”活动在这一时期的中断,并不意味着村民对该活动失去了文化认同。而是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满足“香火龙”活动开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民间仪式性体育活动在政治、经济、社會发展方面具有了新的含义,“香火龙”活动也被赋予新的含义,乡村仪式性体育活动得到了恢复与重构。
在乡村仪式性体育活动中发挥国家“在场”的作用,营造“国家在场”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环境,是传承和发展“香火龙”活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1] 张明霞,范鑫涛.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要义[J].人文杂志,2015(5):22.
[2] 邓正来,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35.
[3]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
[4] 折晓叶.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J].社会学研究,2008(3):1.
[5] 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2(5):83.
[6] 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8(1):42.
[7] 黄剑波.乡村社区的国家在场:以一个西北村庄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05(1):187.
[8] 郑进.国家与村寨社会的博弈:国家在场与社会式微:以贵州省西江苗寨“挂牌”现象为例的研究[J].民族论坛,2012(12):64.
[9] 王广虎,冉学东.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历史动因[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30(5): 440.
[10] 李志清.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与意义(五):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抢花炮[J].体育科研,2007,28(2):51.
[11] 万义,杨海晨,刘凯华,等.工具的展演与逻辑:村落女性体育活动参与行为的人类学阐释:湘西三村女性群体的口述历史与话语解构[J].体育科学,2014,34(7):23.
[12] 汪流,王凯珍.“国家在场”的中国老年体育:回顾与思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48(7):14.
[13] 杨海晨,吴林隐,王斌.走向相互在场:“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之仪式性体育管窥:广西南丹黑泥屯“演武活动”的口述历史[J].体育与科学,2017,38(3):84.
[14] 朱炳祥,夏循祥.屏风村龙灯文化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28.
[15] 申恒胜.乡村社会中的“国家在场”[J].理论与改革,2007(2):72.
[16] 陆群.民间仪式中的国家在场:以湘西花垣县大龙洞村苗族接龙仪式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3(6):64.
[17] 涂传飞.一个村落舞龙活动的变迁[J].体育科学,2010,30(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