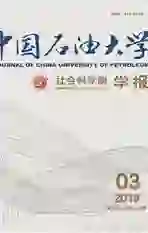论青年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
2019-10-10赵睿夫
赵睿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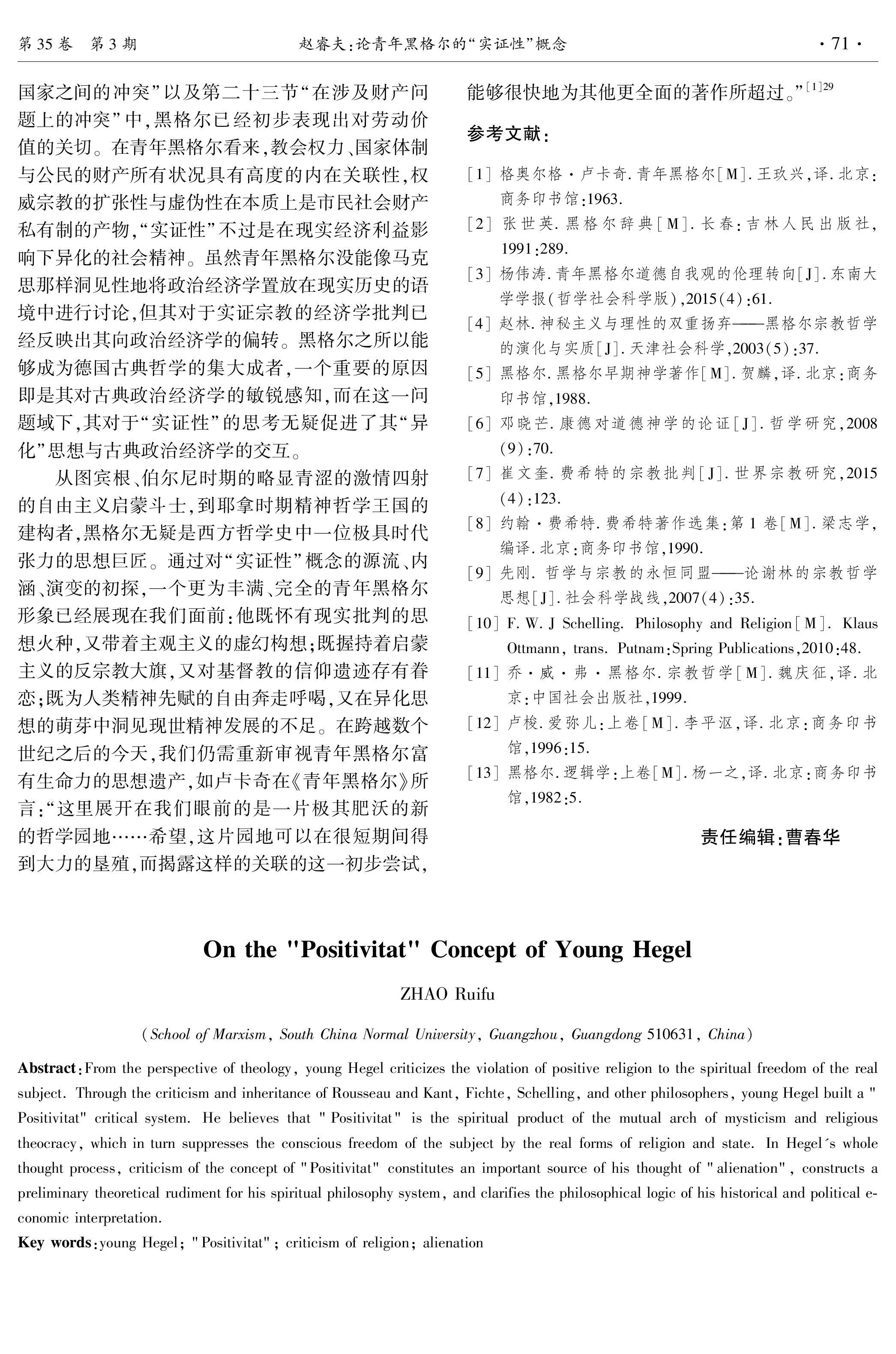
摘要:青年黑格尔从神学的论域出发批判实证宗教对现实主体精神自由的侵犯。通过对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与康德、费希特、谢林等德国古典哲学家思想精髓的批判继承,青年黑格尔构建了带有强烈启蒙色彩的“实证性”批判体系。他认为,“实证性”是神秘主义与宗教神权相互拱卫的精神产物,并藉由宗教、国家等现实形式反过来压制主体的意识自由。在黑格尔的整个思想历程中,对于“实证性”概念的批判构成了其“异化”思想的重要来源,为其精神哲学体系构建了初步的理论雏形,明确了其历史与政治经济学阐释的哲学逻辑。
关键词:青年黑格尔;实证性;宗教批判理论;异化
中图分类号:B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3-0066-06
“实证性”(Positivitat)是青年黑格尔宗教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经由对“实证性”及其现实外显形式的批判,黑格尔精神哲学体系的幼芽才得以萌生,因此,对于青年黑格尔“实证性”概念的关注与讨论显现出充分的理论必要性。
正如著名的青年黑格尔研究者卢卡奇所言:“青年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的中心问题是宗教的、特别是基督教的‘实证性……对于青年黑格尔,实证的基督教是专制与压迫的一种支柱,而非实证的古代宗教则是自由与人类尊严的宗教。”[1]48-49可见,“实证性”是被视作青年黑格尔伯尔尼时期宗教哲学研究的中心概念。事实上,伯尔尼时期的“实证性”批判已经隐含着一条黑格尔成熟时期精神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隐线,即以“实证”与“反实证”为主要矛盾的主体性斗争以及由这种斗争所带来的主—客体之间的不平衡性。青年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与其“异化”“辩证法”等重要哲学范畴具有高度的内在联系性。因此,探源黑格尔“异化”思想的早期显现——“实证性”概念——无疑是构建黑格尔完整思想肖像所不可缺省的关键一环。
一、源流: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的“实证性”
探析黑格尔“实证性”概念,需要率先明确的是Positivitat一词的汉语译法。国内对于Positivitat一词的翻译主要有“实证性”与“权威性”两种,其中,“实证性”的用法可见于王玖兴先生翻译的《青年黑格尔》,而“权威性”的译法则见于贺麟先生翻译的《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而在《黑格尔辞典》中,张世英先生的编译团队明确地采用了“实证性”的译法[2]。尽管译文存有差异,但这并不影响Positivitat在青年黑格尔著作中的表意,即“肯定性、实在性、成文性等意义”[3]。综上,本文拟采取“实证性”“权威性”并置共用的表述方法,对于不同译法的呈现皆以所参照的著作原文为准。
青年黑格尔对于“实证性”概念的集中阐释,可见于其早期著作《民众宗教和基督教》与《基督教的权威性》。《民众宗教和基督教》撰于1792年至1794年年底,《基督教的权威性》则撰于1795年11月至1796年4月。透过这两部作品的时间跨段,可以清晰认识到,青年黑格尔“实证性”概念在图宾根时期便已初步形成,而在伯尔尼时期达到成熟。
在《民众宗教和基督教》这部作品里,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于青年黑格尔宗教学说的影响清晰可见。一方面,黑格尔批判了將教义教条化与神秘化的“权威宗教”(基督教与犹太教),号召驱除困扰在人民心灵之上的宗教桎梏;另一方面,黑格尔赞扬了他所认为更符合人类主观精神幸福的自由的人民宗教(以希腊宗教为代表的“古代宗教”),号召宗教信仰与精神幸福的统一。[4]在此二元性的宗教划分之下,黑格尔将普遍的宗教形式划分为“主观宗教”与“客观宗教”,认为主观宗教中渗透着关照主体精神幸福的自由主义色彩,而客观宗教则意味着以教条式的教义对人的内在自由的禁锢。在黑格尔看来,只有“主观宗教有其独特的真价值”[5]7,而客观宗教则是形式化的、具有物的崇拜倾向的反人类精神的宗教。正如其所言:“换言之,我要考察的乃完全是主观的宗教,如果宗教是主观的,则它表现它的存在决不仅只通过合着双手、俯伏跪拜,把整个的心屈从于圣洁者,反之,它将扩展它自身于人的意欲的一切部门(也许灵魂并不直接意识到这些),并且到处发挥作用——不过只是间接地发挥作用——如果用我的话来说,它是以否定的方式在发挥作用,无论在人的欢乐享受方面或者在实现崇高的行为和履行人间的爱的温柔和德行方面,都是这样。”[5]8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青年黑格尔所批判的客观宗教,已经具备了“实证宗教”概念的雏形,只是,这种客观宗教尚未能彻底显现出“主体的道德自主性的扬弃”[1]49的表征,仍然以“自由与非自由”的信仰状态为判定的基本准绳。正是这种相对单纯的精神自由判准,为青年黑格尔思想上的颠簸埋下了伏笔。在1795年写作的《耶稣传》中,黑格尔一改《民众宗教和基督教》中对基督教的批判态度,反而表现出对基督教道德与教义的理性肯定,认为“那打破一切限制的纯粹理性就是上帝本身”[5]79。总之,《民众宗教和基督教》一文时期的青年黑格尔的宗教学说是不完全成熟的,在对客观宗教的批判过程中,尽管黑格尔的思想境域之内萌生了实证性批判的胚芽,但这种具备强烈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价值倾向的信仰观并未得到黑格尔贯彻始终的坚持。
作为黑格尔伯尔尼时期的尾声作品,《基督教的权威性》一方面延续了《民众宗教和基督教》中对客观宗教的批判,并着力凸显了其中已然提出但并未大力阐释的“权威性”概念,另一方面构建了自然宗教与权威宗教的矛盾对立关系。正如其所言:“从这种对立就可以表明,权威宗教是反自然宗教或者超自然宗教的,它包含着超出知性和理性的概念和知识,它要求不是出于自然人的情感和行为,而只是要求通过安排,勉强激动起来的情感,和只基于命令、出于服从,没有自己本身兴趣的行为。”[5]155在黑格尔的语境中,权威宗教继承了客观宗教一贯的反自由特征,而更进一步的,权威宗教包含有一种制造意识形态规训的潜在机能——这种机能渗透在其所提出的命令、规约与教条之中。如果说客观宗教所损害的是人的情绪自由,使得宗教信仰以压迫人的现实幸福为代价的宗教形式的话,那么权威宗教则是掌控人的自我意识,使得其按照宗教意志行事的潜在的信仰意识形态。至此,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显现出了清晰的轮廓:在对外部教条式信仰的反抗过程中,黑格尔明确了对于自我意识内生性的道德自由的论证,客观的、权威的、实证的宗教形式被黑格尔置于自由精神与道德实践的对立面,单纯的“神”的向度的信仰模式在黑格尔的宗教学说中开始瓦解。
众所周知,康德哲学的认知体系对黑格尔早期神学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感性的时空性到知性的统一性再到理性的超经验性,黑格尔从《民众宗教和基督教》到《基督教的权威性》的整个宗教学说脉络仍然是以康德所设置的知识学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一个具备强烈区分性的概念,“实证性”体现着黑格尔对康德道德神学“理性范围内的宗教”[6]70的界限精神的继承——他试图通过康德式的“划定界线”明晰宗教精神乃至人类精神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矛盾关系。而与康德从二律背反出发验证神学对象的不可知性不同,青年黑格尔更多地是以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的方式来清算神学对主体意识的控摄。“因此,黑格尔之想从道德里把一切神学的——实证的——因素都清除出去,并不是因为他——像康德一样——觉得神学的对象不可认识,而是因为他认为信仰与自由和人类尊严是不相容的。”[1]51因此,在认识到康德对黑格尔宗教思想的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黑格尔试图借助费希特与谢林来超越康德的渴望,从“不可知”的彼岸世界到“不需知”的精神世界,可以说,青年黑格尔对于“实证性”的批判既延续了康德的“实践理性”之目的,又反叛了康德“纯粹理性”之形式。
除康德的道德神学之外,费希特与谢林的宗教哲学理论也对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康德的上帝存在证明砍下了自然神论的头颅,那么,可以认为,费希特的上帝理念荡涤了基督教的神性,触及了基督教的灵魂。”[7]费希特在《试评一切天启》中所阐述的宗教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青年黑格尔。费希特首先提出了宗教形式的两条原理,即“内在的超自然性”与“外在的超自然性”,并以此为依据划分出“天启宗教”与“自然宗教”。正如其所言:“基于第一条原理的宗教完全利用了自然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宗教;基于第二条原理的宗教被认为是通过神秘的、超自然的、确实完全注定服务于这个目的的手段而为我们所接受的,我们称之为天启宗教。”[8]31-32在费希特的语境中,“天启宗教”意味着“上帝将其自身宣示为道德立法者”[8]34,是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对个人道德意识加以限制的宗教形式,这一点与黑格尔在《基督教的权威性》中所批判的权威宗教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二者对自然宗教问题的阐述,十分清晰地体现出了黑格尔与费希特在宗教论域下着眼点的关联性。
谢林的宗教思想与黑格尔的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内在联系。在其“同一性”哲学的总框架下,谢林试图构建起哲学与宗教的同盟,力求实现超越自然宗教与天启宗教的“哲学宗教”。与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机器化或虚妄化不同,谢林主张“国家、科学、艺术、宗教一体”的“同源分流、 万法归宗”[9]的总体性宗教观,这种历史哲学的思考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其挚友青年黑格尔。正如谢林在《哲学与宗教》中所言:“如果有限性(finiteness)被假定为真正的实证性(Positivity),并将其与真实的现实和存在纠缠在一起,那么前者,即人们如避疫病般试图逃离的有限性,将必然成为(在这个意义上的)恒定之物,而那些将自己限制于感官知觉并且完全享受他们想要的现实的人(在他们的意义上)将继续他们低劣的生活方式,陶醉于物质之中。”[10]在谢林的语境中,“实证性”意味着物化意识对主体自由的干预,与黑格尔所批判的实证宗教具有相近的思想内核。此外,卢卡奇亦曾指出谢林所使用的“实践理性”(被任意化了的康德意义上的自由意志)范畴与黑格尔的“实证性”具有较大的相似性[1]59,但在这种相似性的背后,却隐藏着谢林与黑格尔在实证性批判问题上的分歧——与黑格尔从历史维度展开的实证性批判不同,谢林的实证性批判是對整个人类文明体系的神学性质的批判,以致其批判思想蒙上了一层乌托邦色彩。因此,谢林与黑格尔在“实证性”问题上有相同之处也有相悖之处:一方面,谢林同样批判了黑格尔所言的实证宗教,反物化宗教意识对人的能动性的限定,力图形成同一性的“哲学—宗教”联盟,形成同一的总体性宗教体系;但另一方面,陷于客观唯心主义囹圄的谢林又夸大化了国家与人类社会的实证性症侯,使得自身走向了极端的反实证性道路——乌托邦主义。[1]60这种立场上的不同为谢林与黑格尔中后期哲学思想的殊异埋下了肇因。
从康德到费希特再到谢林,青年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在与前人、侪辈思想的碰撞中不断完善:首先,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自由与界限精神确立了黑格尔“实证性”概念的总体思维路径;其次,费希特对于天启宗教与自然宗教的划分为黑格尔的宗教划分勾画了雏形;最后,谢林的同一性宗教观为黑格尔宗教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青年黑格尔“实证性”概念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精神的现实体现。
二、内涵:黑格尔“实证性”概念的五重表意辨析
在明晰青年黑格尔“实证性”的思想谱系之后,下一步即需要厘清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表述:“黑格尔的这个定义(实证性)的本质在于:实证的宗教命题对主体的独立性及其对主体性的要求,它们要求主体对于不是它自己所建立的这些命题盲目地予以承认。”[1]49无疑,卢卡奇的表述较为凝练地揭示出了黑格尔“实证性”概念的内在特征,但仅从卢卡奇的视角出发尚不足以彻底厘清“实证性”概念的全部内涵,必须重新回到黑格尔的早期神学文本,从黑格尔自身的角度出发明晰其语境中“实证性”概念的具体所指。
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包括五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实证性”意味着“超出知性与理性范畴的神秘主义知识”。在《基督教的权威性》开篇,黑格尔明确指出:“权威宗教是反自然宗教或者超自然宗教的,它包含着超出知性和理性的概念和知识,它要求不是出于自然人的情感和行为,而只是要求通过安排,勉强激动起来的情感,和只基于命令、出于服从,没有自己本身兴趣的行为。”[5]155在黑格尔的认知中,“实证性”概念首先意味着超越人知性与理性认识体系的知识存在,即黑格尔所言的“实证性”带有强烈的虚无主义与神秘主义性质。这种神秘主义的、类图腾式的“实证性“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全面超越了康德式主体的认知能力。由此,我们可以感知到黑格尔“实证性”概念所包含的异化色彩,即主体对现实知识获取的空前的阻力与对神秘主义知识的迷信崇拜。
第二,“实证性”意味着“享有无条件真理性的精神规则”。黑格尔指出:“关于一个宗教是否权威的问题,取决于它的教义和命令的内容较少,而较多取决于它证明它的教义的真理性和要求实践它的命令的形式。”[5]160黑格尔所言的”实证性“意味着真理的主观化,即彻底的无条件性。这种无条件的真理性表现为信徒对其的盲从、检验手段的缺失、与现实世界的脱轨等方面。黑格尔的“实证性”批判表明其对绝对真理性的反对与对主体精神主观能力的节制。在黑格尔的宗教语境内,无条件真理性的精神规则意味着主体能动性判准能力的丧失,在这种形式的宗教控制之下,人的主观性处在一种悖谬的境地中——彻底地无视经验现实的真理性,使得人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崇高地位,但这种虚妄的崇高又以匍匐在绝对的神的权威脚下为代价。可以说,“实证性”是希腊真理精神悖谬的显现,是僵死的社会思想境域内对人的真实存在性的瓦解。
第三,“实证性”意味着“不正当且压迫人的道德命令”。此亦是黑格尔“实证性”概念中最为学界所熟知的表意。黑格尔曾言:“一个宗派它把道德命令当作权威的命令来对待,并且把别的权威的命令与道德的命令联系在一起,可以获得某些显著的特点……一旦这个社团或它的信仰得到更广泛的扩展到全民族甚至全面贯彻在整个国家,于是或者它们已不复是适合的了,或者它们实际上会成为不正当的和压迫人的。”[5]190作为来控制信徒的信仰工具,“实证性”的道德完全偏离了康德实践理性范畴内的道德,在这种境地下,道德不再是主体完全自觉自发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道德命令的异化,其原因在于“实证性”权力与神权的混淆,这既是宗教通过神权对现实道德的干预,也是市民社会道德体系的崩解与异化。虽然,青年时期的黑格尔没有像《法哲学原理》与《精神现象学》那样系统地阐述市民社会的道德问题,但在这一维度的“实证性“表意上,有关市民社会道德问题的讨论已经在黑格尔的思想境域中显现。
第四,“实证性”意味着“无穷无尽的扩张欲与支配欲”。在《基督教的权威性》中,黑格尔专门撰写了“扩张欲”一节,用以揭示“实证性”经由宗教信仰产生的现实侵蚀性。黑格尔指出:“权威的宗派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对于扩张,对于为它的信仰和为上天的名义寻求新的皈依者的高度热情。”[5]195黑格尔对于“实证性”的批判,决不止于对其内在威胁的批判,黑格尔清晰地预见到了“实证性“作为一股向外扩张的意识流的隐患。尽管黑格尔并未像德斯蒂·德·特拉西那样清晰表达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更遑论如路易·阿尔都塞那样系统地分析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体的“询唤”,但在《基督教的权威性》中,黑格尔已经窥测到了“实证性”作为一种可能的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影响,而且“实证性”的扩张是盲动且无休止的,这与Jean-Jacques Lecercle在《语言的力量》中所描述的永续运行的“询唤链”颇有类似之处。虽然,青年黑格尔对于“实证性”主体控制的描述尚局限在宗教领域,但必须认识到,黑格尔的“实证性”批判中的确已经包含了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批判思想。
第五,“实证性”意味着“以精神手段监视并统治人民的专制国家”。在青年黑格尔的语境中,宗教与教会并非是“实证性”唯一的现实表现形式,他认为,经由实证教会对现实社会的控制,可能产生一种区别于寻常世俗国家的“精神国家”。“对基督徒道德的监视是这个精神国家的主要目的,因此甚至思想以及那些超出国家固有范围的惩罚之外的邪恶和罪过的冲动也是精神国家立法和惩罚的对象。”[5]210黑格尔所谴责的“实证性”的“精神国家”无疑是专制的、恐怖的,它的存在使得人民在接受现实磨难之余又增添了精神的沉重枷锁。如果说“世俗国家”是直接插入胸膛的刀刃的话,那么“精神国家”的存在即是活活将信仰者晒毙的烈日,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使得信徒沦为刀俎鱼肉。在这个维度上,我们清晰可见一个反抗枷锁的自由主义的黑格尔,这种影响无疑来自卢梭等启蒙者。从某种程度上讲,黑格尔的“实证性”批判不仅仅是其宗教学说的重要部分,更多地,他开始尝试以政治的眼光审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缺憾。
上述五重表意,出自对黑格尔“实证性”概念内涵的文本发掘。当然,作为一个引起数代学者探讨的深邃概念,以上的分析必然不能穷尽“实证性”的本质。即便是如卢卡奇这样虔诚的黑格尔主义者,也无法彻底廓清黑格尔“实证性”概念的思想全貌。总之,“实证性”概念在现当代时空条件下的更深层次表意,仍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三、演变:作为黑格尔“异化”思想内在发轫逻辑的“实证性”
正如卢卡奇所言:“照黑格尔的看法,他所描绘的这种宗教实证性的性质,乃是决定整个中古和近世生活的决定因素。不言而喻,这种规定也适用于认识,知性和理性的领域。”[1]55无疑,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包含着超越宗教学说界限的理论内涵:首先,“实证性”批判的实质已经揭示出黑格尔对主客体关系的深邃思考——尽管他仍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倾向,但他已经分明感受到了自我意识之外的客体对主体独立地位的某种威胁;其次,“实证性”概念意味着自我意识对世界认识的限度与边界,反映出青年黑格尔对康德“物自体”思想的深入思考,为黑格尔后期主客体统一的康德哲学批判奠定了思想导因,在精神自由与道德自律的理性世界之外构造出一个实证性的不可知世界;最后,“实证性”桎梏的来源是人的意志本身,主体为何会生产这样一个自我束缚的意识枷锁的问题开始盘旋在黑格尔的思想疆域之内,“异化”问题得以初步显现。总之,孤立地将黑格尔“实证性”概念视作是其阶段性的“不成熟”的概念是不可取的,必须认识到“实证性”在黑格尔整个哲学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
“实证宗教的那种外来的、僵死的、被给予的,却又具有统治势力的客体,破坏了从前在自由的古代生活着的人所享有的那种生活的自由与亲切,而把认定一切的生活问题转变为一些不可知的非理性所能及的超验的问题。”[1]55“从内部摧毁宗教”——这正是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实质所在。[11]20虽然青年黑格尔将宗教問题置于哲学问题之上,但其精神哲学与辩证法体系的成熟终究离不开对于宗教问题的哲学化讨论。在《宗教哲学讲演录》这部黑格尔中晚期重要著作中,对于宗教“实证性”的揭示显然具有了其“异化”思想的意涵。“在黑格尔看来,宗教发展的下一阶段,作用于种种物体内之力集中化,呈现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的神圣之力,而人则自视为微不足道的、软弱无力存在体。”[11]25尽管在成熟时期的黑格尔处,权威宗教(实证宗教)的概念逐步淡化,但从自然宗教到自由宗教再到绝对宗教的宗教史观被确立起来,其对实证宗教对主体精神自由压制的批判从未消减。从“实证性”概念到“异化”概念,黑格尔通过对早期宗教思想的哲学化,完成了从信仰批判到现实批判的理论过渡,可以说,黑格尔对”异化“问题的阐述脱胎于“实证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