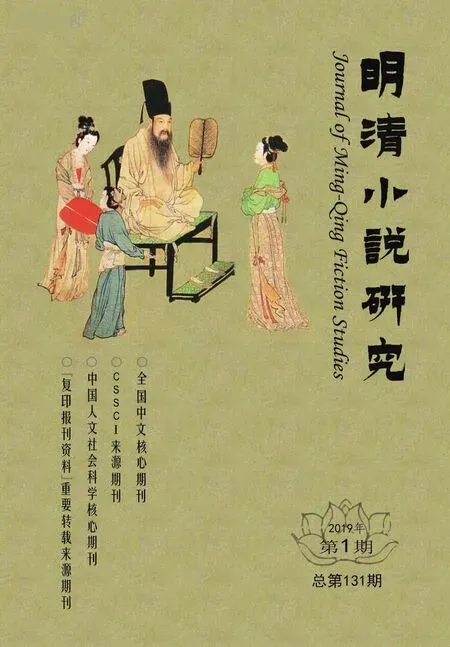清代西域流人“志怪”文学的自我影写*
2019-09-29··
··
内容提要 清中后期,遣戍西域的流人文学创作随着时代、文风的嬗变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记载诸如鬼神精怪、因果轮回等“志怪”故事亦成为文士流人所钟情的对象。结合边地的传说、野史,遣戍流人在考据扎实、多数亲身经历的情况下,记载了他们在旅途、戍地的所见所闻,比照前代乃至清前期东北流人文学的纪实性与自况性皆有所加强。西域流人以小说志怪、诗歌叙事等形式载述怪诞的题材内容,凸显了考据风气下“怪力乱神”的诗文创作形式,标识了流人文学作为疏泄、猎奇、刺激等心理作用下的诗文书写特质,这也是流放文士自我意识的一种影写和映射。
清代文学流派众多,文论繁杂且各执一词,于此期间,小说创作的成就已远远高出清代其他文体。自文言小说的翘楚——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于康熙年间完成后,此后模仿或背离之作就迅速发酵,而与清代流放文人“志怪”题材相关的文学创作亦有一枝独秀的态势。乾隆中后期,流放文士多被遣戍于巴里坤、哈密、安西、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因西域主要包括新疆、伊犁、甘肃三地,清代中后期流人亦多被称为西域流人。乾隆时期,政府在新疆遣戍大量流放犯人垦荒以支付清廷众多的军费与行政开支,“(乾隆)对新疆最成功的运用是将之作为流放之地。一项数据推估1758-1820年间帝国的总督有10%曾被贬谪到此,同样也流放了相当大量的地方官员与成千上万的一般罪犯”①。清代大批贬官遣戍至西域,使得流人文学创作呈现异样的繁盛,以流人纪昀遣戍乌鲁木齐后所作的《阅微草堂笔记》及其他遣戍流人在边地所载的奇谈怪论为代表,流人将边地的奇闻异事以“第一人称”志怪小说的形式加以阐释,甚至改变诗歌抒情为主的文学传统,借助诗前小序或诗歌内容载述怪诞故事。清代文士流人“志怪”文学的“现场”书写,拓展了文学的“纪实性”与“自况性”,将时风、文风与边疆的民情民俗、宗教神话等熔铸一处,创作出纪实与神怪——既对立又统一的清代流人边疆文学作品,建构出清代学者流人气质下“怪力乱神”的西域文学图景。
一、清代西域流人“志怪”文学的生成背景
怪诞(grotesque),来自意大利语grotta,意为洞穴,具指神秘、幽微等事物特点,世界各国对超自然现象的人事物多有所论,但多大同小异②,具有一些共性特质。神仙鬼怪在世界各地都有其存在的土壤,这些文化支撑着人们的生存畏惧、人生信念与美好愿望。神话空间“成为历史和闲适叠加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区域的文明中占有重要的无法替代的地位”③。东晋干宝《搜神记·论妖怪》道:“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④中国的“怪”“妖怪”融合了道家修行的“五行”(木、火、土、金、水)与儒家伦常的“五事”(貌、言、视、听、思)等学说,那些迥异常态的变异,即被视为是妖怪、神魔等物,中国的鬼怪与日本的“妖怪学”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⑤,是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变异现象,通常人们将超越常理的存在称之为“怪”或“怪诞”,因之清代西域流人志怪题材的文学创作有着特定的文化积淀与文体传承。
清乾隆时期,注重乾嘉之学,崇尚考据,使得西域流人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即便谈神论鬼,虽言之凿凿,但仍略有乏善可陈之嫌,这种“主题先行”,亦导致一部分西域流人“志怪”文学创作少文趣而多理趣,其最大的根源便是清中后期皇帝倾力整治“违碍”的政治风向。满清文字狱案在顺治间不过几起,乾隆朝则达一百三十起以上。乾嘉时期,正是满清强化中央集权的时候,史景迁认为“将雍正对曾静案的出奇料理,乾隆的悖反常理、违逆雍正严谕诛杀曾静等的这段过程,视为满人形塑自我认同之重要转折的表征”⑥,经过清帝王持续的努力,国家权力得以强势聚拢,文人士子的个体价值则被吸附、压榨殆尽。纵观大清王朝,中央集权及行政处罚机制的健全,亦属于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集权的巅峰,清朝知识阶层多埋首于故纸堆里,钻攻考据之学,较少过问政事,这种风潮浸染下的乾嘉士子,更是醉心于此。嘉庆时,洪亮吉(1746—1809)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触怒嘉庆帝,从宽免死后被发往伊犁。洪亮吉至伊犁后便买好墓地,以为自己必死于戍所。鉴于朝廷内外的压力,嘉庆帝方才格外开恩,因之洪亮吉在流放地惠远城住了不过一百天,就得以赦免归乡。塞外归来,自觉恍如隔世,心有余悸,洪亮吉由此自号更生(甦)居士,此后便躬耕于学问,不问政事,直至病逝。洪亮吉本“性豪迈,喜论当世事”⑦,他遣徙西域后,对当时朝野产生了轰动效应,洪亮吉隶属于毗陵七子(洪亮吉、孙星衍、黄景仁、赵怀玉、杨伦、徐书受、吕星垣)这一小群体,七子交游广泛、颇有声名。洪亮吉赴边时,其时为之唱酬的文士颇多,如赵翼(1727—1814)评价洪亮吉“忆君惟恐君归迟,爱君转恨君归早”⑧,称赞洪亮吉因戍边反而使其诗歌创作成果斐然。洪亮吉的贬谪经历,在文坛、政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经历对乾隆中叶的文风有着一定的“蝴蝶效应”,自此士大夫多有“噤声”之举,他们愈加潜心于考据之学而较少关心时事政治。
观清代中后期西域流人的小说、诗歌作品,即便是描摹鬼怪小说,依然是把持有度,多就事论事,较少持有铺陈蔓延的创作倾向;所涉及的故事,核心目的依然是用来宣传教化——不是自律本体,便是规劝他人,较少烟火气,而多夫子之道,此种特殊性也是与清代流人“自况”的创作思维以及自嘲、疏泄等目的相对应。时空辗转,亲赴边塞,异域空间行旅使流人志怪文学创作具有作家身在现场的特点。西域小说或诗文当中的怪诞行旅记载,因流人亲身赴边,成为具有实录性质的“自叙性”志怪文学,所叙多为亲身亲耳之所见所闻,让人难辨真伪,更具说服力,实现了清代流人志怪文学的现身说法与教化意义。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除了有讽刺喻世、道德教化的目的,亦有自警自醒、自我调适的想法,鉴于流人所作多处于流放之地,经受流放之刑的折磨,流人精神与情感上皆受到一定的震慑,他们心理的恐惧与焦虑便转嫁于自撰文本世界中“怪力乱神”的对象,所愿便是警醒自己及世人。相较学者刘燕萍对清代《镜花缘》之类的小说所谓“虚构的旅行(imaginary journey),即往往是一种讽刺现实的手法,虚构旅行可被视为讽刺寓言的一类,作者所虚构的异域,或许与现实并不相符,但即使有变,依然相同”⑨的论断,身处戍所,为清代西域流人提供了亲临现场的话语情境,其想象力有着一定的空间载体。
清代文士流人遣戍边塞,各有原因,总不外乎为官不力或触犯朝禁,他们由中原江南移至荒芜边陲,活动范围与空间结构的变化,致使流人的文学书写,将神话、宗教、巫术,乃至道德心理等方面的主观意识,隐喻于“志怪”文学作品异质空间的想象,强调创作者身在现场的真实情境,藉此疏泄其内心隐秘的情绪情感,甚或是变态、猎奇的心理,消解黯淡的人生困局。“人类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宇宙观,以适应新环境。随着一个‘世界中心’受到破坏,人们会在它的附近或者另一个位置建立起另一个中心,新的中心最终会变成‘世界中心’”⑩。失意的流放文士另觅积极乐观的人生况味,在边地开辟出另一场域,他们苦心经营,力图再次踏上原有的道德与官场秩序,寻求个人前程再次突围的机会。以纪昀、舒其绍、祁韵士等为代表的清中后期流人志怪内容的文学创作,在承续《搜神记》《玄中记》等传统志怪小说后,又受到时文的影响,清代流人遣戍边塞,也为亲临虚构的文学空间现场提供了机会,因之流人带有自况、自譬性质“志怪”题材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清代西域流人文学独特的文学景观。
二、清代西域流人“志怪”文学的创作特质
清代西域疆域内新奇的人事、物件拓展了中原、江南文士的创作视域,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激发了清代西域流人的创作热忱。纪昀及其他流人文学创作的主旨是以作家的亲身经历进行道德教化,创作黜华尚质的文学作品。流人身份下被遣戍边关,清代西域流人的小说、诗文便兼顾了实录、自况、怪诞及说教的目的,诸多因素杂糅使得清中后期流人志怪文学具有自喻自辟、铺陈玄奇与道德教化的文学特征。
清代志怪小说的双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同时还有袁枚的《子不语》,这些纯以短篇小说形式为主,以谈神论鬼为内容的玄怪小说,在清中后期成为短篇小说所取法的对象,遣戍西域的文士流人,身处边疆,对此类题材的热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流人舒其绍(1742—?)有诗《喇吗先巴旦咱处见而赋此》曰:“咄咄怪事无不有,斫得头颅同瓦缶。”这些奇谈怪论,弥补了学者流人猎奇的心理,削减了他们紧张、颓败的情绪。流人以个体的生命经验与生活喜好,择取不同神怪题材加以发挥创作,有着学者质性内核的流人,每每以“亲临”的口吻,严谨撰写其所见所闻的鬼怪故事。
戍边的漫漫长路上,惊悚、悬疑的鬼怪故事,刺激了戍边流人的神经,在感官刺激与心理释放之余,流人的不良情绪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疏泄。流人裴景福(1854—1924)曾载:“十二月二十七日,晴,不冷。海秋言有友吴申甫大令,金陵世家也,与海秋有戚谊。述在山西凤台县,有同事某于晋省大饥时,收一童子,年十二,性灵警,能合主人意,亟爱之,人咸呼为小鬼。一日,某与小鬼对榻卧,忽闻某呼声甚疾,廊下有人自窗隙窥之,见小鬼自帐内伸头扑某颈,渐长而身仍在帐中,某呼声渐微,人入,气已绝,启帐,小鬼已不见。某已洞胸而失其心。遣人遍访,竟无小鬼踪迹。不知何冤何怪也。”裴景福所写乃友人之友人的故事,鬼怪的传神形象,让人犹如亲历现场。神鬼故事有着劝善戒恶的作用,给流人带来一定的心理暗示,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藉此渲染其朴素的道德价值观。对边地神鬼故事的叙写,阐发了流人的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使他们戍边时坦然接受惩罚并充满早日赦归的期盼。
清代流人学者式谨慎志怪的手法,间或夹杂考据炫奇甚至认真说教的成分,这种虚实交错、荒诞不羁的文风,亦颇为惊艳有趣。清代学者扎实考据的态度与浪漫、神秘的文风有些背道而驰,这类老夫子式的神妙奇特较蒲松龄《聊斋志异》有意为之花妖狐魅的文人笔法仍有所欠缺。流人祁韵士(1751-1815)《压油鸟》诗曰:“非关觅食往来频,体累多脂解向人。却忆侏儒饱欲死,兰膏徒自速焚身。”作者自注压油鸟乃“大如鸡,色黑。肥则向人哀鸣,为压取其油辄复飞去”。此实子虚乌有、怪力乱神之物,这种撰述只能姑妄听之。祁韵士的诗文兼具志怪与传奇于一体,他注重的是故事叙述与情节完整。祁韵士的“虚妄之说”,亦不同于裴景福神秘鬼怪的阐述,这是祁氏在遣戍途中记叙的具有浪漫色彩的传说。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写法是西域流人作家较为钟爱的表达方式,清代学者这种偶尔为之的虚妄传说与怪力乱神亦是流人文学的一种书写模式。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对传统志怪小说也有所扬弃,他传承了原有神怪故事中鬼魅、狐妖的超人法术,掺杂时代、地域等现实因素,在表现这些玄怪元素时,仍把持有度,不过分渲染非人力量的强大,着重自我影写小说的劝导惩戒作用。《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神鬼妖怪,有着纪昀自身的营构倾向,他以同时代部分西域百姓的社会生产活动为根基,表现西域百姓的喜好与畏惧。卷十三《槐西杂志三》道:“乌鲁木齐千总柴有伦言:昔征霍集占时,率卒搜山,于珠尔土斯深谷中遇玛哈沁,射中其一,负矢奔去。馀七八人亦四窜。夺得其马及行帐,树上缚一回妇,左臂左股,已脔食见骨,噭噭作虫鸟鸣。见有伦,屡引其颈,又作叩颡状。有伦知其求速死,剚刀贯其心。瞠目长号而绝。后有伦复经其地,水暴涨,不敢涉,姑憩息以待减退。有旋风来往马前,倏行倏止,若相引者。有伦悟为回妇之鬼,乘骑从之,竟得浅处以渡。”玛哈沁即清代西部蒙古族额鲁特(又作厄鲁特或卫拉特),土著称劫盗为玛哈沁,泛指野盗,纪昀常在文中视之为野人。纪昀的西域故事多处论及“玛哈沁”,在中原士子的眼中,少数民族身为蛮夷,他们凶狠异常,不通人伦教化,流人将之视为比洪水猛兽还凶险的物种。“霍集占”即大小和卓,此故事以清乾隆的时事政治为背景,含有“善有善报”的寓意。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圈定下,《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槐西杂志四》载曰:“余在乌鲁木齐日,城守营都司朱君馈新菌,守备徐君(与朱均偶忘其名。盖日相接见,惟以官称,转不问其名字耳)因言:昔未达时,偶见卖新菌者,欲买。一老翁在旁,呵卖者曰:“渠尚有数任官,汝何敢为此!卖者逡巡去。此老翁不相识,旋亦不知其何往。次日,闻里有食菌死者。疑老翁是杜公。卖者后亦不再见,疑为鬼求代也。《吕氏春秋》称味之美者越骆之菌,本无毒,其毒皆蛇虺之故,中者使人笑不止。陈仁玉《菌谱》载水调苦茗白矾解毒法,张华《博物志》、陶弘景《名医别录》并载地浆解毒法,盖以此也(以黄泥调水,澄而饮之,曰地浆)。”此处“杜公”乃土地神,纪昀绘声绘色地讲述当地官员所遇之事,他自述早已忘记此官员的名姓,这位守备遭遇所谓已死之鬼为达到再次轮回为人的目的,寻找替死之人,而守备因得到土地神的搭救,终挽回一命。身为学识渊博的学者,文末纪昀再次以科学的态度,考证假设食用山菌中毒后亦不可怖,可据医书所载,及时按图索骥,加以救治,如此便可挽回性命。把持有度的纪昀,不满蒲松龄式的文人笔法,即大肆夸张手法,同时为消遣生活而始作笔记体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他在记载西域的神怪故事时,总脱不了实证考据的味道。纪昀以戍地人物为故事原型,多则故事皆凿凿有据,似确有其事,然则纪昀笔下的怪物身份实在是太过多样——可为山贼,可为山妖,可为野人,故事人物身份的模糊性,正可说明纪昀对不确定的事物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有意为神怪小说却难违其“实录”的创作态度。
纪昀记载边疆的奇闻异事,其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的故事原型、叙述方式、篇末阐释皆体现出他以“实学”为依托的创作特质,他以标举文言小说创作模式为旨归,故事内容取材于西域边地的现实生活及身边亲历,造语省净、文风质朴,其审美品格与乾嘉之学亦有着莫大的干系。在讲述神怪故事时,截取实际生活周边发生的故事,增强真实感与现场感,增强创作主体的自我影写倾向,将儒家传统道德与宗教劝解、惩戒、讽刺的功能相结合。纪昀曾自道:“儒者著书,当存风化,虽齐谐志怪,亦不当收悖理之言。”他希冀凭借文学作品达到济世救人,训诫教化等“经世致用”的目的。身赴边地后,纪昀等人继续以儒家济世救人的核心思想为中心,再辅以道家劝诫、释家因果等观念,杂以流人自身遣戍的生命经历,依托民间传说与民情风俗,宣传他们所设想的理想世道人心与儒家伦理纲常,表现其朴素的劝世、救世理想。《阅微草堂笔记》卷六《滦阳消夏录六》云:“辛卯春,余自乌鲁木齐归。至巴里坤,老仆咸宁据鞍睡,大雾中与众相失。误循野马蹄迹,入乱山中,迷不得出,自分必死。偶见崖下伏尸,盖流人流窜冻死者;背束布橐,有糇粮。宁藉以充饥,因拜祝曰:‘我埋君骨,君有灵,其导我马行。’乃移尸岩窦中,运乱石坚窒。惘惘然信马行。越十馀日,忽得路,出山,则哈密境矣。哈密游击徐君,在乌鲁木齐旧相识。因投其署以待余,余迟两日始至,相见如隔世。此不知鬼果有灵,导之以出;或神以一念之善,佑之使出;抑偶然侥幸而得出。徐君曰:‘吾宁归功于鬼神,为掩胔埋胳者劝也。’”辛卯乃乾隆三十六年(1771),纪昀记载身边老奴将遣戍流人抛尸荒野的尸骨埋于地下后,后因得到死去流人的粮食,且老马识途,托名于神仙、鬼魂的指引和护佑,得以死里逃生。此处,纪昀强调的是多施恩德,与人为善,终有善报的观念。《阅微草堂笔记》所载多与佛道、鬼怪故事相关,借此寓指世事,抒发议论。作为大学者的遣戍文士纪昀,他并不是真得相信鬼神灵怪,而是借鬼神灵怪的故事,阐发他对世道人心、宗教道义的看法。在对宗教故事的解说中,寄寓的是他“人人为善”的希望,寓指纪昀等学者流人自身的道德自省与观念框定,亦是流人作家主观意识形态的一种外化。实学思想影响下的流人学者,在其思想体系中,对轮回、因果之说还是持客观剖析与隔岸观望的态度,从纪昀的本心来说,他既希望达到惩戒人心、劝恶扬善的目的,但又不希望人们沉湎于因果与轮回的思想藩篱。这些志怪小说如实反映了西域边地百姓的认知水平与是非善恶标准,作家在津津乐道、沉湎于“怪力乱神”的猎奇故事时,又杂以宗教、神鬼、玄怪等既传统又现实的具有吸引力的素材,将边地生活中的即目所见,以笔记体小说的形式,虚实并呈,正邪并列,缔造了西域边疆场域中寓说教、玄奇与纪实三者目的并陈的自我影写之作。
清代中后期流人将荒芜、广袤的西域空间场域,经过润色与想象,重新打造成一个符合自己审美趣味与文学观念的异域世界。边地独异空间的创设,流人对边疆的认知,必须依赖于当地的物质条件。文人阶层对怪诞器物的兴趣,使得流人将目光投注于西域的器皿物件,在他们的文本世界中也有所撰述。舒其绍《古方铜》诗曰:“古铜赤仄土花鲜,圈乙分明出闰年。圆法近来边塞远,几人识得藕心钱。”此诗下自注:“伊城掘地,得赤铜方块千百枚。长五分,阔三分,厚一分,重一钱四分,夹二面,破痕三缕,其横头有阳文作一圈一乙,未知何物。按李孝美《钱谱》及宣和《博古图》,有藕心钱数种,皆上下通,缺若藕挺中破状,其殆是欤?伊属掘古物者,遇闰年则多获,余则否。”不经意出土的古铜钱,考证追索,可辨别出大致的形状、年代,末句加上一句“闰年多获”则堕入了神秘主义的藩篱,削弱了考据、实证的为文风格。此处舒其绍并没有赋予古铜钱以过多的诸如驱邪、通灵或祈福等神性色彩,显现了清代学者流人与晋朝葛洪《西京杂记》卷一所记的身毒国宝镜两者之间的区别,葛洪杂记曰:“宣帝被受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此则故事过度渲染宝物的神奇作用,赋予宝镜以各种祥兆、去祸的寓意。晋朝干宝《搜神记》和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都曾强调亲身经历的话语,力图说服别人自己所陈述“志怪”故事的真实性,即所谓自述事实与实录精神,而纪昀、舒其绍等清代学者流人所述明显要更为客观、精确一些。清代流人的诗文志怪作品,无法超越时代、社会、政治等现实因素,在作家自我想象的世界中,虚拟中又带有不容置疑的考据成分,寄寓了流人个体的人生经验与个体况味。
清代西域流人亲临现场,或者变成口耳相闻的旁观者,佐证他们的道德典范与伦理说教意义,同时也证明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志怪”精神亦颇为流行。无论是流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还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多简化为朴素的善恶果报,这是清代西域文士流人自求解脱精神桎梏的方式,因之各种志怪故事都有流人亲身参与的痕迹,相关“志怪”作品带有浓厚的创作主体的个性色彩。为超越现实,重构时空界域,流人将个人的爱憎好恶融入志怪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其自我影写的文学创作特质。
三、清代西域流人“志怪”文学的影写映射
乾隆中后期18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士在小说中擅于建构自我形象并加以自省自律,这是学界早已公认的观点。行为的从众性和从众心理致使清代流人文学具有个体的自况自喻、自律自省、自励自持的特质,创作志怪文学便是其自我心理的一种折射。在文本世界中,西域文士流人自我嫁接、自我改造,采用自传性质的文学书写,反映身为罪犯后,在时代、政治变迁下流放文人的身份变异与心理变态。
对怪诞故事的叙写,亦延伸至西域流人的诗歌创作当中,夹叙夹议的志怪诗歌,如实反映了流放文士的个体情愫,具有作家浓厚的主观色彩。流人舒其绍《赵巧娘》诗云:“邂逅相逢夜未央,锦衾角枕玉生香。金环得协刀环约,我亦频繁荐巧娘。”中国传统文士擅于创设宽慰自己的想象世界,多会采用的一种手段,那便是借助所谓的“意淫”,疏泄内心的郁结及压抑情绪,缓解个体的创伤记忆。流人舒其绍煞有其事地叙述了一位遣戍文士在落魄之时,美女丽人自荐枕席的投怀送抱,尔后又发现此非人类,不过是一只小木偶。他写道:“流人薛筠归绥定,日暮望林中灯火,投之;有丽人,自言赵姓巧娘。绸缪永夕,鸡鸣脱臂上双环为赠,曰:‘留为后验。’他日迹之,乃败屋中奉一小木像,问之,土人云:‘昔赵宦闺中供以乞巧者。’”薛以酒醴奠之,未几而赐环之音至。”即便如此鬼诡异常,流人薛筠仍愿再次招之,所谓天赐艳福,为何拒之。清中后期遣戍流人在受到诸多志怪小说影响后,沿用了“美女投怀于落魄文人”的思维模式,淡化其身为罪犯戍边的沉重事实,充满了落魄流人的美妙幻想。此类故事绝似《聊斋志异》中花妖狐魅自荐枕席的经典故事,因贯之“流人”这一身份,恰能得以谛视遣戍文士奇特的想象力及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蕴含西域流人强烈的主观愿望与自我想象。
清中后期遣戍西北的流人亦以散文式的笔法记载行程,将方志、考据、宗教、神怪故事兼容于一处,穿凿附会各种怪诞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加大其真实性,将内心的想法掩藏其中,创作出异彩纷呈的神怪作品。流人袁洁追慕袁枚《子不语》的写法,叙述神鬼灵怪故事,载曰:“余过聊城邮馆,向为旷宅,传言有鬼为崇,人莫敢居,未之信也。比夜半,方梦寐间,隐隐有男女一双,携手偕行,向余下拜曰:‘我情魂也,生前比邻居,私定终身之约,已四载余。后为父母所阻,事将不谐,乃同投于井。数十年来,无有知之者。今先生与委员史公皆深于情者,故含羞自陈。乞先生以粲花之舌,为我传之,感且不朽。’余亟呼史君醒,梦境亦同。乃挑灯成七古一章,中间云:‘话到别离共悲哽,从此为好难言永。惟将一死了情缘,不愿同衾愿同井。为郎破涕对菱花,潦草尚把花容整。携手双双入井中,百尺清泉坠无影。有梁安得燕双栖,无梦却作鸳交颈。至今井掩不可寻,袅袅情丝如汲绠。’诗成,诵而焚诸火,始膜拜去。”袁洁以第一人称叙述鬼怪故事的套路,在遣戍文士笔下也较为常见,如此篇所述,男女因情而为鬼作崇,及至遇到遣戍官员,希冀他能够帮助弘扬两人至死不渝的爱情,真可谓鬼中情种,读之不觉惊悚可恐,反为他们的忠贞爱情所动。殉情而死的鬼浪漫至极,这类小说为遣戍流人的西行路上添加了些许温情的色彩,身在现场的官员流人亦重拾过去的官阶身份,瞬间变为不再为千夫所指的遣戍罪犯,此类故事寄寓创作者多重的动机与寓意。流放文士经常在边地将这些温情的自我宽慰与自我欺骗,转化为重构美好文本世界的自觉与努力,他们提高贬谪所在地的神秘感与崇高感,藉此抬升自己的身价,借助构想,赋予陌生异域以旧有的生命经验与生存记忆,“命名需要的是区别。能够识别某一场所并将它与其他场所区别开来的能力。荒野,顾名思义是不存在任何区别的。区别,使山成为可名之物的行为,在这里是通过类似、通过隐喻来表达自己的”,宇文所安也突出了命名与幻想的力量,亦可解释清代流人竭力充实西域世界的主观倾向与美妙愿想。
流人记载当中自然也有据实所录者,如流人陈庭学(1739—1803)在《二叟诗》并序中道:“同年施柳南说杭之钱塘清波门酒肆中常有二叟来就饮酒,家保启问则索越酒一瓮,开尝味佳,更索开一瓮,置于座侧,各命倾缶注椀对饮,饮尽,更酌,怀中自出嘉果下酒,不复需他物。瓮既罄,付钱出门径去。如是者六七年,时竞传说,竟莫踪迹。其为何许人也?柳南时方集饮,遂拈酒字邀,即席诸友同赋。”遣戍流人的怪诞之作,也包括真实的人与物,所谓“畸人”不过是行事飘忽、品性高洁、不谐于俗的世外隐居之人,即“但记事堪传,竟莫识某某。君看古畸人,来去无何有”,这种所谓怪人——自由自在、无意于世间功名利禄的人是传统士大夫心中所仰慕的高人,反映了清代流人的理想人物与榜样人物,“畸人”未免不是流人对孤高品行的一种向往。借助怪异人物,西域流人辗转表达了个人的宗法取向,“畸人”“奇士”亦是流人自我期许的理想形象,藉此表达流人内心不谐于俗的渴望。
多数西域志怪文学的载述,依然充满了创作者大胆虚妄的想象,是流人“变态”心理的一种释放。塞外荒野,因流放后所遇到的各种神奇经历,清代流人得以在迥异的时空里,尽情释放个体的遐想空间,夹杂考据精神,他们构筑了惟妙惟肖的“神怪”世界。舒其绍《人儇》诗曰:“品到人儇最末流,一家老幼似猕猴。怜渠也解春光好,红柳花时插满头。”人儇此处应做猿人解,即野人是也。此诗旁注:“高尺许,巢深山中。男女老幼须眉、毛发与人无异。红柳吐花时,折之盘为小圈著顶上。作队跃舞,音咿嗄,如度曲。或至行帐窃食,捉之,则跪而泣;纵之,行数尺必回头;叱之,仍跪;度离远不能追,始骞涧越山大笑而去。或曰:此《神异经》所谓山猿也。”新疆伊犁是否有人猿尚待考证,舒其绍据当地土著所言,大胆臆测,此物乃远古典籍中所谓的山猿,行为举止却具有人类的特征。这些充满了荒唐不羁与大胆想象的西域新物种,还包括舒其绍所述的《两头蛇》:“头角峥嵘气似霓,锦鳞片片日华迷。毒蛇蕴毒偏攻毒,格物争传骨笃犀。”世间确有“两头蛇”这种物种,此乃是类似蚯蚓的一种蛇类。舒诗自注曰:“巨如柱角,长尺许,性最毒,以气吸禽兽入口吞之,而角能解毒;锯为片可贴瘫疽。捕蛇者烧雄黄于上风,即委顿易制。按曹昭《格物论》云:‘骨笃犀碧,犀也。色如淡碧玉稍黄,扣之声清越如玉磬;嗅之有香,烧之不臭’,即此物也。”舒其绍夸张了人儇的诡异凶险,也夸大了此物的凶猛性情及其药效功能。遣戍流人对西域边地各种奇物的记录,皆有渲染、夸诞的成分。当地劳动人民充满民间传奇色彩的想象力,再掺杂文士流人的妄诞联想,西域边地便被描绘成怪象丛生的奇诡世界。遣戍流人对边地的好奇转化成对西域“怪力乱神”事物的热情形貌,掺杂他们曾身为王朝中心之人的优越感,佐以奇特遐想,间或植入他们的流放生活经历,借助西域地域空间与物象景胜的文本表述,重塑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奇世界。
流人文学创作本应以疏泄性情为主要创作目的,对比清初流人家国故明之思,以文士流人的身份,书写离愁别绪、生离死别的情怀,清代西域流人文学则以记叙、叙事为主,不论文体,偶尔染指谶纬、迷信,堕入到超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的藩篱,间杂点染有注重实用,注重考据等时代色彩,乃至出现了多数文体小说化的创作倾向。道光六年(1826)遣戍新疆两年的方士淦(1787—1848),其所著的《东归日记》记录的是道光八年(1828)三月十五日至六月三十日,约一百天,包括从伊犁慧远城至西安之间的贬戍旅程,所述有各地的风景名胜与奇闻异事等。其《东归日记》中曾记:“(一八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桐轩来访,坐谈良久,极风雅,能诗。出城四十里,路旁石人一座。相传我朝岳大将军带兵过此迷路,夜间有两人引出山口至大道。天明视之,则两石人也。此后,不解何时一人移至奇台城外道旁,现亦完好,略为短小。此间石人,高五尺许,头大,而面上有眼鼻形象,乃天生,非人工也。近年,土人因其能行动,践踏田禾,乃建小墙以限之。往来车夫经过,必以蘸车油渍其面,云车无损折,殊为可笑。”传说中土地爷的保护神——两个石人,需途经之人,车油涂面方才允许安然通过,这则记载道明了边地百姓的禁忌,正是当地地形复杂,行路艰险的一种委婉表述。方士淦于(四月)二十六日,八十里行至松树塘,载曰:
二十里,由山脚十余里折曲盘旋而至山顶,关帝庙三层,深岩幽邃,灵显最著。旁有小屋,系唐贞观十九年姜行本征匈奴纪功碑,自来不许人看,看则风雪立至。余丙戌九月杪过此,曾进屋内一看碑文,约四五尺高,字字清楚,不甚奇异。因庙祝云“不可久留”,旋即出屋。顷刻间果起大风,雪花飘扬,旋即放晴,幸未误事。乃今年二月望前,伊犁领队大臣某过此,必欲看碑,庙祝跪求,不准,强进屋内。未及看完,大风忽起.扬沙走石。某趋马下山,七十里至山下馆店,大雪四日夜,深者丈余,马厂官马压死者无数,行路不通,文书隔绝数日。吁!真不可解也(旁有福郡王碑一座,乾隆年间立。此间,《汉书》之祁连山也,唐之“三箭定天山”也)。
西域地形奇特,常有反常的天气状况发生,流放文士必须十分小心,方能躲过殒命路途的厄运。对于边地突现的暴风雪,流人多有所阐述,方士淦此处则凸显了自己的好运气,文中所述,包括行旅历程、神秘怪事、地理数据,甚至还有历史碑记,内容颇为繁多。其他人没有神灵护佑,最终难逃厄运,而方士淦独受神佑,得以保全性命。历经凶险,遣戍文士对神灵多有敬畏,几乎达到逢神必拜的程度,宗教、鬼神信仰使遣戍文士相信神灵会保自己周全,这种自欺欺人的自信,是流人自我影写的内容之一。带有谶纬、迷信成分的生命经历,是遣戍流人文本作品中重点阐述的内容,流人以此疏泄心理压力,借助鬼神冥报、神怪显灵为自己“盼归”的精神信仰注入了强心剂。
相较于大肆宣扬鬼神灵怪的戍边文士,一些流人对于鬼神是否存在这一命题,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们以诘问的形式,辅以鬼神冥报、因果报应等释家教义,阐释自我独受神佑的特殊恩宠。乾隆甲辰(1784)四月二十九日,流人赵钧彤(1741—1805)记载:
余之来西安也。寓馆虽官备而固即逆旅舍,始入,昏暮矣。历五大门户至后庭,庭有坏石,础堂之上,烧巨烛、茵褥,然土臭。夜半,有人大声,屋壁震动,如折栋梁。晓视之,无恙也。堂东西皆有复室,儿辈西而余东。一夜,既登床,对床几上墨,忽磨声隆隆然,又铿然,掷笔橐,若将书者,亟视之,又无有。余窃怪之,而未以语儿辈,恐其馁也。二十六日,天酷热,午食方辍而奴辈大惊呼,其声惨恶,盖暟儿暴蹶矣。……余以所闻之多怪也,方窃念之,而萧喜。……呜呼,果有鬼哉?鬼怒人而余非多财如晋商者招优童触鬼,鬼何恶于余哉?高州官者,直而死耶?强而死耶?直而死也,生而仕宦,没而神灵,返其乡井歆其禋祀,何故滞旅邸,祸行人者也。若强而死,则有所恨,而为厉亦必于彼高车驷马煊赫如其所大恨者;而穷促如余,必感之、伤之、呵之、护之,而反祸之哉?
随后赵钧彤大发议论,他准备尽心规劝此鬼,让他主动迁走。赵钧彤自信满满地确信他的一贫如洗必然会使鬼怪垂怜,自己从而得以免遭祸害,但小厮因中暑,反说屋中有鬼,赵钧彤因此考证了先前住此屋而殒命的人。此故事劝解、劝慰的成分居多,该文的主旨便是鬼怪原应对戍边流人施以同情之心。遣戍流人迷信鬼怪的散文、杂记、小说等文体的撰写,促使流人思考自己的人生命运,从而敬畏鬼神,远离困厄的悲惨生活,最终他们还是将这些奇怪、诡异的现象都归结于神鬼精怪、谶纬迷信等说法,小心翼翼地希望自己能够远身避祸。
至于遣戍文士诗谶迷信的说法,流人袁洁《戍边诗话》卷一有云:“小陶临别诗云:‘高怀雅抱天边月,短发还惊塞外霜。’‘天边’‘塞外’,当时以为不切,今竟有乌鲁木齐之行,诗能成谶,信然。余素性飒爽,轻于然诺,朋友咸知。曩以从幕友何邻全之请,偶为落笔,致罹于讼,亦数定也。”戍边流人中有一定数量的文士,常在其文集中记有与自己相关的谶纬内容,袁洁道:“相士谓余谓猴精转世,适将戍塞外,或戏余曰:‘君可谓孙悟空往西天取经矣。’”对于袁洁自己“西天取经”的谶纬预言,他持有半信半疑的态度,自嘲式的调侃,暗含他无奈奈何的宿命观。袁洁还谈到了流人戍边的随从现象,曾记载:“吴人孤灿,素不识面,闻余事,仗剑来投,欲从出关。投诗有句云:欲跃龙门长声价,甘从虎穴负囊昔。”因仰慕流人袁洁的声名,吴人孤灿自愿忍受旅途艰险,陪伴他出关戍边,如此情景与命运,真乃有“师徒西游取经”一语成谶之感。这些记载在今人看来,实属荒谬可笑,但在流人袁洁处,遭到遣戍变身为罪犯的他,或许可以得到一丝心理的安慰,即个体原本是无法抗争命运的。西域流人文学中谶纬神秘的成分,这种以个体遭逢为叙述中心的表意系统,充盈了清代西域流人的想象空间,是其个体自我嘲弄与自我辩解的铺叙。
通过志怪叙事模式的书写,清代西域流人在鬼神情爱、谶纬迷信等记载当中,适度地释放了自己。流放是身体的限制和惩罚,身为罪人,却成全了他们在文本系统中的自我表述与自我影写,实现流人自我定位、自我辩解与自我安慰的作用,这种志怪叙述对象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正代表了流人遭遇流放后的人格割裂与彷徨意识,他们尝试通过文学手段来呈现自我,探索自我,实现自我治愈的目的。
结 语
西域流人多因亲身戍边,因此诸多故事甚至物象都与西域有关,流人的相关创作也间接转述了西域民间流传日久的故事与传说,这些美丽而神秘的虚幻想象,也是学者流人偶尔为之的娱乐消遣之作,间或有严肃的考据成分,原也是为了实录与教化的目的,这是清中后期西域流人不同于清初东北流人的特质之一。清初东北流人相比反而缺少这种敢于调侃或者描述神秘边地的文笔,东北流人在苦寒之地忙于生存,国家沦亡的创伤记忆成为其情感密度过强,创作麦秀黍离之作的主因,比之西域流人身份多为官员的闲适与似无生命之忧的心理,清初流人缺少了创作“志怪”文学的主客观因素。遣戍西域的文士流人在其学者气质的影响下对边地“怪力乱神”的故事与场景加以描摹,反映了乾嘉之学影响下的学风与时风,这是清代中后期西域流人独特的文学创作特质。
西域流放文士的谈神论鬼与奇闻怪谈,也是基于清代考据之风的盛行。文本叙述系统中,借学者式的说教,记录遣戍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想,虽有想象的成分,但亦节制有度。边地生活中怪诞故事、玄奇景象的记载与创作,是遣戍文士调节自身心理平衡,疏解其压抑心绪的一剂良药。戍边路上,行旅漫长而凄苦,袁洁曰:“抵安西州,城市萧条,飞沙丛积,其崇如墉。……过安西至哈密,相去千余里,并无城郭村市,惟住宿处所,荒店数家而已。行客须带米菜等物,藉以果腹,且有须带水者。其沙碛荒滩,水草不生,呼为‘戈壁’,所谓‘苦八站’是也。”遣戍流人的西行苦旅,经行之处,多有故事可挖,对西域“怪力乱神”事物的描写,满足了他们寻求猎奇、刺激的心理,减轻了他们的精神压力,同时将现实生活中不如意、不敢言的部分,借助荒诞、诡怪的故事得以含蓄表达。
就文本意义而言,以遣戍旅程或戍所生活为素材的鬼怪事情,因其载体是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亦承载了西域人民的禁忌、畏惧及对社会、自然、生活的认知水准。遣戍文士对边地奇诡事物的书写,体现了清中后期在实录基础上,流人创作题材广泛、叙事简洁明了的创作风格,以宗教教义为依傍的劝善抑恶说教,则体现了流人的价值观念体系,反映了时风的变化。鬼怪故事的创作基础是人类社会的生活万象,儒家教化思想与宗教因果轮回下,对西域故事的搜奇志异,表现形式虽为愚昧、迷信的神鬼灵异事件,却体现了遣戍文士对西域民情风俗、地理舆地的叙写方式,通过对其文本深层内蕴的分析,可解析边地、流人之间互为阐释的关系,这些“怪力乱神”的创作疏导了遣戍文士的心理情绪,所虚设的“鬼怪”世界,是清代流人在现实中遭遇西域地域文化及自身经历所面临艰难险阻的折射,他们以此为端绪,杜撰各种系列怪诞的鬼怪故事,重组个人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与行为准则,重新教化、规范读者的行事标准,在自我影写的“志怪”文学创作下,间接表达了他们的政治隐喻与情感诉求。
注释:
① [美]罗威廉著,李仁渊、张远译《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72页。亦载于[美]Joanna Waley-Cohen(卫周安).Exile in Mid-Qing China:Banishment to Xinjiang,1758-1820《清朝中叶的流放:发配新疆,1758—1820》,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② For a study of the supernatural legend as a genre,and its ideological nature,see David J. Hufford,The Terror that Comes in the Night: An Experience-Centered Study of Supernatural Assault Tradi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2.
③⑩ [美]段义孚(Yi-Fu Tuan)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123页。
④ [晋]干宝著,谢普译注《搜神记》,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版,第85页。
⑤ 此问题的相关内容,可参考[日]小松和彦《妖怪学新考 妖怪からみる日本人の心》,讲谈社2015年版。
⑥ [美]史景迁著,温洽溢、吴家恒译《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0页。
⑦ 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一百四十三,民国17年清史馆本,第4036页。
⑧ [清]赵翼《瓯北集》卷四十二,清嘉庆十七年湛贻堂刻本,第491页。
⑨ 刘燕萍《古典小说论稿》,台湾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