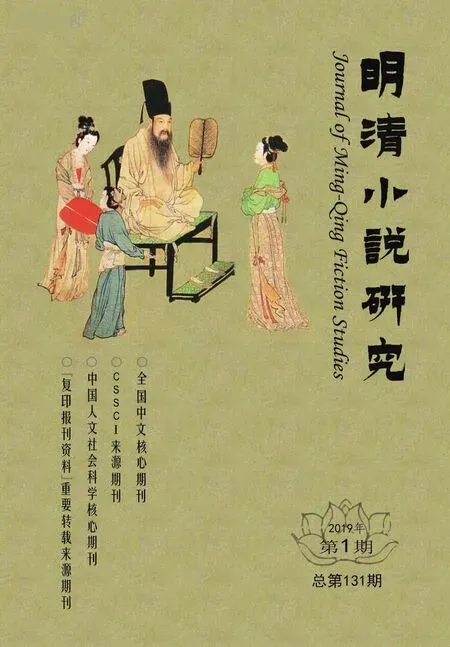焦虑中的禅意之思:贾宝玉与塞林格笔下青少年之比较*
2019-09-29··
· ·
内容提要 玄妙的佛禅义理为东西方文人提供了精神超越的自由空间,《红楼梦》与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都在探究人生的终极价值及人的终极关怀命题,贾宝玉与塞林格笔下的一群青少年在相似的困境中,执著于禅宗求真意识,守护着本真,捍卫着精神的纯洁性,在经历了对无执无念的顿悟后选择了超知性、超功利的审美生存方式,了却生死困顿,以充满诗意的孤傲美超越一切异化现实带来的烦忧,以禅意之思伴随着澄澈的审美境界解构着焦虑。
思是人类对自身生存价值及生存意义的追问与探究,当笛卡尔自豪地喊出“我思故我在”时,人类曾经为之扬眉瞬目,并把它看作向上帝及诸神挑战的宣言。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以二分的世界观为基础的对象性的“我思”,恰恰是对“我在”的猎杀,因为它压抑了富有生命力的浪漫幻想,污毁了原本安宁和美妙的感官世界,使得我们只知人的社会服从性,不知人的个体超越性,只知苍白理性,不知血肉情怀,被权威的社会所控制,被功利与欲望剥夺了心灵的感悟和诗意的追索。于是,深感困惑的西方人一再慨叹“无家可归状态成了世界命运”(海德格尔语),弗洛伊德的“我在我不在处思,我在我不思处在”,克尔凯郭尔的“我思故我少在”便被誉为大彻大悟之语。而东方禅家的玄妙之思不仅以反权威的独立精神、适意的生命体验及纯净、空灵的审美意蕴给我国文人提供精神超越的自由空间,西方文人亦在惶惑于世界的荒谬、彷徨于自我精神的困境之中对禅宗进行着不同角度的选择,捕捉禅之现代意义,寻求心灵的解脱与拯救。如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品中,同样焦虑的人们在禅思中抚慰着曾经的狂乱心境,而作者即于禅悟中将对个体的深切关注引向具有旷达韵味的人生哲学。这样,《红楼梦》与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就有了比较分析的可能。
有学者提及,《红楼梦》的深刻意蕴在于“从根本上追问和体验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写出了不同时代的人所共有的体验和感受”①,同时,禅意的渗透与浸润,使小说的精神内涵更得以丰富与深化。迷恋禅学的塞林格也一直都在试图从禅境中探究终极关怀的命题。贾宝玉与塞林格笔下的一群青少年有着惊人的相似,前者是贵胄子弟,在看似优裕的生活中却满怀惆怅和叹息,后者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世间喧嚣而带来的精神负累无法安顿,身陷困境中的他们,因其独特的人格和对于社会负面性表现出的决绝的精神恶心而不能和粗陋的物质世界共存并在其中苦苦寻求栖息之地,为了克服这种疏离感走上自我追寻的旅程,或恣肆无忌地挥洒生命的灵性和本真的自我,或以不为物拘的襟怀参禅悟道,由此给在异化社会生存的焦虑个体指出消解对立之路。
一、守护本真:关于生命境界之思
心性论是佛教文化的主题,也是禅思智慧的核心,所谓“性”就是人性的本来面目,即本觉真心,心是世界的本体,性是心的本质。六祖慧能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②在禅家那里,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心的本质是清净、澄明。而当世俗纷扰剥夺了生命的诗意,对于本真的追寻便成为贾宝玉和塞林格小说中诸多青少年执着的目标。不过,每个人会在相似的困境中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渠道表达并守护着本真,捍卫着精神的纯洁性,在敏感自我与恶浊俗世、精神与物质、入世和出世的二元对立冲突中由“生命之轻”走向“生命之重”。
中国人的生命境界在曹雪芹看来是一种病态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荒唐状态,是“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的矛盾痛苦状态。一首《好了歌》是关于“世人”信仰危机的歌,不仅流露出事与愿违的失望之情,更透露出“世人”在世空无所依的绝望之叹。信仰的危机,主要就是从这种在世的空无所依中产生出来的。贾宝玉的忧虑来自人之“灵性”的被遗忘,故以率性的言行举止守护追求着“真”:不喜孔孟时文八股,对经典提出质疑并进行拷问,厌恶仕途经济,嘲讽“文死谏,武死战”;视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无稽之谈;不愿结交贾雨村之类的官僚,称他们为“禄蠹”……贾宝玉在世俗眼里是一个永远读不懂、闹不明白的“呆子”“傻子”,是不能成为栋梁之才的蠢物,是人格扭曲的“另类”,而这种扭曲恰恰是对人性本真的守护,超越礼教、纵浪大化、放任自然,在文明者眼里就是离经叛道的“疯子”,他甘愿成为“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众矢之的,凡劝他读圣贤之书、走入仕之途的,无不引其反感,受其奚落。在宝玉看来都是真实自然的个性显现却在各种社会规范、家族规范、人生规范中变得言不由衷的虚假,而他却在这种“礼”的拘囿中守护着生命的本真,提升着生命诗意的高度。
塞林格小说中年轻的主人公们亦如此,同样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霍尔顿(《麦田里的守望者》)不喜欢“求学问,出人头地”,抵制潘西学校那种思想简单的集体精神,否定体现在他哥哥生涯中的那种典型美国式成功神话,不接受中产阶级的功利思想和虚假的唯理智论,于是他成了精神上的流浪汉、孤独痛苦的个体。西摩(塞林格笔下格拉斯家族中信奉禅宗的大哥,被作家描绘成佛的形象,总是以禅意教化引导他人)不愿融入于人群,甚至认为和他人的结合都是对其“诗意”以及“禅意”人生的破坏,故在女友及其母亲的眼里拥有“精神分裂”的人格,在心理分析师的盘问和过“不完美”的生活、接受自己及别人“弱点”的劝说下,执意于“道”之道以及诗的遐想。西摩的妹妹——大学生弗兰妮因世俗社会中的虚伪而格外痛苦,对炫耀自己论文的男友表示反感,指斥那些名实不符的教授、无聊轻浮、利欲熏心的伪精英,在无所不在的虚假中,在不被理解反而被认为无病呻吟、无事生非的状态下,痛苦得无法呼吸,晕倒在地。青年德·杜米埃-史密斯心烦意乱地嗅着空气中的酸腐味道,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喧嚣、肮脏令他沮丧不安。
贾宝玉的焦灼、叹息、恸哭更多地体现了对世事无常的慨叹和悲天悯人的无奈。美人迟暮,花开花落,人际分离……都会让他心生感伤,其中饱含生命郁结不开的悲剧意识,这已不再是对世俗法规的违抗,而是进入对人生在世及其意义的反思了。他希望能挣脱“假”的捆缚,永远与“真”相伴相守。从这一角度来看,宝玉的确与霍尔顿颇为相似,霍尔顿憎假求真,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悬崖边守护纯真,然而,在“假模假式的”现实中,理想趋向幻灭。宝玉的忧伤更在于其对真的守护换来的竟然是“真”的灭亡,最终唯独能找到的一方真实的所在,便是禅心。
生命的本真就是诗意的本真,既然贾府上下皆无真纯无诗意,宝玉便从大观园黛玉、晴雯、妙玉、香菱等众女儿身上去寻觅,只有她们最少被世俗恶浊之气所玷污,在诗性的追求中守护着精神的纯净。《红楼梦》从生命美学的视角看,就是以众女儿为代表的精神符号如何与以男人为代表的肮脏的世俗符号相对抗的历史,这也是作品中“男女泥水论”的深刻含义,是诗性与俗性纠结的具体体现。而对这些姑娘们,宝玉亦亲疏有别,之所以疏远宝钗、袭人而亲近黛玉、晴雯,其原因就在于前者绝无后者那般真实,特别是黛玉这个净水世界中的女儿,更是宝玉的精神领袖,曾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点破宝玉。刘再复先生指出这八字禅思禅核乃是《红楼梦》的“文眼和最高境界”③,这是黛玉对宝玉的诗意提示,已达到惠能“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相同境界。世上本无一物,何必执著于功名物质?黛玉已超越了离合之缘牵扯,引导着宝玉走向生命的纯粹,而贾宝玉人生“其实就是一块多余的石头否定一个欲望横流的泥浊世界”④的经历。
在塞林格小说中,可爱聪慧不带有任何矫饰的女孩身上同样也是集中体现着理想化的本真人格。作为“善与真”的化身,她们能够以未被异化的本我意识做出合乎天性的自然选择,能够在主人公面临精神危机或生死关头作为救赎者给予他们启示。禅宗所谓“本心”或“本觉真心”,即人性的本来面目,是本真人格的特质之一,真实无瑕,无虚伪,无掩饰,具有超越性和澄明性的特征,没有受到任何世俗尘埃的浸染。在塞林格作品中,最早出现的具有本真人格象征意义的是《最后假期之最后一天》中的玛蒂,在哥哥贝比看来,在那一群刚听完《呼啸山庄》朗诵的女孩中,只有玛蒂是真心希望凯瑟琳和希刺克利夫而不是和林顿在一起,因为后者是世俗社会的代表,希刺克利夫则是更加真实的反世俗的代表,其他人则根本不喜欢《呼啸山庄》,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好成绩而已,他赞赏的就是妹妹超功利的脱俗气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霍尔顿的妹妹菲芘同样代表着浊世中难得的纯净与温暖,给霍尔顿灰暗的生活增加了一抹亮色,给予他寻回本真的热望。《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中,如天使般形象的女孩西尔比的言行戳穿了成人社会里的社交面具,连被视为“不会任何社交微笑”“每一个表情都是真诚的”⑤西摩都被反衬得似乎虚假了,其率真无邪是世俗世界中充满矫饰的“常人”们所欠缺的,从她身上,西摩似乎感受到人在本真天性中自我反省并得以救赎的可能性。《弗兰妮与祖伊》中,伤心愤怒感觉到房间里到处都是幽灵的祖伊被窗外与狗玩耍的七岁小姑娘所吸引,透过女孩的纯真发现了美的存在;《抬高房梁,木匠们》中,巴蒂从自己见到的以及哥哥西摩诗中提到的小女孩那里亦感受到本真的呼唤……
禅宗把“心”作为哲学和美学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柱,主张“明心见性”,保持自家本来面目,“本心”在佛禅那里属本体世界,故超越于现象世界之外,不受现象世界的约束,可用“天不拘兮地不羁”来描述。诗人艺术家则强调反思人生,洞察灵魂;同时禅宗反对束缚、追求绝对自由的意识曾促使明清之际的文艺创作形成追求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潮,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王士祯、袁枚等人便是其中代表,他们蔑视程朱理学、名教礼法,独抒性灵,张扬个性,和贾宝玉不愿拘束于世俗礼教的人生姿态、任性恣肆的个性气韵一样,都贯穿着强烈的禅宗求真精神。而东方禅宗的痴迷者塞林格虽未深得禅中三昧,但其对权威蔑视与超越以及对本真的执着探寻隐于禅味十足的语言背后,深沉的反思便凝聚于此。
二、无执无念:关于生存方式之思
一般来讲,我们的价值选择常常会执着于对立二元之中的一元,而佛禅则强调对于任何一元都不能执着。禅宗之“禅”又称为本来面目、自见本心。人与万物不分的“无分别心”,就是禅宗的内在逻辑。它通过“无分别”的逻辑超越自我,寻求本心。禅宗美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惠能的“道由心悟”,到南禅提出的“即心即佛”,再到马祖道一晚年提出的“非心非佛”,“‘即心即佛’阶段还未完全摆脱个性与佛性、污染心与清静心的二元分别。‘非心非佛’阶段,人性与佛性、污染心与清静心之间就不存在区别了”⑥。按照禅宗的理解,人类烦恼源自分别识。六祖慧能在《坛经》中指出:“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⑦这里的善恶还包括是非、好坏、高下、圣凡有无、虚实之类僵执两边的相对观念,马祖针对那些不返心自求,却拼命向外追求,求而不得便痛苦烦恼的人们,提出“非心非佛”,正是意在强调要从对象性思维中抽出身来,重返真实的生命存在,不执著于彼此,这其实也是慧能“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思想的延伸。“无念”即不执著于念,自在无累,“无相”即不为事物外相所迷惑,“无住”则指不停留在执迷的心理状态,如是则会进入自由的空间。
《红楼梦》便以形象化的艺术表达传递出过于执着会导致“增病”的佛禅观念,假如不贪恋、不痴迷,就不会心生痛苦,所谓“烦恼即菩提”,就是把烦恼(有限)和菩提(无限)视为一体,排除了烦恼,等于排除了菩提。在此有限烦恼中悟得无限菩提,这就是一半入世、一半出世的过河脚不湿的自由境界,超越了世间困境而获得解脱。小说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中宝玉有感于人与人之间的难以理解、自己热情的空耗、活于世上的孤独,体验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句戏文的真实和残酷,不觉悲哀泪下,于是提笔立占一偈:“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自觉无挂碍,心中自得,便上床睡了”,虽据脂批,其悟为一时率性,非大彻大悟,但确是在痛苦中为自己找到了一方纷扰的现实所没有的清净之地。塞林格的《弗兰妮与祖伊》中出现了与此颇为相似的情节:“在美国那个充满虚伪与自我的荒原上漫无目的地行走”⑧的弗兰妮,蜷缩在洗手间的角落,甚至这里的四面墙壁都带给她无以复加的压迫感,眼含绝望的泪水,内心的痛楚逼得她行将崩溃。塞林格将弗兰妮塑造成美国知性丛林里精神救赎的寻求者,而当哥哥祖伊以巴蒂的身份启示弗兰妮“超脱、无欲”,弗兰妮释然地轻吸了一口气,把床清理干净,钻进被子微笑着睡去。
人类具有两种生命方式,一种是知性的、功利的非审美生存方式,另一种是超知性、超功利的审美生存方式,禅宗选择了后者,只向生命本体归依,不向外物和偶像归依。《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当袭人等担心宝玉将玉还给和尚会再犯疯傻之病时,宝玉肯定自己因已“有了心”不会再病了,即已恢复“本心”的清净澄明,跳出声色货利的圈子。原本“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的通灵宝玉即是“本心”的象征,佛禅强调为尘垢所污蔽而失去本心,其生命状态则迷乱癫狂,故当宝玉将其丢失时变得昏沉呆傻。弗兰妮也曾病倒,面色苍白,神志不清,晕厥在饭店,当然与宝玉所不同的是,弗兰妮的“病”是源自于被知性、虚伪、循规蹈矩等压迫的无能为力感,面对男友的自我吹嘘,她打断其自以为是的独白,将他膨胀的自我和那个以鼠目寸光的方式批评每一个作家的助教相比,她颤抖着独自在卫生间痛哭,昏倒之前她甚至承认自己快疯了,“我受够了自我,自我,自我,我的自我和所有人的自我。我受够了所有想去某个地方的人,想做出点成绩的人,想讨人喜欢的人。真恶心——就是恶心,就是”⑨。贾宝玉从与现实的不合并寻求精神出路到在禅悦中寻找寄托再到看破世情、渐入禅悟之境直至遁入空门,是无奈中的别无选择,更是对世俗名利的主动疏离,很多人是在追求名利而不得之后生发空幻之感,而宝玉则是身处富贵之家却已看出名利的空幻。弗兰妮的痛因为挣扎于世俗社会和纯粹本真所构成的精神家园之间而加剧,二人皆曾以“悟”放下心灵的重荷。
关于禅悟,铃木大拙有深刻的阐释:“悟可以解释为对事物本性的一种直觉的参照。它与分析或逻辑的了解完全相反。实际上,它是指我们习惯于二元思想的迷妄之心一直没有感觉到一种新世界的展开,或者可以说,悟后,我们是用一种意料不到的感觉角度去观照整个世界的”⑩,禅宗的顿悟就像一首诗,表现了禅者一瞬间的生命体验。塞林格因其犹太身份的尴尬及战争的伤痛而对西方文明的理性主义提出质疑,于是便在包括禅学及老庄思想的东方宗教哲学信仰中寻求精神依托,以走出困境,通过笔下那些经历了顿悟的年轻人,作家送给世人一种超越对立、了却世俗烦恼的人生抉择。《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里西摩和女孩进行了一番极具禅宗话头味道的对话,之后女孩告知西摩见到了那因吞下过量的香蕉导致身躯膨胀而无法游出洞口的鱼。不管这种鱼是否存在,不可否认的是,与满足欲望相随的是毁灭个体,而佛禅之意亦隐含于此:妄想因六根而起的执著,便会迷失真性,作家由此暗示西摩的顿悟。《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假期》里心绪烦乱的主人公以萨特笔下存在主义者洛根丁的生存感受厌恶着一切:街道、人群、司机、同学、同事、自己的生活、商店里摆放的搪瓷尿壶、便盆……甚至长期以来养成了坐下来承受绝望的习惯,倒是一副蕴含着禅意的水彩画令他痴迷,暗示着获得救赎的可能性,最终的瞬间顿悟实现于某个夜晚,在神秘的眩晕中,曾经令他沮丧的尿壶便幻化为精致圣洁的花朵。
当然,禅并未教导人们远离甚至弃绝现世人生,而是让人去除障蔽,超越相对,回归本心自性,即“明心见性”,随缘任运,日用是道。禅门有段公案如下:
师示众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功夫,总是痴顽汉。’你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境来回换不得。纵有从来习气,五无间业,自为解脱大海。今时学者总不识法,犹如触鼻羊,逢着物安在口里,奴郎不辨,宾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闹处即入,不得名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
临济慧照禅师在此提出真假出家人的区别,平常生活中只要放下执著,就是真出家人,反之,即使削发为僧,也只是俗家人。有学者指出:“《红楼梦》一书的妙处就在于能借人生本身蕴含的大机大势而出意境和情景。世人的种种痴心在宝玉那里纯化、境化为看似乖张之极实则醒人之极的痴情,以至满盘皆活,气韵生花。”宝玉的“痴”实际上就是禅宗那种不离生活日用处处可修道悟禅的识度,宝玉从第二十二回悟禅机到经历了姐妹夭亡和家族败落等大变故后“弃宝钗麝月”“悬崖撒手”出家为僧直至与湘云相遇并结合,正说明宝玉并未寂灭空无,而是顿悟之后重归红尘现世,如果真的离弃红尘,那并不是真正的禅悟。在塞林格的小说里,由于西摩的启示,巴蒂心中多了一种入世的领悟,他不再抗拒可怕的“307教室”,接受曾经内心厌恶的“身上散发着时代的错误信息”的女士们,消解了与世俗及他人的对立。德·杜米埃原本时时体味到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卑劣,处处感觉到周围莫名未知的喧嚣,顿悟后回归俗世。当妹妹弗兰妮身陷成长的困惑与彷徨中时,哥哥祖伊借用自己年少时西摩要求其为“胖女士”擦鞋的故事给予她启示:那位胖女士就是耶稣,而耶稣之所以是伟大的即怀有佛禅的不离众生而超越众生。禅宗的心性论缩小了众生与佛之间的距离,打破了此岸与彼岸、在家与出家、生死与自由之间的界限,倡导过着日常的现象界的生活,却又自在自得于盎然禅意、花草清泉亦或尘土瓦砾中感悟存在的真相,证得生命的永恒。
三、超越分别:关于生死之思
禅宗把人类思维分为“分别识”和“妙悟”两种,前者即对象性思维(逻辑思维),以二分的世界观为基础,是和科学、伦理、逻辑相等同的,固然,对象性思维可以解决政治、道德、科学等问题,但倘若以“分别识”作为生存方式,最终会使人类的生命世界丧失清纯、鲜活与丰富。正如铃木大拙所言:“逻辑对人、对人生的影响太深重了。逻辑已成为人、人生的主要内容,或者说,逻辑就是人、人生,在逻辑之外人便无所适从,人生的意义便无法证明。而如果依据逻辑来描绘完整的人生图画,其结果是人的思维活动必将遵循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法则,所谓生命力和自由便难以实现了。”逻辑就是束缚心灵自由的精神枷锁。
塞林格笔下有位十岁的早慧灵童特迪,拥有哲人般的睿智,在与他人的一段极富于哲学意味的对话中指出,静止的木头并非就是木头,一只胳膊并非就是胳膊,“逻辑是你首先必须摆脱的一样东西”。“你知道那只苹果是什么吗?逻辑。逻辑和智慧那类的东西。苹果里面全是这些东西。因此……你必须要做的就是把它呕吐出来,如果你想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话。”禅宗认为,世上事物本无凡圣、垢净、空有、善恶的区别,本无主体与客体之二分,然而,由于“人自虚妄计箸,作种种解会,起若千种知见,生若千种爱畏”,这样,就出现了主客体的二分,出现了概念与逻辑,如不消解这一切为自身带来的缺弊而沉迷于概念和逻辑的束缚,便不能进入生命的真实存在。为此,禅宗经常发生如下诘问:“两手拍有声,无两手,只手亦有声。”“如闻只手之声,也让我听听。”塞林格便将“吾人知悉二掌相击之声,然则独手击拍之音又何若?”一句置于短篇小说集《九故事》的扉页。独手击拍何以实现,世人皆知此毫无逻辑,禅师就是要破除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去掉逻辑,搁置功利,以一颗无尘无染的清静本心洞悉生死而获取生命的真实。在宝玉那里,逻辑理性便是中国经典文化的价值取向,都是人为设置的正宗和正统,都是值得怀疑和否定的无稽之谈。从笃信到质疑,贾宝玉留给世人的是一个决绝的背影。在质疑中他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对正统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肢解,揭示了这些价值取向下面藏着的无数“小”来。在他来看,现象永远都是质疑的对象,尤其是政治功利、社会伦理秩序,他希望人们超越这天罗地网的社会人生层面,走向自由澄明的审美之境。
伴随着对逻辑理性的探究,特迪还表达了对于生死问题的感悟:“大多数人甚至都不想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们甚至都不想停止老是这样地出生和死亡。他们只是不断地要新的身躯,而不想停下来与神共处,那样的境界才是真正美妙的。”故恰如预知生死的宋代德普禅师那般,特迪平静地接受自己死亡的命运,而西摩的自杀与其说是源自对世俗的绝望,更不如说是顿悟后对生死的超越。而对于人生聚散、生离死别这样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超脱的特迪与西摩似乎倒像是林黛玉,作为宝玉的精神导师,黛玉看得更深更透。在宝黛对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死”,其中心话题已经超越了世俗的甜蜜厮守和山盟海誓。二人对话经常话露机锋,含有禅悟的味道,很明显,宝黛二人的情感已如禅境,正如黛玉的禅语:“无足立境,是方干净。”宝黛之爱,至此已经超越了生死聚散,也超越了思念和牵挂的灵肉之分。
当然,《红楼梦》中时时萦绕着一股悲凉的气息,“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气场一直荡漾在每一回的字里行间,一曲《葬花词》包含着黛玉对生命“旅居客寄”的感叹和追问。人是匆匆过客,是“桃飘与李飞”,相对于“桃李明年能再发”,人的生命只是一张单行车票,失去而不可复得,最终也是“人去梁空巢也倾”“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于是这部生命哲学意味很强的巨著弥漫着生命迁逝、永不复返的哀伤,宝玉在生命的失落中也在不断地以死亡抗争,或许当绝望来临,选择死亡恰恰是对生的成全,更是对生命的捍卫,人活得越清醒,死亡的帷幕就看得越分明。但不管怎么样,宝玉相信生命精神的永存,“文死谏,武死战”,在贾宝玉看来都不是正死,而是邀功扬名的“不得好死”,一切外在于内心的死都不是正死,都是死名死节,这种死是对生的蔑视,是对生命的践踏。死是生的最后绽放而不是凋零,生生死死,自自然然,平平淡淡,那种所谓为名节的壮烈而死其本身恰是对生命静谧质朴的嘲弄和亵渎。从幻形入世重新回到天地浑沦一体的自然本真中去,正所谓“我所居兮,青梗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相比较《红楼梦》的悲凉,塞林格小说似乎少见大悲大喜的波澜,会让人品味到一种“哀而不伤”的审美韵味,虽然代表人性本真的美好时光在年轻的主人公们生命里留下怅惘的青春记忆,毕竟如佛禅所说万事无常,但作家更是将禅家适意、超脱的人生哲学寄予人物身上,使之少有癫狂与悲恸,而是以自悟的方式得到内心的平衡。
作为诗化宗教的禅宗空灵明觉地静观万物,认为生和死、动和静、空和实都是无分别的,既然万物为“空”,“无自性”,没有实体,也就没有生与灭、常与断,自我与非我、意识与无意识、有限与无限并存,此观点来自公元3世纪印度哲学家龙树菩萨的中观思想:在任何逻辑思想体系中,都无法找到真理;只有超越排他性和逻辑概念,才能把握真理。超越分别,心灵便可保持生命活力,而生命只有经过诗化的熏染,我们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无限趣味。“人类的诗哲本来就是自然精神的本体——人类生命本体的象征,人们正是通过它们的存在,才能体会和领悟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就是为我们展示了诗意生活的内涵。宝玉闻一缕幽香竟不知其所焚何物,警幻冷笑道:“此香乃系诸名山胜境内初生异卉之精,合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名曰‘群芳髓’。”那种叫“千红一窟”的茶也由“仙花灵叶上所带之宿露而烹”。那种叫“万艳同杯”的酒也是“以百花之蕊,万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麯酿成”。这香、茶、酒固然是作者自撰,一方面表现作者“悼红、怡红、颂红”的宏大主旨,同时也是对“人迹希逢,飞尘不至”生命品味的向往与追求。我们在读《红楼梦》时,往往会陶醉在那各种各样诗情画意的宴饮、赏花、扑蝶、葬花的诗境中。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我们揭示了生命沉重的原因是“被抛”到尘世,尘世里的情令人斩不断理还乱,那么,该如何面对如此的沉重,小说提出用“生活的飘逸”与之对抗。生命的“有”诞生于“无”(空),“有”即“色”(物质存在),在禅宗意识中,色是假象,心是虚空,即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心的本质是清净、虚空的,生命的美丽和沉重都源自“因空见色,由色生情”,而生命由沉重走向飘逸就在于“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宝黛二人就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在塞林格的小说中,盎然的禅家诗意来自于那幅澄澈清雅的画卷——白雁从淡淡的蓝灰色天空中飞过,“那淡蓝的天光”“天蓝的神韵”缓解了德·杜米埃—史密斯的焦灼;来自于特迪于吵闹喧嚣中对舷窗外漂浮在水面上的橘皮的玄想,执有增添了他人生命的负累,而特迪则在这玄想中专注着清静虚空的精神世界;来自于浸染着日本禅式文化的俳句——“路途何寂寂,无人行与此一秋日之黄昏”,这份静谧澹泊的情趣正是特迪所欣赏的;更来自于酷爱中国诗词及俳句的西摩诗歌中幽玄闲寂的意境:一轮满月下坐在草坪上的年轻男人和白猫,飞机上的小姑娘和身边的洋娃娃……空灵恬淡的审美表达赋予塞林格的艺术创作以诗化色彩。
所以很显然,在曹雪芹和塞林格笔下人物身上,都洋溢着浓厚的贵族精神,他们鄙视权贵,傲视陈规,无视生死,最后凝结为一种充满诗意的孤傲美。一部《红楼梦》就是作者对自我心灵的书写,是在“经历了人生困境和内心孤独之后,发出的对生命的深沉感喟”。当代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说过:“中国的氏族贵族传统过早中断,但也产生贵族文学的三个伟大个案。一是屈原,二是李煜,三是曹雪芹。屈原‘天问’之后找不到精神归宿,最后只能投江而亡,以‘无’否定现实的‘有’。而李煜和曹雪芹,皆走向大慈悲,把个人的忧伤化作对一切生命的大爱。用王国维评价李煜的语言,是‘担荷人间罪恶’,走向释迦牟尼和他们不知其名的基督,灵魂终究与释迦牟尼、基督的伟大灵魂相逢。但他们都不是救世主,而是自救的心灵的天才,都在审美中得到某种解脱。”对于塞林格,让霍尔顿、格拉斯家族的孩子们、特迪等青少年的故事传达出的信息是,既在现代社会里挣扎生存,又要在痛苦中寻找崇高和永恒的真理,并且利用这些人物不断进行探索,“最终进入所有信仰精神的和宗教的生命:追寻纯粹”。
结语
将写作视为禅思的塞林格一直试图通过对笔下青少年生活或信仰的修正,超越并消解异化现实导致的焦虑感,探究在多元宗教与文化背景下以及粗俗而物质的社会中如何保留精神自由的命题,在对压抑个性的异化社会提出反叛的同时,其作品更是充斥着对人类寻求精神归宿的人文关怀。或许感性个体的血肉泯灭了,便再也难以维系自身内在固有的激情、灵悟和冥思,《红楼梦》在崇尚个性解放及求真精神的时代下,融合晚明“童心”“性灵”之说的佛禅意识,把人从本真出发的审美之情发挥到极致,面对无法理解宝黛等人痛苦悲怆根源的芸芸众生们,发出了哈姆莱特式的对生命终极的追问,生命的觉醒也便赋予宝黛们悲天悯人的情怀,相较其实并未真正深悉禅家三昧的塞林格所构想的艺术世界来说,《红楼梦》更是将心灵的高洁及超拔的精神追求置于人生无限的荒诞和诡谲之上,让禅意之思伴随着澄澈的审美境界解构着焦虑,于滚滚红尘之中构筑起别样人生。
注释:
① 叶朗《红楼梦的意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② [唐]惠能著,郭明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③④ 刘再复《红楼梦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1、15页。
⑤ [美]塞林格著,丁骏译《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⑦ [唐]慧能《坛经·自序品第一》,杨五湖主编《传世藏书·佛典》,第282页。
⑨ [美]塞林格著,丁骏译《弗兰妮与祖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⑩ [日]铃木大拙著,耿仁秋译《禅风禅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