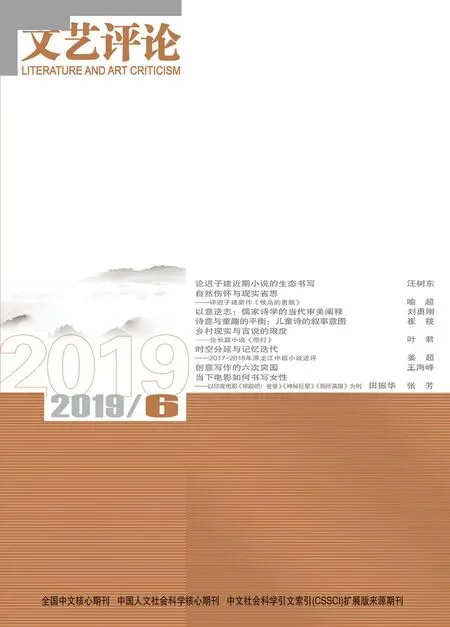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诗学思想及历史价值
2019-09-28○肖逸
○肖 逸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战国竹简出土,由上海博物馆发现并编辑整理,诗论部分现有完简加残简共29 支1006 字,因无书名,上海博物馆将其命名为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其内容是有关孔子对《诗经》的评论。在诗的篇目、诗的顺序、诗的用字上,《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诗经》有许多异处。《孔子诗论》是先秦时期诗学发展的重要证据,充分体现了当时诗学的思想内容与特点,这对后世研究先秦时期诗学内容和诗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一、《孔子诗论》的内容
《孔子诗论》记录孔子授诗的方法。这29支简的内容大致划分为八章,既有总括性的论述,也有条例清晰的分论,每一章都论述了有关《诗》的价值或功用。首章为总论《诗》《乐》《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举例《诗经》中的具体作品;第二章总论《颂》《雅》《风》所蕴涵的德性;第三、四、五章承接第二章总论,进而分论《周颂》《大雅》和《小雅》,偏重《周颂》,篇幅简短;第六章分论《国风》,以《关雎》《葛覃》为主要论述对象;第七章合论《风》《雅》;第八章合论《风》《雅》《颂》。整体来看,《孔子诗论》中涉及《诗经》中的具体篇目共58 篇,其中《国风》占据 29 篇、《小雅》22 篇、《大雅》和《颂》各有3 篇,由此可见,孔子对《国风》十分重视。在诗论中,孔子对诗义的解释是从道德和思想上来考虑的,虽然与今人观念中的《诗经》有所差异,但体现出孔子对《诗经》的独特见解,这对后世研究《诗经》的传世价值多了一重借鉴。
传世文献《诗经》按照内容分类,《毛诗》划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目前流传的《诗经》分类是以《毛诗》的划分为标准。《风》又称《国风》,《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个部分,《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三个部分。而在《孔子诗论》中,《风》《雅》《颂》分别被称作《邦风》《大夏》《小夏》和《讼》,在称谓上完全不同。据马承源解释,今本《诗经》经过汉代学者编辑而流传至今,早期古本现已亡佚,汉代因需要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而将“邦风”改称为“国风”。在《说文解字》中,“讼”与“颂”为古今字,“雅”与“夏”在古字中可以通用,所以即使《孔子诗论》中对《诗经》分类的称谓与后来所编纂的有所不同,但两者在原本意义上完全一致。
二、《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
(一)在崇诗的基础上释诗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崇诗的气氛十分浓厚,《诗》是重要的传承载体。对于孔子来说,其一生致力于“复礼正乐”,传播“中庸”之道、“大同”理想,为的是实现自己所期盼的“礼乐时代”再次到来。因此,在春秋战国诗歌如此普及之际,孔子解释诗的方式与春秋的用诗之道一脉相承。《孔子诗论》第一简中写道:“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无)隐志,乐亡(无)隐情,文亡(无)隐言。”开宗明义,概括出了“称王于天下”的前提条件,即通过《诗》来抒发意志、通过《乐》来表达情感、通过《文》来传达意涵,将《诗》《乐》《文》三者紧密结合,《诗》中所蕴含的情感就是《乐》与《文》情感的融合,这正是孔子通过对《诗经》中有关于“礼”的阐述,进而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志”。也正是通过“志”,孔子才能抒发对“礼”的情感。这样的表达可以具体概括为“诗”对“志”的作用,即“诗言志”。“诗言志”既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本质特征,也是先秦时期诗歌创作的公认标准。它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最早是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通过“感发意志”等方式来对自己的志向进行表达。①因而这一简具有整体上的总结性含义,整部《孔子诗论》是以这个命题为中心指导而展开论述的。将其置于篇首,总论《诗》《乐》《文》三者的关系,既符合先秦时期崇尚诗歌的时代风尚,也符合《孔子诗论》中各个章节分论点的整体阐述,为接下来的具体论述提供了主要纲领。
(二)重视诗歌的“性情”价值
《孔子诗论》着力歌颂诗歌中所蕴涵“性情”价值,普遍存在着“重情”的倾向。这种“情”指的就是人的真实性情。如“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中反复强调“民性固然”这四个字,这恐怕是有意而为之的。②在《孔子诗论》中,“民性”主要指的是“性情”,这是人的本原,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因而“民性固然”是指人的天性本来如此。而“性”与“情”又是不可分割的,“情”也是人性的一种本能,是“性”的一种直观表现。③孔子既以“情”字作为对《诗经》的评论,也以“情”为中心思想来剖析《诗经》中体现出的关于“情”的作品,这都体现着孔子的“诗言情”观。这也表明《孔子诗论》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尊崇人的本性。李泽厚认为:“孔子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来源。④先秦时期人们通过“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认为“诗”是表露心声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同时又是十分符合礼仪规范的。所以,纯粹的叙事诗很少,“诗”多用于抒发人内心的各种情感,文中所提及的“情”也是多种类的,如“《关雎》之改”所涉及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甘棠》之报、《绿衣》之思、《汉广》之智”所描写的是一种相思之情,“《燕燕》之情”所描写的是送别之情,每首诗以一个字概括出其中所蕴涵的情感,言简意赅又准确精炼,体现出孔子重视人的“性情”,进而将人性道德化。
(三)对“礼”“乐”思想的重视
虽然孔子重视《诗》的性情,以人为本,但并不代表情感可以不受理性的节制,可以超越理性而存在,孔子也强调调节情感,强调情感需要“礼”的约束和教化。《孔子诗论》十分重视对“礼”“乐”的思想表达,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处于“礼崩乐坏”之际,周王室逐渐衰微,诸侯僭越频繁,而《诗经》中充满这种孔子所尊崇的“礼”“乐”思想。
《孔子诗论》追求的是将“礼”与“情”融合统一,充分体现在“情”基础上“重礼”的思想。例如,第六章分论《国风》中写道:“《关雎》以色喻于礼。”而简紧接着写道:“《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等,都是通过对《诗经》中《关雎》篇的描述分析,表达孔子的“礼”是用来约束“情”的这一观念。即便君子有着内心的愿望也是不能随意表达,而是要遵守“礼”制的管束。再如第十三简“《汉广》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恒乎”,就是遵循礼仪而不做浪荡之举的最佳证明。⑤《孔子诗论》中重视“礼”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周王室先王的尊敬与赞美。因为孔子所推崇的“周礼”乃周公制定的王室之礼,所以要通过对周民族的先祖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赞美,来表达对礼乐制度的肯定。在第三章分论《周颂》这一部分写道:“《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前面说到《颂》的内容属于平正的德性,而《清庙》是赞美周文王圣德的至高无上,所以祭祀文王时一定要遵循礼制,有着恭敬谨慎的态度。在第八章合论《风雅颂》这一部分写道:“《文王》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同样表达孔子对文王的深切歌颂和赞美之情,这种浓厚的尊王思想,是孔子崇尚礼乐制度的突出表现,与孔子追求的“复礼正乐”观点是一致的。孔子在赞美周代先王美德同时,还通过叙述小人危害来劝诫统治者要重视贤才远离小人。在第五章分论《小雅》中,举出《十月之交》善于批评、《小宛》稍微接近“仁”、《小弁》《巧言》写馋人的危害等,都是通过讽谏的手法来劝诫在位者勿信小人、任用贤人,遵循文王的美德,成为明智的君王。
(四)以培养君子人格为目的的教化观点
孔子释诗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诗经》来教书立人,培养人们高尚的君子人格。孔子在向弟子授诗时,往往十分注意强调诗的社会功用以及诗对人们品行的影响。在《孔子诗论》中“德”“情”“志”等表述人们品行的词多次出现,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些品德的重要性。而当人们具有这些品德才能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君子人格。
《孔子诗论》中对《邦风》的评论:“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这里的“善”包含着“德”“情”“志”“礼”等美好品德的集合。《国风》能普遍接受所有人物,广博地观看风俗,广泛地汇聚人才,它的用语很有文采,它的声音充满美善,这是对《国风》社会功用的赞美和极高评价,从中可看出其所具有的教化功能。“诗教”学说发展了《诗》的教化功用,也较早建构了诗歌的社会功能理论,对中国文学史和美学史上的影响巨大而深远。⑥
三、《孔子诗论》的历史价值及影响
(一)蕴涵丰富的哲学思想和重要的诗学意义
《孔子诗论》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诗学思想逐渐发展、用诗现象十分普遍的背景下产生的,展现了先秦时期儒家的诗学观念,为后世全面理解《诗经》的社会价值提供了参考。
《孔子诗论》的哲学价值在于其论述始终体现儒家人性教化的思想,发现了人的价值,如对“情”“性”“德”等情感的谈论,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观念。“诗”不再是从纯粹的文学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和剖析,孔子赋予它们以“仁”为核心的哲学层面上的含义,尤其是它的“诗言志”“诗传教”等理念对诗学的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由于当时社会的礼乐文化背景,“诗”成了“礼”的象征符号,⑦而“诗”本来所具有的文学性则被掩盖。
《孔子诗论》推崇人的“性情”的价值、探讨“民性固然”的含义,又在“礼乐”基础上发掘出了“诗”中所蕴涵的真情实感,赋予了“诗”本来所具有的诗学意义。“诗”既表达了“礼”的规范,又不再是“礼”的附庸,具有了传达情感、关注民性的重要作用。孔子提倡的“学诗”和“用诗”,既是提高个人修养的章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礼乐”规范,而且对后世的《毛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的“诗言志”就是《毛诗》继承《孔子诗论》中的诗学思想,这种文学性的传承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间人们对《诗经》的解读。
(二)具有创新性的价值
《孔子诗论》是目前为止所出土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专门论诗的理论著作,在此之前从未有体系如此完备、逻辑如此严谨的论诗作品。《孔子诗论》集合了周代前人的传统思想和春秋时期社会上的流行观念,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论诗理论。内容简约,体制短小,却层次分明,逻辑严密。
《孔子诗论》的出土也正好印证了传世文献《论语》中所蕴涵的孔子的诗学思想。由于《论语》并非孔子所著,是经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的语录体文献,其中所体现的孔子的诗学思想,后人往往只能从只言片语中进行剖析,对孔子所重视的“诗”学会有多重阐释甚至讹误,再加上孔子一生致力于教学,称自己“述而不作”,因此,流传下来的研究孔子思想的原著非常有限,而《孔子诗论》的出土则更好地填补了这一缺憾。其系统地对“诗”的内容及价值的阐释与《论语》中的诗性观念得到了相互的印证,使人们可以正确地理解孔子的诗学理念,更能纠正历代对《诗经》的注释中所出现的多种观点中的错误。
(三)具有社会教化的功用
孔子论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借“诗”来教化世人,传递儒家的思想观念。《孔子诗论》中“礼”“乐”“德”等字眼多次出现,可以看出孔子在解释作品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将诗的内容与人的德性和政治理念相融合。孔子提倡恢复周礼,重建社会稳定的政治秩序,将诗歌中蕴涵的君子高尚品行提取出来加以赞美与发扬,这都表明孔子将《诗》看作是周代的礼乐制度的一种文学体现。传统的诗歌是需要配合着舞乐演奏来展现给统治者以观风俗的,在孔子眼中“诗”不仅仅是礼乐制度的本身,更是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背景下用以教化人伦、复礼正乐的重要凭据。
传世文献《诗经》共有305 篇,另有6 篇《笙诗》有目无词,这是经过孔子“删诗”改编而流传下来的篇目。先秦时期的诗歌何止305 篇,孔子进行删改也是有意为之,选取了其中符合儒家思想教化的篇章加以评定,赋予了它们深层次的意义,教授弟子“不学诗,无以言”,将“仁”与“衷恕”的儒家核心思想与“诗”中所蕴涵的礼乐文化体系相融合,在哲学的层面上升华了“诗”的教化意义和政治作用,不仅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在汉代更是成为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思想主导,而且在此后两千多年中维护了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伦理与政治体系,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
“诗”的流传发展到汉代,已出现“齐、鲁、韩、毛”四家诗,其社会地位显著提高,社会功用价值也明显增强。在西汉初年,“诗”被正式列为“经”类文献,足见《诗经》有着重要的教化作用,体现了统治阶级对它的重视。在汉代以后,以“诗”言志的表达方式以儒家思想为载体继续传承下去,诗的内容和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文人也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大量地引用《诗经》中的典故。《诗经》也反过来影响了文人阶层的思想观念,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提升了人们的道德品行的修养。“诗言志”“诗言情”作为我国古代诗歌题材中最富有表现力的核心观念,历代文人的诗歌作品都着重通过这种创作方式,或直白或含蓄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世界。
总之,《孔子诗论》是先秦时期论述诗学的重要著作,它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诗学理论,探讨了“礼乐”“性情”的重要价值,集中体现了儒家传统的诗学观念。《孔子诗论》对“诗”的论述模式,从一个创新的角度发掘出《诗经》的重要文学作用,开创了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与诗歌批评的先河,尤其是诗论中所体现出的教化性的功用价值,成为了规范我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道德修养的主要依据,为深入研究先秦诗学与思想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依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①③杨铁梅《〈孔子诗论〉论析》[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②马媛媛《早期儒家“礼”“情”关系下的“以色喻于礼”思想》[J],《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106-109页。
④李泽厚《初读郭店竹简印象记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⑤钱志熙《先秦“诗言志”说的绵延及其不同层面的含义》[J],《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5期,第6-18页。
⑥董碧娜《孔子诗教观探索》,[J]《文学教育》(上),2018年第4期,第149页。
⑦王秀臣《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诗学结构及其意义》[J],《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2期,第171-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