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东流去》为何三十多年仍不褪色
2019-09-25陈浩文
陈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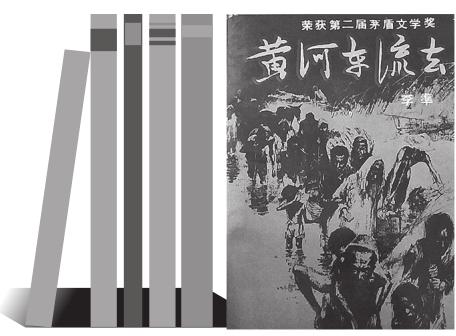
在小说《黄河东流去》的《代后记》里,作家李凖回忆了1942年自己作为流亡学生在逃荒途中的所见所闻:
当时的陇海铁路线,是一条饥饿的走廊,成千上万的难民,向西边缓缓地移动着,他们推着小车,挑着破筐,挎着篮子,小车上放着锅碗,筐子里坐着孩子,篮子里放着拣来的草根树皮。
饥饿,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灾荒年代的主题。饥饿,不仅意味着死亡,还意味着秩序的混乱,意味着作为尊嚴的丧失。
《黄河东流去》写的正是赤杨岗七户普通农民家庭在灾荒与饥饿中的生活。小说开头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花园口”事件。黄河堤坝被挖,直接导致河南、江苏、安徽三省被淹。上千万百姓流离失所,赤杨岗的农民便是其中之一。在“花园口事件”之前,赤杨岗的村民虽然贫苦,但是有固定居所,有家人朋友,日子有盼头。李麦是死了父亲和丈夫的寡妇,为人直爽刚强,儿子海天亮在黄河上跟着艄公梁恩老汉学艺;徐秋斋是赤杨岗村的蒙学先生,虽然私塾没落,他在村中仍能靠算命糊口,也颇受村民照拂;海老清、海长松、春义、王跑等人是家庭和睦,基本能自给自足的农民;陈柱子、蓝五等人,则靠着自己的手艺在赤杨岗长期定居……
“花园口”事件发生后,赤杨岗一众村民在逃难途中离散,每家每户的故事各有不同,但大都不幸。李麦和儿子海天亮成为抗日队伍中的一员,但小女儿嫦娥流落他乡,下落不明;长松、海老清等家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在城市流浪。这些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民,在进入城市之后,原有的伦理关系遭到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海老清的女儿爱爱为养家糊口,成了女说书人。这直接导致父女关系破裂,邻里关系疏远,海老清最后饿死在伊川县的农村。春义的妻子凤英努力适应城市生活,在金钱的驱动下,自力更生开饭馆,却因为春义无法认同妻子抛头露面的行为,二人的夫妻关系逐渐恶化,最终离异。在李凖的笔下,这些失去了土地和家园的流民,没有一个人在灾荒和饥饿面前,能够维持自己身为“人”的体面。
当代作家的作品中不乏对灾荒年代人性沦丧的描写,譬如莫言的《丰乳肥臀》里那些为了一个馒头抛弃贞操的女性,又譬如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中那段40年代河南饿殍千里,老百姓为了一口救济粮可以随意向传教士下跪,甚至为了活下去不惜人吃人的历史。虽然在这些作家的笔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灾难有时似乎沉重得过分轻易了。李凖的难得之处在于,他没有一味地去塑造人间地狱般的图景,造成读者心灵上的恐惧,赚取善良读者的眼泪,而是着重表现了中国普通劳动人民在困境中迸发出来的惊人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仅仅是求生的欲望,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熄灭的人性之光。
李凖曾这样自述自己的写作目的:
我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称量一下。
中国农民的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是李凖在这部小说中想要探索的主题。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份初心,有这样一份对农民、对民族甚至可以说对“人”的信仰,作家在处理“难民”题材时,才不至于把小说变成再现历史惨景的冷冰冰的媒介,而给读者带来了一幅厚重而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画卷。
从整篇小说来看,《黄河东流去》的人情味体现在老百姓质朴的家国观念、人伦情感和道德原则中。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细胞”,他们真挚地热爱着自己的土地和国家,痛恨着日本侵略者。小说中海老清和长松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他们一生的信念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长松耗尽家财,就是为了拥有十亩属于自己的土地。花园口决堤,洪水淹没的不仅是土地,还是“他的心血和希望”。海老清相信只有在土地上劳动,才能“活得干净、活得清白”。他对土地的眷恋,除了劳动的信念之外,还表现在对牲畜的情感上。农民喂养的牲畜对他们而言已经超越了耕作工具的意义。在海老清眼里,买回来的小牡牛“简直成了他的大孩子”。小说对海老清的小牡牛用了许多拟人化的词语来描述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当牡牛被胡乱征用致死时,海老清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在你看来,它是畜牲,你是人,在我看来,它却是人!你们知道我们做庄稼人的心吗?你们知道我们把牛当作一口人的?……
海老清对崔副官的声声质问,既有不能挽救牡牛生命的痛苦,又有对国民党部队在抗日上不作为,只会一味压榨百姓的痛恨。小说中农民的家国观念,就是这样通过他们对土地的深厚情感传递出来的。
在李凖的理解中,中国的“国家”观念里,“国”与“家”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家”是组成“国”的基本单位。《大学》讲“家齐而后国治”,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经营是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家庭的经营,离不开夫妻、父子、兄弟之间的伦理情感、血缘亲情。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将“孝悌”视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中国人正是在这一套文化传统的熏染之下,形成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黄河东流去》这部小说不同于一般“难民”小说的地方,恰恰是作家极为细腻地写出了失地流民家庭的这种伦理情感。
小说中无论是海老清还是海长松,都是极其疼爱子女的父亲。海老清只有两个女儿,但是“平常他待这两个女儿特别娇,从没打过一巴掌,骂过一句,家里不管再困难,过年时总要给两个女儿买一双袜子,扯两尺头绳”。当女儿爱爱沦为农民观念中的“下九流”说书人时,海老清也努力地去理解她的行为,但爱爱与军官关相云的纠缠最终使他失望离去。然而即使海老清和女儿在生活观念上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也无法割舍。海老清临死之前最终原谅了女儿,说出了“她没有罪……我都能体谅她们……”的遗言。
《黄河东流去》中的家庭伦理情感的动人之处,不只父母对子女的爱,还有家庭成员面对灾难彼此牺牲的勇气。海长松一家在洛阳遭遇大旱灾快要饿死的时候,女儿秀兰和玉兰先后为救家人自卖自身,为家人换来了维持生计的粮食。小说中刻画了许多坚毅的女性,她们命运坎坷,却可以为家人牺牲一切。而这些家庭中的男性,并不是心安理得地接受女性的牺牲的。当他们被灾难打压得无力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时,面对女性的牺牲,他们是自责而愧疚的。小说中当长松要面对卖女儿来维持家人生活希望的困境时,“他感到自己犯了弥天大罪,他浑身哆嗦了一下,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皮鞭,在抽打着他的灵魂”。李凖笔下的这些人物,并不是“高大全”的化身,各有各的性格缺陷。但这些普通人物,都不是为生存本能折磨的“鬼”,在灾难面前,依然有对亲人的无私感情。正因为如此,小说中长松一家的悲剧才有了光彩,显得深刻而隽永。
在家庭之外,小说还写出了赤杨岗村民的邻里之情,以及男女间忠贞不渝的爱情。当家园被淹时,赤杨岗村民没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而是努力互帮互助。徐秋斋在赤杨岗村,是一个平时爱在各家蹭饭,占点小便宜的滑头。在逃难途中,他却展现了中国传统下层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情操。当王跑的驴子被缉私队讹走时,他能够挺身而出为王跑讨回买驴子的钱;当梁晴、嫦娥和李麦失散时,他担起了照顾晚辈的责任。李麦作为小说中贯穿始终的正面人物,她的行为最为典型地反映了赤杨岗村民的人性之善。她敬爱老人,当申奶奶不愿拖累乡亲,打算死在家中时,她坚定地表示“走不动路,我们背着你;要不动饭,我们给你要”;她善待晚辈,在赤杨岗,她是唯二平等对待四圈的人;在逃难途中,她是主持晚辈家务事的主心骨。而梁晴和天亮,蓝五和雪梅,这些年轻人尽管长年分别,但他们始终为对方保留了最纯粹最忠贞的感情。赤杨岗村民面对灾难表现出来的团结友爱,青年男女愛情的至死不渝,正是中国劳动人民道德观念中最为光辉的一面。
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发表之后,曾获得了80年代批评家们的高度赞扬,被誉为“新时期我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来读这部小说,可以说它的光彩是没有褪色的。这不仅是因为作家在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立场和严肃的艺术态度,还因为他通过塑造一系列的典型人物,让读者发现了中国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当下实现“中国梦”,建设当代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