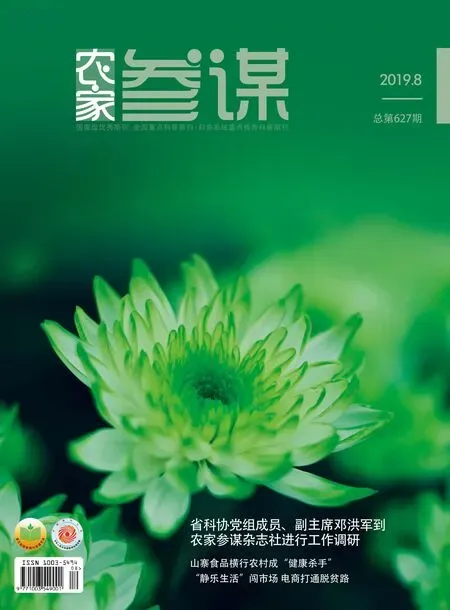乡戏
2019-09-25张俊苗
张俊苗

过去的乡村里,几乎村村都有庙,龙王庙、女娲庙、三皇庙……有庙就有庙会,逢庙会必唱戏;戏是唱给神听的,说到底,挤在台下那些一脸焦苦看戏的人,其实不过是蹭戏的。
戏楼一般正对庙的正殿,雕梁画栋很是精巧,台上唱戏,台下拱桥式的过道里专供村人自由出入。
一些山庄窝铺、圪圪梁梁的,拣地方盖个山神庙也窄小寒碜,自然也就没有了唱戏的场地。好在村里唱戏一般都在秋后,庄稼收了,农人闲了,戏台就搭在刚腾出的庄稼地里。一旦定下要唱戏,方圆几里的年轻人都被招呼了来,多半天的工夫,就能用木头檩子在空地上搭座戏台。
山里人生活粗糙,心却不粗糙,村里有专门写戏的人,被派去写戏的人,走个三五日,要货比三家,察听了又察听,才能把剧团定下来。
一个村唱戏,牵动得方五八村都群情高涨,把排子车拉出来,用笤帚把灰土清扫干净了,备上牲口,有舅舅去接外甥的,也有女婿去接丈人、丈母娘的,山沟沟里,两辆排子车碰一块了,面生面熟的都互相打招呼:“去瞧戏啊?”“可不是吗!你也去瞧戏啊?”“是嘞!是嘞!女婿来接了。”脸上的皱纹涌到了一起,堆成一朵花。
戏一般是上党梆子或者上党落子,有时候也唱豫剧,不管啥剧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喜欢瞧老戏,一出戏瞧它十几回也不觉得腻,那一腔一调,都熟悉,唱到高潮处,台下人就喜欢摇头晃脑地跟着唱——说到底,乡人看戏,不为新鲜,只图过瘾。
等杀了戏,不管自己日子过得好与坏,总要大方一回的,在戏台下称一二斤麻糖(油条)拎着回家。麻糖一溜一溜在案板上摞得老高,卖家称好了就用土黄色的草纸和纸绳包扎好,乡人在接麻糖时,动作一定是很夸张的,脸上写满了舒畅与满足。
如果说大人瞧戏为的是放松、图的是过瘾,小孩子瞧戏就完全是凑热闹了,但凡邻村唱戏,都要哭嚷着硬跟了去,即便黑夜也一样。于是,大人、孩子,拿了手电,一行10多个人,沿着山沟沟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小孩子不敢走前边,又不敢落到最后边,挤挤抗抗地走在人群中间,偏有胆大的孩子,指着斜对面的山梁喊:“快瞧!鬼灯!”抬眼一看,果真见山梁上有两个飘飘忽忽的圆球,遂尖叫着扑进大人怀里。此时,大人一定是要骂的:“瞎嚎叫啥?哪有鬼灯?那是马灯!”心仍然扑通扑通跳得厉害,但还是抬眼仔细看了,果真是马灯,是赶着去看戏的人手里提的马灯。
到了戏台下,孩子们也看不出个孬好来,只看见戏台上一片花花绿绿的人影,看着看着就倒在大人怀里睡着了,回去的路上,都是被父母背回去的,风声尖利,小人儿却一个个睡得死沉。
印象里是和母亲去公社看过一回戏的,是个深秋的下午,那天快杀戏的时候,正好碰上了我五姨。从戏台院里挤出来,路便岔开来变成“Y”字形了,较宽敞平坦的那条通向姥姥家,由于去往我家的那条山道崎岖难行,母亲就让五姨把我领到姥姥家去(那会儿五姨还未出嫁),我一听,就哭喊开了,要让母亲跟着一块去,可是,家里有猪、有鸡,夜里得有人照应,最后,母亲还是掰开我的手,狠心走了。
至今忘不掉那个黄昏——我伏在五姨背上,伸着两手、扯着嗓子喊娘,隔着一条山沟,母亲在对面的山道上一边匆匆赶路,一边应着我一声紧似一声的哭喊。
等我到了入学的年龄,父亲几经周折把家迁到了邻近县城的一个村子里。村属于大村,早年过庙会唱戏也是在龙王庙的戏楼上唱的,后来因为那个龙王庙紧挨村里的小学校,只要一唱戏学生们便得停课放假,于是,村干部便另挑了一块平坦的场地盖了个大戏院。
戏院很气派,有红砖围墙、有黑色的铁大门,而且戏台下还安置了100多条水泥长条凳,这样,看戏的时候,村人就省去了拎椅子、搬板凳的烦琐。小孩子们一放学,便如鸟雀一样飞到戏院里去占座位,他们跑到戏台下,专找前几排正中的位置,用绳子把家里带来的麻袋片、蛇皮袋或者硬纸壳绑在水泥条凳上,表明这一截的位置属于自家的了,别人是无权侵占的。
费尽心机占来的位置是留给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的,小孩子是不看戏的,一到晚上,当大人们看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软硬兼施,待讨到三毛五毛钱,就泥鳅一样钻出人群,买零食吃去了。
年轻人也不是真心来看戏的,不过是找了个由头,来戏院和恋人调情叙旧罢了。他们一般不坐,喜欢三五成群地站到水泥凳的边缘处,双手插在喇叭裤的裤兜里,大声地说笑。那些订了婚的,自然挨得近一些,以便在黑暗里偷偷攥一下手;那些没有对象的,就东张西望,一旦在人群里眊上个顺眼的,小伙子会怂恿自己的同伴和自己一起挤过去,找个理由搭讪。
我真正迷上戏曲,已经有十一二岁了吧。记得一次我随母亲去看戏,那晚唱的是《珍珠衫》,那个扮演蒋兴哥的女子嗓子清亮,而且扮相好,一举手一投足都勾人魂魄,我竟然看得入了迷。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天,我就吵着还要去看戏,由于那天下午母亲有事走不开,还有就是我家离戏院较远,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去看戏,后来被我吵烦了,就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不就是看个戏吗?我感到无比的委屈,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从那之后,每逢节假日,我就盼着父母外出,只等他们一走,我就把我的好伙伴们召集来。我们把沙发巾、被单都披到身上,然后每人到院子里掐一朵花,插到鬓角,然后就开始咿咿呀呀地过戏瘾。有段时间刚好电视里演越剧《红楼十二官》,我们几个女孩子竟然为了争演一个角色而吵得面红耳赤。
后来我痴迷上了文学,闲暇时喜欢看书,就疏远了戏曲;但没想到多年后我转了一个大圈子又绕了回来,为了写剧本,我开始重新走进戏院,重新站到了戏台下。戏依然是当年那几出老戏,台下看戏的多是耄耋老人。
几年前我曾和县文化局的人去市里看过一次京剧《霸王别姬》,戏是折子戏,那个虞姬身上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柔美,舞剑时翩然娉婷、惊鸿照影,剧院里静悄悄地,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生怕错过了某个细微的动作。回来的路上,大家都说这戏看得不过瘾,都觉得京剧过于“静”了,少了上党落子的那种喧嚷和闹腾。
前些时候,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和市里的赵宏伟老师聊了一个多小时的戏曲。他说,京剧是“剧”、上党落子是“戏”,“剧”和“戏”是有区别的:“剧”侧重于剧情,而“戏”则更侧重于唱腔。一席话真让我有胜读十年书的感慨。但说老实话,可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缘故吧,对于生于山野、长于山野的我来说,还是更喜欢我们太行山的戏,喜欢它那种响彻云霄的酣畅淋漓、喜欢它那种土得掉渣的喧嚷和闹腾。
相关链接
河南戏曲“家底”大盘点
作为中国戏曲之乡,从明代万历十年算起,相继在河南境内产生、存在和流行过的各类剧种有近80个,其中戏曲剧种65个,属本土产生的占2/3。400多年来几经兴衰,几多蜕变,目前仅剩37个剧种,其余均已消亡或退出河南。
豫剧、曲剧和越调是目前仍广泛流传在河南各地的三大地方剧种,除此之外,另外30多个剧种生存状况不容乐观,有的已濒临灭绝。专家们将这30多个剧种归为四类:一是宛梆、怀梆、道情戏和豫南花鼓等4个河南独有的剧种和大弦戏、大平调、二夹弦、四平调、落子腔、坠剧等6个源于河南的剧种;二是嗨子戏、柳琴戏、清音戏、扬高戏、柳子戏、五调腔、山梆等7个剧种,分别与安徽、江苏、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交织串连,均已呈现式微;三是已经做过抢救工作的濒危剧种,如八调腔、豫东花鼓、丁香戏、蛤蟆嗡、梨黄、灶戏等6个剧种,残存的几位艺人先后谢世,其残留的曲调有关部门已录音记谱,另外,200多年前曾极度盛行的清戏、罗戏、卷戏3个剧种,有关部门已以对其进行过抢救性发掘整理;四是河北梆子、山东梆子、上党梆子、汉剧、京剧、蒲剧、秦腔、评剧、越剧、迷胡、黄梅戏、昆曲等12个剧种,虽然不是在河南本土产生,但曾在河南流传甚广。
据统计,河南地方戏的传统剧目有4000多出,从尧舜传说时代,到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有各不相同的剧目,纵贯时间几千年,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士农工商,以至天上的神仙,地下的鬼怪,可谓三教九流,无不包括其中,其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思想内容之丰富,是其他民间艺术不可相提并论的。长期以来,由于保护传统剧目工作不能持续进行,传统剧目正面临生存的危机。保护传统剧目,也是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势在必行的一项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