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的一个误读
2019-09-23张建辉
张建辉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鸠出生于法国波尔多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祖父曾担任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589年—1610年在位)的宫廷内侍,其父投身行伍,战功卓著。孟德斯鸠少年早慧,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父亲精心安排下,先后进入朱伊公学和波尔多法学院学习,170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成年后,孟德斯鳩生活优裕,交游很广,博学多识。1713年旅居巴黎期间,孟德斯鸠曾遇到由耶稣会士带到法国的中国教徒黄嘉略。孟德斯鸠的伯父是法尔多法院的一名庭长,在丧失独子后,他将职位和财产传给孟德斯鸠,1716年孟德斯鸠任波尔多法院的庭长,并成为波尔多科学院的成员。1728年,孟德斯鸠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为了解各国情况,于4月5日启程出游,游历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意大利、瑞士、英国等国,其间同多位名人交谈,其中还有一位从中国返回的耶稣会传教士。1931年孟德斯鸠回到法国后,从事著述,其中最重要的即《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从20岁起,就开始为《论法的精神》准备材料,对卷帙浩繁的各种民法著作,进行了条理清晰的摘录。为了将“世界各地的居民置于他们的实际状态和彼此可能发生的关系中进行观察”,孟德斯鸠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其中就有他本人收藏的《马基雅维里全集》。甚至在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孟德斯鸠也请人帮他阅读。因题材广泛,孟德斯鸠多次放弃,又多次拾起这一宏大的写作计划,他曾说:探索传之久远的历史和法律著作,如同面对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对“冷冰冰的、枯燥的、乏味的、艰涩的著作,统统都要读,要把它们吞下去”。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孟德斯鸠最终完成了这本巨著,1748年《论法的精神》在日内瓦发售,1752年出版意大利文版,1754年增补后的定本出版。1755年初,孟德斯鸠在巴黎染疾,2月10日去世,享年66岁。
《论法的精神》由“说明”“、序”和六编内容组成“,说明”是孟德斯鸠为回应冉森教派的指责而写下的,于1757年刊出。在“序”中,孟德斯鸠首先表明:《论法的精神》探讨内容众多,如果有冒犯之处,请求读者原谅,因为他本性并不喜欢与人抬杠。其次,孟德斯鸠请求读者认真对待这部耗费了作者20年心血的著作,不要粗翻几页,就妄下断语。孟德斯鸠对自己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原则颇为自信,认为自己的著作毫无突兀之处。孟德斯鸠丝毫无意贬斥任何国家业已确立的东西,认为只要自己的著作对民众、对国王有益,使人们捐弃成见,他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最后,孟德斯鸠历数著书的艰辛、波折,认为《论法的精神》的宏伟主题,以及自己的才具将能使该书获得一些成功。《论法的精神》第一编从“一般意义上的法”入手,探讨了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与法律的关系;第二编探讨了法与防御力、攻击力以及自由的关系;第三编探讨法与气候性质、土壤性质的关系,以及法与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风尚赖以形成的原则之间的关系;第四编伊始,孟德斯鸠插入“向缪斯女神祈求灵感”一节,因为《论法的精神》篇幅冗长,内容沉重,他想让读者轻松一下!接着探讨了法与贸易、货币、人口的关系;第五编探讨法与宗教、法与事物秩序的关系;第六编探讨法国公民法的起源与沿革、制定法律的方式以及法兰克人的封建法理论与君主政体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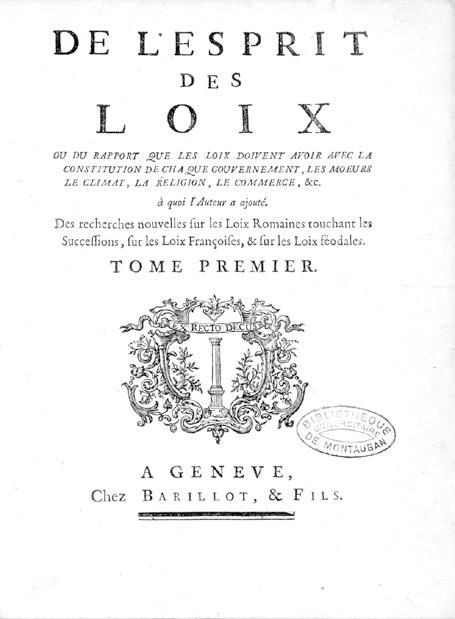
孟德斯鸠认为一度出现于整个欧洲的封建法,是世界上曾经发生过而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的事情。封建法通过将领主权利交给若干人,削减了整个领主权利的分量;封建法在疆域过于广阔的帝国中设置界限,制定带有某种无序倾向的规则,然而无序状态具有倾向秩序、和谐的趋势。具体到法兰克人的封建法理论,孟德斯鸠以宫相和采地作为考察的核心,认为宫相的崛起导致墨洛温王朝王权衰微,在教皇的支持下,王权与宫相的权力在加洛林王朝合而为一。
孟德斯鸠在论述法兰克人的封建法理论与君主政体建立以及君主制巨变的关系时,盛赞凯撒和塔西佗的著作,但是把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状况,与墨洛温王朝的历史直接相连,忽略了历史演进中的某些环节,最突出的是关于国王与宫相的问题。
孟德斯鸠指出,根据勃艮第法,宫相绝非国家最高职位之一,最初几位法兰克国王在位期间,宫相也不是最显赫的官职。由于法兰克王国当时存在奥斯特拉西亚、勃艮第和纽斯特里亚等几大势力,之后成为纽斯特里亚国王的克罗泰尔二世(584年—629年在位),为了反对布伦豪特王后,与时任勃艮第宫相的瓦讷歇尔密谋,克罗泰尔承诺瓦讷歇尔终身担任宫相,绝不逼他离职。孟德斯鸠认为这是法兰克王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场革命,之前宫相是国王的官员,由国王遴选;之后宫相是国家的官员,由民众遴选。在克罗泰尔二世的孙子、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国王克洛维二世(639年—627年在位)统治时期,王太后南特希尔德要求勃艮第的领主们选举佛罗卡图斯为宫相,这被认为是宫相执掌国务的肇始。宫相要替王族理财,协同其他官员对采地实行政治管理,并处理军务,指挥军队。孟德斯鸠认为墨洛温王朝时期国王是世袭的,宫相是选任的;加洛林王朝初期,国王则既是世袭的,也是选任的,王权与宫相权力合而为一。可见,宫相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从卑微到显赫,进而取代国王的变化。
孟德斯鸠将墨洛温王朝时期国家已有国王,却还要遴选宫相行使国王权力的政体追溯到日耳曼人那里。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后裔,孟德斯鸠引述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的话说:日耳曼人在血统高贵者中遴选国王,在品德高尚者中遴选首领。孟德斯鸠认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和宫相就是如此,国王是世袭的,宫相是选任的,从而在日耳曼人的社会状况与墨洛温王朝的政体间建立了直接联系。然而,孟德斯鸠并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我们先看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的相关描述。塔西佗注意到日耳曼人中已出现国王,国王按出身推举,也就是说,国王必须出身王族,拥有王室血统,但王位的继承并不是父子相继,而是要通过选举才能产生。国王并不拥有无限的权力,不能一意孤行。恩格斯在探讨易洛魁人的氏族时,也指出酋长在氏族内部只拥有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权力,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带领士兵作战的将军,以勇力为标准进行选拔,他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以身作则统率士兵,靠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来获得士兵的拥戴。除部落大会外,亲兵队是日耳曼人中另一个重要的组织。出身高贵或祖上有战功的日耳曼少年可以担任酋帅,然而即使他们也不以做年富力强、阅历深厚的成年人的侍从为耻。侍从们竞争谁是第一侍从,酋帅们竞争谁拥有最多、最勇敢的侍从。有一群优秀侍从环绕的酋帅,在邻近的部落中享有盛名,会受到外族使臣的称赞,被赠以厚礼,凭威名可慑服敌人。在战场上,酋帅和侍从要同样勇敢。酋帅慷慨地赐给侍从战马和长矛,供以充足的筵席饮宴,这些全要从战争和劫掠中得来。如果本部落长久太平,很多青年自愿到正在发生战争的部落,因为他们天性好动,在危难中容易博得名声,在干戈扰攘中才能维持人数众多的侍从。可见,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尚处于父系氏族阶段,并没有步入国家阶段。
亨利·皮朗在《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中指出:“唯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罗马皇帝的权威不屑一顾。对于其他蛮族而言,罗马皇帝仍是卓越的统治者。”因此,作为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在日耳曼民族迁徙后,盎格鲁—撒克逊人较早地建立起自己的王国。那么,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从部落向国家过渡中发生了哪些转变呢?

449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受不列颠王沃蒂根的邀请,乘三艘巨船到达不列颠,同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作战,初战得胜。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现不列颠富饶而不列颠人胆怯,因此将不列颠的状况告知在故土的族人。撒克逊人组织更大的船队、更强的军队来到不列颠。比德依据传闻,将移居不列颠的最早首领记载为亨吉斯特 (约455年—488年?在位)和霍沙两兄弟,他们的祖先可追溯到沃登神,也就是说,他们出身于王族,同时又成为军事首领。史蒂文·巴西特认为盎格鲁—撒克逊诸小国的建立有两种理想模式:一是邻近的定居地区稳定地合并,占支配地位部落的首领转变为国王;一是外部集团强行控制后罗马时代早期已经存在的领地,即盎格鲁—撒克逊诸小国的形成有和平与暴力两种途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记载的多是暴力立国的情况:455年,亨吉斯特和霍沙同不列颠王沃蒂根作战,霍沙战死,之后,亨吉斯特和他的儿子埃什(488年—512年?在位)继承王国,他们被认为是肯特人的祖先。477年,埃尔和他的三个儿子率领三条船来到不列颠,杀死许多不列颠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829年记载“盎格鲁—撒克逊盟主”的条目下,埃尔被称为“南撒克逊人的国王”。彻迪克(519年年—534年在位)和他的儿子金里克(534年—560年在位)也是在征服不列颠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西撒克逊人的王国。《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到伊达(547年—559年/560年在位)在547年继承诺森伯里亚王位,是诺森伯里亚王室的起源。东撒克逊王国最早的国王是斯莱德,在他的儿子萨伯特统治时期,东撒克逊人接受基督教。东盎格利亞王国最早的国王是韦哈,他的曾孙雷德沃尔德是第四位“盎格鲁—撒克逊盟主”。麦西亚最早的统治者是伊切尔。

如果将立国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状况,同日耳曼民族迁徙前的状况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尽管此时期的国王依然必须出身于王族,但是同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军事力量,成为军事首领,成为血统出身与军事领导权的统一体,不再像他们部落时期,依据出身选举国王,依据勇力选举将军。而且王位之间已是父子相继,也不再是从王族中选举产生国王。血统出身与军事领导权的统一,王位在父子间相继,表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已走出部落时代,步入国家阶段。
反观孟德斯鸠关于墨洛温王朝时期国王和宫相的论述,尽管他认识到克罗泰尔一世(511年—561年在位)的祖父希尔代里克在世时,法兰西国尚未建立,但仍在日耳曼人的社会状况与墨洛温王朝的政体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忽略了两者之间存在的本质不同,它们并不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国家的产生横亘于两者之间。孟德斯鸠发现的墨洛温王朝时期的国王和宫相,同日耳曼人迁徙前的某些状况具有相似性,只能是法兰西王国建立后出现的新情况,而不能追溯到日耳曼人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