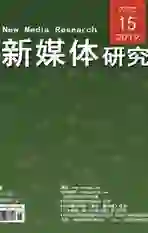智能算法推荐与用户情绪关系的实验探究
2019-09-23郭浩张芷茵
郭浩 张芷茵

摘 要 愈来愈多的新媒体利用智能算法向大众推荐新闻。文章试图探索新媒体的智能算法推荐与用户情绪之间的关系,通过设置实验场景,向读者每日推送其所感兴趣主题的新闻信息。基于实验前后的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测试结果的对比,发现持续性的正面信息推荐会提升用户的正向情绪、降低用户的负向情绪,而持续性的负面信息推荐会减少用户的正向情绪、抬升用户的负面情绪,并且会使得情绪体验变得更为集中;此外,持续性的负面信息推荐所施加的影响要强于持续性的正面信息推荐。因此,文章认为新媒体应审慎地对待智能算法技术。
关键词 智能算法推荐;用户情绪;实验法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15-0015-03
1 研究背景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可持式移动终端的普及,想要获取信息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事。现代社会的普罗大众在遇到问题后会利用各式各样的新媒体寻求答案。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最近李华在纠结到底是要考研还是考公,于是打开了一个资讯类的App,在上面输入“考研还是考公”,于是下面就会弹出许多条信息,诸如“我是如何找到自己的毕业方向”“普通二本学校考研逆袭成功”“弄明白这三点,考公不在话下”,当李华点击进去看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后便认为自己肯定也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而诸如“考研的不公平,我该如何面对?” “没有关系,我还要考公务员吗?”“985名校的他,毕业却也失业了”,逐一浏览下来,李华感觉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光明。尽管在单个个体层面可能出现上述情形,而本文关注的是这一现象是否普遍成立?不同性质的新闻消息对用户情绪的影响呈现的是正向还是负向加剧?何者的影响将更为强烈?这都有待于实验的证实。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智能算法推荐是一种编码程序,通过特定的运算把输入数据转化为输出结果[1]。迈克尔·德维托(Michael DeVito)曾经对算法推荐的运作机制进行研究,他以Facebook为例,通过对其公开发布的专利、新闻稿、博客等进行内容分析,概括出九大算法价值要素[2]。智能推荐就是根据这些内容进行推算、描绘出用户的画像,再在汇集了网络上众多信息的基础上主动、迅速地向用户推送他们感兴趣或关注的相关内容[3]。
通过梳理以往的文献研究,可从中发现研究的思路一般有两种:一是从新闻媒体行业出发,探究智能算法推荐这一技術对新闻选择的影响,从而新闻媒体行业的发展提出建议;二是智能算法推荐这种新兴技术对用户之间社会网络关系的影响。但对智能算法推荐与用户情绪体验之间关系的探讨较为稀疏,因此本文将从用户的情绪出发,探讨用户在接收到大量由智能算法技术推荐的新闻信息之后在情绪上将有何变化。
智能推荐对用户情绪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对用户的主观意识产生影响,包括用户的主体性认识、思维方式、自我异化情况等,再引起用户的情绪变化。二是对用户的客观行为产生影响,包括斗争行为、迷失行为、用户的现实存在方式等,从而引起用户的情绪反应。三是把算法推荐看作是一个媒体技术,是一种被制造的风险,媒体可能会在词语的选择上存在偏倚。他们着重使用极具煽动性的词汇,又或者是迎合用户偏好的词语,这些词语的使用便于算法的筛选与分类,然后根据算法得出的用户偏好结果,再把内容推送给用户,从而达到推送效果。而这些带有取向性的词汇在吸引用户的眼球以后,也会加剧用户的情绪。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算法推荐会影响用户的情绪,且负面信息所带来的影响要强于正面信息。
3 研究设计
3.1 资料来源
本次实验研究中通过Watson等于1998年编制了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PANAS)测量用户的情绪[4]。该量表设置了20个描述不同情感、情绪的词汇组成,并被广泛地应用在健康心理学、组织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领域。本研究选择量表中10个情绪表现较为鲜明的词语进行实验,分别为:感兴趣的、兴奋的、热情的、备受鼓舞的、意志坚定的、心烦的、沮丧的、紧张的、恐惧的、害怕的。其中,前五个词语反映的是积极情绪,后五个词语传递的是消极情绪,从而直接、生动地表现出用户的情绪体验。量表中的题目均为5分制:1表示几乎没有某一情绪体验,2表示比较少出现某一情绪体验,3表示偶尔出现某一情绪体验,4表示时常出现某一情绪体验,5表示某一情绪体验大量出现,随着数字的增加表示实验对象的某一情绪体验愈强烈。
本次实验推送的内容来自于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知乎、小红书和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笔者与实验对象进行初步沟通,了解实验对象近期感兴趣的话题内容,在上述软件或网站上直接输入被试者感兴趣内容的关键词,然后将搜索得出的内容转发给被试者,以高度复原实验对象自行搜索时得到的推送内容。
3.2 实验过程
本次实验一共招募到24名大学生作为实验对象,他们的背景信息大致相似,从而保障实验效果。本研究先进行前测,要求实验对象完成正性负性情绪测量表,确定实验对象对于问题的偏向性。然后将实验对象分为两组,分别为实验组(积极情绪组)和对照组(消极情绪组),以观察有两种不同初始情绪的被试者在实验过后情绪是否都会更加激烈。实验组和对照组人数均为12人。实验总共进行一周,笔者根据每一位被试者感兴趣的话题在网上搜索出相关的内容并推给被试者,每天共推送5条消息。根据组别不同推送不一样情绪倾向的内容。为了确保实验者能认真阅读推送内容,笔者会在每天22点到23点这段时间发送内容。在实验结束后,实验对象再次填写正性负性情绪测量表。
4 数据分析
本研究从实验前和实验后的数据去阐释智能算法推荐对用户情绪的影响。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实验开始之前,实验组内“感兴趣的”和“紧张的”两项情绪得分最高,均为3.67分;而“沮丧的”情绪得分最低(2.50分)。在实验结束后,实验组内得分最高的情绪是“感兴趣的”(3.83分),没有了“紧张的”情绪体验,得分最低的是“沮丧的”和“害怕的”,均为2.33分。实验组的五项积极情绪中除“热情的”以外,得分全部呈上升状态,而五项消极情绪的得分全部呈下降状态,且积极情绪的变化幅度要高于消极情绪。同时,除“热情的”和“恐惧的”两项情绪以外,积极情绪的分值和消极情绪的分值在实验前后的变化差值全部均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05),这表明当智能算法推荐持续地推送正面信息给用户时,这些信息确实会提升用户的积极情绪,使用户抱有更加正向的态度面对问题,与此同时会减少他们面对问题时的紧张、心烦等消极情绪。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实验前后各项情绪分值的标准误基本上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受众的情绪在智能推送的持续性影响之下变得更为集中。
同样由表1可知,在实验开始之前,对照组内“感兴趣的”情绪得分最高(4.17分),“沮丧的”情绪得分最低(2.08分)。在实验结束后,对照组内得分最高的情绪是“感兴趣的”(3.67分),相比实验之前有所下降;“兴奋地”情绪得分最低(2.33分)。对照组的五项积极情绪中除“意志坚定的”以外,其他情绪分值全部呈下降状态,而五项消极情绪中除“心烦的”情绪持平以外,其他情绪分值全部呈上升状态,且消极情绪的变化幅度要高于积极情绪。同时,除“备受鼓舞的”“意志坚定的”和“心煩的”三项情绪以外,积极情绪的分值和消极情绪的分值在实验前后的变化差值全部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05),这表明当智能推荐持续低推送消极信息给用户时,这些信息确实会降低用户的积极情绪,放大用户的消极情绪,使用户怀有更加负向的态度面对问题。此外,同样也需要注意的是实验前后各项情绪分值的标准误绝大部分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消极情绪的下降幅度大于积极情绪,这意味着智能推送的负面信息将让用户情绪更多地集中在“沮丧的”“害怕的”等负向情绪之中。
表1关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均分也反映出智能推荐所带来的整体平均变化,实验组的积极情绪整体平均上升了0.28分,对照组的积极情绪整体平均下降了0.27分;实验组的消极情绪整体平均下降了0.4分,对照组的消极情绪整体平均上升了0.47分,且四个数值变化都具有显著差异(p<0.05)。结合前述分析,智能推荐不仅仅对用户的情绪产生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不对等的,持续的正面信息推送带来的正面心态变化程度要低于持续的负面信息推送所带来的负面心态变化程度。
5 总结
基于智能算法推荐在新媒体中愈发广泛应用的背景,本研究采用实验法探究此项技术是否会对用户的情绪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的前测与后测结果的对比分析表明:持续性的正面信息推荐会提升用户的正向情绪、降低用户的负向情绪,而持续性的负面信息推荐会减少用户的正向情绪、抬升用户的负面情绪,并且会使得情绪体验变得更为集中;此外,持续性的负面信息推荐所施加的影响要强于持续性的正面信息推荐。数据分析证实了研究假设,这启示着新媒体从业者需审慎地对待技术的应用。
但齐美尔认为,尽管人会因为机器的出现而感到迷茫甚至否定自身,但主体具有双重统一性:不仅有对过去和现在的不满与否定,还有对将来的期盼与肯定[5]。换言之,技术发展是个大趋势,人们的迷茫也“非一日之寒”,面对未来,人们依然会在焦虑的同时报以期待。人们该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进行搜索的同时依然保持自我仍然值得去探讨。
参考文献
[1]王茜.打开算法分发的“黑箱”——基于今日头条新闻推送的量化研究[J].新闻记者,2017(9):7-14.
[2]DeVitoMichael.From Editors to Algorithms[J].Digital Journalism,2017,5(6):753-773.
[3]吴延溢,王健.技术时代人的主体性迷失与出路——评京特·安德斯技术批判理论[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30-37.
[4]郭明珠,甘怡群.中文正性负性情绪量表—扩展版在660名大学生中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24(7):524-528.
[5]周来顺.文化危机与双重救赎——齐美尔视域中的现代性危机理论研究[J].学海,2013(2):154-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