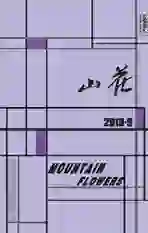时间流变与在地经验
2019-09-20陈哲
陈哲
“首届重庆国际实验影像双年展”中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关于重庆的时间记忆。这一点,同过去西方所建构的单一的摄影艺术形式是不同的,是将摄影这项西方艺术形式与东方的话语体系相结合,而且对于针对性地再现城市文化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一、在地性的产生与场域空间的表达
此次重庆首届国际双年展之主展场计划中,国际摄影作品里首先就融入了在地性的经验模式,而谈到在地性,首先我们就要想到一个关键词“剧场”。因为“剧场”的出现,才使得艺术的在地性发生成为可能。“剧场”作为一个艺术概念出现于1960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与极少主义博弈与对抗的产物。此次双年展中的影像艺术从形式上看只是单纯的二维静态艺术,但这些二维图像的背后其实强调的是对重庆这座西南城市的在地性、空间性的场域探索。要探究这些影像背后的实在意义,我们就必须厘清“剧场化”这一概念,而这一切都与1960年代极少主义的创作有关。
极少主义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强调媒介的物性;第二个阶段开始重视物置身其中的空间或者场地;第三个阶段强调观众与物、空间所形成的剧场或场域关系;第四个阶段是赋予场域社会学、文化学的意义。从时间创作的节点来看,这次国际双年展中的摄影作品无疑属于第四个阶段。无论是土耳其艺术家Ferit Kuyas的《雄心之城》,还是英国艺术家Bruce Connoll《重庆,在1994》,以及来自法国的Yann Layma的《1997年的重庆日常》,荷兰艺术家Robert van der Hilst的《重庆人家》,他们都曾亲自到访重庆,仔细观察城市的面貌,走访于重庆的各个乡镇,这种艺术家行为的介入与场域的拓宽,使得西方现代主义从20世纪以来格林伯格所倡导的先验性、原创性、个人神话的精英主义被消解,人、物、场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意义生产机制。这组国际艺术家的影像作品充分的印证了1969年以后极少主义的崛起,为“剧场”注入了新的意义。他们的艺术作品不仅从室内走向户外,而且走向了更为遥远的东方,走向了人民生活的社会空间。应当说,这种“社会剧场”的行为使得艺术摄影作品的在地性表达成为可能。
而在地性的摄影作品得以真正的实现,在这里还需要第二个关键词,即“参与”。所谓“参与”,实质上是要打破既有的二元对立的话语。如Kuyas的《雄心之城》,作者在三年间走访重庆数十次,拍下了这些宏伟壮阔的图片,他在深入考察后作出了这样的论断:自1997年升格为直辖市以来,重庆就开始向外界展示他们的雄心壮志,这座城市从未停下向巨型现代化城市迈进的脚步。与此并列展出的摄影作品还有《重庆,在1994》,当Bruce Connolly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时,他就被这里的风景深深地震撼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执着的英国艺术家在近距离观察中国的码头和城镇景色十天之后,又从码头出发前往汉口,一路沿着长江拍下了这动人的作品。在Robert van de拍摄《重庆人家》期间,七旬高龄的她每天都会和随行的翻译一起穿行于下浩老街,在当地人热情的邀请下走进他们的家中,观察他们每日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在重庆人家特有的山城光影中按下快门。法国人Yann Layma在摄影作品《1997年的重庆日常》中深刻地再现了重庆这座山城所特有的“在地的全球化”。在这组图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看到“车间生产”“小店理发”“街头一角”这些具有时代感的影像资料。通过这几组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艺术家在创作之前,首先是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的,他们试图通过纪实性的手法和历史意识的构建,引导受众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去理解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人文生活的关系。他们有的选择了社会调查,有的选择了参与合作。不管在形式上有何不同,大家对“参与”的强调,在于以艺术(这里指视觉影像)为通道,构建一种平等的、协商的、共享的文化理性与交往理性。这些艺术创作的理念与工作方式,不再局限艺术本体以及所谓的风格、形式,以及个人才情等范畴。因此艺术家的主动介入与“参与”,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极少主義中所形成的“剧场”关系,都使得这组摄影艺术创作中所强调的在地性成为了可能。
二、艺术家视角下的重庆“在场”
艺术家们显然是立足于重庆这一西南城市的在地性而进行的视觉语言符号编码,但是这种场域的形成同时是建构于一种西方的话语体系中的。尽管在消解精英叙事,强调在地性的前卫艺术中取得了全新的突破,但是这种创作背景仍然无法彻底摆脱极少主义后期的“后殖民”主义与西方霸权的话语体系操控,如Ferit Kuyas的代表之作《雄心之城》(2005-2008),十多年间多次在欧洲多国展出,获得了国际性的大奖。Ferit Kuyas这样讲道:“我被重庆的城市边际线条吸引,在这些地方,重庆虽然不能被真正看见,但却如此地可被感知,就像丛林中一只猛虎的移动,不被人所见,但你知道它就在那里。”就他个人而言,上世纪用来形容繁荣蓬勃状态下的曼哈顿的“雄心之城”现在看来同样也是对重庆最为贴切的描述。Ferit Kuyas以一位西方艺术家的视角来反观东方的城市,很明显他是立足于在地性这一观念表达进行创作的,而他所强调的在场就是重庆。我们可以类比一下Bruce Connlly的《重庆,在1994》这件作品,表面上看这几组摄影作品仿佛只是对重庆的城市面貌进行了一种记录或者客观的还原,但是在深入了解作者艺术创作的动机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是Bruce Connlly首次对于东方文化体悟后拍摄出的影像作品,这种影像记录更像一种外来视角介入并欣赏东方文化的心理体验,那么这种具有纪实性的影像作品在“时间之镜”这样的“语境”以及特定“场域”中所传达的视觉符号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它成为了西方语境视角下的别样的东方情境,这种创作表达具有突破性、前卫性、在地性。如果把这种西方语境下的东方视觉语言置换于世界的图像语言建构中,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精英性,在东方语言介入西方“后殖民”的时代背景上讲,它正试图打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话语霸权所操控的艺术形式,众所周知,在这样的文化霸权的语境中,大量的艺术创作都要依附于商品消费文化,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劳申伯格的波普艺术,杰夫·昆斯夫妇的艳俗影像艺术等等。Bruce Connlly和Ferit Kuyas反映重庆日常生活的在地性表达的摄影作品就是对西方商品消费文化的一种挑战,具有东方语言特色的视觉符号使得在地性的场域表达意识形态化,并赋予了其社会学、文化学的意义。
三、在地性表达中的“时间之镜”
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组视觉图像背后同样也包含着时间的流变。
众所周知,摄影艺术的发生起源于法国人达盖尔的摄影术。至今已有160年的历史,现存最早的照片是由路易斯·达盖利用银版照相机拍摄的,但最初的影像作品只是作为一种纪实性的手段,如清朝末年大量洋人在中国留下的诸多影像资料。尽管摄影师在进行一种在地创作但我们很难将其作品归纳为一种在地性的艺术表达,尤其是绘画形式与摄影技术的不断融合,使我们很难再用单一的纪实性表达来完整地概括摄影。此时的摄影艺术正在形成,为了更好地梳理这一时期的艺术流变,我们不妨采用较为折衷的方法,将一些风格比较接近、创作方法比较相似的摄影大师集合在一起,这样摄影艺术创作看上去就似乎形成了各种艺术风格特点的群体和个人,但是语言体系并不完备,在纪实性和观念表达中显得十分混乱。到了20世纪中叶的四五十年代,在照相技术和感光材料的迅猛发展中,摄影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艺术门类。随后各种艺术思潮不断涌现,艺术风格不断诞生与消失。此时的摄影艺术已经开始同商业符号相结合,观念摄影也开始涌现。通过这种对于摄影艺术的历史梳理,让我们再来反观这些西方艺术家的作品,艺术家在地性的表达同样也受到了东方观念摄影作品的影响,他们将观念中的在地性创作结合了历史与时间的流变,如《雄心之城》和《重庆,在1994》,两组作品深刻地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变迁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这座西南腹地城市的崛起与复兴,而《1997年的重庆日常》与《重庆人家》则是对于重庆日常生活中岁月流变的最好见证。所有的在地性发生都可以成为鉴证重庆历史文化发展的“时间之镜”。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视野对于东方文化的介入使得影像艺术不仅成为了艺术创作的前沿阵地和实验领域,而且在当代视觉文化有了较强的实效性与纪实性,将艺术家所存留的历史记忆纳入到了技术所建构的新场域之中,形成了具有时间流变的在场性表达,在纪实创作和观念表达之中实现了过去与现在的交集,打破了时间概念中所固有的依存关系,在现实与变换的场域内具有了超越经验、常态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