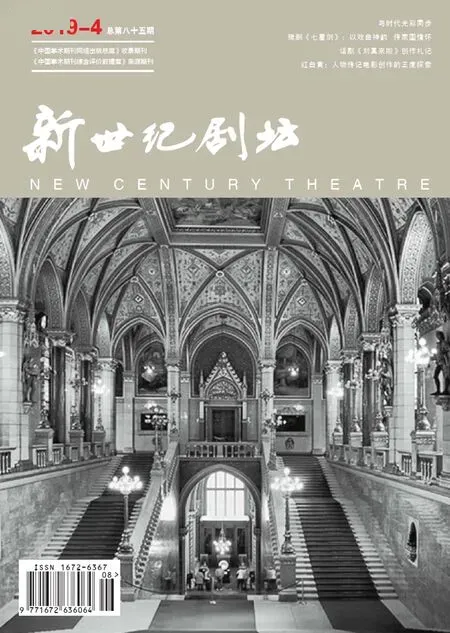评论视野中的言菊朋和余叔岩(下)
2019-09-17张伟品
张伟品
进入20世纪三十年代,言菊朋常以“谭派硕果”为号召。1938年以后,更提出“新旧谭派”的口号,自居“旧谭派首领”。实际上,是将自己和余叔岩作了划分。由此,在评论界引发了重大反响。很多人以为,言菊朋其时所唱之腔,已与谭鑫培有了很大距离,并非谭氏面目。这种意见不仅出于贬言者,即使捧言诸君,也多此种论调。如苏少卿说:“他四十岁的那年,得了一个怪病,头大如斗,名曰大头瘟,在北平德国医院治病半年多才好。病虽痊愈,体气虚弱已极,永不能复原。嗓音变成窄小低狭,和从前大不相同。还得唱戏吃饭,只好就他坏过的嗓音,杜撰新腔怪腔。这个时期收的唱片有《大保国》《雁门关》《让徐州》《白蟒台》《上天台》《骂殿》等片。有的地方还好,有的地方简直怪得不像皮黄,又不像大鼓,听着刺耳。这是他晚年的东西,害人不浅,真要不得,然而今之喜欢听菊朋的人,偏喜欢听他病后变坏的晚年片子,他壮年唱片人多不知其中好处,信邪不信正,这正是乱世的怪现象”[1]。也有人主张言菊朋可自称言派:“他(言菊朋)早年倒是的的确确宗法英秀,(据我所知,较叔岩为忠),可是现在若和旧日相比,那就有些个‘今’、‘昔’之慨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认为用其以‘旧谭派’这个不通的名词,倒不如直标自称‘言派’来得简明些。何况现在已有不少人在那里以菊朋为法并标着‘言派’的头衔呢”[2]。总之是对“旧谭派”不以为然。
而实际上,言菊朋提出“旧谭派”,自认为学谭,是“旧谭派首领”。其实是一个审美命题,而非具体形态特征。在当时一般批评中,经常被庸俗化理解。其实是以固化的谭鑫培为标尺,来衡量处于实践中的言菊朋。这和以固化的余叔岩为标尺来对照言菊朋,本质上并无不同。当时也有些评论者,虽不一定能意识到言菊朋这一命题的美学意义,但从各自的角度加以理解,得出不同于俗流的批评。如郑过宜认为:“菊朋叔岩,系同宗谭,而又各具风格。是以言腔故固不字字皆谭,而余腔亦多发明自己。学人而不求似,斯善于学人者。要能不越谭派楷模仪型,即不得举以相非。今人于余腔推美备至,于言腔或致骇异,殊非持平之论也”[3]。从艺术变化过程的必然性角度,以余叔岩为对比,为言菊朋辩护,这一见解还是相当高明的。刘慕耘则直接以为:“菊朋之唱,实非谭派旧规。惟其唱法,则为谭是法”[4],是脱离了外在形态的看法。
在众多评论者中,徐凌霄的评价,独具特点。他从其一贯的戏剧观出发,批评言菊朋:“菊朋在《中报》指出叔岩在《捉放》《战太平》唱法不合老谭,在他处争持新旧真伪之诉词亦多,叔岩既无答辩状,自不须评判。惟此事与学戏的取径有关,故申论之,以资公共之参考。凡学前辈者不只谭派,如继仙之学楞仙,凤卿之学大头,皆‘学的是人演的是戏’,此乃公共的当然的原则。叔岩并无特秘,不过依例而行,自然句句有戏味。菊朋则刻划字眼腔板,而无精气神为主宰,研技而忘戏,根本已入歧途。故致力愈勤,去此道愈远。即使老谭,亲授三十年,亦还是个旁皇门外者。然菊朋亦代表一派的人,即以名伶作古玩式研究者,此风自谭迷始,以之消遣则可,根本不是‘台上人’”[5]。
1943年余叔岩去世,徐凌霄撰长文纪念,对余、言又进行了对比评论。而立场观点,仍一如其旧。他自己也说:“只因我自己立场不同,不能不再三审慎。生平宗旨,戏剧为主,伶技为宾,昔年勉副朋好之要求,偶撰记伶之文字,仍处处抱定戏为本位之观念。盖剧场上的一切,是整个的,伶人在台上,只是表演之一分子,与歌舞明星武术杂伎之仅系个人者,迥乎不同。抛戏而评伶,则伶艺之优劣,亦无准确之估价,此在识者自能理解,而积习相沿,本末倒置,解人何在,正自难言。如余叔岩者一世辛勤,盖棺论定,专篇评述,理亦宜之。《古今》为学术之刊物,主者多明通之哲人,相属既殷,亦乐于执笔……以客观的态度,作综核之评判。所纪者余氏而谭鑫培与其他谭余系诸伶之异同得失,亦灼然可见”。然后批评言菊朋为笨学,“何为笨学?枝枝节节,不识本原,专研技式,而无心灵控制。如,言菊朋者,确曾下过工夫,竭力揣摩,一腔一板一字一句,必刻画而步趋之,是犹学书者取前人碑帖而勾描也。知勾描之不足以成书家,则知言等之不足以云名角矣。菊朋之指摘叔岩,亦惟其某字不合,某腔不符,斤斤计较,而于运用之法及精神控制之道,完全门外,只可供谈料,而不适于剧人”。然而其评余叔岩,谓:“叔岩之喉咙,根本不宽,不厚,不润,因将发音之本营移上一步,在上腭与鼻之门成一小结构,宽窄粗细高低均于此中施展腾挪,或用气厚托,或用口法轻拢,或用别音替代,使听者不致有偏缺之感,煞费调停,百般苦练,其不及老谭者在此,其胜于谭派余子,亦在此!三是音节之苦。谭鑫培以悲剧见长《寄子》之悲酸,《卖马》之悲凉,《乌盆记》之悲楚,无限低徊,尤其是他的酸鼻音,无处不用,成为凄音苦节。叔岩无谭之水音,嗓不腴润,却从贾洪林学来一种苦撑之法,干紧苍朴的味儿,以此唱谭腔而凄苦又有甚焉。试以其唱片于月白风清之夜,荒村旷野之间,沉默听之,真是秋坟鬼唱,一片呜咽之音,戏苦,音苦,嗓苦,腔苦,凄上加凄,苦上加苦”[6]。

昆剧《宁武关》剧照 言菊朋饰周遇吉
这里,显然徐凌霄并未对言菊朋的戏加以真正的解读,而仅是以其自身观念为依据,做出概念化解释。虽然其基本理念“学的是人演的是戏”确具卓见,但以“戏剧为主,伶技为宾”为立场,而过于轻视戏曲形式表现手段(徐氏所谓伶技)本身的独立价值,把具体的技术分析一概斥之为“古玩式研究”,所以其分析往往脱离了戏曲本身的形态规定性,而滑向一种虚无状态。其评论中“悲酸、悲凉、悲楚”等形容词,以及“试以其唱片于月白风清之夜,荒村旷野之间,沉默听之,真是秋坟鬼唱,一片呜咽之音,戏苦,音苦,嗓苦,腔苦,凄上加凄,苦上加苦”的文字,无非是个人主观感受,与其自我标榜的“客观的态度,作综核之评判”并不一致。实际上,言菊朋晚年,无论在一般评论中,还是其自己的演出实践中,在外在具体形态上,与谭都有了不小的差异,迥非徐凌霄所谓“竭力揣摩,一腔一板一字一句,必刻画而步趋之”。至于用嗓、发音等等,其改变也无非和余叔岩一样,是就其本人条件和局限,在谭的基础上加以变通运用而已。这一点言、余(甚至所有演员)的继承过程都不能出其外。言菊朋指摘余叔岩的那些地方,如《战太平》之“扫荡烟尘”,应为“奏凯掩尘”之类,不仅涉及词义,更涉及“以字声行腔”的基本原则,而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又是中国传统的“以文化乐”理念的体现。绝非一字一句的小技巧,其所涉及的深度,甚至远在徐凌霄所谓“戏剧”概念之上。
言菊朋和余叔岩在1942年6月到1943年5月不到一年时间内相继去世。二人死后都算是颇具哀荣。批评界发表的评论大多以为是京剧的巨大损失。而对于两人的比较文章也相对多了起来,颇有为之盖棺论定的意味。自此,言菊朋和余叔岩一样,都是作为古人而出现在后来的时评中。1947年的一篇文章:“余、言堪称谭派老生之两大贤人,惜各因天赋所限,未能全遵谭路。因各自成一派。论唱功,余言各有千秋。论武功,叔岩梨园世家,菊朋票友下海,自不能同日而语。论念白,叔岩重气口,菊朋重字韵,至若身段之边式,表情之精到,言则较余逊色矣。但此二人之成名,皆由刻苦磨练中得来,于今日之老生相较,着实令人有‘良才已去难再得’之叹也”[7]。代表了当时大多数评论者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1949年以后,传统戏曲的环境发生巨大改变。对于余叔岩、言菊朋等人艺术的评论也与前不同。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京剧舞台上老生演员以后四大须生以及李少春等影响为最大。因当时主流意识对于流派的看法,余派并不如后来那样被奉为京剧老生主流。李少春虽是余门弟子,但在实际中也多以个人面目出现,并不以余派为标榜。同时对于余叔岩的专题评论和研究也几乎缺失。相反倒是言菊朋,因为各种原因,促成了对言菊朋及言派的一次振兴活动,从而使言菊朋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这一次活动后,1959年出版了《言菊朋的舞台艺术》一书,收录了言少朋、言慧珠、马少波、景孤血、李慕良、李家载等人的回忆和介绍文章,以及两篇有关采访。这一时期,余叔岩和言菊朋两人不再被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评论。
1976年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等拍摄了一批传统戏曲电影。在这一过程中,言菊朋和言派又重新被提出,且成为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其一,是拍摄言派戏《卧龙吊孝》和《让徐州》时,因对参加演出的言少朋的唱和李家载的身段不满,重新拍摄时下令由言少朋表演,李家载配唱,演出了双簧。二是在拍摄《贺后骂殿》《梅龙镇》等剧目的时候,要求老生演员孙岳、张学津都要按照言派唱法演唱。所以,二人后来在电影中的唱法与其本来所学都不尽一致。
“文革”结束以后,传统戏次第恢复,余叔岩也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并且对其地位的评价忽然直线上升。1982年,最高级别的戏剧官方杂志《人民戏剧》,刊出答读者问,明确提出“余、高、马、言”和“马、谭、杨、奚”前后“四大须生”。到1987年4月,由《人民戏剧》改名的《戏剧报》刊出翁偶红的文章,《京剧老生的第二个里程碑——谈余叔岩》,称:“可以这样说,自余派风靡剧坛,除沪滨之麒派(周信芳)自成独立王国外,其它各地的老生演员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余派的影响。就是那些仍以谭派自居的演员,也在潜移默化中吸收了余派(也就是新谭派)的精华……直到现在,虽然马、谭、杨、奚芳馨交溢,各有千秋,可是形成这些流派的创始人,他们都不讳言自己曾受熏陶于余叔岩,曾撷风韵于余叔岩。这与当年‘谭派’形成后之‘无生不学谭’,并无二致。客观的存在,事实的雄辩,似乎有理由在老生艺术的程途上,把余叔岩‘余派’的成就,视为谭鑫培以后的第二座里程碑”[8]。这样的断语貌似雄辩,却并不合乎逻辑。以里程碑论,何以程长庚不算第一座?以影响论,大概后人之受前人影响,天经地义。“潜移默化”以及“受熏陶、撷风韵”云云,与“无生不学”还是大有区别。然而,余叔岩的地位,因此而大大提升却是事实。
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和台湾的交流增多。孟小冬门下弟子往来两岸,也带来了新的评价模式。首先是依青帮传统,将大陆京剧界已然淡化的师徒宗法关系重新激活,确定了谭、余、孟的所谓谱系,并强调“行拜师大典、开门授徒”。很快催发了一种风气。其次是为余、孟上尊号。1992年8月,李炳莘在台湾印行其《余派戏词钱氏辑粹》一书。后于1995年10月在天津再版印行。书中称余叔岩为“剧艺完人”,称孟小冬为“一代宗师”。余叔岩开始被捧上神坛。
20世纪末,随着戏曲理论对戏曲本身认识的深入,整体理论从流派风格、剧目主题意义等传统方面,转向对舞台戏曲形态,对戏曲自身形式的规定性开始有了更多的探讨。1999年,刘曾复出版了其《京剧新序》一书。此书的特点相对以前京剧理论和评论性书籍,主要是突出了对表演本身的关照,对表演艺术的评判,不仅出于主观感受,更多的是对表演原则的探讨。也就是说,在审美价值判断之前,先进行了真假判断。后者恰恰是长期以来在戏曲理论和评论中有所欠缺的。

京剧《洗浮山》剧照 言菊朋饰贺天保
在书中,刘曾复作《名家歌谱》,以线段图的形式在谭鑫培的基础上对余、言二人的表演进行了对比。刘曾复认为,言菊朋和余叔岩总体上说水平相当、而趣味、风格各异。以老谭为基准,言和余在学谭的广度上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也各有不到和越出老谭边界的地方;老谭以“自然”为风格核心,而言菊朋和余数岩在“情”和“技”两个相对的方向上各自用力,且都在极端上超出了谭鑫培的范围;并因而在具体技术上表现出“刚柔”“虚实”和“宽窄”“厚薄”的对立。言菊朋以“情”为追求,在唱腔上显示出“薄窄虚柔”的特征。而余叔岩以“技”为目标,以“厚宽实刚”为表征。他说:“看一下余叔岩和言菊朋吧。两位的唱腔味道不同(即使主要的工尺相同),是出于天赋呢?出于功夫呢?还是出于理论呢?客观的说,在这三方面,余叔岩与言菊朋二位没有根本上的区别。由于出身的不同,余重技、言重情是一种容易被想到的事。但是二位演戏的基本法则是相同的”。因此,刘曾复最后提出问题,“分析余、言唱起来味道不同的问题,要换一换思想、换一换方法”。刘曾复的这一段话,很清楚地描述了余叔岩、言菊朋艺术表象上的差别,也指出了两者的不同追求。但最后却仅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只是说“谭鑫培的京剧老生艺术是广谱型的。学谭各家常是掌握谭氏艺谱中较宽的一段精髓,但随个人天赋、功夫、理解(论)的活用,就会表现出个人特色”[9]。也就是说,余、言等各人的区别,原因在于分别获取了谭鑫培广谱型艺谱中的一段,根据各人条件加以创造、适应,从而形成不同风格。这些不同风格之间不分轩轾。这里,刘曾复对谭、余、言的艺术表象进行了“质”、“量”分析,但没有进一步作出审美价值判断。
从审美角度而言,艺术自然以情感表达为目的,所以言菊朋“重情”,恰恰是符合艺术本质的选择。而余叔岩的“重技”,虽不合于审美价值,却有其文化上的理由。京剧,虽然被视为一种艺术样式,但实际上,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似乎更合乎实际。中国的艺术,尤其是民间文艺,向来没有形成纯艺术的观念。任何艺术样式,在审美价值以外,更多地附加着因艺术的功能性而产生的各种附加因素。在很多时候,这些附加因素往往遮蔽了艺术目的的审美唯一性。对绝大多数京剧从业者而言,唱戏这一活动,究竟是一种生存手段还是审美体验,估计很少有人会去考虑。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功能性要远大于其审美作用。所以,余叔岩在审美以外,更具有了广泛的功能意义。可能,这就余叔岩在当下多种语境中成为京剧老生发展正统,而言菊朋则被认为是一种支流的原因吧。
注释:
[1]苏少卿.言菊朋唱片[J]戏剧春秋,1943
[2]李云影.麟爪剧话[J]十日戏剧,1939年,第2卷,29期:16
[3]过宜.聆言菊朋后感言[N]新闻报,1939-7-24(第4版)
[4]刘慕耘.关于言菊朋是否为谭派之解释[J]戏迷传,1939年,第2卷,11
[5]徐凌霄.言菊朋之误何在[J]立言画刊,1942年,218期:3
[6]徐凌霄.於戏!叔岩[J]古今半月刊,1943年,26期:7
[7]徐幼云.余叔岩与言菊朋之比较[J]军中娱乐,1947年,第1期:17
[8]翁偶虹.京剧老生的第二个里程碑——谈余叔岩[J]戏剧报,1987(4):42
[9]本节引文及转述,均参见刘曾复.京剧新序[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