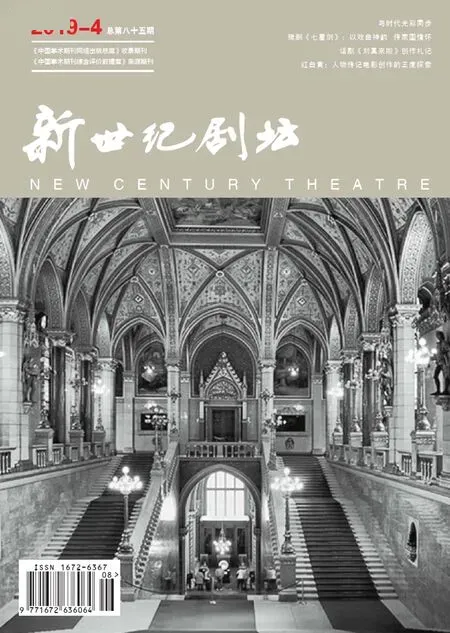我喜欢的烟火气
2019-09-17郝岩
郝 岩
一
可无情的现实还是继续打脸。辅导了几次儿子的作文,本来还沾沾自喜,等着儿子回来转达老师的致敬。可得到的反馈,大多不是首肯,说我的指导把孩子的思路带偏了,不符合凤头猪肚豹尾的应试好作文要求,得不了高分。有几回儿子还搬出我的名声小声反驳,老师更不乐意了,说那你回家让你爸教去。这让我万分沮丧,一度怀疑起自己的文字能力。
倒是儿子安慰我,老爸是大学生水平,他只是小学生,写得太超前了自然不会符合老师对小学生作文的要求,我宽慰些许。可很快又从媳妇那里得到反馈,儿子已经开始质疑他这有作家证、编剧证的老爸是否江郎才尽。儿子表示这很重要,直接涉及到我们全家人的生活水平是否还能保住小康标准。
儿子的担忧,其实早年在他姐身上也发生过。他姐的做法是作文从来不让我辅导,数理化更是不用我沾边。学校的老师每每问起你爸是干什么的,女儿一句话就给打发了,写字的。有时候老师看到报纸上的名字,会跟女儿求证,女儿轻描淡写地说:“重名”。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师都以为我是书法家,有一年还让女儿找我写几幅春联。好在我一直都是正经八百跑文化线儿的记者,认识几个真正“写字的”。辗转完成了任务,也算没穿帮。
后来,我越发明白女儿不让我辅导作文是明智的。每年高考时,语文试卷一经披露,我们报纸总会在第二天刊发几篇同题高考作文,邀请的作者除了有次年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还有我们本报的记者,然后匿名请高考老师批阅。有趣的是,每回分数垫底的都是我们记者。回头再看那几篇同题作文,记者确实没有学生作文的词藻华丽,论点论据论证也不鲜明,更是鲜见铿锵有力哲理丰富的句子。但看着这些工整的文字,你却又总觉得少了点好文章该有的灵动鲜活,更不见生活的毛边儿。
我曾问过女儿,为什么不跟老师说你爸是作家或是编剧,女儿说这两样身份都不给你发工资,不是正经工作,有虚头巴脑之嫌。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早年很多人喜欢在名片上印一长串头衔,冠冕堂皇的名头基本都是虚的,开工资的地方却往往挤在犄角旮旯处。或许正是受了女儿的影响,虽然自己从工作开始就一直依赖文字生存,却一直没把自己当成所谓的专业编剧。
我一直认为,创作上的事,就不应该有专业和业余之分。再专业的编剧和作家,也有写得业余的东西,很多并不专业的作者,也发表过许多令专业编剧和专业作家望尘莫及的文字。这样的例子,国内外不胜枚数。回想起来,我走上编剧之路,一是受益于文学,二是受益于生活。
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好像是中国文学最为热火朝天的年代。文学爱好者遍地,大小图书馆里的文学书籍很难借阅到手里,书店里的文学图书也很是畅销。那个时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现在几乎都能在我的书柜里找到。几年前搬家时,看到许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杂志,惊讶自己当年居然把他们都看完了,而这些年读书的时间却少之又少,想来也是惭愧。
那个时候,每一个文学讲座都座无虚席,印象里作家王蒙到大连时,在大连政协礼堂举办过一次讲座,门票要托关系才能搞到。茹志鹃、王安忆母女俩的讲座,更是放在了能容纳上千人的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举办,楼上楼下挤满了文学爱好者。几年前,我自编自导的一台幽默讽刺话剧《风声越来越紧了》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连续演过三场。因为是纯粹商演,没有赠票,没有包场,那些日子,最让我操心的事,是每场的上座率能达到几成。所幸我们的演出特别成功,大麦网上的门票在开演前一两天便全部售罄。门口的黄牛党都觉得奇怪,他们手里居然没有一张门票。那时我脑海里闪过的记忆,就是当年茹志鹃、王安忆母女俩举办文学讲座时的盛况。
3)混合臂高空作业车在举升过程中由同1个PLC控制器控制,即伸缩臂、折叠臂和工作斗的三个输入间为互锁关系,提高了工作斗的平稳性和可靠性[3]。

电视剧《暗红》剧照
文学给我的营养,多少年里一直潜移默化滋养着我的影视作品,使我在编织故事、塑造人物,甚至写出每句台词时,都在吃着文学的红利。《暗红1936》是一部以“西安事变”为背景的谍战剧,主人公毫无疑问以特工居多。剧作中用一句话表达了对特工的理解:“特工的工作有两个基本元素:一是阴谋,一是暗杀,合起来就是阴暗,阴谋就是布局,暗杀就是吃子。”简单的一句话,分析出了特工的工作性质。
剧中对男女情感的描写,用了一句“妻子是干粮,情人是点心”的台词,相信观众听到这句话之后,肯定能会心一笑,简单的一句话,一下子就把妻子和情人在男人心中的位置准确定位。涉及到职场时,把自己对职场的理解用台词表达出来:“是猴子就给他一棵树,是老虎就给他一座山”,点出了用人之道。“人世间有两种东西最让人难以抗拒,一种是戴高帽,一种是拍马屁,一上一下,锐不可挡”,则道出了人无论在何时,身处何位都不可避免的人性弱点。
类似有一定文学性的台词,在全剧中随处可见,比如,“勉强是一种暴力”“人就活三件事:钱,事业,爱情”“乱世想太平,就得枪说话!”“中央日报,反着读好不好,上面说一片大好,那就是天下大乱了”“人这一辈子有两件事比较重要,一是活着,二是死去”。
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剧的台词,充满思辨性、逻辑性,却不乏睿智与幽默。在带来美感享受的同时,又让人产生了共鸣和震撼,这是台词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作者具备的文学功底和生活感悟。

电视剧《幸福生活在招手》海报
二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这些年,我的影视剧创作涉猎面比较广、比较杂,抗战剧、谍战剧、年代剧、现代剧都拍了几部。这并不是说我有多大的本事在各个题材间自如穿梭,而是我觉得任何题材的影视剧归根结底都是写人的,无论是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长,只要是写人,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就一定有共性的东西,只是不一样的人干的事情不一样罢了。
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视剧,应该是1997年发表在《中国电视》上的文学剧本《红帆》。这是一个讲述老师坚守海岛几十年教书育人的故事,当时是因为我去海岛采访,写了一篇通讯报道《多罗母的旗帜》。但更多深层次的内容却难以在文章中呈现,比如新老两代人面对教育的分歧冲突,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迷茫抉择等等。该剧同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的播出,坚定了我做一个编剧的信心。
我的本职工作是报社记者和编辑,每月都有繁重的采编合一任务考核。所幸我完成那些任务还算轻松,连续十多年的任务量都在报社排名前三位,年年能拿到一个“总编辑奖”。我的剧本只能算是业余创作,这决定了我的创作不可能像专业编剧那样拿出大量时间专门就某一题材深入下去。好在我有过八年的工厂生活,后来又一直在媒体工作,深入生活、扎根生活对我来说几乎就是天天在做的事情。特别是记者工作,几乎能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样的生活经验让我更喜欢写那些平凡质朴的生活,写有温度的人。我知道,那样的生活和那样的人,才是真实的,我相信平凡的生活里蕴藏着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
在编剧行当打拼这么些年,因为是“业余编剧”,我没有惶恐感,不必遵循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有一次我写了一个剧本,片方找了十多名剧本医生来谈意见,他们说,“剧本五分钟要有一个小高潮,十分钟要有一个爆点,这是规律”。我说,“这不是我能做到的,我也不喜欢这么做”。我很坚持,因为剧本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是带着温度的情感的集合体。任何情节的发生都应该是合情合理,而不是刻意为之。一个故事,一个人物,首先得打动我,我才能写好。
多年来,我挑选项目的首要条件是能不能打动自己,如果创作者自己都不能接受,观众当然更加不能接受。尽管当下影视创作中流水线模式大量存在,并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仍然愿意做一些“笨”功夫。流水线出来的作品,是模式化的千篇一律。艺术创作不是零件组装,那些成功的作品都具有独特性,不是拼接出来的“成品”。
从业多年来,我写的基本都是自己喜欢的题材,特别是烟火气十足的故事,而当年我恰好负责编辑过报纸副刊《人间烟火》。每个人的创作习惯都不一样,我每天基本是早晨送孩子上学后,逛逛早市买点菜,然后回家坐在电脑前翻翻正经或不正经的各种资讯。在不断的自责中眼看着大半天的时间要滑过去了,才强逼自己静下心来开始码字。偶尔有合得来的好友一声招唤,也会忍不住跑出去扯上半天蛋,回来再内疚地争取把当天的任务给完成了。
我编剧的剧目里,或多或少都想追求一种烟火气。《幸福生活在招手》《大声歌唱》《王大花的革命生涯》《高大霞的火红年代》(又名《碧海丹心》),都属于这类作品。
创作“王大花”的初衷,是因为最开始喜欢王大花这个名字,但是一个名字不可能构成剧作。我之前写过谍战剧,也写过生活剧,我一直希望能将这两个剧种做一个结合。正好王大花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喜感,有生活流的东西,已经赋予了剧作人物上的喜感。刚开始创作时,不少人并不看好这个故事,认为市场上没有这个类型的作品,怕不被观众所接受。确实,这部作品跟以往的谍战剧不同,讲述的是一个普通家庭主妇的人生经历、革命生涯。这个剧把强烈的喜剧元素和生活质感融入到谍战剧里,主人公王大花从做鱼锅饼子的家庭主妇逐渐成长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与初恋情人夏家河从相斥到相吸,矛盾重重,却又相互依存。演员不仅要诠释王大花身上的喜剧色彩,更要演绎出王大花心中复杂的情感变化、成长蜕变。相比较于大格局、高大上的人物及剧情,我试图以更平民化的视角拉近和观众的距离,我觉得小人物的人生经历更能打动电视机前的观众,把这样一个懵懵懂懂的家族主妇放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写她的感情故事,写她的艰难人生,不可能没有新意。
同“王大花”一样,今年4月初刚刚完成前期拍摄的《高大霞的火红年代》,同样是一部谍战喜剧。与剧中频频反转的紧张故事相比,我其实更喜欢的还是作品中各色人物的烟火气。希望这部献礼共和国70周年的作品,能让更多朋友喜欢,这里就不过多剧透了。

电视剧《碧海丹心》剧照
三
编剧是决定一部作品高度的人,很多项目想法很好,但是最后实施不下去,其实跟编剧的能力有很大关系。几年前我接过一个改编项目,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改编。此前,这部战争题材的网络小说,改编了五六年都没有改成,前前后后换了六任编剧,交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是第七任了。当时我不知道制片方找过那么多人,还包括两位著名编剧。到我改编结束后,项目终于做成了,对方才告诉我。
如果说导演、演员、制作部门之间的合作是团体作战,那么编剧的创作过程更像是孤军奋战。一部剧本的好坏不但取决于编剧的才华,同时也取决于编剧的责任意识。在项目前期,如何拿捏题材,如何设计好大纲,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做好了,后面的事情才能更为顺利。作为编剧,一定要把剧本做得尽量扎实,在开拍前,把方方面面的想法都照顾到,让大家都能接受。这是很难的事,但又是必须得做好的事。
一部影视剧的完成过程就像一场接力赛,编剧负责跑的是第一棒。既然拿了“第一棒”,就得把自己该跑的一段路跑好,这是我时常提醒自己的话。“第一棒”决定一部剧作的整体定位,后面“几棒”更多是为这个项目加分或者减分。剧本交出去后,很多情况就不是编剧能够决定的了。投资方、制片人、导演、演员、摄影、美术等等,几乎剧组所有人都能对剧本提出各种意见。这里改一下,那里动一下,有时可能会给剧本加分,但更多的时候是减分。如果编剧交出来的是一个90分的剧本,那还经得起各种因素减分,最后起码还可能及格。如果编剧交出的是一个70分的剧本,哪一棒出点闪失,拍出来的作品就可能不及格。“第一棒”跑不起来,交不出去,后面的一切都只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