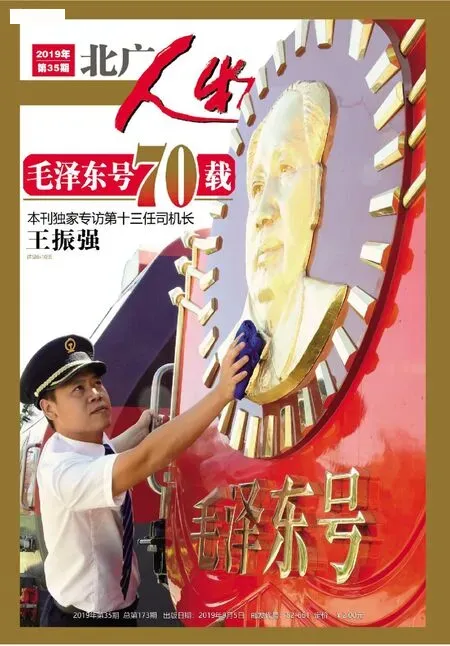看《特赦1959》聊功德林里的那些事儿(四)
2019-09-17
1948 年10 月被俘于辽沈战役的范汉杰是黄埔一期生,之后,还去了德国陆军大学留学,也算是国军中的一位足智多谋的悍将了。1956 年,他从佳木斯被解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加速改造”。刚被解送来时,他认为自己必死不疑,一度心情十分沮丧。后来,他知道自己不但不会被杀,如果改造得好,还有可能恢复自由,于是,他那爱开玩笑、喜欢作弄人的习惯,又慢慢地表现了出来。
一次,他伏在桌上写东西。因他字写得一向很小,所以写东西比较吃力,他一面闭目养神,一面用手轻轻地揉着眼睛。这时,小组长正从外面进来,看到他两眼发红,忙问他为何如此伤感?他一看房内没有别人,便赶忙把写好的东西翻过来放在桌上,然后两手抱头伏在文件上做痛哭状。这位组长吓了一跳,就一个劲地盘问他,究竟为什么伤心。他头也不抬地哽咽道:“这样下去,活不成了,所以先把遗嘱写好……”组长转身就跑到管理员那里去汇报了,管理员又急忙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所里的领导。一会儿,便有三四个干部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和颜悦色地问范:“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说出来,我们帮你解决。”没想到,范竟一脸茫然地说:“我没事呀!哦,我就是眼睛有点发胀,休息一会儿就会好了。”
那位组长一听,马上气呼呼地质问他:“你不是说你活不成了,要立遗嘱吗?”“哪有?我好好地立什么遗嘱?”组长一个健步冲过去,把他覆在桌上的东西翻了过来,结果看到的竟是他抄的当天《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
不过据沈醉讲,范汉杰对政治学习还是相当认真的,特别是他早年曾学过测绘,在测量方面十分在行,平日还爱看数学方面的书籍,除了爱开玩笑外,并不怎么发牢骚。
和范汉杰性格相反的,是廖耀湘。这个人相当骄傲,且有点自命不凡,乃因他是黄埔七期生中,唯一当上了兵团司令的。他在功德林时,常对人说:“湖南宝庆(邵阳)出了两个杰出人物,你们知道吗?一个是蔡锷,一个就是我廖某人。”
一次,沈醉在给廖理发时,廖又吹嘘说他如何会打仗。沈就问他:“那你是怎样被活捉的?”他还不服气地说:“非战之罪,更非我之过,国军在东北的失败,要怪只能怪最高统帅部的举棋不定,让我们错过了最好的突围时机。”但之后,他也不无感触地说道:“记得抗战胜利之初,我带兵到东北时,到处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耳目众多,几乎是战无不利;可是到了后来,我指挥部队准备从东北撤出时,路上想找一个老百姓带路都很难找到了……”
沈醉在他的回忆录中,还记录了一件有意思事。他刚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移交到北京功德林时,有天早上,正和杜聿明等几个熟人在谈重庆的情况时,杜聿明看到有个人匆匆忙忙地从门口走过,便大喊一声:“九百九,干什么这么忙?”那人理也不理,便走过去了。
不一会,又有一个人来问杜聿明要一张八分邮票,这人刚把邮票拿走,杜聿明又叫他“九百九”。沈醉感到很奇怪,怎么会有两个人同一个编号。只见那人一面向外走,一面冲着杜聿明说:“你才是‘九百九’呢!”
沈醉便忍不住问杜聿明:“到底谁是‘九百九’,你的编号不是二〇一吗?他怎么也叫你‘九百九’?”杜听了忍不住大笑了一阵之后,才告诉他说:“这‘九百九’不是什么人的编号,而是指那些有钱不舍得花,老是去揩别人的油的吝啬鬼。”
看沈醉还不明白,杜聿明又跟他解释说:“从前有个土财主,专门放高利贷盘剥别人。有天他收账回家,天快黑了,过河时,河边只有一条船了。他正想上船,驾船的人便故意说,今天过河不给一千文不给渡。他一听大怒,说平日只要十文钱,今天怎么便要这么许多?驾船的说,少一文也不让上船,他一听便卷起裤腿,把鞋袜脱下提在手中,准备涉水过河。因为他背上扛了几千文钱,走起来很吃力,走了几步,就软了下来,于是,自愿加一倍,‘二十文,渡我过去。’驾船的理也不理他。他就一边走一边加,船夫还是坚持非一千文不可。后来,快到河心了,水都淹到他的胸部了,他已加到九百文,船夫还是一动不动。他气极了,再往前走,水已到颈部,他加到九百八十,船夫仍不理。最后,他一脚踩进了没顶的深水中,还用力猛地向上一蹿,大叫了一声:‘九百九!’临到要淹死时,他还是舍不得多出那十文钱,所以,后来一些人就把吝啬鬼叫做‘九百九’了。”木匠
塞尚和左拉的友谊是怎么掰的
塞尚和左拉是中学同学,塞尚高大魁梧,左拉瘦小,左拉经常被人欺负,塞尚则总帮他解围。两人是好朋友。
塞尚老爸很有钱,但总是不被巴黎上流社会认同,他想让塞尚学法学,好跻身于上流社会,偏偏塞尚很固执,一心想学画画。于是,他爸就不给他钱了,所以青年时期的塞尚有点落魄。左拉出身贫寒,但由于口才、文采出众,很早就被巴黎上层社会接纳了。他时常会接济一下塞尚。两人的友谊持续了30多年。
但是,两人的审美却有很大不同。
左拉也提醒塞尚,你能不能多画点主流社会喜欢的题材?但塞尚却很执拗,他认为自己一旦画上商业画,就没有回头之日了。所以,就没听左拉的话。后来,他的老爸去世了,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有钱以后,他对于自己的作品卖不卖得出去,就更不在意,也就在他自己认为正确的印象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
1886 年,左拉的小说《杰作》出版。这部小说就是以塞尚为原型的,他刻画了一位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的艺术家。他还把书寄给了塞尚,没想到,平时温和平静的塞尚一看就火了。
于是,两人30 多年友谊的小船,也就说翻就翻了。

冯友兰:等我把我的新书写好了,再有病我也不治了

冯友兰最后几年,每年秋天都要到医院去住上一段时间。每次出院,他都会向医护人员表达真诚的谢意,一次,他对大家说:“我并不是想多活些年,才为你们这里的常客的,是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等我把我的新书(《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好了,再有病我也不治了。”人们问他这是为何,他说:“我都这个岁数了,想做的事情也都做完了,风烛残年,又是多病之身,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又何必浪费国家的医疗费?”
1990 年夏天,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终于完成了,11 月26 日,他在病榻上说出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然后,就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