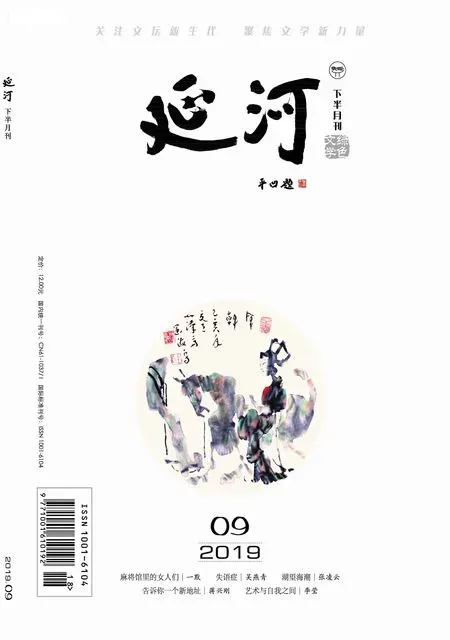一个女人的死亡之谜
2019-09-17夜阑
夜 阑
很长一段时间,一桩扑朔迷离的自杀事件像一团乌云一样,笼罩在丹枫新村的上空。那天中午,新村居民的集体睡眠被一阵横空而起的警车声粗暴地打断了。可以看到,那些肮脏模糊的玻璃窗上,布满了一张张惊惶失措的面孔。
报警人是一名自称雷肖肖的中年男人,民警赶到事发现场的时候,他正在楼道口不停地抽烟,不停地走来走去,神情焦虑异常。他的旁边,站着一个四、五岁模样的男孩,冷漠,孤傲,是他留给民警的第一印象。雷肖肖看到民警后,随即扔掉了手中的半截香烟,指了指对面的一扇门,105 室的周围早已被闻风而来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几个好事者争先恐后地向人民警察报告情况,在110 开锁匠开锁之际,他们已经七嘴八舌地将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汇报完毕。
105 室住着一位叫谢兰芷的妇人。五年前,她的丈夫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后来被拾荒者在一条河流的尽头发现,由于河水长时间的浸泡,死者的面目早已浮肿变形。据说,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为伺机离开这个家庭寻找着合适的机会,严重的抑郁症让他的精神几近崩溃的边缘,而女人对他的病情不但视而不见,反而充满了鄙夷和不满。在一个接一个痛苦难耐的夜晚里,男人被失眠折磨得形销骨立,而他的女人却不知为何变得异常娇艳。终于有一天,他怀着一种无比轻松的心情,爬上高高的悬崖,以飞鸟的姿势俯冲而下,从此结束了困扰他多年的抑郁症。
男人死后,谢兰芷一直过着独居生活。她有一个女儿叫丁晓仪,几年前已经嫁人生子。谢兰芷虽然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得出,这个女人的姿色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变故而日渐衰退,相反,那些悄悄爬上她额头的细细皱纹不但没有向世人告密她的年龄,反而别有用心地为她增添了一种丰厚的成熟美,再加上她的体态依然轻盈,所以即便这个女人一向独来独往沉默少言,她的一举一动却还是被无所事事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好色之徒尽收眼底。
说来奇怪,这两天不止一个细心的人注意到,谢兰芷的身影好久没有在小区里出现了。虽然她家的防盗门是紧锁的,可是里面的那扇木门竟然一直都虚掩着,似乎女主人随时都在做着出门的准备,却迟迟不肯出现,这种情形和她向来紧闭门户的情形完全迥异。临近中午,来了一名邮局的工作人员,去敲105 室的门,敲了半天,里面也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他又去敲,还是没有动静。这时,对门的张奶奶探出脑袋来,她那沙哑的叫声在沉默的楼梯口仓促地碰撞过几个回合后,回应她的依然是长时间的令人不安的寂静。奇怪!一种不祥之感就是在这个时候骤然降临的。当这个头发花白,精神高度紧张的老人在慌乱之中拨通雷肖肖手机的时候,这个中年男人正带着儿子在菜市场就猪肉是否注水的事情和肉贩子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雷肖肖是一名人民教师,他平时言语得体,性格温和,很少与人争执,更谈不上吵架。可是今天的他,显得有些异乎寻常。他一面用力挥打着面前蜂拥而来的苍蝇,一面神思恍惚地从一个肉铺游走到另一个肉铺。
这时候,雷小马就躲在不远处,漠然地打量着这一切。临近下午1 点,菜市场的高峰时段已过,菜贩子有的三五成群在打牌,有的趴在菜摊前打盹,空气中飘浮着一股腐肉和烂菜相杂的难闻气味,令这个夏日的午后,一时间变得酸腐难耐却又冗长无比。雷小马看到父亲那只握惯粉笔的手,在一团团血肉模糊的肉团之间迷失了方向,显得失落而又无力。后来,他好像看到父亲的嘴巴嗫嚅着说了句什么。
这句话借助一股风的力量,不偏不倚地飘到了摊主的耳朵里。只见那个肥头肥脑的男人一个阔步冲到父亲面前,怒气冲天地吼道,说我的肉注水,我看是你脑子进水了!
父亲的手在衣服上胡乱蹭了两下,脸色涨紫,气急败坏地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无奸不商,你小心着,我要去工商部门告你们!让他们查封你们!我现在就去!”
摊主盯着父亲的脸足有五秒,轻蔑无比地说道:“明明是想吃肉却吃不起,跑到这里来装什么蒜啊!”
父亲沉默片刻,突然对着面前那张因长期从事屠宰业而横肉四起的屠夫,骂出了平生罕见的一句脏话。
摊主神经质地跳起来骂道:“你×放屁!你敢再放一遍!”
“傻B!”父亲的声音听上去清晰响亮,就像他在课堂上朗诵诗歌一样,极富有质感和力度。
父亲的话音刚落地,雷小马就看到他的衣领被对方揪住,整个人被连推带搡,像一片树叶在风中摇曳不定。雷小马的心也仿佛给人一把揪住了,全身立刻变得软弱无力。紧接着,他看到父亲的身躯被高高架起,在半空中滑出了一道优美的抛物线后,随即演化成了一枚重磅炸弹,訇然落地!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叫!
就在那一刻,父亲的手机旁若无人地唱响了。
刚开始,雷肖肖并没有去找手机,他斯文扫地,心情懊糟,气急败坏。可是,那天的电话铃声听起来格外刺耳,有着一种歇斯底里的执着,仿佛一个垂死的人不肯放弃生命的最后一刻。无奈之下,雷肖肖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接通了来电。接完电话后的雷肖肖,脸色阴郁,眉头虬结,只见他拉过儿子,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菜场。
电话是张奶奶打来的。说来奇怪,按理说,如果有事,张奶奶第一时间打出的电话,应该是谢兰芷的女儿丁晓仪,而不是她的女婿雷肖肖。别看这张奶奶年纪大记性差,可她老人家还没老糊涂。据她仔细观察,作为女儿的丁晓仪,基本上是不来看望母亲的,偶尔来一次,也是急急匆匆,碰到人也不打招呼。倒是女婿雷肖肖比亲生儿子还要亲三分,虽说这小两口离异了,女婿照样像过去那样,三天两头地往岳母家跑。
雷肖肖带着儿子在第一时间赶到了那里,正如张奶奶电话里所讲,门,敲不开,谢兰芷,去向不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雷肖肖拨通了110 报警电话,之后拨通了前妻丁晓仪的电话。
防盗门终于被打开了,里面的情景却让人大吃一惊。只见谢兰芷面目平静地躺在沙发上,像是睡着了。民警上前一试,这位妇人早已气息冰凉,死亡多时。
从目睹这骇人的一幕到丁晓仪赶来之前,雷肖肖一直蹲在角落里抱头痛哭,这个一向懦弱的男人被眼前这一幕彻底击倒了。雷小马站在父亲身旁,惊恐的眼睛里不停地有眼泪流出来,残酷的现实让一个年仅五岁的孩子一下子变得成熟了。
丁晓仪出现时,现场周围已全部拉起了警戒线。当这个面色苍白、身材略微发福的女人急匆匆出现在楼下的时候,周围的议论声马上消失了,人们盯着眼前这个不幸的女人,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当丁晓仪看到母亲的遗体被抬出来时,浑身开始剧烈地颤动,几双飞奔而来的手几乎在同一时间将她牢牢按住。面对着呼啸而去的警车,丁晓仪用手捂住了脸,身体一寸一寸地软了下去,紧接着,无声的悲怆从她苍白的手指间一点一点地流淌出来,最后,岩浆般喷薄而出!
这种发自肺腑的痛苦让现场所有的人为之泪下,丁晓仪再无情,说到底,她是死者的女儿,血浓于水,这一点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一如她的痛苦无人可以比拟。善良的人们总是很感情用事,他们很快原谅了这个不孝的女人。
作为这起案件的负责人,钱芳菲队长在翻阅案件卷宗的时候,看到里面是这样记载的:经现场侦察发现,所有的房屋和门窗都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攀爬、撬窃的痕迹。室内衣橱柜、箱子等处也没有翻动的迹象。尸检报告上是这样记载的;死者胃里发现大量安定成分,身体其他部位无异常情况,属自杀事件。
这起不幸事件在事发第三天的当地晚间新闻里一闪而过,之后很快就被一起离奇的强奸案给覆盖掉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即使是形形色色的离奇事件,也会像白驹过隙一样,忽然来临又悄然消失,有谁会在意这样一起普通的不幸事件呢?然而,一个月后的一个举报电话,让这起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的不幸事件重新弥漫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
电话是由接线员转给钱芳菲的。举报人的声音听上去有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天知道你们这群废物是怎么破案的,105 室怎么会是自杀?她为什么要自杀,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调查?”钱芳菲正要询问他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他杀时,电话里的人似乎根本不屑于听,继续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凶手整天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转悠,你们却浑然不觉,你们这群酒囊饭袋!”电话突然挂断了。钱芳菲被这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弄得一头雾水。然而,接下来每隔一段时间,那个人的电话又会打来,说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话后突然挂断。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说:“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有病才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们,我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凶手逍遥法外!我还可以告诉你们,这是一起蓄意杀人案,杀人不见血,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么?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么多了,否则要你们这群废物干什么?!”
后来,当钱芳菲从暗红色的档案橱里,重新翻出那叠已经蒙上一层细细灰尘的卷宗时,举报人在电话里所说的话,再一次萦绕在她的耳边。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钱芳菲在司前巷1-15 号找到了丁晓仪现在的住所。和雷肖肖离异后不久,丁晓仪就搬到了现任男友李向前的住处。李向前是个采购,经常出差在外。钱芳菲找到她的时候,这个女人独自在家。
丁晓仪坐在钱芳菲的对面,钱芳菲注意到,女人脸上略施薄粉,看上去精神状态还不错。她还注意到,一条神秘而不失妖媚的婚纱悬挂在床头。墙上,挂着一幅巨型结婚照。只是准新郎的脸隐藏在婚纱背后,若隐若现,仿佛丁晓仪依偎的,是一个缥缈而模糊的梦。谁会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噩耗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婚姻涂上了一层悲剧色彩,想到这里,钱芳菲不禁感慨世事无常,命运多舛。
当话题涉及到母亲的不幸死亡时,丁晓仪马上低下头,记忆重新把她拉回到了不久前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母亲是什么时候?”
丁晓仪抬起头,抽噎着说:“半年吧。说完,旋即又把头低了下去。”
“半年?可是有人说,就在事发的前几天,看见你从母亲家出来。”
丁晓仪猛然扬起头,悲痛在极短的时间内转换成了愤怒。
“谁说的?他们在胡说!”
停顿片刻,她又极力使自己冷静下来,解释道:“我和母亲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见面总免不了吵架,特别是我离婚后,基本上就不怎么来往了,最起码有半年的时间。警察同志,我说的可都是实话,你说,我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难道你们怀疑是我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说到这里,女人又显得悲愤无比。
“请你不要误会,这不过是一次例行调查,希望你能配合。”
沉默片刻,丁晓仪终于下定决心似地说道:“其实前不久我是去过一次,可是待了很短时间我就走了。因为那次我们又吵起来,吵得很凶。”说到这里,丁晓仪猛然在钱芳菲毫无预料的情况下,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
“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那次吵架,我母亲也不会……”她激动地抽噎着几乎说不下去,突如其来的泪水毁灭性地破坏了她的妆容,使她的脸看上去惊心触目。
“为什么吵?”钱芳菲心头一亮。
丁晓仪的眉峰紧蹙着,似乎回忆过去,对她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还不是因为我的婚姻。当初,我母亲就极力反对我离婚,现在又不同意我和李向前的婚事。为这些事,她老是和我吵,那天吵得很凶。她这个人脑子原本就有些问题,那天可能我的话刺激到了她,她很激动,骂了好多难听的话,可我没想到她真的会走上这条绝路!”
“神经病?”钱芳菲感到有些意外。这一点和她所掌握的关于死者的有关情况存在不少出入。据对门那位寡居多年的张奶奶之前报料:“他家的什么事能逃过我的眼睛?这女人苦啊,她家那位先开始是抑郁症,后来抑郁着抑郁着,不知道怎么搞的,又成了神经病。他犯病了就打老婆,我可不是瞎说啊,警察同志,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有一次他把女人的头摁在地上一下一下地磕,像鸡啄米一样……”这位神思已经有些恍惚的老人一边说着,一边还伸出鸡爪似的手在钱芳菲眼前比划着,唯恐自己语焉不详。
还有一位看上去别有用心的老年男子,有一次在丹枫新村的门口冷不丁截住钱芳菲的去路,他先是神情紧张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然后压低嗓门:“谢兰芷是个好女人,她死得太突然了,为什么说走就走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一连串的追问让钱芳菲一时无从回答,直觉告诉她,这位痛苦不堪的男人,大概是那个已故女人的暗恋者之一。
“你知道我母亲为什么反对我和雷肖肖离婚吗?”丁晓仪沉默片刻,神情诡秘地向钱芳菲问道。
“她经常趁我不在的时候去我家,而每次从我家离开之后,雷肖肖的短裤都会莫名其妙地失踪,你不觉得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么?更无聊的是,有一次,我竟然无意间在她的皮箱里看到了一大堆男人的短裤。我看她病得不轻!”说这话的丁晓仪,和刚才那个痛失母亲的女人简直判若两人。
敏锐的职业洞察力让钱芳菲对这个看似与调查毫无联系的无聊话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她正想追问下去,一个男人突然推门而入。钱芳菲立刻意识到,他就是丁晓仪现在的男友——李向前。
和雷肖肖的单薄瘦弱相比,面前这个男人除了高大强壮之外,眉宇间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阴鸷。
李向前一言不发地看了一眼钱芳菲,丁晓仪连忙解释道,钱队长是来了解情况的。
“了解情况?”李向前语气怪异,“不都结案了么,自杀,还有什么好调查的?!”说着,他往卧室一头走去。
“你觉得她为什么要自杀呢?”钱芳菲颇有兴趣地盯着男人的背影问道。
“为什么?”李向前回过身来,他的手在剃得发青的下巴颏上摩挲着,似乎觉得这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看看钱芳菲,又神情暧昧地看看丁晓仪,语气深沉地说道:“绝望,我想是绝望吧。”
“什么绝望不绝望的,你别胡扯好不好!我说过,我母亲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一个脑子不正常的人干出点什么不正常的事,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丁晓仪说着,狠挖了李向前一眼。
钱芳菲从丁晓仪家里出来时,已经是晚上八点。漫天的星星在遥远的夜空里静静地散发着光芒,一声声蛙鸣从池塘的荷叶下传来,更增添了夜的宁谧。
丁晓仪的变化莫测让钱芳菲心里疑窦丛生,凭她敏锐的职业嗅觉,她能感到这个女人除了痛苦之外,内心一定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真是他杀,凶手又究竟是谁呢?
钱芳菲后来又去了雷肖肖家,雷小马一个人在家。一碗方便面,一包榨菜,就是这个男孩一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晚餐。很长时间,这个沉默少语的孩子只顾着低头吃面。
钱芳菲环顾四周,没有女人的家,到处都是冷清,狼藉,报纸杂志胡乱堆放。她注意到,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家庭合影。照片上的丁晓仪,左半边脸不幸被一滩墨水浸染,整张脸看上去滑稽可笑。雷肖肖的一只手轻轻搭在女人的肩上,雷小马当时还被母亲抱在怀里。谁会想到曾经其乐融融的一家人,现在却是陌路?唉,世事难料!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钱芳菲,此时也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约莫半个小时的样子,雷肖肖胁里夹着一沓作业本从外面回来了。他胡子拉碴,神情疲惫,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重的烟味。见到不速之客时,一丝惊慌从他眼里一滑而过,不过,他很快就神态自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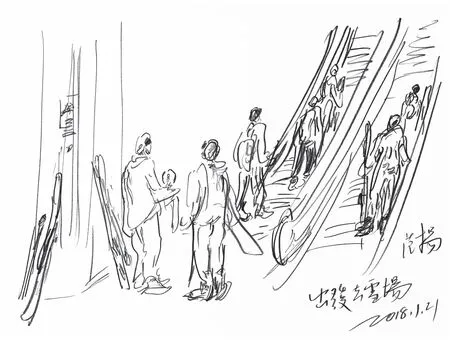
钱芳菲单刀直入:“6月21 号、22 号这两天你都在干什么?”
雷肖肖稍稍沉思了片刻,就用语文教师那种特有的流畅自如的语言叙述了过去两天发生的事情。
21 号下午,雷肖肖突然接到儿子班主任的电话,班主任在电话里火药味十足,一接通就狂轰乱炸:“你们这些做父母的怎么回事?!一点责任心都没有,都几点了,也不来接小孩,不打招呼不请假,当老师一个个是保姆……”
雷肖肖心慌意乱,挂断电话,急匆匆往学校赶,快到校门口时,一眼望见雷小马呆坐在花坛边,目光茫然,神情黯淡。
“外婆怎么没来接你?”雷肖肖语气里充满了对岳母的怨怒。
雷小马不说话,反瞪了父亲一眼,起身就往外婆家走。
父子俩一前一后到了谢兰芷的家门口,防盗门是紧锁的,而里面的门却虚掩着。雷肖肖敲了几下,无人应答。雷肖肖嘟哝道:“毛病!”后来,父子俩就离开了。
晚上十点左右,雷肖肖再次拨打岳母家的电话,电话依然没人接听。十点一刻、十点二十分、十点半,雷肖肖每隔一段时间就打过去,而电话那头像被催眠了,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雷肖肖再三迟疑,终于耐不住性子,拨通了丁晓仪的手机。
“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打了一个晚上的电话,家里也没人,会不会……”
几秒钟,也许不到几秒钟,雷肖肖却觉得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昏睡过去,过了很长时间,才听她冷冷地说道:“她能出什么事?她要出事倒是好事,所有的账从此可以一笔勾销!”说完,丁晓仪摔断了电话。
第二天,一整天,雷肖肖都心神不定,他觉得有种不祥之气仿佛天上的乌云一样,越积越厚,越积越多,似乎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后来,就接到了张奶奶的电话。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雷肖肖努努嘴巴,以示自己的话已经说完。他走到窗前,点燃一支烟。一簇红色的火光在暗夜里一眨一眨,仿佛一只只诡秘的眼在无边的黑色幕布下大施魔法,不断吞吐出一缕又一缕的烟雾。
“你们为什么离婚?”钱芳菲话锋一转问道。
夜色中,男人的肩膀微微一颤。
“为什么?”雷肖肖的语气颇有些嘲弄,他对着黑暗吐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烟圈,说道,“碰到有钱人,哪个女人不想跟了去?”
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钱芳菲想起了李向前和那幢隐藏在林间的红色小楼。显然,男人在物质上的悬殊差距,让有些女人做出抛夫弃子的举动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除此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理由?她想到临走时与丁晓仪的谈话,如果谢兰芷的特殊爱好,可以看作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的正常表现的话,那么,雷肖肖呢?难道他作为一个正常人,就泰然自若地接受了这件令人无法启齿的事情?况且,作为一个丈夫,如果发现短裤屡屡丢失的事情,为什么对妻子只字不提?为什么谢兰芷总是挑女儿不在家的时候出现在她的家里?一系列的疑问,让钱芳菲对这个特殊的家庭充满了疑惑。
“听说,丁晓仪的母亲一直很喜欢你,几乎把你当亲儿子看待?”钱芳菲假装漫不经心地问道。
“她母亲这里有毛病。”雷肖肖指指自己的脑袋,“她病了好多年,动不动就要发作。我想,丁晓仪可能已经告诉过你了。”
钱芳菲注意到,他点烟的手有些颤抖。
当晚,钱芳菲接到侦察组小刘的电话,他说打匿名电话的那个人查到了。虽然他每次变换使用的都是公用电话,但是因为他的长相过于惹人注目,所以据公用电话亭的一位老人提供线索,这个叫冯一清的男人很快浮出了水面。他在离丹枫新村不远的地方开着一家私人药店。
钱芳菲出现在药店门口的时候,这个长阔脸,狮子鼻,年过半百,已经谢顶的药店老板,正翘着二郎腿横躺在树荫下,屁股底下的藤椅随着他身体的摇晃,不时发出一连串扭捏的叫唤。他斜扫了来人一眼,嘴角得意地向上扬了扬,似乎对她的到来尽在意料之中。
他那只胖得出奇的大手在玻璃柜台上得意地一拍,说道:“我一开始就觉得奇怪,他先开始在我的店里转来转去,后来说什么要买一瓶安眠药。一瓶安眠药?我说你开什么玩笑?如果我卖给你一瓶安眠药,明天我的药店就可以关门了。他又说,‘半瓶呢?半瓶总可以吧?’他揉揉额头,似乎头很痛的样子,说,‘我晚上睡眠不好,你总不能让我为买这样一个东西,一趟趟地来回跑吧。’我说你以为这是菜市场买菜,还可以讨价还价?没有医生的处方,别说半瓶,就是半粒,我也不可能卖给你!”他后来走了,第二天又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处方,从我这里买走了六颗安眠药。后来,他一连来了好几次,每次都是买六颗。我还好心劝他,这种东西吃多了,要依赖的,你为什么不试试其他方法?比方说心理治疗。他听到这句话居然大为光火,说,‘你看我像是有病的人吗!我只是睡不着,睡不着而已!’他后来不来了,再后来,丹枫新村就出事了。”冯一清说到这里,故作诡异地冲钱芳菲眨眨眼。
钱芳菲有种直觉,他所说的这个莫名其妙的男人就是雷肖肖。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雷肖肖一次又一次地设法从冯一清手里买走安眠药,不是买给自己吃,而是买给他的岳母吃!钱芳菲不由得为这个大胆的推断感到一震!然而,她还是疑惑不解,因为从现场侦察和尸检情况来看,死者应该是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那么,谢兰芷为什么要自杀呢?毫无疑问,她的自杀与雷肖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勾连。一时间,钱芳菲觉得眼前的一切忽而明亮,忽而迷茫。
“雷肖肖?可是我们凭什么断定他是凶手呢?你知道,法律是讲求证据的,可不容许妄加揣测。”钱芳菲神情严肃地说道。
“证据?你以为我吃饱了在这里胡说?我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这里面难道还有假?!”冯一清一时间激动得额头油亮。
“你看见什么又听到什么?”
“他们抱在一起,抱在一起你懂不懂?”冯一清说着双臂交叉将自己的身体抱住了。“后来,我看到那家伙又一把把她推开,跪下来苦苦哀求她,我求求你,不要再纠缠我了,行不行?!”
女人看到他哭,还上去抚摸他的头发,可是被那家伙的手一把挡开了。
她还不肯罢休,“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是不是?是不是?”她紧追不放,一次次试图把他的手抓到胸前,可是他却像躲瘟疫似地逃开了。
女人恼羞成怒,“你是个骗子!你当初为什么要背着晓仪勾引我,为什么?后来给她知道了,她却认为是我在勾引你,她心里恨死我了。我是个罪人,我真是个罪人!”呜,呜……女人说到这里时,不由得失声大哭,后来突然跳起来从对面的五斗橱上抓起一把水果刀就往胳膊上划去,给那个家伙反应过来,扑上去一拳打飞了。”
“你当时在哪里?”钱芳菲听到这里时,不由得打断了药店老板的叙述。
冯一清表情讪讪地笑笑,拍拍自己的额头说道:“那天晚上我正好路过她家的窗口,当时窗帘半掩着,我只要头稍稍一探,就可以看到他们扭扯在一起。过了一会儿,我听到那个家伙居然无耻地说,‘你想死是不是?好,我这里正好有一瓶安眠药。’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的药瓶,扔到她面前,然后夺门而去。”
听到这里时,钱芳菲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当时的情景,女人饱含泪水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疯狂,这种不伦之恋在给她带来巨大幸福的同时,也挟裹着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足以让她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情。而那个弃她而去的男人,恰恰是引她走上这条不归路的罪魁祸首!
那个家伙走后不久,丁晓仪就来了。她一进门,一下子就嗅出了房间里弥漫出的一股非同寻常的气息。看到母亲坐在床头一副失神落魄的样子,她迟疑了一下,把一个红色的请柬放到她面前,表情平静地说:“我要结婚了。”
谢兰芷听到这句话时,猛然抓起请柬撕个粉碎。后来,她们母女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
丁晓仪气急败坏地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的那些破事,我告诉你,你们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可是瞒不过我,瞒不过你们的良心!你们要遭天打雷劈的!”她说完摔门而去。
“我看到谢兰芷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可怕极了,我想这个女人肯定是绝望了。”冯一清说到这里,长叹一声,神情变得黯然忧伤。
钱芳菲从药店里出来时,一股冷风冷不丁灌进了衣领,让她不由得从心底升起了一股无法抵挡的寒气。至此,谢兰芷的死亡之谜应该算是真相大白了。然而,这个结果却让钱芳菲的内心沉重无比,一件没有凶手的凶杀案,她明明可以看到凶手亲手制造了一场杀人案,却只能任由他逃脱法律的制裁。这时候,她似乎听到了死者谢兰芷的苦苦哀求,一次次地在耳边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