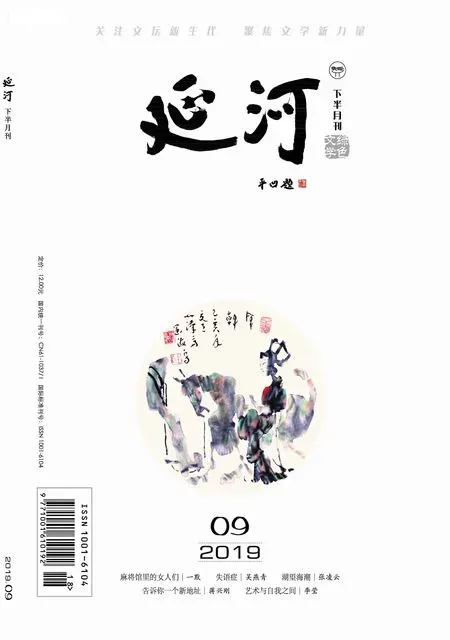到城里去
2019-09-17刘国星
刘国星
单从空气里就能分辨出城里和草原的,老牧人像个空气美食家,一路从草原“品尝”到这个叫作大板的城市街头的,一边清新,一边冷浊。鼻子嘴巴的感觉百分之二百得真切分明——草原的空气清新而凉爽,还微微杂点花草泥土的香味,沁人心脾。城里的空气呢,又浊又冷,时隐时现地涌动出臭豆腐的气息。嗅到这样的空气,城里生活的其其格能有好心情?老牧人咳嗽了两声,对其其格的怜惜又沉渣般泛起来了……是时天色临近黄昏,城里却蓦然地飘起雪花子,落地即化的那种。灯突然全亮起来了,灯光掺杂水光呈现出流淌的动态趋势。老牧人每一步都能踏出水声,不大不小,执着的,很粘脚,弄得老牧人心里也有了波动和起伏,也有了些许的疙疙瘩瘩。草原不是这样的,落了雪,有枯草承载着,就不易化。草地益发显得厚重而又轻盈,绵绵的,软软的,像个熟透的娘儿们。这样,每一脚踏出去,都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令人浮想联翩啊!雪花有意无意地落在老牧人银白的胡须上,胡须的白和白雪的白慢慢融在一处,晶莹着。当落在老牧人背后的马头琴上,琴弦就不甘寂寞地发出弱小的叮叮声,雪片子和琴弦之间有了窃窃私语的呼应,听在老牧人的耳朵里,像其其格百灵鸟般的呢喃呐。车流人流汇聚成河,老牧人也“流”在这条河流里,随波涌动……可前后左右的人影车身,倒让他觉得有种窒息的东西压迫着。抬头望望天空,城里的天空也不是天空的样子,不分明,倒是楼群的暗影,刀劈斧凿般,一簇一簇地笼罩下来……想象着其其格穿梭于楼房森林的脚步,老牧人低头长长地叹了一声,没想到却连带出来一口痰。这可麻烦了,面对摩肩接踵的行人,老牧人一时寻不到“处理”的地方……这时背后突然响起一声尖锐的喇叭声,骇得他一哆嗦,嘴里的东西也不自觉地滑咽进肚里。
其实老牧人本应也是一个城里人的——孙女其其格前年就要接老牧人到城里一起住,摆出的理由都挺“硬”——其其格先亮出自己是电台主持人的大牌子,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应该做个“孝顺”表率,要不民众这块是说不通的。接着列举了爷爷孤雁一般的生活状态,再说了她家的楼房和医院的邻里关系。其其格那天小嘴叭叭的,说着说着扭麻花般依偎过来,都孩童般撒娇了。多年来,这是其其格的撒手锏,百发百中的,杀伤力极大。谁知老牧人却坚决的像棵树,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逼急眼了,就用车轱辘话左搪右塞招架着,爷爷好呢,真的,爷爷好呢!其其格再坚持,老牧人索性眯缝起眼睛,笑而不答,磐石般水火不侵、烟酒不进……那时的老牧人,皱纹堆叠,咧开嘴露出牙的,都弥勒佛了。爷爷心里自有爷爷的弯弯绕,理由也挺“硬”,不说罢了。——其其格结婚才两年,还添了孩子,自己大马金刀地住进去,能做个啥?出来进去不方便不说,哪会不增加她的负担哩?再说,老牧人也确实离不开草原,离不开他的牛马羊驼。别人离开是别人的事,自己离开不离开是自己的事。七十多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出场、跑青、接羔、打草,天天和牛马羊驼滚在一处,根须都扎在草原的地层深处了,哪一根不扯着骨头连着筋呢?再说了,老牧人是草原琴师,早已是人琴合一,须臾离不开马头琴的,若在楼房里拉拉琴,四邻不安的,这哪儿是去享福,这是去添乱。不去,真的不能去啊!
现在,走在大板城的街头上,老牧人十万个未想到自己会不“请”自来。自己是不是像个小孩子?想一出是一出的!让老牧人自己说,却又是十万个说不清的。也许只有长生天才知道吧!
昨晚牧归的空气里飘荡着老牧人悠扬的琴声,也弥漫包裹着一股浓浓淡淡的奶香。母牛母羊忙忙地进食一天,并未忘记栏里的羔子和犊子。也可以说,它们忙忙的进食,就是为了能与羔子和犊子早一分钟相见,能有充足的奶水供给它们吃。一天了,十几个小时呢,做额吉和做羔子犊子的彼此牵着肠,挂着肚啊!羔子和犊子这会儿可算逮住了,吃得咕咚咕咚响,嘴角沾挂雪白的奶浆子。这都无可厚非。还前膝跪地,英雄般晃荡起小尾巴,兴奋得无以复加。这当然是天下最幸福的了,这当然也算无可厚非。可做额吉的呢,失却了端庄和稳重,有点“过”。“奶”就奶吧!母牛母羊竟然齐展展伸出热乎乎水淋淋的舌头……舔了。出格喽!拉琴的老牧人成了“多余的”,他在那时自觉不自觉地止住琴声,眼巴巴地看过去,发出笔直笔直的渴盼光芒——母牛母羊舔一下,老牧人的心也跟着颤一下,仿佛那“舔”,就舔在了他的心尖尖上,有点甜,有点酸,还有点想流泪,说不清的那种。慢慢地,老牧人觉得“融化”了,心里湿漉漉得一塌涂地,泛滥了,一阵阵的暖流冲垮了他。他知道,他想其其格了——他的“小犊子”离婚了,若不是嘎查达告诉他,他还蒙在鼓里,以为小犊子好着哩!小犊子,小犊子现在就一个人在闹嚷的城里单打单,成了孤雁。老牧人看一眼茫茫的夜色,拉了几下琴,想给其其格听,可远远的,总觉得够不上。后来就做了一个决定:无论如何,到城里去,到那个叫作大板的城里去,去看看他的“小犊子”。
老牧人没乘车,却骑上马,半夜急颠颠地开始往城里赶。不是他不想坐车,是他闻不惯汽车的汽油味。坐上车,他的五脏六腑都会翻江倒海,那会要了他的这条老命。老牧人一夜未眠,夜的漆黑与宽广放大了他的思念,其其格的音容笑貌,像影子一样在他的头脑里远远近近。想抓,却又无能为力;不抓,她又执拗地矗立在那里……就是有张照片也是好的啊!细细想来,十几年了,草蛇灰线般从未曾离开,但却从未如此这般的清晰强烈过。小犊子,成了孤雁的小犊子。陪伴我的有草原,有马头琴,有活蹦乱跳的牛马羊驼。你呢?你有啥?——降生不幸失去额吉的红皮子小兽,五岁上又没了阿爸,她哪儿有人“舔”啊?十几年前跟着自己,考学进城后回草原的次数都能用手指头数过来。说是“忙”啊!挺幸福的!四周人翘大拇指都说好。人啊,还是忙点“好”。老牧人也只能说好啊!他的小犊子像个陀螺,在一片的“好”声里,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他的视线,走出草原,走进城里,还扎了根。让他连一句阻拦的话都没机会说!也不敢,也不能。生活像被啥“东西”推搡着行进!老牧人看不见“那东西”,但却能感觉到“那东西”的力量,强大到无与伦比。想到这,老牧人急切起来了,马儿喷出热气,呼哧呼哧地跑,蹄子敲击路面,砰砰地,一如急促的心跳。老牧人依旧连连挥鞭,马儿扑扑地打起响鼻,翻蹄亮掌,浑身都包裹了一层水汽。坐汽车也就两个小时的路,可骑马却要走一天。老牧人恨不得一步跨到其其格的身边。从头发梢一直到脚后跟,认认真真地看看他的小犊子,把她“烙”在脑袋里。让她知道爷爷爱她,她不是孤雁,爷爷和草原还博大地站在她的身后。老牧人矮矮地对骑马恳求说,老伙计,你这回体谅一下我,啊,体谅一下我!老牧人说着还大幅度地抹了两把。在城郊处,老牧人跳下马,来来往往的汽车喇叭声惊吓了骑马。骑马脚步变得突然,眼神也变得躲闪、飘忽。有几次险些跌下老牧人。到了城里,老牧人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急切的心情也得到了缓解。老牧人见车越来越多,路上也有了行人,就决定步行进城去看其其格。骑马歉疚地用嘴唇嗅嗅他的手,像是对它的胆小如鼠做检讨。老牧人大度地拨转了马头,拍拍马屁股,安慰说,回吧!骑马颠跑几步,回转头看老牧人,目光中像是不舍。老牧人刚举起手要再重复说回吧!可一声喇叭响让马儿惊得连连尥蹶子,跟头流星地跑出了老牧人的视线……
前边不远处是文化广场,转过广场,就是其其格住的小区。老牧人不急不缓地走着,深深地呼吸几口平服住了过快的心跳。多少年来,他始终以为自己和其其格在一起。你想着我,我想着你。可现在看,完全不是那回事!城里还是城里,草原还是草原。雪不知啥时候停了,满地的雪水在霓虹的映衬下,大写意般涂抹油彩,赤橙黄绿青蓝紫,像极了其其格小时候穿过的那件七彩蒙古袍子。其其格是老牧人一手带大的。老牧人明里是爷爷,暗里也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额吉”。面对那个红皮子小兽,老牧人先是抱着,后来背着,再后来是领着。一口羊奶,一口牛奶,一口马奶,一口驼奶,喂活了她。她活长了。奶要烧开了喝,放点糖,还怕烫伤她。老牧人那条老舌头就变成了温度计,百分之百的准。后来,竟然连其其格发烧不发烧也能“测”出来,而且还能报出温度。四五岁上,其其格就能和老牧人一齐去草原深处放牧、玩耍了。他们那时天天和牛马羊驼的羔子犊子驹子混杂一处,气味相投,两两都散溢出一股浓郁的奶芽子味,都成了朋友。也采山丹花、喝山泉水,狗儿跳,畜儿跑的。牛马羊驼也欣欣然接纳了他们,其其格给牛犊子编过花环,给追风的马驹子喂过青草,给羊羔子头顶头地比过力气,也给驼羔子治疗过背上的“包”……其其格和老牧人跟草原上的一根草、一朵花,和牛马羊驼并无区别,他们也都成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兽”。都忘记了岁月的流淌,只在蓝天白云绿草长风间“悠然”。每每折腾累了,老牧人会席地盘腿拉起马头琴。其其格抖肩、颠步,头上的小辫子随影晃动,翩翩起舞,七彩蒙古袍子迎着霞光,就像盛开在草原上的一朵花。牛马羊驼的羔子犊子驹子羡慕的不行了,都停住吃奶吃草的嘴,大睁着黑眼睛黄眼睛蓝眼睛看啊看。就是牧羊犬还算机警,看几眼,回头听听风声。看几眼,回头听听风声。那时,其其格这朵花成了草原的中心,你看你看,其他的花是迎风来回晃的,没有风则静止安然。而其其格这朵呢,能跑、能跳、还能唱,是一朵喜煞人的“花”。老牧人手上在拉琴,可眼睛却一刻也未离开过其其格,仿佛其其格那里有根线,在紧紧地拴住他,也让他的目光在抖肩、颠步,翩翩起舞。老牧人高兴啊!可老牧人没想到其其格竟然上学去了,其实也必然会上学的。在别人那里是“正常”,孩子成长呢!在老牧人这里却有了一点点的“意外”。老牧人慢慢看出来,其其格也仅仅是有股“奶芽子”味,其实在本质上,和这帮“朋友”,和这群“兽”,“路”却是不同的。这孩子是个念书的料。小嘴特别地好使,背起诗歌一嘟噜一嘟噜的,像一串串水格灵灵的紫葡萄。别人都说“好”,老牧人心里却有了一点黯然,可表面上却是一片泰然和欣喜,也跟着别人一齐说“好”。那时的老牧人就不敢想,其其格到底是属水性的,早晚是要随着唐诗宋词流出草原,走进城市的。老牧人的心里就常空落落地空出一大块。其其格还常从商店里,买回小汽车、楼房模型等玩具。嘴里模仿汽车的马达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在炕桌上驾驶得有滋有味。老牧人拉了马头琴的高音,指着包壁他新买回的丰收图,让其其格看。丰收图上画满肥壮的牛马羊驼,有点卡通有点夸张,但却和老牧人脸上一样充满蓬勃的喜气。老牧人指点着说你看,你看多富态!其其格瞟瞟眼皮却仍专注在她的汽车上,随口说那有啥看头?草原上全是那“玩意”。老牧人脸上的喜气一下子就以百米的速度跑光了,变得僵硬而狭长。包里复又充满了其其格嘟嘟嘟嘟的马达声。每每上学分别时,其其格都要依偎进老牧人的怀里,摸着老牧人一大把的白胡子,说,爷爷,我念好书接你进城坐汽车!嘟嘟嘟……
路过广场老牧人没想到会被“绊住”。城市夜晚的广场是从不寂寞冷清的,即使在这样的天气里,也没有阻止广场大妈们的舞步。相反,这样的天气,在灯光水光的照耀反射下,大妈们的舞步身姿却凭空增添了一种魔幻鬼魅的东西,亦真亦幻。难得的一种效果出来了,刺激的人膨胀着,血沸了。音乐和舞姿的河流汹涌出一幅画面:压抑不住的海潮一涌一涌的,涌在悬崖的边上,有几只海鸟飞过来戏水,却被海浪拍死在悬崖之上……没拍死的那几只仿佛拥有了胜利,癫狂了,嗥叫着,飞窜着,呼唤着远处的海鸟来加入狂欢……老牧人路过大板文化广场时,见大妈们正随着刺耳的音乐忘我扭动。可也日怪了,老牧人匆忙的脚步自觉不自觉地踩在了点子上。仿佛那声音似套子,老牧人跺跺脚,可一踏出去,又落在重音上,老牧人不觉哑然笑了一下,脚都不敢往外迈了。广场里,音乐亢奋,人也亢奋,灯光变幻色彩推波助澜,大妈们一个个好像立在南海的浪头尖上,青春、阳光、少女,在赛啰啰,在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地在弄潮……音响说停就停了,海潮说退就退了,露出了水淋淋的磨石地,一块一块凸起细碎的颗粒。大妈们突然从浪头上下来了,有些不适应,有些不爽。有人说可能电路检修。广场里漆黑一片,黑色的人影摆置在黑色的背景里,失去呼应失去光彩。好一阵才远远地看见头顶夹缝中的那轮残月。今天不行就到这吧!到这!大妈们齐齐“嗨”一声,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大妈们收拾行头时,身边悠悠地响起了马头琴声,如月光一样自然地撒过来。月光!城里的月光!久违了,真的久违了!大妈们稀罕起来了,开始和着琴声翩翩舞起来。可也怪了,人还是那些人,那舞姿却失去了当初的劲爆,一个个变得袅娜、端庄、雅致起来了。老牧人运弓、揉弦,双目微闭,在心里也不禁浮现出一幅画:月光如水,草原五畜丰收了,空气中散发着奶香酒香和草香,牛马羊驼静卧栏里反刍,苗条挺拔的其其格身着盛装起舞。围定篝火。仰谢长生天,俯拜厚土地……在人与天地的交汇中,人得到了一种大“静”,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舒展和自由。
音乐是无界的,老牧人对马头琴的琴技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音响是啥?是机器。马头琴是从“马”的皮毛骨骼里幻化来的。音响再掩盖也会发出金属撞击的冰冷声音,而马头琴发出的声音却有马的体温和嘶鸣,能与琴师的心灵相伴相偎。相传,马头琴是草原牧人苏和制作的,他为了挽住死去的白马。按梦中白马教给他的技术:用白马的马皮制作了琴箱,用马尾马鬃制作了琴弦,用马的腿骨制作了琴杆,还在琴头上雕刻了马头。每每拉起琴,嘈嘈切切,像他对白马诉说,也像是白马对他诉说,更像是天地长风对他说,也像他对天地长风说……马头琴一代代传下来,老牧人拉了一辈子琴,慢慢体会到,琴就是联系天地和五畜的语言。草原上赛马之前要拉,摔跤之前要拉;射箭之前要拉,祭祀之前也要拉。最神奇的就是拉给五畜听。草原上的母畜失了孩子,小羔子小驹子小犊子在寒冷的冬季里的失了额吉。是要认干亲的,只要把这对母子放在一处,拉响马头琴,唱起认亲歌……吃草的母畜慢慢就会停下来,眼里流出泪,还把饱满的乳房凑过去,哺育孩子直到长大成人的……琴声是一条神秘的“路”,把额吉和孩子联系在一起,也把母畜和羔子犊子驹子联系在了一起。让它们的“心”走近了“心”,实现了“零距离”。

没想到,电说来就来了,蓦然地整个广场都亮了,人与人的距离立马就出来了。你仍然是你,我还是我。也好像是城市巨人一翻手就甩出了天上的那轮残月。不需要的。也是的,城里哪能离开强劲的电呢,没电的城市还叫城市吗?大妈们的音响也响起来了,劲爆且尖锐,盖住了老牧人的琴声。老牧人自觉地住了手,现在进了城里,老牧人觉得他和其其格住进了一个营盘,圈进了一个栏里。虽彼此看不见,却已然近在咫尺。他的鼻子又被烤羊肉串的气味吸引过去了。离开时,他看见大妈们的身姿又扭起来了,仿佛也注上了电,亢奋而激越。
烤羊肉串的是个身着白衣的瘦子,他的身边却立着一个能装下他的胖女人。店面不大,却人头攒动,看得出,生意很不错。瘦子看老牧人的眼光里有点“痴”的东西,他手握羊肉串凑近老牧人,讪讪地说,老人家!吃串、吃串。可目光一刻也未离开过马头琴。目光吐出了舌头,有点“馋”的意思了。老牧人接受了瘦子的热情,吃了一口,觉得嗅着气味好,却失去了草原手把肉的那股鲜。羊肉串的香气是在外面的,诱惑的只是你的鼻子。手把肉的香气还含在肉里,能安抚你的舌头、嘴和肠胃。老牧人终究还是发现了瘦子的目光,老牧人就推了推琴,问,你拉吗?瘦子触电般缩了手,擦了擦,样子怕“脏”了琴,嘴里喃喃着,我……我不配拉。十几年了。瘦子握住了老牧人的手,瘦子说,我最爱听那首《万马奔腾》。老牧人摸到了瘦子指肚上的条形茧,知道遇上了知音。你咋进城?咋烤上羊肉串了?老牧人话尚未问出,瘦子急急抽出手,颠跑着去忙生意——灶台上的胖女人早嚷嚷起来,声音比得上珠穆朗玛。——巴特,你挺尸哩?!老牧人才知道瘦子竟然叫个巴特。竟然跟儿子重名。巴特可了不得——在草原上,那可是英雄的意思啊!等老牧人走时看见巴特两手并用,扭起腰身,翻烤扇子般的羊肉串,一层一层的烟火气包裹了他,再也是看不清了。老牧人呛得接连打了两个喷嚏,心里无来由地漫过一座山的影子,说不清悔恨还是伤心的。
1997年草原修来铁路,说是还要开矿。嘎查达推荐其其格的阿爸去当火车司机,要让老牧人一家的日子锦上再添一朵花。老牧人却挡住了,铁青的下巴仰仰着,拿出了做父亲的姿态,很权威,很说一不二。老牧人说,蒙古汉子都是骑马的,我们不开那个喷气的长虫子。这句话惹得其其格阿爸咧开阔嘴大笑,却气得嘎查达翘起了胡子,嘎查达手指戳点着说,你们,你们真是个穷命!巴特看看父亲,父亲看看巴特,有点唱双簧的意思了,巴特说,够用就行啦!我看你们现在有些贪!“那朵花”我们不想要啦!哈哈哈哈……嘎查达在笑声中摇摇头,走远了。牛不喝水咋能强按头?谁知那年冬天,其其格的阿爸出意外,竟早老牧人一步升上长生天。嘎查达得知消息后,连连摇头,在屋里走柳,右拳一下一下砸着左巴掌,嗨嗨个不停。当初要是听我的,嗨!老牧人知道消息后,连续拉了三天琴,儿子融入长生天了,儿子死得其所,没啥悔的!琴声中,儿子巴特颈戴七彩章嘎,雄鹰一样地盘旋在搏克场上,每每能捧起最后的奖杯。也每每要把其其格和奖杯高高抛起。儿子巴特力气大,能徒手放倒生个子马,常和几个蒙古汉子抛掷着酒袋,在如飞的马背上,唱歌狂奔。老牧人听说是那个暴风雪之夜放倒了儿子巴特。他和几个汉子放夜马,却遭遇上暴风雪,狼群也适时发动了进攻,惊吓的马群顺风直扑冰封未固的达里湖。巴特骑马追出十几里,终于在湖边追上马群,圈它们回转头来,救了它们的命。可狼群恼羞成怒攻击了他,把他的人和马逼进了冰窟窿,等到众人找到他时,他已然和骑马冻成了冰雕……一条人命换回群马的命,值吗?老牧人没算过这笔帐,在他眼里,天地牲畜和草场是一个“环”——天降雨露,滋润土地,生长百草。牲畜吃草,人吃牲畜,地又吃人,魂魄返回长生天。这是一个循环,谁也打破不了的。老牧人把儿子葬在赛罕坝顶,野狼和神鹰分食带走了他。三天后,老牧人特意又登上赛罕山顶,见狼在儿子的胸骨间搭了窝,几只狼崽在嬉戏、玩耍。老牧人心里念了一声佛,他仿佛看见儿子安然走在那个“环”里,抛掷酒袋,唱起那支古老的牧人之歌,“只要唱起歌,只要喝了酒,大风也挡不住,大雪也压不住……”老牧人知道,早晚有一天,自己也会安然地升上长生天。可对他的小犊子,他却是连个阻拦的牙缝也是不敢欠的。
老牧人记得其其格领着小白脸来,也是喝酒唱歌了。那天小白脸和其其格缠缠绵绵地来到包里,像两只飞进来的蝴蝶。其其格又抱了老牧人,还摸了他的胡子。撒手锏让老牧人的心情好极了,嘴都合不拢了。其其格拉过戴金丝眼镜的小白脸,说这是爷爷!又对老牧人说,这是我朋友!老牧人当然知道“朋友”的意思,见小白脸细声细气地问好。老牧人嘴上应着,心里和眼睛如计算器一样地给他评判打分,其实那个娘家人没这样做过哩!咔嚓咔嚓一阵子加减乘除,结论出来了,太文弱,有股娘娘腔!在“结论”的驱使下,老牧人就想到了鲜花和牛粪。可看到旁边心满意足的其其格,又强装笑颜地去煮把肉,用草原最隆重的礼节欢迎他。席间,老牧人唱了《牧人之歌》,其其格唱了《长城长》,小白脸唱了《千里之外》,嗡嗡嗡地,像蚊子,老牧人一句没听懂。老牧人再请小白脸喝酒,小白脸又连连摇手,说不能喝,头痛。老牧人问他年纪多大?小白脸说,二十五。老牧人想起自己二十五时,放牧、驯马、摔跤、射箭,一座山一样。哪有个醉啊!老牧人看着花朵般的其其格,脸上却满是春风。其其格暗暗告诉老牧人,爷爷,你别看他年轻,读博士哩!天才啊!别人都说我们是郎才女貌。老牧人看着其其格心里就软了一下子,乐了,还接二连三地说了几个“好”!你说,你说,老牧人后来听说博士和其其格离婚悔得打了自己好几巴掌。博士学的是导演,拍戏就和女演员拍在一起了。老牧人心里悔啊!在其其格面前,他咋就不会说个“不”字呢。老牧人的那一套,在其其格面前不好使哩!其其格也许跑到了那个“环”外了吧?
老牧人敲响其其格的家门时,其其格显然是十万个没想到。先是在猫眼里侦察了一阵子,又确定了一下子。问找谁?这哪是草原人的待客之道,防范心总在真心的前面。老牧人半恼半笑地说,找小犊子!其其格才打开门,拉住老牧人的手大嚷道,真是你吗?爷爷。既兴奋又激动的。老牧人见其其格一头水汽,显然是刚洗过澡,穿着鼻涕一样的睡衣,走路飘飘洒洒,既迎着风,又沐着雨的。老牧人说,都不像你了,其其格!
橙黄的灯光照过来,空气里散发出一股好闻的香水味。老牧人陷在软塌塌的沙发里,不认识地打量着小犊子,可他首先看到了小犊子眼里的疑惑。老牧人喘了几口,掂量了几个词,轻描淡写地说,我进城来逛逛!顺便看看你!看着老牧人皱纹堆叠的脸庞和雪白的长胡子,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其其格还是看清了老牧人背后的心思,眼圈说红就红了,这让所有做长辈的心里都会有种“碎”的感觉。爷爷——其其格带着哭腔唤一声,依偎过来。就像牛犊子羊羔子见到了额吉一样,可见着了。老牧人抚抚其其格的脑袋,轻轻拍着其其格的后背,不说话,但却像是一座大港湾了,里面贮满温暖,有安慰也有鼓励,很复杂。其其格不说话,只是抽抽噎噎地小声啜泣着。老牧人一时恍惚了,好像回到了多年以前,小犊子受了屈,哭一哭,就好了,就雨过天晴了。老牧人久违了那种稚嫩的呼唤与娇弱的偎依,都额吉了。可现在,一个城里,一个草原,窝在爷爷额吉的膝前哭一哭,也是难得了。唉,不容易了。老牧人从这个“哭”里,好像看出了点门道,欣喜地猜测,是不是,是不是小犊子要回头了?
电话铃声说响就响了,曲子还是董文华的那支《长城长》。其其格擦一把立起身,脸上瞬间破涕为笑,都灿烂了,外交家似地对着话筒说,喂——你好!“电话”说,是娜娜吗?快看看你最后一期的新闻播报吧!其其格嘴里说着谢谢,奔向电视机。娜娜?老牧人愣愣地问,娜娜是谁?其其格边开机边说,是我的艺名。老牧人心里咯噔一下子,咋还改名了呢?还?电视打开了,老牧人见一个女子着件白西服烫个大波浪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其其格不无自豪地说,爷爷,你快看,你还没看过我做节目呢!其其格边说边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拍了几张要做纪念。老牧人疑惑地问,这……这是你?其其格笑着点了头,老牧人又盯了盯电视,摇晃着脑袋说,不像,一点草原的腔调也没有了呢!
第二天家里来了好多人,一个长头发说要搓一顿,庆贺庆贺!老牧人问娜娜原委,庆贺啥?娜娜笑着尚未说出来,长头发抢先说,娜娜明天就是深圳的人了!咋成了深圳的人了?老牧人一急,把蒙语都说出来了。长头发疑惑地拿眼睛去看娜娜。娜娜做了一个跳水的动作,高兴地说,爷爷,是跳槽了,从小大板一下子就跳到了大深圳。你,你?老牧人眨巴着眼睛,心里五味杂陈的。大板不是俺的福地!你孙女牛叉,一万多人选拔,考了个第一,棒棒的!娜娜说着就抱住了老牧人的脖子,拿眼睛坏坏地逼视老牧人,有点自得有点撒娇,问老牧人棒不棒?老牧人用蒙语说的赛白努!只到现在老牧人才看明白了,他的好是赛白努,与其其格和众人的“好”是不同的。形式不同,意思也是不同的。两码子事哩!他要其其格用蒙语说个“好”!说个“赛白努!”其其格拖着长声说:——赛——白——努!老牧人紧紧握住其其格的手,像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的稻草。长头发早打开了一瓶香槟,白色的泡沫劈头盖脸地“喷”过来,弄得娜娜和老牧人满头满脸全是。一时间,屋子里的尖叫声,音乐声,响彻天地。几个人忘乎所以地跳成一团,兴奋成一团,快乐地扭曲着,还手拉手的。老牧人顶着一头的啤酒花子,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当晚,娜娜就坐上了发往深圳的特快,送行的长头发他们羡慕地说,你可真拽,去了深圳那样的大城市,啥时去你们大营子,别不认识我们啊!娜娜笑着说,你们带足了钱,游深圳,我给你们做导游。哈哈哈哈……你可真抠门!几个人笑作一团。老牧人背着马头琴很复杂地站在站台上,看着其其格和长头发们,像看一处风景。
列车鸣响一声尖锐的汽笛,带着其其格,也就是那个艺名叫个娜娜的女孩子,冲进茫茫的夜色之中。老牧人觉得其其格像一支发出的响箭,没有靶子,却以全速的姿态在飞……充满了十足的危险性。漆黑的夜像一张嘴,一下子就吞噬的火车无影无踪,也可以说嘴就是漆黑的,火车载着其其格就行进在嘴中……老牧人拿过马头琴,盘腿坐下欲拉一曲,为其其格送行,可是,可是,马头琴居然断弦了,一副的七零八落,接续不上了。咋会这样?老牧人急得头脑一片空白,失声喊道:其——其——格!他抓了几把,紧紧抓住兜里的其其格拍的那几张照片——那几张咋看也不像其其格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