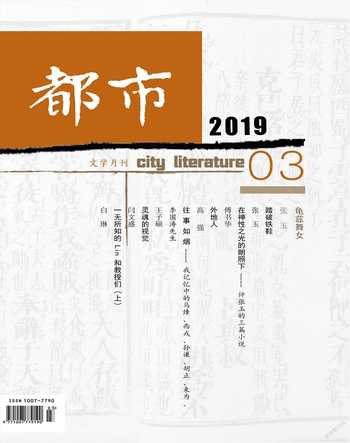往事如烟
2019-09-10王子硕
王子硕
马锋先生
1977年,我从大同矿务局工程处正式调入《汾水》编辑部。在此之前,我被借调了一年的时间。
在借调的那段时间,老作家孙谦带我到昔阳县体验生活,把我下放到昔阳县赵庄大队。我在赵庄住了半个月的时间,回太原后我相继写出报告文学《花儿越开越鲜艳》和短篇小说《评工会上》,先后发表在《汾水》杂志。有一天,在胡同里面碰到马烽,他把我叫住说:“子硕,茹志鹃给我来信了,她在信里面夸奖了你,说你的《评工会上》写得好。”说话的时候,马烽脸上笑眯眯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比夸奖他本人还高兴。茹志鹃是上海市的著名作家,她写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我读过不止一次。我很崇拜她,能够得到她的夸奖,心里面特别高兴。后来《评工会上》被选入《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和马烽茹志鹃王汶石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收在一本书里面,马烽又把我叫过来说:“趁着年轻,多写点儿这样的作品。”那种舐犊之情,让我特别感动。
1978年,山西省文联恢复之后,马烽被选举为省文联主席,但他仍然是那副老样子。他不许我们叫他马主席,也不许我们叫他马老师,只许我们叫他老马。老马真是一匹好马,他一边主持工作,一边奋笔创作。电影《泪痕》《咱们的退伍兵》,小说《结婚现场会》《伍二四十五纪要》等优秀作品相继出世,得到广泛的好评。而我这个后生则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很长时间没有突破,但是他仍旧不断地鼓励我鞭策我,让我向其他作家学习。
有一次,马烽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到太原机场接两个河北作家。一个是《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一个是《代表》的作者张庆田。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是没有完成。马烽黑着脸问我:“你接的人呢?”我先是愣住了,接着撤退就跑。马烽喊了一声:“你给我回来,人家在机场白白等了一个小时,自己找车过来了。”我垂头丧气站在那里,等候更加严厉的批评。没有想到,马烽放缓了语调:“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外?”那意思很明显,假如我有意外,他会原谅我的。但是我没有意外,我看电影去了。什么电影呢?轰动一时的香港电影《三笑》呀!早知道这样,我还笑得出来吗?马烽问我:“老实说,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到处找不见你?”我只好如实作答。马烽长出了一口气:“好吧!看在你诚实的份上,我也不批评你了。不过你要记住,凡是重要的事情,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不敢大意。”我点点头,表示牢牢记住了。
1990年,马烽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那一年我到北京出差,忘带身份证,北京的宾馆招待所没有一家敢让我住。眼看天黑了下来,还没有一个睡觉的地方,情急之下我给马烽打了一个电话。马烽说:“没有住处?那就到我这里来吧!”马烽调北京之后,中国作协刚好有了一座新宿舍楼,分配给马烽一套房,马烽没有住,让给了别人,自己仍然住在鲁迅文学院的招待所。我到了招待所,看见马烽夫妻住在一间很小的房间,根本住不下我。马烽说:“跟招待所打招呼了,你住另外一间房。”第二天一早,马烽的妻子段杏绵老师敲门,叫我到他们那里吃早饭。早饭很丰盛,小米粥小笼包子,一盘咸菜还有一盘煎鸡蛋饼。马烽说:“这是沾了你的光,你要是不来,段老师不会给我煎鸡蛋的。”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眼泪几乎掉了下来。下午办完事情,回招待所的路上,看见有卖荔枝的,很新鲜,就买了一些给马烽夫妻带回去。段杏绵老师看见荔枝,皱眉头说:“这样不好吧?”马烽说:“没什么不好,他早饭不是也没给咱饭钱?”段杏绵笑了,我也笑了。马烽剥着荔枝跟我说:“大学生上街游行,说是要反腐败,你怎么看?”我想了一会儿,一字一句地说道:“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也只能当作好话来听。”马烽问我:“当初调你们来作协,我抽过你一支烟没有?”我说没有。“吃过你们一顿饭吗?”我说也没有。马烽说:‘这就对了!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党,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时过境迁,想起马烽说过的这些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马烽离休之后,仍旧回到太原市的老房子,他有哮喘病,冬天不能出门。我劝他说,可以到海南去过冬天。他说:“海南我去过,到了那里,我不咳嗽也不气喘。可是那里没有熟人,比在太原更难受。”马烽热爱山西这片土地,热爱南华门东四条(山西作协驻地)的一草一木,他不愿离开这里。马烽去世的时候,温家宝总理送了花圈,中国作协送了花圈,国内外的著名作家纷纷来函来电,表示了沉痛的哀悼。更为感动的是,马烽的追悼现场,还有自发赶来许多普通的读者,有工人也有农民,他们像马烽的家属一样痛哭流涕,就像他们失去了亲人一样。
马烽老师,您生前不许我们叫你马主席,不许我们喊你马老师,当我们想念您的时候,就让我们尊您一声马烽先生吧!
西戎先生
1978年夏天,西戎老师要下乡体验生活,准备为自己的创作积累一些素材。但是西戎的身体不好,还有心脏病,编辑部怕出意外,就让我陪同他一起下乡。
下乡的第一站是临汾市,地区文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天晚上,地区文联安排我们看蒲剧,西戎对蒲剧情有独钟,他很高兴地答应下来。到了剧场,观众早就坐满,但是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开场的动静。人們窃窃私语,说是要等一位重要的领导。又等了一阵功夫,报幕员激动地喊道:“全体起立,热烈欢迎省委领导的到来!”人们纷纷起立,鼓掌欢迎这位领导。西戎有些不高兴地问道:“多大的官呀?用得着这么大的排场?”有人告诉他:“是韩英来啦!”听到是韩英,西戎更加不满了:“刚上来的年轻干部也这么牛?”韩英原来是大同矿务局的一个技术员,“文革”时成为“三结合”的局革委会成员。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下子成了“九大”的中央委员,再后来被提拔为山西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四人帮”垮台后,他没有受到牵连,仍旧是省里面的重要领导。这场蒲剧,西戎老师看得很不痛快。因为什么呢?因为韩英中途离场,全体观众又集体起立鼓掌欢送了一回。
在临汾,西戎只待了两天,要不是地区文联从电影公司特别调来一部电影来看,西戎第二天就要离开。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就是西戎编剧的《扑不灭的火焰》。这部电影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直到1978年还没有解禁。地区文联的领导劝说道:“要不是你本人来了,我们也调不出这部片子,就让我们沾点儿光吧!”西戎这才答应再住一天。电影是在一个小播映室里面放映的,因为还没有得到平反,只允许很少的人观看。西戎看到自己编剧的电影,心里面还是很高兴的,但是至今不能公开放映,他也没有高兴到哪里去。
从临汾市坐车到了运城,同样受到运城文联的热烈欢迎。西戎说,我是下来体验生活的,你们千万不要给我安排什么节目,我得赶快下乡。于是,我陪同西戎参观了地区农科所,听技术人员介绍了他们培育小麦新品种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接着,我又陪同西戎到了闻喜县,拜访了全国劳模吴吉昌。吴吉昌因为棉花种的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表扬。但是在吴吉昌家里采访时,出现了一个非常寒心的场面。两个农民打扮的老年人走进吴吉昌的家里面,低声下气地说道:“吴劳模,你行行好,给我们点吃的吧!”吴吉昌站起来,不好意思地看了我和西戎一眼,赶紧翻箱倒柜,给讨饭的农民寻找出一些粮食。西戎问道:“你们是哪个村的?”讨饭的农民见西戎是个干部穿戴,赶紧从兜里面拿出一张介绍信。介绍信上面写着:因为受灾严重,家中无粮可吃,外出请求帮助,特此证明。然后还盖了一个红红的公章。西戎看着红红的公章,眼睛湿润了,他对我说:“子硕,带着钱没有?给他们匀点儿!”我赶紧掏出钱包,只有五元钱,全部给了那两个老农。
对青年作者的培养和扶助,是山西老作家的共同美德,西戎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82年,张平从山西师范大学毕业,由于在学期间就发表了不少好作品,临汾地区文联就想把他留下。但是他属于师范生,毕业之后应该从教,所以学校就把他分配到一个偏远山区去当教师。张平感到很苦恼,就给西戎写了一封信。西戎爱才惜才,毫不犹豫地给省人事厅厅长写信,建议厅长出面干预,把人才留在创作岗位。几天之后,张平就顺利地去临汾地区文联报了到。从此之后,张平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他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先后获得了赵树理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1999年6月,山西省文联和作协为张平举办作品研讨会,西戎精心准备发言稿,对生活与作品,作品与人品以及新时代的文学前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那一天,他早早起来站在门外等候,但是没有等到单位的车辆,只好搭马烽的顺风车来到会场。上午没有安排他发言,陪坐了一上午,有些累。年纪大了,中午也没有休息好。下午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强打精神滔滔不绝地讲了五十分钟,讲话完毕之后,突然身子一歪,倒在了他亲密战友胡正的身旁。由于脑溢血突发,他从此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2001年1月,西戎在经历了19个月的昏迷之后,终于因病医治无效撒手而去。聊以自慰的是,在西戎昏迷的那些日子里,我陪伺了他几个夜晚。西戎老师的次子席小军去北京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在病床边目睹了他对父亲的恋恋不舍之情。西戎老师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好作家,他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
孙谦先生
山西的老作家里面,我最早熟悉的应该是孙谦。1976年,为了写电影剧本,孙谦和周宗奇来到大同矿务局采访。因为我在《汾水》编辑部借调的时候就认识孙谦,所以他经常和我开玩笑。孙谦不知从谁那里听说我在矿务局橡胶厂搞了一个对象,所以就在厂里采访时特意多看了我对象几眼。回到招待所之后,孙谦就笑嘻嘻地对我说,橡胶厂那个穿粉红上衣的姑娘如何如何,把我羞得无处可藏。
正式调到《汾水》编辑部之后,孙谦经常和我下象棋,我经常输给他。周宗奇说我是故意输的,其实我没有那么多的故意。真实的原因是,我下棋的手特别臭,张石山经常赢我还要嘲讽我,并且给我起了一个外号,把我叫作“王慢棋”。在老作家里面,孙谦是最容易交往的一个人,不是说其他人有架子,而是说孙谦更容易亲近。孙谦带我到昔阳县大寨村去采访,大寨村的农民见了他,搂着他的肩膀说:“你这个黑秀才怎么又来了?”黑秀才三个字听得我一愣二愣,孙谦却笑嘻嘻地应答着,没有一点儿生气的样子。
在老作家里面,孙谦是最像农民的一个人。他的生活方式衣着打扮说话习惯,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说他像个农民,没有丝毫贬低他的意思,而是说他勤劳朴实耿直幽默的脾性像个农民。和孙谦混熟了之后,私下里他对我讲,他其实是个老运动员,不是体育运动的那个运动,而是政治运动的那个运动。每当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他总是被批判,所以他是个老运动员了。解放初期,许多老革命进了城就换老婆,孙谦看不惯,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奇异的离婚故事》,結果被批判了。为了一些个人琐事,村里的兄弟俩反目成仇了,孙谦看不惯,就写个短篇小说《伤疤的故事》,结果又被当作“中间人物”给批判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孙谦更是被批判得不亦乐乎,说是要在他的背上踩上一千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他作为一个老运动员,早就锻炼出来了,烟照样抽,酒照样喝。烟不管好赖,能冒烟就行。酒不管贵贱,能痛饮就行。有一次,孙谦连夜赶稿子,边抽烟边写字,烟头扔了一地。早上起来,他的女儿进来扫地,把烟头扫进铁簸箕里面数了数,竟然有一百多个。
按道理来讲,老运动员那么多的经验,完全应该总结出教训来了,他怎么就屡教不改呢?是不是忘性太大了呢?1976年春天,上海电影厂的人来到太原,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一部名为《小凉河的春天》的电影。在这部电影里面,有许多暗射邓小平的情节和细节,说是要和还在走的走资派斗争到底。孙谦又看不惯了,他在座谈会上发言说:“一部电影从写剧本开始,到找演员和导演,再到写出分镜头剧本,然后再开始拍摄,再后期制作,怎么也得半年六个月吧?现在刚刚反击右倾翻案风,电影咋就这么快地拍出来呢?”上海方面的来人当下就把眉头拧了起来,他声色俱厉地反驳道:“右倾翻案不得人心,革命群众的眼睛比雪还亮,早就看破了走资派的狼子野心!”座谈会的气氛马上紧张了起来,主持人怕出问题,赶紧宣布散会。当时我也在现场,暗地里替孙谦握了满手的汗。幸亏四人帮很快垮台了,否则的话,孙谦不被批判才怪呢!他又得当一回运动员了。
1995年夏天,孙谦患病住进了医院,托人捎话给我,说他想看看我主编的《笑话大王》,让我带几本过去。我当时也不知道孙谦患了肝癌,以为他只是想解解闷,就拿了几本近期的《笑话大王》去医院看望他。到了病房,孙谦很高兴,接过《笑话大王》翻了翻,然后就跟我聊开了天。他说他和“小日本”打了那么多年仗,和美帝国主义斗争了那么多年,但是到了日本和美国一看,人家科技那么发达,生活那么富裕,真是没有想到啊!他说他去了日本,看见日本人把自己的煤矿封闭了,说是怕破坏自然环境。他说他去了美国,亲戚开车走在公路上,路边有一只被汽车撞死的鹿。孙谦对他的亲戚说,咱们把那只鹿拉回家吧!鹿肉很好吃的。亲戚说,万万使不得,美国的法律严厉得很,我们不能犯法呀!孙谦跟我说,要是在咱们这里,那只鹿早就被人吃进肚里啦!听得出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认真地比较和思考当代的历史呢!
后来的日子,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事情的结果了。赵建平他们的影视中心要给孙谦拍摄一部传记片,找到我让我给他们写个脚本,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是我自信我的写作水平,而是觉得我就应该去写。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留个念想。
胡正先生
说起胡正先生,人们常说他性格豪爽,精明能干。但是胡正性格中的另外一个特征,大家都不说,或者是很少说。什么特征呢?就是他的原则性不太强。原则性不太强,不是说他不讲原则,而是说他思想比较解放,思路比较灵活。这话怎么讲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1977年我正式调到《汾水》编辑部之后,因为家属没有调来,只好吃单位的机关食堂。说是机关食堂,其实没有几个人吃饭,而做饭的大师傅也只有一个。经常在食堂吃饭的人,除我之外,还有周宗奇和胡帆等。大师傅姓范,光头,瘦弱,年纪大了,终身未婚,脾气有些怪。他的手艺不敢恭维,但你还不能说他做的饭菜不好。你说咸了,他就给你更咸。你说淡了,他就给你更淡。外地到编辑部修改稿件的作者,吃个一两顿没什么,常年在这里就餐的人就有些受不了,比如我和周宗奇胡帆。胡正当时是单位的秘书长,负责行政和后勤,他听到我们几个人发牢骚,就跟我说:“大锅饭不好吃,你们可以开小灶呀!”我说:“怎么开?”他说:“自己买锅碗单独做。”我有些疑惑:“我们单个做饭,范师傅怎么办?”他哈哈一笑,说:“你还怕他失业?大锅饭的好处就是没有失业。干好干坏都不会失业。”这是他在1976年说出的话,好像有些原则性不太强吧?
1984年,我到榆次采访,去郑义家看望他,哎呀,那还是个家吗?那是在工厂的一个大仓库里面隔出来的一间小库房。小库房是土坯墙,墙上连泥都没糊一层,不仅是家徒四壁,还四面透风呢!看到郑义家的困苦艰辛,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写出来的《远村》。回到太原之后,我给单位的领导们做了汇报,他们都表示出极大的同情。我又给《文艺报》写了一个内参报告,呼吁当地的领导能够关心此事,尽快帮助郑义解决困难。但是晋中地委宣传部的领导不仅没有帮助郑义解决困难,反而组织人马对我进行围攻,四处写文章递材料告我的状。告我什么呢?无非就是说我以偏概全扩大阴暗面,污蔑了晋中地区的大好形势等等。这样一来,郑义的困境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艰难了。省文联的领导们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坐不住了,决心把郑义从晋中地区文联上调到山西省文联,给他创造一个好的创作环境。怎么办呢?就是派胡正出马到晋中地委宣传部协调,让对方同意把郑义调到省文联。这个协调的难度很大,主要的障碍是我的那篇内参材料。叫我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我是不会同意的。让他们自己写一篇宣传自己成绩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报》,这个还可以考虑。为了把郑义调到省文联,胡正使尽了浑身的本领,他陪着地委宣传部的领导吃饭喝酒,甚至陪着他们一起洗澡。事情办成了,郑义顺利地调入省文联,成为一个专业作家。这件事情办的漂亮不漂亮?当然漂亮。但是在原则性方面,是不是有点儿不太强呢?
1988年,我担任《山西文学》的副主编,期间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大同市的一个叫王祥夫的作家,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篇名是《永不回归的姑母》。小说写得不错,但是里面有一些性关系的描写,在《山西文学》发表之后引起了争议。为此,《山西日报》在副刊栏目陆续刊登了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有的说可以写性关系,有的说不可以写,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由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马烽出面一锤定音。马烽写文章说,性关系不是不可以写,但是要看怎么写?夫妻俩睡觉还要拉个窗帘,还要避开孩子,文学作品就更要注意笔下的分寸。事情到了这里,应该是结束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结束。年底时,《山西文学》要评选本年度的优秀小说,《永不回归的姑母》进入候选名单。该不该给它评奖呢?问题摆在了评委会的桌面上。因为意见不统一,身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评委会主任的胡正建议投票表决。表决之前,胡正向大家展示了他的票面,上面是空白的,没有写一个字。他说:“我弃权。”最后的结果是,多数人投了同意票,《永不回归的姑母》成功获奖。大家说说,胡正的弃权是不是有点儿原则性不强呢?
当然,原则性不强也容易出错,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作为一个人民的作家,胡正还是名副其实的。
束为先生
五位老作家当中,束为先生是最迟认识的一位。为什么认识的最迟呢?因为我1977年调入《汾水》編辑部的时候,束为先生还在太原市委宣传部工作。
我认识他,是从1984年开始的,那一年,他重新回到山西省文联担任党组书记。为什么是重新回到山西省文联呢?因为束为先生从1953年起就是山西省文联的主席和党组书记,直到1968年才被当作“走资派”而打倒。束为先生重返山西省文联担任党组书记,在南华门东四条掀起了波澜,就像大海里面漂浮的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只有三分之一,而在平静的海水之下,暗流涌动。
大家都知道山西文坛五战友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相聚在决死二纵队的吕梁剧社,又一起到延安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在硝烟战火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建立之后,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分别在北京和四川东北工作,而束为却一直没有离开山西。1953年山西省文联成立,束为当选省文联主席并担任党组书记。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马烽西戎孙谦胡正陆续回到太原市。束为在他们五人当中岁数最大,他以兄长的情怀欢迎马烽他们归来,并安排他们成为省文联各部门的领导。五战友再聚首是个好事情,但是在一口锅里面搅稀稠,也免不了磕磕碰碰。这方面的内容,陈为人在《马烽无刺》一书当中有详细而又精辟的论述,我就不多说了。对于没看过《马烽无刺》的读者,我要简单介绍的背景就是: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四人比较亲密,束为则有点儿高处不胜寒。1984年,束为重返山西省文联担任党组书记,五战友再次聚首,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是亲密合作呢?还是一对四的博弈?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束为主持省文联的领导工作之后,我和他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向他汇报郑义在晋中地区的困境。听了我的汇报,束为对郑义的处境非常同情,随即召开党组会议,决定派胡正去和晋中地委宣传部进行沟通。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五战友在扶持青年作者方面,态度是非常一致的。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比较微妙的情况出现,比如马烽就对我说:“子硕,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直接向我汇报就行。”在这种情况之下,山西省委领导明察秋毫,随即做出了山西省文联和山西省作协分署办公的重大决定。这样一来,南华门东四条就有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边是束为领导的省文联,另一边是马烽他们领导的省作协,原先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现在要分开站队了。大家各自报名,想去省文联的去找束为,想去省作协的去找马烽他们。报名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力。束为知道我的老家在山东,他笑着对我说:“小老乡呀,你到我这里来吧!”但是我仍然选择了省作协,一是和马烽他们更熟悉一些,二是我比较爱好文学,对其他的艺术门类知之甚浅。
山西省委的正式任命书下来了,束为是省文联的党组书记,胡正是省作协的党组书记,接下来就是正式的分署办公,现有的房产物产和财产都要在协商的基础上正式分开。俗话说,好兄弟,明算账。但是好兄弟分家,也免不了摩擦,也难免不愉快。胡正看我年轻,腿脚也利索,非要把我从编辑部调出来,让我担任行政后勤方面的副秘书长。让我离开编辑岗位,我有些恋恋不舍,但是对于领导的器重,我也不能不知好歹吧?那毕竟是一个正处级的岗位呀!那一年,我33岁,让我去领导一些年纪比我大许多的下级,我是不知深浅呀?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也就被赶着上架了。两台车,一辆上海牌轿车,一辆北京吉普,束为书记很大度,要了北京吉普,把上海轿车留给了作协。但是在办公房间的分配方面产生了分歧,谁都想多占一些。报名去省文联工作的某个人,为了向束为书记表忠心,竟然对我大打出手,还用墨汁泼了我一身。我穿着墨迹斑斑的衣服去找束为书记,束为书记大吃一惊,他生气地说:“怎么能这样呢?我要狠狠地批评他!”后来,这个表忠心的人在省文联也没有得到重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让我意识到,秘书长的岗位不是一个好差事,同时也给我重返编辑岗位埋下了伏笔。
束为从1953年就开始担任正厅级的领导职务,行政事务繁忙,所以他的文学创作就比较少。他写得最好的一个短篇小说是《于得水的饭碗》,第一次发表的时候,小说中透露出农民在公社食堂吃不饱,不得不偷盗集体的山药蛋度日。这篇小说公开发表后,先是获得读者的大量好评,后又被领导批评为歪曲大好形势。迫于压力,束为不得不重新改写,把描写农村贫困的文字一笔勾销。改过重写的《于得水的饭碗》第二次发表,虽然还是原来的人和事,却变成了一篇宣扬浮夸风的作品。这件事对束为的打击很是沉重,从此之后他就很少写小说了,要写也只写报告文学和散文。束为在报告文学方面的创作很有成绩,他写的《南柳春光》,当时的影响不次于孙谦的《大寨英雄谱》。
李国涛先生
1975年,省文艺工作室召开了一个创作研讨会,我参会之后被留下来改稿。改稿的过程当中,我又被借调了一年。那时候,省文艺工作室准备创办《汾水》双月刊,李国涛是《汾水》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
那时候的李国涛四十五六岁,很清瘦的身材,戴着一副很儒雅的眼镜。我住在单身宿舍,李国涛经常来我这里串门。一般都是晚饭后,李国涛晃悠着就来敲门了。除了一些日常的话题,谈的最多的就是读书。李国涛会问我,以前读过什么书?读过以后有什么看法?好看不好看?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么?“文革”之前,我所在的中学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除了四大名著,还有三红(即《红日》《红岩》《红旗谱》)等等。外国的小说也有,以苏联作家居多,比如高尔基的《人世间》《我的大学》等。李国涛说,你看过的小说还不少呀!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看过吗?我说看过秦牧的《艺海拾贝》,还有《金蔷薇》等。李国涛说,严格地讲,这些书都属于文学评论,还不是文学理论。接着,他就给我讲二者之间的区别。那时候,可看的书很少,李国涛告诉我,办公楼的地下室里面有许多旧杂志,空闲的时候可以到那里面翻着看看。我听了李国涛的指点,没有事干的时候就去地下室乱翻。地下室没有人管理,门也不上锁,那真是一个宝库呀!不仅有《火花》历年的合订本,还有许多“文革”时期的造反小报。从这些造反小报上面,我知道了省文联在文革时期分成两派,一派拥李(束为),一派拥马(烽),两派斗得不亦乐乎。有一篇批判马烽的文章,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马烽写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后,得到了八千元的稿费,马烽没有把稿费装在自己兜里,而是全部交了党费。造反派批判马烽说,这是在拿钱收买党。我看了之后感到很可笑,党是那么好收买的吗?交党费也有错吗?
后来省文联恢复了,《汾水》也改为月刊了,一切都在慢慢地恢复正常。1977年,我在审读稿件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篇名为《顶凌下种》的自然来稿,作者名叫成一,是从原平寄来的。我看过之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短篇小说,于是就填写了推荐意见,按程序送给了小说组的组长。过了几天,组长把《顶凌下种》的稿子给我退了回来,说是不能用。不能采用的理由是,那个时候的农民干不出那样的事情来。我就纳闷了,“文革”时期的农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但是要抢季节播种,这关系到农民的口粮问题,出于生存的本能,农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抵制“极左”路线呀!让我把稿子退回去,我心有不甘,于是就越级把《顶凌下种》送到了编辑部主任李国涛的面前。李国涛审读之后,又征求了另外几个编辑的意见,不仅决定要留下来发表,而且还要发短篇小说的头条。《顶凌下种》发表之后,好评如潮,还获得了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创作的大奖。李国涛说,假如我们把《顶凌下种》这样的好小说埋没了,也许就会毁掉一个作家的前程。成一获得大奖之后,又写出了许多的优秀作品,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小说大家。
1982年,省文联组织省内的文艺工作者去北戴河疗养,我和李国涛、张改荣、刘彤芳他们是同一个批次。那个时候的李国涛,因为发表《且说山药蛋派》一文的巨大影响,已经在文艺界非常有名了。站在北戴河的岸边,面对大海的滚滚波涛,李国涛深有感触。他对我说,人的一生,就像是大海里面行舟,你拼命地往前划桨,但是一个浪头打过来,也许就把你打回原处,甚至把你打翻在水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有了如此的感慨,也许是提醒自己在名誉面前不要自满?也许是想到了前辈人的坎坷遭遇?也许是想起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惊险过程?为了转移这个沉重的话题,我想起了一个诗人,他在文章里面写道:“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我问李国涛:“这也太流氓了吧?怎么能这样写呢?”李国涛笑了笑,他说:“还有更绝妙的呢!我记得有个俄国作家在小说里面写道:‘我紧紧地趴在地上,就像是贴在女人的肚皮上。’文学作品嘛!就是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呀。”李国涛的话让我非常惊讶,他以前从没有在我面前说过类似的话,稳重和谨慎才是他固有的风格啊!李国涛看见我吃惊的表情,笑着对我说:“你放心好了,我喜欢什么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也知道,在工作当中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做取舍。”
1994年,李国涛退休之后,他以高岸的笔名写起了小说,长篇中篇短篇他都写,而且写的都很好。一个搞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学者,写起小说来驾轻就熟,真让我们刮目相看。我私下里问过他:“您以前是否就写过小说?”李国涛说:“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写过小说,但是写小说也不是我最喜欢的事情。那时候我喜欢演话剧,想当一个大明星。”啊呀!很难想象李国涛在话剧舞台上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年轻时候的理想,竟然是想当一个演话剧的明星。小说写了一阵之后,李国涛又转而去写随笔和散文,几年的时间竟然写出了近百万字的篇章,而且深得读者的好评。
李国涛就像是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是他干不成的?李国涛在他晚年的时候,自己亲自选定了《李国涛文存》五卷本。他选定的文存,也许就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吧?他不需要考虑岗位的责任,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想怎么寫就去怎么写,他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