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2019-09-10杨振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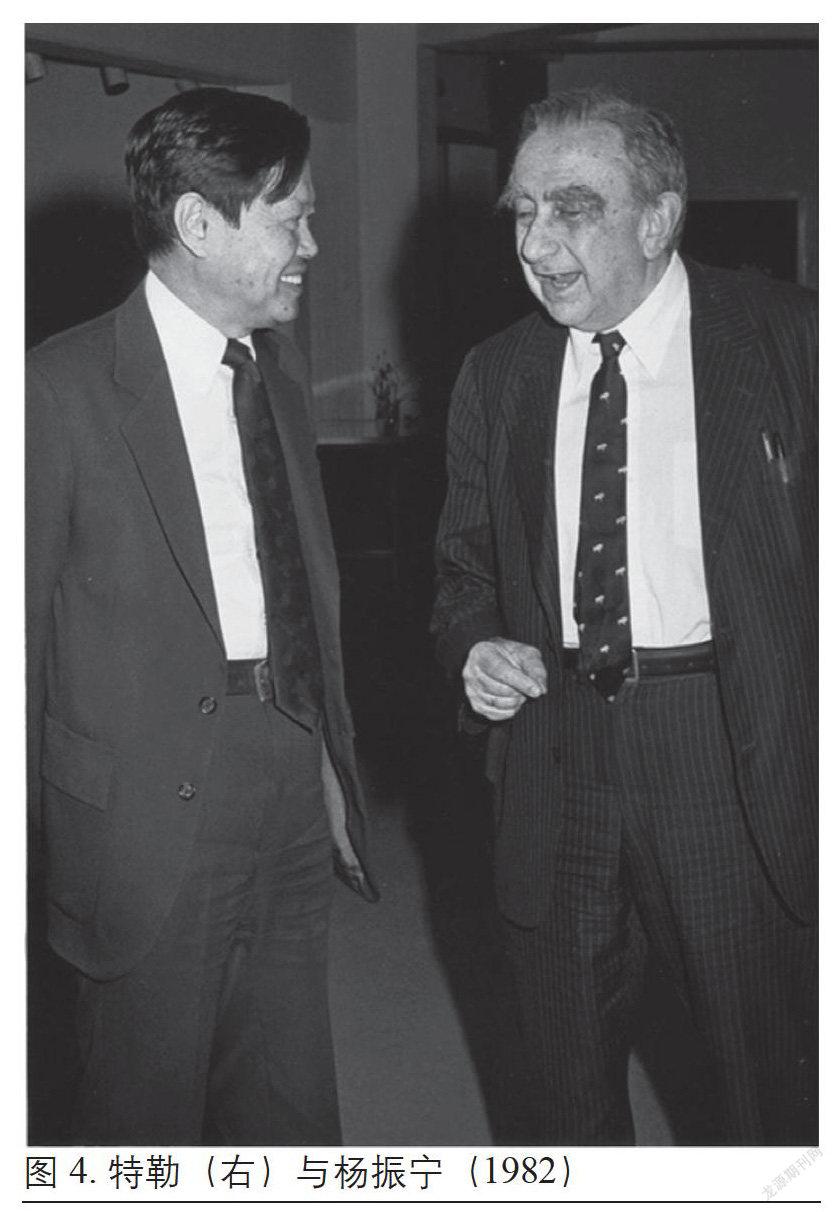

编者按 杨振宁,著名物理学家,1922年9月出生于安徽合肥。1938—1944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先后得获学士、硕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创立“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因与李政道先生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历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和洛克非勒大学董事。美国国家科学院、巴西科学院、委内瑞拉科学院、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科学院荣誉院士,曾经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鲍威尔科学成就奖,费萨尔国王国际奖等科学奖项。
2019年4月29日,杨振宁先生应明德讲堂思想系列主持人、人文学院汪前进教授的邀请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做客“明德讲堂”,李树深校长主持了本场讲座。杨先生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近两千研究生再次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与研究经历(图1),并明确重申,对于几年前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这一观点,“我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本刊特将报告及听众交流全文整理,经杨振宁先生审定发表,以志盛事。
座谈时间:2019年4月29日
座谈地点: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礼堂
整理人:张岩
我去过上百个大学演讲,今天这个演讲厅绝对是我所看见的演讲厅里最大、最讲究的。而你们是一个新大学,我想这很清楚地显示出中国现在发展得多么快。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我的学习和研究经历”。我是1922年在安徽合肥出生的。因为父亲做了清华大学教授,7岁开始,我住进了清华园。然后在北京读了四年小学,毕业以后读了四年中学。中学是在宣武门附近,当时的崇德中学(现北京市31中学)。那个时候是1930年左右,全北京市的中学里,我想有差不多一半是教会中学,崇德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只有大概300个学生,其中有1/3住校,我就是住校生之一。学校很小,没有真正的图书馆,只有一间图书室,我常常到这个图书室里去浏览一下。我想我对于物理学第一次发生兴趣,就是看了这本书——《神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发生兴趣是因为书里讲了在20世纪初物理学中的重大革命,即包括了量子学和相对论。后来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经过合肥,1938年到了昆明。因为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大合起来,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开始招生。那年夏天,我中学5年级刚念完,还缺一年才有中学文凭。可是当时因为中学生流离失所很多,所以教育部在重庆就有一个命令,学生中学不毕业也可以参加考试,叫做同等学历,我就以这个资格考进了西南联大(图2)。因为我的中学最后一年没念,高中的物理我也就没念过。可是入学考试需要考高中物理,于是我就借了一本高中物理的书在家念了一个月。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给了我很深的教训。高中物理中的等速圆周运动,有一个加速,它的方向是向心的,我就觉得这个不对。在纠缠了一两天后,才懂得,这个速度不仅有大小,它还是一个向量(vector),这个向量是在转弯。
这是我一生得到的非常重要的教训,我后来永远记得。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直觉(instinct),而直觉有许多是需要修正的。换句话说,如果你随时能够接受修正直觉的话,就继续在向前进。向量的重要性就是那两天发现的,直觉与书本知识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老师的教学态度、同学学习的态度都非常好。大家觉得这么困难的情形下,还能够读书、能够做研究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都很珍惜自己的机会,学习得很好。四年念完后,我又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那时物理系研究生有六七个同班的,我和黄昆、张守廉住在一间屋子里,非常熟。黄昆后来对于中国的半导体研究有决定性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半导体研究还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做了一系列演讲,带了许多的学生,今天中国的半导体工业、半导体研究里主要的人物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张守廉后来到美国改学了电机,做了很多年电机教授,黄昆和张守廉两位现在都不在了。我们三人共同于1992年照了一张照片(图3),当时周培源教授是北大校长,90岁,在北京有一个庆祝会议,张守廉和我也从美国来了,之所以那天我们三个人要特别照相,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整天辩论,声音很大,所以大家叫我们三剑客。
这种辩论对于我们对物理学的了解非常重要。后来我曾经这样写过,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今天大概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量子通信、量子糾缠都跟哥本哈根学说有密切的关系。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灯上床,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有什么观点,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看海森堡(Heisenberg)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我们的这种辩论是无休止的,事实上不止物理学的,天下一切的事情都在我们讨论范围。我想这个对于每一个年轻人,这种辩论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可以增加知识,增加视野,更增加了解别人的思想方法。
在西南联大有两个老师对我有长远的影响。第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是因为我在四年级要毕业的时候,需要写一个学士论文,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大学是不是还有这个制度,其实就等于写了一个报告的样子。讲某一小的领域里有些什么新的发现。不需要有真正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成绩。那么我去找吴先生,吴先生就要我看一篇文章,是讲怎么用群论来解释物理的现象,尤其是分子物理学,因为分子物理学是吴先生的领域。群论所讨论的是对称,我们知道有左右对称,有圆周对称等,把对称的观念用了数学的语言叫做群论。用群论的这个数学语言,来了解对称在这个物理的应用,这是20世纪最最重要的物理学的精神之一,而那个时候把对称的观念用到物理的现象是刚刚开始。所以吴先生把我引到这个方面是我一生最大的一个幸运。我在写完了学士论文以后得了学士学位,又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在研究院我的导师是王竹溪先生。王先生的领域的是统计力学,统计力学那个时候也是有个新的革命。所以王先生把我带进了这个领域。
梳理后发现,我以后一生中2/3的工作是在对称理论,是吴先生带我走的方向;1/3在统计力学,是王先生带我走的。我一直说自己实在是幸运极了,因为一个年轻的研究生,如果能够走到一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在以后五年、十年、二十年是发展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跟着这个领域共同发展,这是最最占便宜的事情。这么多年我看到了成千个研究生,很多都非常优秀,可是十年以后他们得了博士学位再看,有的人非常成功,有的人非常不成功,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本事差了这么多,得到过博士学位的人通常本事都还不坏的;也不是因为有的人努力,有的人不努力。主要是有人走对了方向,要是走到一个强弩之末的方向上,那就没有办法的,而且越走越不容易走出来,要换一个方向不容易,继续做那就走成了最不幸的一个人。这点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研究生都理解到这几句话的意思。
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我考取了一个留美公费,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有两位物理教授对我最有影响,一位是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那个时候他还不到40岁,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当时已经很有名了,可是后来他变得更有名(图4)。
在20世纪50年代,大家晓得原子弹做完以后,要用原子弹来引爆一个氢弹。这个窍门很多年没能解决,最后解决这个窍门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就是特勒,所以国际上说他是氢弹之父。他不喜欢这个名字,可是我想他是逃不掉这个名字的。大家知道中国发展氢弹整个是晚了一些。中国的原子弹是1964年造出来的,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原子弹引爆到氢弹只花了两年八个月的时间。这在世界上是一个纪录。因为法国比中国先造了原子弹,氢弹做不出来,而中国晚了一点,却在1967年就爆炸了氢弹,法国的科学家非常不高兴。中国先成功的缘故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有非常聪明的年轻人,而且有非常努力的年轻人。在这里面氢弹主要的贡献者、关键想法的提出者是物理学家于敏,他最近刚刚过世。另外一位对我影响更大的,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教授,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就是他率领二三十个物理学家,第一个做出反应堆,制造的地方就在芝加哥大学,所以芝加哥大学现在有一个小的广场,上面有一个雕塑是来纪念人类第一次用核能发电。
我在芝加哥大学学的物理对我非常重要,我在西南联大学的物理也非常重要,可是这两种物理的学法有一个分别。在联大的时候,我所学的物理学方法是推演法(理论——现象)。我到芝加哥大学以后发现,这些却不是那些重要的教授整天所要思考的,他们想的恰恰是反过来的,即归纳法(现象——理论),从现象开始,归纳出来理论。就是这个现象我懂不懂?如果把它想清楚了,这个跟从前的一些理论是符合的,所以就是从现象到了理论,从而了解了这个现象,也就更近了一步。假如你发现跟从前的不同,那更好,因为那代表这是修改从前的理论的机会。归纳法注重的是新现象、新方法,少注重书本上的知识。所以从现象到理论的这个研究方法,事实上是更容易出重要成果的。而我自己觉得在联大时推演法学得非常好,后来根据这个根基,又吸收了归纳法的精神,将二者结合起来,就又是我非常大的幸运。
在1946年1月到1947年,是我感觉最困难的一年。因为在昆明的时候学了很多理论物理,也念得很好,可是基本上没做过什么真正的实验,而我知道物理学根基是在最后的实验。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就下了一个决心,要写做实验的博士论文,所以到了那边就开始进入实验。当时艾里逊(Allison)教授在做一个加速器,那时算是很大的。他带了有六七个研究生,我就是其中之一。前后做了20个月。可是我不会做实验,笨手笨脚的,所以实验室里的同学都笑我:“Where there is Bang,there is Yang!”后来我懂得,自己不是做实验物理的材料,就不做了!
而理论方面我一去就找了特勒,他给了我几个题目,但都不合我的胃口。他喜欢的题目和研究方法,以及他注意的事情跟我不一样。在和他做了一个题目后,他认为结果很好,要我把它写出来,却写不出来了。因为中间需要做一些近似的计算,而近似的计算没法控制它的准确性,所以我这个论文写不出来。那么他说没关系,觉得我是个很聪明的研究生,就做另外一个题目,结果又是发生这个现象。这样几个月后,他跟我都知道,我们不是一类的理论物理学家。虽然他跟我的关系一直很好,可是我认为不能从他那得到题目,就开始自己找题目了。
我可以跟大家讲,研究生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普遍的现象。假如在座哪位研究生现在弄得很困难的话,你不要以为这是自己唯一的现象!原因是因为在本科生的时候,学的是已經有的知识,而研究生要自己找题目,自己找方法,在本科念的多好,都不见得在这方面很快就容易达到一个顺利的地步。做的不成功,当然会不高兴,不过也不要沮丧。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幸亏我在联大的时候念了很多东西,有好几个问题是别人做了,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我就把这些问题拿出来研究。在那一年一共研究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贝特(Hans Bethe)在1930年关于自旋波(spin wave)的数学工作,自旋波跟固体的构造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有几个很年轻、很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们有一套理论,在中国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芝加哥大学,我就把他们的文章拿来拼命的念。第二个是昂萨格(L. Onsager)在1944年的文章,昂萨格做的是统计力学,其中有一个非常难的数学问题,被他在1944年解决了。我还记得这个文章当时印出来的时候,我还是王竹溪先生的研究生。王先生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没能做出来。忽然看见昂萨格做出来了,他就告诉了我。王先生是一个平常不苟言笑的人,可是那天我可以看出来他很激动,这么困难的问题居然被解决了,我就知道这个里头有文章!所以在1947年,就对这篇文章进行研究。第三个题目是泡利(W. Pauli)关于场论的文章。第四个是特勒的一个理论。这四个题目我都去研究了,每一个花了好几个礼拜到一两个月。结果前三个都不成功!那个时候,除了第四个题目以外,芝加哥大学既没有老师又没有同学对那三个题目发生兴趣,所以我就一个人在图书馆里头研究。又比如说昂萨格的文章,有十几页,看不懂。他说把公式一换到公式二里头就得出公式三,照着做果然是对的。以此类推都是正确的。但所以说不懂,最主要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走?只是跟着一步步操作下来,不能够算了解。最后感觉就像变戏法一样得出了结果,这说明并没有念通。
所以那一年是很不高興的。不过幸好第四项做出来的东西,特勒发生了兴趣。他来找我说,你不一定要写个实验的论文,这个题目上做得很好,把它写出来,我就接受这个作为你的博士论文。所以以第四个题目的工作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但由于前三个题目都是没有成功,所以在1947年,我曾经在给黄昆的一封信中,说自己disillusioned(理想破灭)。可是我今天要特别给大家讲的是,前三项花的力量并没有白费,因为后来都开花结果了!我要把这个经验告诉大家。
在1948年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我留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助教。1949年理论物理有个新的发展,叫做重整化(renormalization)理论,是个崭新的理论。芝加哥大学没人搞这东西。在普林斯顿一个知名的高等研究所(图5)里聚集了很多重要的、年长的以及年轻的研究员在搞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请求到那儿去做博士后。这是一个很小的机构。既没有本科生也没有研究生,只有大概十几个教授,有几百个博士后以及一些访问学者。在那里前后待了17年。
在我去的第一学期,大概是1949年10月,因为一个同坐班车的机会,路丁格(Luttinger)对我说,昂萨格的文章被他的学生考夫曼(Bruria Kaufman)简化了,昂萨格这个难懂的文章被用一个考夫曼的新方法解决了。他在那仅几分钟的功夫里,告诉我新方法的关键部分,是几个反对易矩阵(anticommuting matrices),而我对这部分极熟悉。所以一到研究所,立刻就放弃了当时在做的场论研究,把新的想法用到昂萨格的问题上去。因为这确实是关键,所以不过用了两三个钟头,就完全做通了。后来我也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者。
这个事情对我启示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能够从路丁格的话得到那么大的好处呢?第一,因为我曾经在昆明做过狄拉克矩阵(Dirac matrices)的仔细的研究;第二,更因为在1947年的不成功,但对昂萨格工作的研究使得我对于总体的困难有所了解,问题在哪里比较有掌握。所以等到路丁格的出现,自然会把它们加在一起,也就成功了。
这是说明,第一就是要有兴趣!我为什么有兴趣?就是我做研究生的时候,王先生告诉我,昂萨格解决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妙!第二个重要点,就要花功夫去研究。我花了几个礼拜去研究不成功,但那不要紧,不成功是为后来铺了路;第三个是要有机遇,当然这是要有点运气,我那天的运气就是碰见了路丁格,产生了突破。
结论是:要做好一个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三个步骤是兴趣、努力的准备和最后突破。这三步曲也是后来我所有研究工作所遵循的路线!
有趣的是100年前,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写到的境界论,非常有意思。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
大家对这境界论的解释多多少少都是统一解释。第一境界说的是对于想要追求的事情要有点执着,所以要独上高楼,去追寻你所要看见的天涯路。说的就是兴趣。第二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人变得消瘦了也不要后悔,还要继续下去,要努力的准备;第三境中,在不经意间,一回头,忽然发现秘诀在哪里,就是机遇带来的突破。我认为这就是代表兴趣、准备、突破的三步曲,不仅在科学领域里是一个好的道路,在文学里同样是这条重要的路径。
听众交流
中国科院生态研究中心研究生:杨老师您好,今天有机会听您讲自己的经历,感到非常难得和荣幸。不管是您对兴趣的坚持,还是对科研方向的敏锐直觉,以及您广交朋友不懈钻研的精神和态度,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如果请您给国科大的学子们一句鼓励或者赠言,您会对我们说什么呢?
杨振宁:我希望各个同学都把握住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大时代,而且要了解到,你们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要努力!我想如果努力足够多的话,不敢讲一定有大成绩,但在今天中国的发展情形之下,取得一定的成绩必定是可以达到的。希望你们记住!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杨先生你好,我是来自高能所研一的学生,研究生之后会从事CEPC(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工作。您是高能物理界的老前辈,为粒子物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全所人都非常的崇拜您。但是2014年我们所提出的中国要建CEPC,当时您是反对的,所以在今天这个机会里,我代表我所有的同学们想再问您一次,您现在对我们要建CEPC这个想法有没有改变?
杨振宁:我完全没有改变!我要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你们到网上找一下我两年以前发表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这个事情与我们刚才讲的有密切关系!一个年轻的研究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其实不是你学那些技术上的内容,要使自己走入将来五年、十年有大发展机会的领域,这个才是做研究生的时候所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的。
根据这个目的,不要去搞大对撞机,现在处于没落的时候。这个领域在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刚开始大放光彩。事实上你也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在物理学里面大家认为最重要、最大发展的就是这个领域。可是这领域在30年以前开始,就已经走在末路上了!可是多半的人不知道。我再三讲,我不是今天讲,不是两年以前讲,在1980年间就讲了。那时候有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周光召先生也参加了。会上讨论到,以后十年高能物理向什么方向发展?我在会上讲了一句话——“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过。当时就看出来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是高潮期,名气非常大。可到了80年代,重要的观念都已经有了,后来还可以去做,但是没有最重要的新的观念,尤其对于理论物理方面,没有重要的新的观,就做不出东西来。不幸的是,很多年轻人没有听清我这句话,那些老师也没有懂我这句话,所以今天我再讲得更清楚一点。
有人就对我说,杨振宁你这个话完全错误,因为2013年有科学家在瑞士做了一个实验,证明了五、六十年代那些观念是对的,这当然是重要的贡献。可是这个重要的贡献的理论源头,不是30年前,而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以80年代的时候我会讲,这个领域做实验的还可以做,那么2013年就做出来了,获得诺贝尔奖。可是这个实验当时是6000个人在做,那时候的文章,每一篇署名人都是几千人。那么这个做完了以后,需要更大的机器,要花的钱至少是200亿美元。别的国家都没有,大家说中国有钱,所以就到中国来了。
我知道我的同行对我很不满意,认为我要把这行给关闭掉。可是要让中国花200亿美元,我没法子接受这件事情!我很高兴中国政府没有上当。我再加一句,为什么非要搞高能物理呢?現在重要的东西多了。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杨先生,首先,就像您刚刚报告中讲的,我们对高能物理肯定是有兴趣所以才会去做。而且高能物理到底还有没有前途?可能要靠我们的努力来证明,科学的未来谁也说不清。
杨振宁:我想你讲的这个话,代表了你的态度是好的,值得赞成。可是这个想法,不是目前整个世界科技发展的总方向!所以我趁这个机会再说一下,整个的科技发展,包括任何一个领域,它都是在经常改变的。19世纪物理学所研究的东西、方法、态度跟20世纪是不同的。那么21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方向,研究的题目同20世纪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要注意,20世纪变得非常红的东西,到21世纪还继续下去,是很少有的。20世纪的后半世纪最红的物理学是高能物理,那么绝对不会是21世纪的方向。你为什么不走到21世纪将要发展的方向上呢?如果要问我21世纪发展些什么,具体的没法讲,可是总体是看得很清楚的!可以自信地告诉你,我懂高能物理,我认为你不要走这方向。
中科院物理系学生:杨老师您好,现在物理的发展越来越细、越来越多,投入其一都是一生的时光。可是感兴趣方向的可能有很多,如何平衡兴趣和自身精力有限这个问题呢?
杨振宁:我常常想,在我做研究生的时候物理学,与今天的物理学有很大分别。那时候物理学比较简单,有几个大的方向,在每一个方向上学习一两门课,大概的意思都可以掌握了。今天的物理或者说所有的科学前沿,都是越来越细、有很多方向。所以你要问怎么选择,我想是这样: 要问你自己,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哪个方向?哪方面做得好?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兴趣。我在美国教了很多年的书,美国大学生和中国大学生有两个最大的区别。一是美国学生训练的不够,而中国学生训练得比较好。第二点是中国学生比较成熟,比较努力。但并不是说中国学生就绝对好,不好的地方就是不够灵活,不够胆子大。我的建议是,一方面要问你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东西,真正的能力在哪个地方。一方面考虑一下,想法是不是可以朝着胆子更大的方向走一下。美国学生对于掌握自己方向的能力比中国的学生要好。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生:杨院士您好,吴健雄先生帮您和李院士一起完成了宇称不守恒下的弱相互作用的实验证明。但是可惜的是,吴健雄先生并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再有,一些学术上的热点我们需要追吗?
杨振宁:需要补充一点,之所以吴健雄是个伟大的物理学家,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李政道和我1956年写了这篇文章以后,认为宇称可能不守恒,然后我们就提出来了好几种实验。每一种实验都比较复杂,比较困难。当时很多的实验物理学家都不肯做这些实验。记得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对他说,我觉得和李政道的这个文章有点道理,其中有一个实验,你的实验室比较容易做,为什么不做呢?他开玩笑回答,这么难的一个题目,我要有一个好的研究生,我就让他去做,我自己不做。这是一般的态度。所以大家都觉得吴健雄很傻,她去做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做不出结果的事情。吴健雄厉害的地方,也就是她伟大的地方,就是她认识到,这是一个基本的实验,基本的实验既然还没有做,当然应该做了,所以不要管做出来结果怎么样,这是研究科学的真精神!这是她伟大的地方。那么至于说她为什么没有得奖,这是所有的人都不理解的。这个事情我想几十年以后,恐怕会有人研究出来的。最重要的是研究的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开会记录。诺贝尔奖基金委员会曾有一个规矩,某个奖50年以后可以公布当时讨论的记录。可是他们现在改了,要在当事人都不在了以后才可以公布,那么李政道跟我现在都还在,所以不能公布。
关于追逐热点问题,选择热点的方向这当然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掌握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自己的能力、兴趣与热点,这三个哪个更重要?我会把热点放在第三位。因为现在门多得很,如果你有能力又在某一方向有兴趣,这样较容易成功。如果你对热点问题并没有兴趣,只是听说这个东西红得不得了,我想这个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