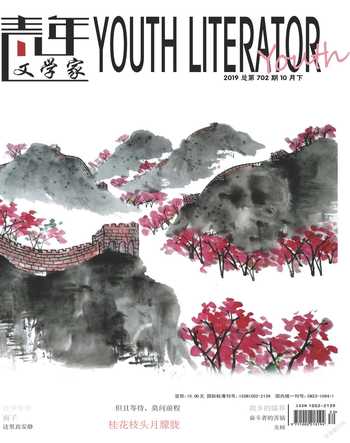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我爱比尔》
2019-09-10白婉宁
摘 要:在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语境下,第三世界的女性面对着男性意识形态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双重建构。《我爱比尔》中的阿三,既体现出对西方虚构的文化标签权威下的顺从,在追寻自身社会身份时的迷失,又体现出了父权制、男性家长下的权力依附关系。但将男性/女性作为符号,象征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将性别话语与政治话语交织起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出了性别对立的两极,与目前的权力话语有着共谋关系。
关键词:《我爱比尔》;后殖民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他者;权力话语
作者简介:白婉宁(1995.8-),女,辽宁省葫芦岛人,辽宁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0-0-03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概述
玛莎·李尔于1968年在纽约时代杂志上撰文提出了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概念,并从此得到公认与沿用。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指的是19世纪主要由中产阶级女性发起的对女性在社会与法律等方面不平等的改良运动,其关注点在于教育、就业、婚姻法以及中产阶级单身知识女性的困境等方面。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则是指在60年代后期在美国与欧洲发生的一系列女性主义运动,鼓励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利争取,其中心仍旧是白人女性。直到1992年,瑞贝卡·沃克在《女士(Ms.)》杂志上撰文宣称“我就是第三次浪潮”,从此女性主义的第三次浪潮也登上历史舞台。与前两次相比,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不仅反抗父权与夫权,也反对之前的女性主义者将全世界的女性同质化这一主张,试图反映女性独特的生活经验,并将关注点投向少数群体,例如同性恋、跨性别者与第三世界女性等。
后殖民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着眼于(主要包括而不限于前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与权力话语压迫:“结果,东方就被东方主义的话语典型地制作成沉默、淫荡、女性化、暴虐、易怒和落后的形象。正好相反,西方则被表现为男性化、民主、有理性、讲道德、有活力并思想开通的形象[1]”。而在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一部分支持者眼中,妇女与第三世界(权力关系中被压迫的对象)有着内在的相似性:都被“少数话语”的主要代表,都被权力话语所歪曲,都是“哑言的主体”。斯皮瓦克在其《下属群体能说话吗?》中表示,第三世界的女性在数重压迫之下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以一种扭曲、变形的形式由他人代言,这种歪曲不仅仅来自于男权话语,也来自于西方白人女性对想象中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殖民化。
因此,也有一部分学者将后殖民女性主义称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但“第三世界”这个分类未尽人意,因为这种地理空间的分类范畴太过狭隘——“后殖民不只限于一个被外来政权统治的地区,而是统合不同模式的权力压迫结构[2]”,因此后殖民女性主义也应运而生,美国黑人女性的处境就是一个例子。对此,印度学者莫汉蒂给出了再定义:“第三世界是通过地理位置以及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况来定义的。因此,它也包括美国所谓的少数民族或者有色人种。[3]”就像《东方主义》一书中的“东方”并非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而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可以引申为所有被压迫、被歪曲、被想象出的地区一样,“第三世界”也包括了在发达国家中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群的含义。
二、后殖民主义:殖民化过程的烙印与标记
1、文化标签的权威与顺从
赛义德在《东方学》的开篇就写道:“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4]”尽管《东方学》中的“东方”并非指的是远东(东亚),但其面临的境遇几乎没有差别:中国文化并不单一,而是融合而生的产物,在内部有着无数差异与矛盾,也逃离不了被标签化的命运。在面对有所了解却不精通的事物时,标签化是最为方便快捷的方式,尽管这种标签可能反映出一部分现实,但更多体现出一种想象与误读。
在《我爱比尔》的文本中,这样的情节表现屡见不鲜。作为美国驻沪领馆的一名文化官员,比尔声称他爱中国,而他似乎也是这么表现出来的:他爱中国饭菜,中国文字,中国京剧,中国人的脸,他还起了个吉祥的中国名字,毕和瑞,“和”与“瑞”都有其背后的典故。但实际上他在与阿三交往的最开始便亮明自己的态度:“我们并不需要你来告诉什么,我们看见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就足够了。”而阿三自己也敏锐地有所察觉,“再听到比尔歌颂中国,就在心里说:你的中国和我的中国可不一样。”比尔对中国的热爱是隔着层纱的,是浪漫与模糊化了的,他爱着的是自己想象中的中国,而非现实中的、他亲眼可以得见的中国。
比尔的态度是一种代表。他对中国的印象更多地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相关资料,但资料本身有限是一点,现代中国早已与古代中国相差甚远是另一点,因此比尔以及一部分与他相似的西方人所追逐的只是他们构想中的古老符号,他们也将这样的符号以偏概全地贴在整个群体身上。中国古代的烈女传给比尔留下崇高与恐怖的印象,比尔便认为阿三在性观念的想法上也是如此;等到阿三用自己的画向他展现自己的性观念时,他则有一种盲目的自信:“中国人对性不是这样的态度”。在比尔眼中,东西方的文化是泾渭分明、是格格不入的,就算将事实摆在他眼前,他也仍舊会去维护自己想象中的刻板印象。
而与此相对的,这样的文化标签下,是被贴上标签的对象的顺从。阿三清醒地理解比尔的中国与自己的中国不一样,也知道自己之所以吸引比尔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女孩,但有她为了迎合比尔的喜好,或者说迎合在话语权力处于支配地位上的西方人的喜好,也很多次主动将自己标签化了。当第三世界被遮蔽与歪曲的时候,它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这种遮蔽与歪曲。
2、社会身份的建构与迷失
在这种情况下,阿三就面对着在身份认同上的困境。一方面,她渴望摆脱掉自己的原始身份,离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将自己同化进西方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她又无法真正脱离自己原本的文化身份,同样也没办法让自己真的变成一个西方人。阿三看比尔,觉得比尔是“铜像”,比尔看她也一样:“两人互相看着,都觉得不像人,离现实很远的,是一种想象样的东西”。
阿三对此也心知肚明。“她不希望比尔将她看做一个中国女孩,可是她所以吸引比尔,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孩。”她的目的也同样明确:她不想成为对比尔来说异质的存在,也不希望比尔对她的感情仅仅停留在猎奇心理,她渴望与比尔同化,渴望站在一个与他平等的角度上,也渴望成为她理想中那个世界的一份子。但在这样的社会身份的建构中,她就遇上了矛盾。她不希望被比尔称赞“特别”或是“奇异”,但想要把比尔的目光留在她身上,她就必须要延续这种“奇异”:她化浓妆,穿奇装异服,让自己保持一种几乎是触目惊心的姿态。当比尔故作惊讶地说着胡话,将上海比作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的时候,阿三确实地感受到了欢喜,因为那一瞬间她几乎认为自己要消弭这种隔阂,她便双手叉腰,摆出法国歌剧中那个热情的吉普赛女郎的姿态:“我是卡门!”但她永远也成不了卡门。
这种文化背景的隔阂是无法消除的。如果说比尔否定她的愿望的借口是政治(“作为我们国家的一名外交官员,我们不允许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子恋爱”),而这还给她留下了希望,那么法国画商马丁对她这种重新建构身份的否定则给了她更大的打击(“但是马丁却比比尔更加破坏阿三的生活”)。她与马丁之间存在着更切实的情感交流,但却没有办法互相理解:“现在,阿三觉得和马丁又隔远了,中间隔了一个庞然大物,就是上帝。”這样的隔阂就是致命的。因此最后她哀求马丁将自己带回法国,马丁却给予她冷静的回答:“我从来没想过和一个中国女人在一起生活……因为,这对于我不可能。”而阿三的幻想,也就仅仅止步于幻想。她在社会身份的漩涡中迷失,虽然知道重构身份不可能,却无法自拔。
三、后殖民女性主义:女性的两难处境
1、双重权力话语的压制
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强调殖民霸权文化压迫的同时,由于将第三世界作为被压迫的整体对象进行研究,对社会性别差异也存在着一定的漠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关注第三世界男性,而第三世界女性与之相比也有着独特的身份处境。与在西方权力话语的权威下的顺从所相对的,第三世界的女性也同样承受着父权与夫权的压迫,这种压迫并不仅仅在于现实物质层面,也在于精神层面,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隐形压制,而不是单纯的性别歧视或者性权利的控制。
作为一个在画画上有着才华的知识女性,阿三却似乎并没有自我。当她与比尔保持关系时,她的世界里几乎只有比尔:“阿三自己也忘了自己。……没有比尔,就没有阿三,阿三是为比尔存在并且快活的。”但后来我们得知,阿三对比尔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阿三想到,当时听到这消息的漠然劲,她简直不知道,她究竟爱还是不爱比尔。”阿三对于自己理想与欲望的追求过程始终处于一种权力依附关系上面,她看似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她会画画,也有一定的才气,她英语口语流畅,也擅长社交,在宴会上也可以应付自如——但她却从未想过以自己的才华与手段,在她向往的西方世界找到一个立足之地。她的才华与手段,全成为了她寻找并依附于一个男人的筹码,而她自己则成为了客体,成为男权关系下的附庸。
但阿三自己还浑然不觉。在酒店大堂“寻求机会”的时候,她还会被同样寻求机会的其他女孩所伤害,只因为别人会将她们分为一类。她之所以还拥有这样的自傲,因为她有着更远的期望,因为她似乎已经掌控了自己的亲密关系(“她以她流利的英语制服了他来自经济强国的傲慢。此外,在性上面,阿三也克敌制胜,叫他乖乖地低下头来。”),但实际上,只要她还存留着靠保持亲密关系的男性来达成目的的想法,她便是权力关系中真正的受制者。
2、性别话语与权力话语的交织
王安忆自己曾谈起过《我爱比尔》的创作初衷:“其实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这和爱情、和性完全没有关系,我想写的是我们第三世界的处境。[5]”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比尔就是西方世界的象征,阿三是第三世界的象征。这似乎可以解释王安忆这部小说对于性格构建过于平面与夸张化的原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因为虚无缥缈的追求草率退学,最终沦落为暗娼,这样的故事情节夸张到不让人信服,但因为阿三这一形象是第三世界的象征,那么故事情节也有着相应的象征化。从这个角度来说,阿三便从本应有血有肉的女主角,降级成为了政治讽喻需求的一个载体。
用两性关系来象征政治关系的作品屡见不鲜。在1940年一幅以英法协约为题材的德国漫画中,法国的化身玛丽安娜便以一种荡妇的形象出现。她背对着德国人,挽着约翰牛的手,以一种轻蔑的姿态昂首阔步地离开。爱尔兰诗人威廉·叶芝创作的剧本《胡里痕的凯瑟琳》中,爱尔兰的化身凯瑟琳则是表现出一种号召群众牺牲的姿态。她则因为这种牺牲,从一位老妇人转变为“迈着女王步伐的年轻女孩”。
但当性别话语与政治话语交织在一起时,无论是西方与第三世界,还是男性与女性的关系,都被进一步固化,以至于建构出对立的两极。在这样的两极中,第三世界在西方的文化霸权下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女性也在男性权力话语的掌控之下失去自我,以一种附属物的方式存在。这无疑是对女性化的东方与男性化的西方这样的建构的一种延续,是男性认同的一种延续,也是对女性的轻视的一种延续。在这样的话语建构中,女性再一次成为了他者,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衡量女性的并非女性自己,而是男性的标尺。当后殖民主义将第三世界男性看做西方眼中的他者的时候,第三世界女性同样也成为了“他者”眼中的“他者”。而“他者”是无法为自己的形象辩白的:对她们作出定义的是其他拥有话语权力的群体,尽管这样的定义与她们本身的情况大相径庭。
王安忆的本意可能是对这种不平等关系的讽刺,但她同时却加重了这种加诸在第三世界女性身上的刻板印象:女性的身体以及婚恋关系已经不再是私人问题或自由选择,而是与政治问题挂钩,上升到了公共空间。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任何人都可以对女性的自由选择作出批判:即,“她并非由于爱情,而是由于物质原因与社会身份的再建构,是一种抛弃祖国向西方臣服的行为”。尽管这其实仍旧是自由选择,但随之而来的道德压力与荡妇羞辱让这一选择不仅仅是自由选择那么简单;即使某位女性的选择与上述原因无关,她也要承受同样的审视与误读。而与此同时,女性特质再一次与软弱、低效、神经质挂钩;男性特质则(一如既往地)与坚强、高效、理性所挂钩。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女性更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力量,她们很显然并不具备这种力量,或是声音太小,无法让大多数人能够听到。因此,将性别话语与政治话语交织起来,无疑加重了这样的误读:当下属群体的呼声更加微弱的时刻,这种建构就与目前的权力话语产生了一定的“共谋”关系。
结语:
王安忆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我确实很少单单从女性角度去考虑问题,好像并不是想在里面解决一个女性的问题,我没有这样想,总是觉得世界是男女共有的,这是很平衡的生态,偏哪一方都不行,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也许和女性主义有关联的。”但同时她也表示:“这些东西我写出来以后就不属于自己了,就是任人评说的。[6]”王安忆将第三世界整體的困境通过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她自己也说并非单纯的情爱。然而只要用爱情故事和两性关系的手段表现出来,这篇小说也就与性别叙事离不开关系。当将一个复杂的群体具象化为某个人物的时候,主题先行的弊端也就不可避免。
后殖民女性主义仍旧是在发展中的一系列理论,并非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尽管从目前来讲,第三世界女性的处境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但也依旧面对着哑言的困境。对《我爱比尔》这篇小说文本的思考,也不应仅仅停留于作者想要并试图表现的部分,而是需要向更广阔的地方开掘。
注释:
[1](p44-p45)巴特·穆尔-基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2](p12)肖丽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3](p2)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 Russo & Lourdes Torre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4](p1)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第一版.
[5](p252)王安忆,刘金东:《我是女性主义者吗?》,选自张新颖,金理编:《王安忆研究资料 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6](p250)王安忆,刘金东:《我是女性主义者吗?》,选自张新颖,金理编:《王安忆研究资料 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01):100-108.
[2]林树明.性别意识与族群政治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03):14-21+167-168.
[3]余海艳.“民族寓言”:后殖民理论视阈下的王安忆小说[D].温州大学,2015.
[4]葛亮.全球化语境下的“主体”(他者)争锋——由《我爱比尔》论“第三世界”文化自处问题[J].文史哲,2010(02):157-166.
[5]张蓉,贾辰飞.后殖民主义文化心理下的生存困境——《我爱比尔》[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9):179-180.
[6]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7]肖丽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