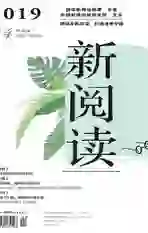“微阅读”:缘何从求知转向娱乐
2019-09-10陈定家
陈定家
从阅读心理学的角度看,读者的联想往往也和作者的思路一样错综复杂,千回百转。读屏者通过相应的视频、图像和声音以及可以任意跳转的网络超链接,将线性阅读变成了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式的“悦读”。网络文本对经典作品的通俗化、快餐化、图像化、影视化、视频化等,为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提供了多种渠道和途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形形色色的移动终端,把阅读从书斋、教室引向了无限广阔的任意空间,风生水起的可穿戴设备,也正在将随身阅读变得更加精巧,更加有趣,更加有效,更加人性化。读者在一种审美化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地被改造成了一位“悦读者”。
对于文学阅读来说,网络作品显然是比传统作品更近似于热力学中的“耗散结构”。作者借助于符号载体所传递的信息,以比特流的形式进行着文本存储、复制、修订、续写,新生文本与既有文本之间有如沟壑纵横的水流,彼此融汇到一起。网络阅读作为一种虚拟空间的超时空的“对话”行为,无论其阅读对象是否有乔纳森·卡勒所谓的“逻辑预设”“文学预设”“修辞预设”或“语用预设”,它所具有的超文本查询和超时空跳转等多媒体特征,是传统单向性接受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当下流行的“微阅读”更是使网文用户体验获得了千变万化的可能性,在这种无休止的变形改造过程中,再简单的作品也会在万花筒式的变幻过程中丰富起来。读者在一种游戏化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被作品改变着,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在改变着作品。
众所周知,传统阅读,以求知为目的,以苦读为美德,历史上有很多妇孺皆知的动人故事,如悬梁刺股,雪案萤窗,燃荻夜读,闻鸡而起……苦读的核心是一个“勤”字,所谓“天道酬勤”“业精于勤”都可以说是“苦读”观念中的应有之义,极而言之,“一勤天下无难事”。一般说来,苦读者往往是为情势所逼或为名利所惑,有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紧迫感,因而读书的目的性十分明确。或为颜如玉、黄金屋,或为金榜题名、光耀门楣,抑或是为高职高薪、豪车豪宅,甚至为救亡图存、民族崛起,但无论动机如何,在目的明确的苦读者看来,读书只是一种手段。
网络阅读往往是以一种游戏心态介入的,因此,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悦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当然,传统的苦读者也会修炼出“以苦为乐”的境界:“富贵于我如浮云,诗书不知老将至”。“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但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要修炼到这种“至乐莫如读书”的境界,绝非易事。
随着读屏环境的不断优化,网络阅读穿越了图像与文字的屏障,弥合了写作与阅读的鸿沟,而且还在文学、艺术和文化的诸种要素之间,建立了一种交响乐式的话语狂欢和文本互动机制,它将千百年来众生与万物之间既有的和可能的呼应关系,以及所有相关的动人景象都一一浓缩到赛博空间中,将作者梦想的审美精神家园,变成更为具体可感的数字化声像,变成比真实世界更为清晰逼真的“虚拟现实”。套用麦克卢汉的说法,数字化对阅读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如今,电脑延伸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意识被迁移到网络世界。“大脑移植”以及“人脑复制”已不再只是科幻小说,“用脑电图扫描的方法,把莎士比亚和伊拉斯谟的感知和博学植入自己的大脑。”若此项技术普及开来,书籍则如同飞机上的机翼图案一样只具有装饰意义,而阅读也从求知彻底转向了娱乐。
事实上,已有许多网络作品完全撇开了书籍,而只能存活于网上。如迈克尔·乔伊斯的《下午》、麦马特的《奢华》等就是如此。著名的“泥巴游戏”(MUD)其实就是一部永远开放、永未完成、多角互动性的集体创作的小说。多媒体是网络文学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它使我们不仅沉浸在纯文字的想象之中,还让我们直接感觉到与之相关的真实声音、人物的容貌身姿以及他生存的环境等,甚至我们还可以与人物一起“生活”,真正体验人物的内在情感和心理过程。如网络小说《火星之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断有音乐、图片、视频相伴。在这里,体裁、主题、主角、线索、视角、开端、结局、边界这些传统文学的概念已统统失效。读者只需把鼠标轻轻一点,文本、图像、音乐、视频等数字化军团便呼啸而来,偶有感想,还可以率尔操觚,放开手脚风雅一回、互动一把。
网络“微阅读”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搜索引擎的应用,它能变“大海捞针”为“探囊取物”。因此,网络为知识获取提供了无穷的便利。在参阅资料方面,网络的优越性是无可限量的。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季羡林的“想自杀”和何道宽的“幸福死了”——足以说明许多问题。博学多闻的季羡林教授,家藏万卷书,自称“坐拥书城,睥睨天下,颇有王者气象”。但藏书太多,也常常给他带来烦恼,平时像老朋友一样熟悉的书籍,急用时偏偏玩起了“躲猫猫”,千呼万唤不出来,逼得季老“简直想自杀!”他仿诗以自嘲说:“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与此完全相反的另一个例子是翻译《理解媒介》的何道宽先生,他在退休后的十年间,翻译了2000万字的学术著作,记者问其高产秘诀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有了网络,如虎添翼!何先生感叹说,现在做学问的人“真是幸福死了!”过去要查点资料,东奔西突,南征北战,而且还往往会劳而无功。现在完全不同了,无论想要什么资料,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一键可得!
更为值得欣喜的是,“微阅读”并不像书籍那样被动地等候读者查阅,许多网站还专为读者量身定制了“末页推荐”之类的“私塾先生”,它们以智能化的形式,为读者推荐最符合其喜好的同类书籍。例如,“安卓读书”的“末页推荐”,通过对读者阅读书籍记录、平均阅读时长等客观条件的综合分析,系统可以有效地推算出读者的阅读喜好,并从服务器的反馈中,测算出读者最有可能喜欢的书籍目录——而后,这些书目便会出现在“末页推荐”栏位。假如你平时甚好反乌托邦风格的小說,那么在看完《美丽新世界》之后,“末页推荐”栏位就可能会向你推荐《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等;如果喜欢的是西方奇幻类小说,在你看完《魔戒》之后,系统就会推荐《龙枪》和《冰与火之歌》等。
“微阅读”还可通过各种“17K”“追书神器”“安卓读书”“书旗小说”等APP使阅读变得“有声有色,传神传情”。何为“有声有色,传神传情”?我们只要想象一下手机视频上的方明朗诵《岳阳楼记》或乔榛演绎《蜀道难》,就能轻易找到美读的完美范本了;网络对“声”与“色”的开掘是多方面的,它甚至可以使阅读由“看书”变为“听书”。如“懒人听书”软件,可以使他人随时为我美读。这与晚年视力不济的李贽、毛泽东等人的“借目阅读”还要方便许多;至于视频等诗、画、乐融为一体的艺术化呈现会给阅读带来什么样的享受就更不用说了。凡是看过电视散文《江南》或《荷塘月色》的人,一定会对“美读”之美有更深刻的理解。
至于“微阅读”中即时互动也是传统阅读望尘莫及的。读者可以“点赞”“跟帖”“围观”“吐槽”“板砖”,甚至直接参与写作!在线互动的种种景象大多是书面阅读无法想象的;与网络阅读相比,传统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无声无影的寂静的世界。读者成为集阅读与写作于一身的“作者—读者”。为此,罗森伯格杜撰了一个新单词“写读者”(wreader),用以描述网络阅读过程中“读写界限消弭一空”的新角色。显然,这个新单词是将作者(writer) 与读者(reader)两词斩头去尾后拼合而成的。总之,网络上的写读所体现的那种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和互动意识,是传统写读过程中“描红”式练笔难以比拟的,传统写读或多或少地会夹杂着一些对经典文本学舌式的模仿。网络写读则更多地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砥砺。眼下的移动“微阅读”,把读者从固定屏幕前解放了出来,使欧阳修式的孤独“三上”变成了热热闹闹的“群聊”,碎片化阅读过程中的思想火花和瞬间感悟,随时随地都可与相识和不相识的“信友”们分享,事实上,即便是传统书籍,也正在日益变成超越时空的开放性“游戏”。尽管有不少人担忧网络时代的碎片化浅阅读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危机,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作为“一机在手,乾坤在握”的“悦读者”,在网络大数据的海洋里,我们无法阻止潮起潮落,但我们可以选择乘风破浪。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