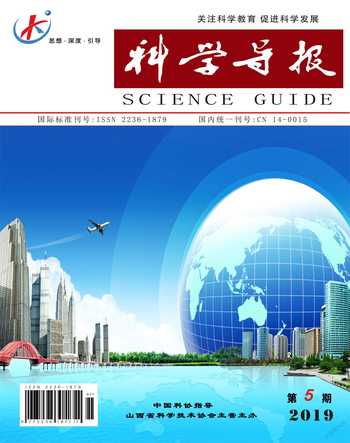近代山西体育与社会发展窥探
2019-09-10郭园
摘 要:1919年4月15日,第七届华北运动会在山西太原举办,此次运动会为近代山西举办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区域性运动会,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运动会相关报纸、杂志、秩序册等资料,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第七届华北运动会对山西体育的影响,及其映射出的山西社会面貌。
关键词:第七届华北运动会;近代山西体育;近代山西社会
华北运动会,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影响力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性运动会。1919年,第七届华北运动会在山西举办,作为区域性的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在山西的举办便是近代山西体育以及社会的一个缩影,这届运动会的筹办阶段、正式举办、运动会具体内容等相关资料不仅反映了近代山西体育的发展状况,又充分展示了体育与社会的关系,是理解近代山西体育与社会的重要素材。
1 步履蹒跚:近代山西体育运动会的发展历程
19世纪末,近代体育项目开始传入山西。兵式操形式开始出现,体操、田径、球类依次在军校、教会学校、普通学校开展起来,逐步在社会推广,这是山西近代体育的奠基期,山西近代体育也在蹒跚中起步。
清光绪31年(1905)十月,为庆贺慈禧70大寿,在太原举办了“万寿节”学生大运动会。比赛项目有迅跑(短跑)、最远驱奔(长跑)、排害猛进(障碍赛)以及民俗体育等内容,赛后,大会给优胜者颁发了奖品和纪念银牌。此次运动会已初具近代体育比赛的内容和特点,这也是田径传入山西的标志性事件。[1]这次运动会使普通民众得以近距离接触近代体育项目。1907年孔祥熙从美国留学回到故乡太谷,创办了“民贤学堂”,这所新式学堂便成为孔祥熙实施其体育理念的主要场所。民贤学堂为太谷县第一所中学,除了各门文化课程外,学校还专门开设了体育课。体育教育的开展则进一步推进了近代体育思想在民众的传播与启蒙。
之后,山西舉办了多届运动会,如1915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学生以上运动会及1919年4月初举办的山西省第一次学校联合运动会,这两次运动会参赛主体都为学校学生,同时运动会项目也大为增加,近一步促进了体育项目与近代体育理念的的传播,如第一届中学生以上运动会期间,撑杆跳高首次在山西人士面前亮相,时任山西教育厅厅长的虞铭新颇感惊奇,便走进体育场邀请参赛选手为他三番五次地表演。对于1919年山西全省第一次学校联合运动会,观众热情更为高涨,史料记载:“观众达八万人,连日来会场各界之参观者每日不下数万人。可谓省垣体育界空前之盛会”[2]这次运动会主要的目的是为在太原举办的“第七届华北运动(1919.4.15)会选拔运动员和预演。
近代在山西举办的运动会,随着时间的推进,体育项目逐年增加,体育参观的人数也不断扩大,不仅促进了体育项目在山西的发展,更推进了近代体育理念在民众中的传播与推广,另一方面随着运动会规模的不断扩大,运动会从前期筹办、正式举办到最后终结的具体过程,也从侧面鲜活的反映了当时山西社会的发展状况及民众对待体育的态度。
2 盛况空前:近代山西的体育盛会
华北运动会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倡导创建于1913年,由华北体育联合会组织各种运动会,按会章规定:“每年应在华北各省市轮流举行运动会”[3],由于当时其他各省市在“场地设备、人员配备、办会经验等,没有北京天津的条件好”[4]所以前5届运动会在北京、天津两地举行。第6届华北运动会在河北省保定举行,“从此打破了只在京津两地轮流举行的局面”。[5]与此同时,山西省也逐渐具备了办赛条件。
1919年阎锡山兼任山西省长,通过各种手段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在省内推行“六政三事”,使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局面,同时在学校教育中开展体育教学,促进了体育运动在山西的发展与普及。政府的这些措施,为山西举办区域性的大型运动会提供了客观条件。1919年4月14日至17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了第7届华北运动会。
2.1 政府支持下的筹备工作
小五台运动场的建立说明,政府开始积极参与到民间体育组织举办的运动会。为承办此次运动会,当时的山西政府,临时将小五台(现并州东路通往火车站的一段,当时为太原旧城池,东南一片旷野)派工兵部队平整碾压成为“小五台体育场”。场内搭一木结构席棚为主席台、贵宾台。东西长约200多米,南北宽约70米,设400米环形跑道。空地中央挖九个坑,放些沙子便是跳远、跳高、三级跳远及撑竿跳高场地;南北跑道则是掷铁球、铁饼、标枪场地。[7],“省长布置田径赛场,固不恤经费制”[8]这一措施也成为“地方政府与民间体育组织合作举办运动会之开始”[9]。
从运动会职员构成来看,政界、教育界官员成为本届华北运动会职员构成的关键。运动会会长为阎锡山(山西省长),副会长赵戴文(山西督军公署参谋长)、虞铭新(山西教育厅厅长)、南桂馨(山西警察厅厅长)[10],且《第七次华北运动会秩序单》还专门印有以上四人的肖像照片和阎锡山本人小传,由此而见,当时山西省政府非常支持此次运动会,这一点从运动会所需经费来源也可以看出。
根据《第七次华北运动会秩序单》记载,运动会赞助人有“蔡团长、朱厅长、崔议长、徐道尹、徐局长”[11]等,从赞助人员名单来看此次运动会赞助人员多为军、政、教育界要人。此外,据《申报》记载“对于来宾之便利照料亦极周到,凡省外选手来与斯会者,其住与太原之用费皆由省长供给,不需外来选手破钞也”[12]。
由此可以看出,在运动场第修建、运动会职员构成、和经费来源方面,第7届华北运动会已不是单纯的民间体育组织举办的运动会,
“作为公益性民间体育组织的华北体联,因经济负担日重,转而寻求山西督军阎锡山的支持,自此华北体联开始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运动会”。[13]另外一方面,运动会的举办也成为了政府展示其政绩的一个窗口。据《申报》记载,英、美、法国公使来晋除了参观运动会,更重要的是参观“我晋新政治即社会上一切新事业”[14],运动会也成为当时山西展示其“模范省”形象的一个窗口。
2.2 运动会概况:
本次运动会以学校为参赛主体,参赛单位有:“北平清华、北平中国大学、北平国立第一高师、北平汇文、天津南开、天津新学书院、天津一中、奉天二师、保定农专、山西大学、山西二中、山西阳兴中学、山西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保定农专、保定青年、保定陆军官佐中学、保定育德中学、保定高师附中、直隶二师、直隶四师、直隶六中”[15]等50所学校,参与单位及人数的数量较前几届运动会大为增加。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足球、网球4项、跳高、跳远、撑杆跳高、铅球、铁饼、标枪、五项全能、十项全能、田径等项目、”[16],运动项目也大为增加,此外本届运动会“增加了男子中级组进行比赛”。[17]
由上可知,无论从参赛单位、参加人员的数量还是从运动会项目设置来看,此次运动会较前几届运动会有大的进步,运动会的举办也促进了近代体育项目在山西的传播及普及,同时也推進了近代山西体育发展的步伐。
3运动会视野下的大社会
运动会除了展示其本身的体育内容之外,透过运动会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所展现出的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内容。依据《第七次华北运动会秩序单》中对于运动场职员的记载,可以看出此次运动会的总裁判长、发令员为外国人,其他项目的裁判员也多数由外国人员担任。可以看出,外籍人士在运动会裁判评定方面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一现象也反映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始终是与民族命脉相连的。
于此同时,随着我国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民族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也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可,也从本届运动会开始,运动器材部分使用国货,“1919年以前华北运动会所用的运动器械,除了跳高架、竹竿子、起跳板用国货外,其他器械和各种球类都采用舶来品,从1919年以后,部分采用国货,如采用保定布云工厂所制造的铁饼、铁球、标枪”。[18]
随着运动会的开展,众多外籍人士到达山西,而当时山西民众对外籍人士态度,也反映了山西社会风气的转变。据《字林报》记载:“太原在十九年前风气尚未开通,官吏人民成以驱逐外人为务。今则(英、美)两大公使联袂来此参观运动,是诚可谓破天荒之事也”[19]。19世纪末期,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一部分西方传教士来到山西设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由于因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引起部分山西民众的反感和误会,从而于1900年爆发了山西教案,众多传教士被伤害。
到了教案发生19年后的1919年,对于来晋的外籍人士,晋省民众“无不引为全省光荣欢迎一致”,不论政界领导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外籍人士热烈欢迎,阎锡山还特别派特别代表赴石家庄相迎,并在省城为他们准备好宅邸。来临之时“除阎锡山亲率文武各官员到车站迎接外,还责令闾长、街长、街付率领商户、民户分作八组,各学校职员率领学生全体按照排定地点出迎。各学校学生要手执纸质英美法等国国旗,及中国国旗,商户、民户所执之旗上写欢迎二字,其旗由军属发给,数量达四千,见外宾远来时,各校学生由体操教员、商户、民户每组由一名军官指挥,学生左手持旗,右手扬帽,并高呼‘黑点浦’,商民则呼欢迎”[20]。
4 结语
第七届华北运动会作为做为近代山西举办的大型区域运动会,是近代山西体育发展的见证,同时也是山西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第七届华北运动会的举办,促进了近代山西体育发展的水平,为山西举办运动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同时通过对第七届华北运动会的筹办、举办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体育与社会的互动,一方面,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随着国人体育意识的增强,政府也将运动会作为其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积极参与到民间体育组织举办的华北运动会,使第七届华北运动会得以顺利开展。另一方面运动会的开展,也反映了当时山西社会的发展状况及社会风气,成为当时山西展示其“模范省”形象的重要窗口,而且运动会的举办在传播近代体育理念、改善社会风气、振奋民心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第四十二卷)体育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 山西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山西体育文史第4期[M],1981.
[4] 杨明,邹凯.体育与救国: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述评[J].史学月刊,2011(11)
[5] 龚飞,梁柱平.中国体育史简编[M].四川: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8).
[6]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华北运动会(1913-19334年)体育史料[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9.
[7]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8] 阳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阳曲县志[M].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620.
[9] 纪山西华北运动会一.上海《申报》,1919,4,19.
[10]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华北运动会(1913-19334年)体育史料第15辑[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9:2.
[11] 第七次华北运动会秩序单,编者及出版日期不详,4.
[11] 第七次华北运动会秩序单,编者及出版日期不详,15.
[12] 纪山西华北运动会一,上海《申报》,1919,4,19.
[13] 杨明,邹凯.体育与救国: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述评[J],史学月刊,2011.
[14] 纪山西华北运动会一,上海《申报》,1919,4,19.
[15]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体育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296.
[16]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体育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296.
[17]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著.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02.
[18]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著.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02.
[19] 纪山西华北运动会一,上海《申报》,1919,4,19.
[20] 山西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山西体育文史合订本.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1990,75.
作者简介:郭园(1987-),女,硕士研究生,助理馆员 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