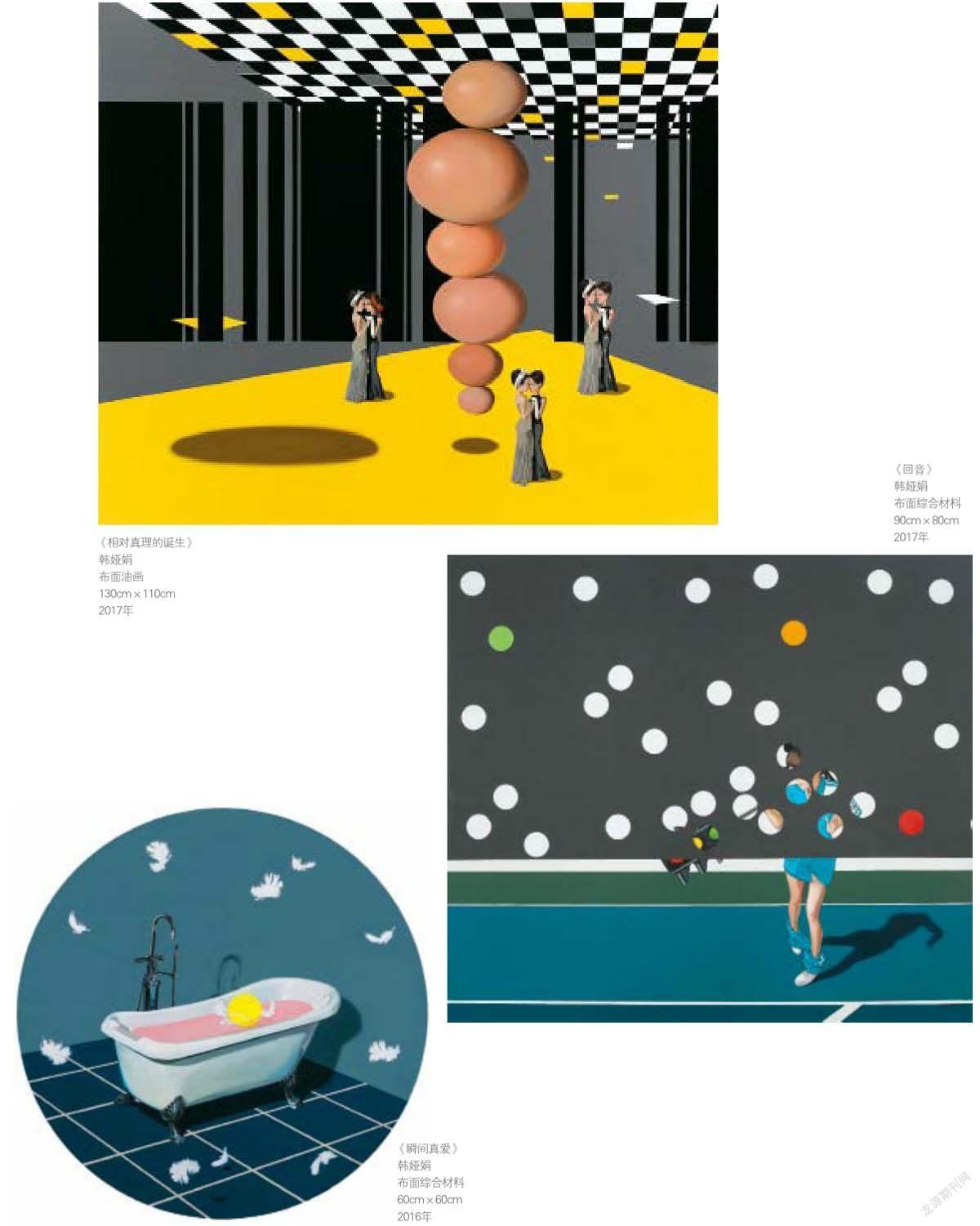亦是过去,亦是未来
2019-09-10韩娅娟
韩娅娟
记得我接触的第一本绘画“教材”是本文艺复兴大师素描集,深蓝色的封面上朴素地印着“素描”两个黑体大字,裸露的装订线有几根已经断开,岁月在书角备注了一层层抚不平的卷。这本《素描》是当时教我学画的老师从大学图书馆借来的,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画册真是件稀罕物,之后它就再也没被还回去。后来我的日子在向古典主义大师的致敬中飞快过去,那是一种沉醉在“看见什么画什么”中的满足。这种满足直到一个闷热的午后,瞬间蒸发,化成无数黑洞,散落在我脑子里的每个角落。那天,老师煞有其事地把我叫过去,说是有个好东西要给我看。来到画室见面坐定,老师下意识地在裤腰上擦了擦手,随后小心翼翼地从皮包里端出一本崭新的画册。他说这是费了老大的劲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原版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勒内·马格利特,《藝术的故事》里面收录的是他的一张叫“Attempting the Impossible”的作品,画面只有简单的两个人,画中画家本人正试图在空间中画出一个女模特,画笔停留在未画出的模特的左手臂处,颇有点像100年后的今天利用VR技术在空间中作画的意思。奇特的空间的错位、现实与幻觉的矛盾瞬间抓住了我。我清楚地记得那种触动——不是感官上的,而是认知上的,就好像青蛙突然跳出了井底,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认知升级。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很多,作为一种虚构出来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模式,对无意识表达的追求无可厚非,如果就此打住,马格利特也没什么特别。然而,与大多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帕格森的直觉主义为理论根基,强调直觉和非理性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不同,马格利特更像一个另类的思辨者。剥去绘画语言表层的超现实主义元素,他的作品非但不是非理性的,反而是一种建立在极端理性下的构想;他营造的是一种现实中的非现实。这个区别有点像魔幻电影和科幻电影,前者纯属虚构,而后者则有理性和科学作为背书。马格利特的思辨还颇有东方哲学的意味,他所关心的并非无意识的自由意象,而是关乎认知的根本问题。《易·系辞》云:“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这里的“形”并非事物的自身变化,而是人对事物的认知,它的主体就是人的理性。马格利特反复触碰的是认知与事物的边界,延展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同时也挑战和颠覆着人们的惯常思维:画了烟斗的画并非是一只烟斗,一个符号如何能够实指一个存在物,一个定义指向存在物时,这种关联的确定性来自何处?在我看来,马格利特是超现实主义画家中最具哲学倾向的一个,他作品里的思辨和观念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具有了当代艺术的气质。与其强调其超现实主义特质,不如去发掘马格利特提供的另一种可能性:在一个没有权威答案的虚构空间,亦是过去,亦是未来,而现在存在于你的解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