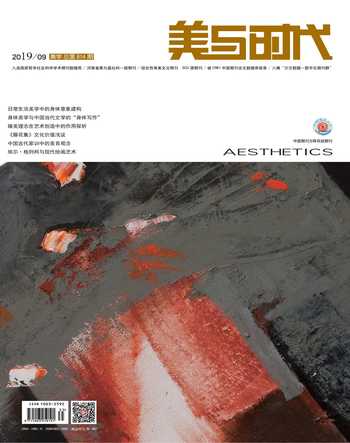浅谈《金瓶梅》的狂欢化色彩
2019-09-10魏鲸酾
摘 要: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视阈下,《金瓶梅》打破传统艺术思维,深植于民间文化土壤,着力刻画传统文化鄙夷的边缘性群体的日常丑态,并克服了先前小说中人物原本凝固化、平面化的倾向,多色调地塑造了美丑并举的矛盾形象。在体裁上,用民间广场语言、讽刺性模拟、戏谑谐趣、雅秽结合等庄谐体展现了民间文化的笑谑精神,深化了文本的狂欢主题,其狂欢式的脱冕、加冕仪式彻底打破了传统诗学惯于宏大叙事和理想演绎的僵化区域,进而表现出作者对当时社会强烈的讽刺意味,以及对生活在当时社会中的边缘性群体的深深悲悯之情。
关键词:金瓶梅;巴赫金;狂欢化
巴赫金认为,狂欢化通过消除各种体裁和风格之间的轻蔑,使得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和新的研究方法成为文学批评和文本分析的代码、诠释策略。欧洲文学发展中的这种狂欢化精神“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1]190。
作为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章回体小说,《金瓶梅》描绘了一个巴赫金视阈下不受官方主流文化支配的、充斥着原始世俗欲望的狂欢化世界。边缘性群体的丑态在这个黑暗不堪的现实社会中暴露无遗,兰陵笑笑生以审丑思维展示市井中的人情世态,冲破正统文学的禁锢,给传统文学脱冕,给正统文学轻蔑的人物题材加冕,从根本上就了该小说的狂欢化色彩。
一、边缘小丑的狂欢化形象
巴赫金认为,狂欢广场的主要演员是处于边缘性群体的小丑,是非官方真理的传播者,其生活不受正统规范束缚,在体制文化中找不到位置,便用伪装的形式与体制文化周旋,用狂欢颠倒的视角对体制文化进行审视。《金瓶梅》中以审丑美学多色调地塑造了在现实生活中处于边缘性地位的群体形象,他们被作者从种种禁令和规范中解放出来。小说中的三个边缘小丑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组成了《金瓶梅》这一书的书名,此外还有另一层涵义:“金”代表金钱、“瓶”代表酒、“梅”代表女色。[2]前言。《金瓶梅》中的边缘性小丑们在弥漫着金钱酒色的广场上肆意狂欢。
小丑为了获取自己的位置空间,常常能直击他人的虚荣心,通过抬高旁人来赢得对方欢心,用诙谐戏谑的话语来贬低自己。小丑创造出一种开心活络的生活环境以隐藏自身的真实情绪,因此,更容易被他人认可和接受。例如李瓶儿坑了两任前夫,作为书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女性,却处处降低自我姿态讨取西门庆及其妻妾的欢心以获得认可与接受;西门庆所谓的结拜兄弟们也在遮掩着内心的利益需求,处处阿谀奉承西门庆,通过取笑自己来讨好他从而获得利益。主角尚如此,更遑论其他蝇营狗苟,这些小丑们在这场狂欢中演绎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作者把讽刺运用到了极致。
巴赫金说:“狂欢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合二为一的,它们身上结合了嬗变和危机两个极端:诞生与死亡(妊娠死亡的形象),祝福与诅咒(狂欢节上祝福性的诅咒语,其中同时含有对死亡和新生的祝愿),夸奖与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当面与背后,愚蠢与聪明。”[1]180《金瓶梅》中的边缘性小丑是多色调的、立体的,克服了先前小说中人物性格单一化、凝固平面化的倾向。如追逐金钱利益与女色的西门庆在李瓶儿死后大哭不止,为她畫像、守灵,恨不得跟着一起去了;宋惠莲在来旺儿发配徐州后闹两次上吊死了,之所以寻死,主要是出身底层的她对同样出身底层的来旺儿有一种同情和痛惜感,她心里还有正义在,故而决然赴死。这些美丑并举的矛盾形象深刻复杂,体现出兰陵笑笑生对边缘性群体的慈悲怜悯之情。
狂欢化世界在毫不留情地摧毁一切的同时也不断交替和更新着一切。西门庆死后,他的影身陈经济继续登场,重演着相同的戏码;潘金莲死了,她的影身庞春梅接替她上演类似的命运。一波又一波边缘性群体在风雨飘零的命运轮回中苟且偷生。从该角度出发,狂欢化诗学理论类似于中国的佛老思想,即认为价值是相对的,世界是变量的,用相对性精神代替了被摧毁的绝对理念。这种能瓦解绝对权威并否定中心力量的狂欢化精神隐藏着虚无主义的因素。因此,看似充斥着肆无忌惮狂欢气息的《金瓶梅》,其内核还潜藏着佛老因果报应、沧海桑田的轮回思想。
二、庄谐结合的狂欢化语言
《金瓶梅》引用笑话、诗词曲语、佛经道文、脉案药方、公文邸报、状子批文等,将它们与叙事交织在一起,体现谐趣特色。庄谐体的民间性首先体现在它的口头白话上,用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运用“还活着的方言和行话”[3]。《金瓶梅》中的口语充满着浓厚的市井气息,代表了语言发展遵循口语化、俚俗化的方向,有力地挑战了传统美学中语言朝雅驯化方向发展的规范。
庄谐结合的狂欢化主要表现在其本能地蕴含着讽刺性模拟,即“模拟一定风格的语言和仿效一定格调的叙述”[4], 是指文本通过模拟他人的风格而形成的讽刺效果。在该书中表现为对诗词的模仿,如西门庆拿鞭子抽打和书童偷情的潘金莲后,因小厮与金莲都抵死不认,“又见妇人脱的光赤条条,花朵儿般身子,娇啼嫩语,跪在地下,那怒气早已钻入爪洼国去了”[2]第十二回。写完这段后,用“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词评价金莲这一番受辱,该词出自唐代白居易的《太行路》。又比如“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2]第二十五回。该词出自李清照之作,本是生动地刻画一个天真纯洁、感情丰富却又矜持的少女形象。作者一本正经地把这词引用过来,接下来写陈经济帮几个娘推秋千,直推送得“李瓶儿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红底衣”,无疑是很有性意味的场景。这种诗词的模拟更能体现出其语言于生动中颇含讽刺,“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5], 也就是说,《金瓶梅》中的讽刺主要是一种“暗色的讽刺,涉及的是罪行”[6]。
《金瓶梅》具备通俗小说中的“俳谐色彩”[7],这种语言上的谐趣正是狂欢化体裁特色。如为了刻画一位“为人正直”的霍知县形象,书中是通过描写他从不主动向嫌疑犯索要贿赂,而是“被动接受”嫌疑犯所给的贿赂,便一夜改了招卷。兰陵笑笑生用谐趣的语言把讽刺的锋芒直指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贿赂公行等社会丑行,揭露了当时的政治糜烂和社会黑暗。该书还利用人名制造谐趣,如应伯爵暗讽该人物“白嚼”的帮闲奉承姿态,吴典恩寓意“无点恩”,游守、郝贤合起来为“游手好闲”,道士石伯才暗讽其实“不才”等巧妙的谐音关系极为戏谑风趣。从语言效果来看,《金瓶梅》的谐趣语言使看客发出狂欢式笑声,并能在笑声中感受文字强有力的讽刺力量,窥探出作者批判当时社会黑暗的良苦用心。
《金瓶梅》的庄谐结合,也体现在雅言与秽语的结合。例如该书用大量谐趣的语言描写了骂人的场景,雅词之间混合着大量的荤话,这种把经典去神圣化的庸俗化写作,刻画出狂欢广场上边缘群体的狡诈虚伪、市井的无耻堕落,蕴含极其深刻的讽刺。
三、狂欢化的“脱冕加冕”
狂欢节的中心场地是广场,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而狂欢节进行当中,除了狂欢节的生活以外,谁也没有另一种生活”。[8]《金瓶梅》通过描写西门庆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衰败的兴衰史,将上等贵胄、太监皇帝、中等商贾士子、中下等官吏、下等小贩农户、市井流氓无赖、奴婢贱女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尽收书中。据统计,全书中男性角色共553人,女性角色共347人,展示出一个全民性参与的世界,在全民参与的故事框架下揭示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权贵与豪绅富商之间无恶不作的社会现实。
从艺术架构来看,《金瓶梅》体现了文学艺术思维的“脱冕加冕”仪式。从整体结构上看,《金瓶梅》以狂欢化创作思维实现了脱冕加冕。其一,它从传统诗学理性视野中跳出来,打破描写英雄豪杰、神仙妖魔等传统小说中的猎奇创作的理念,转向家庭生活、平凡人物,完成了对传统文学的脱冕,给正统文学所鄙视的创作观念加冕。借普通人物的人生际遇来表现整个社会的变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具体来看,西门庆一生的兴衰暗含加冕脱冕的狂欢化仪式,他以小商人身份通过聚敛钱财、结交官员、经营政商成为山东第一个财主,官方政治话语被脱冕,普通小人物得到了讽刺性的加冕。原本巴结的人在他死后立现丑态,上演了狂欢化脱冕场景。从宏观角度来看,整个西门庆家族向上连接的是蔡京这一贪腐体系所形成的另一个更大的家族。《金瓶梅》不只是家庭鸡毛蒜皮的狂欢,而是把狂欢广场延续到社会,整个朝廷、国家同样上演着脱冕加冕的仪式。这种狂欢式的脱冕加冕仪式像个“超强粘合”剂,把整个封建社会从个人到家族、社会、国家全粘在一个大结构上。“狂欢式的逻辑——这是反常态的逻辑、‘转变’的逻辑、上与下及前与后倒置等等的逻辑、戏谑化的逻辑、戏耍式的佩戴桂冠和摘除桂冠的逻辑,……它废旧立新,使‘圭桌’有所贬抑,使一切降之于地,附着于地,把大地视为吞噬一切、又是一切赖以萌生的基原。”[9]
其二,《金瓶梅》实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审美观念的极大转变,一反之前讴歌美好理想、渗透浪漫主义色彩的创作逻辑,废旧立新,极力描写世态人情之恶、市井生活之丑,成为一部彻底的暴露文学。《金瓶梅》真实描摹颓靡的社会风气,将人性的丑陋龌龊、肮脏罪恶暴露无遗,这些边缘小丑们拥挤到小说艺术的前台,使传统的诗情画意荡然无存。该书以罪恶作为中心架构,污言秽语横行,癫行异举肆虐,在“审丑”的狂欢中透视人性逐渐糜烂的整个过程。
通過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可看出,该书的美学意义在于打破粗俗和高雅、卑下和崇高、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滑稽和神圣之间的界限,使其融为一体。降格先前的高贵范畴,给它进行脱冕,打破并挑战古典美学基本范畴的优越性和权威性,给古典美学所蔑视的范畴加冕。这是兰陵笑笑生对低迷社会风气的不满和对无能政治集团的强烈讽刺,又隐含着深深的悲凉况味。
四、结语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长篇世情写实小说,书中有大量的性描写是毋庸讳饰的,也是历来为人们所垢病的。如果我们从广泛的文化视角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来客观评价,不难发现这本书中的性描写其实是一种化丑为美的艺术手法,在暴露当时社会现实、展示人性本能、揭示社会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阿城在《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中说过:《金》书即使删去一万九千字的性描写也不失为伟大的作品,它绝不会因没有这一万多字而失去它的光彩。
《金瓶梅》把整个封建社会从个人到家族、社会、国家全粘在一个大结构上,致力于表现人性的复杂。没有“人之初,性本善”,也没有“人之初,性本恶”,如莎士比亚所说,人,毕竟是用尘土做出来的,所以他会老、会死,容易生病,会产生邪念,会做坏事。这就是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小说开头兰陵笑笑生说:“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2]序言 兰陵笑笑生眼神极冷,心肠极热,一边用犀利的笔锋将人性的丑恶批判得淋漓尽致,一边又对其予以悲悯和同情。对对象采取相当写实的态度,又渗透着深深的悲悯之情,这正是作品的伟大之处。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崇祯本)[M].台北:里仁书局,2009.
[3]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43.
[4]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12.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0.
[6]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M].尹慧珉,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150.
[7]宁宗一.说不尽的金瓶梅[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57-61.
[8]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8.
[9]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M].魏庆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59.
作者简介:魏鲸酾,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