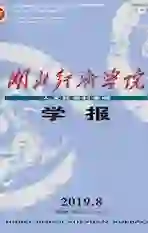试论贾平凹《山本》中人物群像
2019-09-10孙晴
孙晴
摘 要:《山本》以民间说野史的叙事方式说尽秦岭之事,展示了秦岭的山之本色和人之本性。通过对《山本》中的人物群像的分析,揭示在战争年代的芸芸众生的人性异化,唯有儒道佛融汇的广博的爱和悲悯才能对人性异化的救赎,这爱与悲悯正是秦岭文化精神的核心。正如小说中所道:“世道荒唐过,飘零只有爱”,而这种文化精神也会如秦岭一般,生生不息。
关键词:人性;迷失;救赎;儒道佛;秦岭文化精神
贾平凹的《山本》从广义上来说,是一部民间说野史,将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用小说的形式叙述出来。正如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中》说道:“所有的诗歌中都含有历史的因素,每一个世界历史叙事中也都含有诗歌的因素。我们在叙述历史时依靠比喻的语言来界定我们叙事表达的对象,并把过去事件转变为我们叙事的策略。”[1]《山本》将厚重苍凉的“民间记忆”通过诗化的反映,呈现出秦岭本色,以及人之本性。
一、山之本色,人之本性
《山本》中写道:“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嶺之志”。作者贾平凹生于秦岭的棣花镇,在小镇上度过了少年与青年时期,秦岭的风情与文化对贾平凹先生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山本》的诞生是必然。秦岭是中国最伟大的山脉,横亘与中国南北之间,也是长江和黄河的分界线,无论是对中国的地貌还是气候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处于南北之交的秦岭的物候、风土人情和民风民俗也是独具特色。《山本》是以秦岭为大背景,描写兵荒马乱的岁月各方势力在秦岭西一带上演的走马灯似的拉锯战。以涡镇为地理中心,盘踞了包括了土匪、秦岭西一带的刀客、逛山、保安队、红军游击队以及以井宗秀为代表的预备团(后为预备旅)。在这战乱的年月里,各方势力互相征伐,互相算计,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评判与标准。作者以民间说野史的叙事方式,述说了在秦岭大地上发生的一幕幕的悲喜剧,通过对人物故事的叙述,展示了秦岭的博物风情和地域文化。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道:“那年岁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走兽、那么多的鬼魅魍魉,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2]
《山本》则是要触及那个时代家国的痛楚,表达秦岭之本,即秦岭的本质,秦岭文化的本质以及秦岭人的本质,而这“本”是隐藏于万象变化之中。“山本”即是指民间大地,因此这部秦岭志在揭露山之本色和人之本性。在小说中,作者解构了传统小说中塑造典型人物的方式,采用了碎片化的方式展现众多人物,更加注重通过对叙事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这些众多人物的不同性格无一例外的都是代表着典型的秦岭人的性格特点,也是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中国人的普遍心理状态,展现人之本性。
二、苦难中迷失的芸芸众生
小说开头便说道:陆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从这三分胭脂地是龙脉开始说起,牵扯出涡镇所以的是与非,也展现了在战火中挣扎的人生百相。
(一)暴力和权欲中迷失的英雄
在《山本》中作者并没有把任何角色塑造的毫无缺陷,同样,小说的主人公井宗秀也不是一个扁平的草寇英雄人物,既有着人性的光辉,同时也具有人性缺陷。不仅仅是井宗秀,包括在红军游击队中的井宗丞、土匪五雷、阮天保等涡镇枭雄的性格也是如此。井宗秀是个清秀白净,寡言少语却又心思缜密的男人。人物出场时主动承担下父亲的债务,并在得到第一笔金后立刻还了“救济会”的钱,后来他是涡镇的守护者,是涡镇的英雄。井宗秀具有着优秀领导所具备的品质,但同时也颇具心机。利用土匪五雷轻而易举的得到吴、岳两家的财产,致使两家家破人亡,发现前妻与土匪有染,制造事件杀了妻子,并利用自己的小姨子挑拨了土匪内部关系,使其四分五裂。在战争之时,则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妄杀无辜者,甚至用剥人皮做鼓的酷刑来“杀鸡儆猴”等。这样的井宗秀如同五雷、阮天保等人,虽英勇善战,却又杀人如麻,草菅人命,逐渐在权欲中迷失了自己。
无论是井家两兄弟,还是土匪、阮天保等人,在成立自己的武装队伍之时都是用残酷暴力的方式实现武装力量的积累。“无论这历史中有多少血污、暴行和不公正,都由于它是‘通向未来’的堂而皇之地谅宥了:付学费、必要的代价、难免论、‘吃梨削皮总要带点肉’等等”。[2]作者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秦岭这些力量积累,打破了历来表彰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行为,从个人与生命的人文关怀看待这里人民的血和泪。在《山本》中,无论是土匪、保安队、预备旅还是红军,这些枭雄所带来的战争,受苦的最终还是秦岭普通百姓,消解了这类英雄引发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意义,放大了人性中的恶。正如其他研究者给暴力美学所下的定义:“它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是对暴力的细节化渲染、铺陈,让暴力来抒发个人对生活的悲剧感觉,将人生的痛苦撕裂开来,使人们看到这人世间的悲惨、仇恨、蔑视、践踏人性的罪行。”[3]井宗秀将三猫处置,以剥皮作人皮鼓。作者对剥皮过程做出细致的描述,:“陈皮匠并没有拿了捅条在三猫的脖子处往下捅也没用气管充气,从怀里掏出个酒壶要往三猫的嘴里灌,但嘴里有一块木柴片咬得死死的,取不出来,硬拽了出来,右嘴角就撕裂到腮帮上。”[2]当场的看客甚至有晕倒的,呕吐。在七天之后在老皂角树上挂了人面鼓,自此老皂角树便没有任何动物在上面,只有在下雨之时,人面鼓被打得噗噗的声音。井宗秀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树立他在涡镇的威信,以儆效尤,严惩叛徒,却也在暴力的杀伐与权欲之中完全丧失了人性,完全转化为兽性。井宗秀、土匪和阮天保等人具有典型的封建武装起义的色彩,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好大喜功,贪图享乐。这些人在不断的战争中,人格不断的异化,人性不断的丧失转化为原始的兽性,在权欲中不断杀伐。
(二)在自保中迷失的劳苦大众
在《山本》中,作者放弃了传统长篇小说的典型人物的塑造,而是将人物碎片化,在写秦岭的传奇英雄的同时,也叙述了很多在战争中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示了兵荒马乱的年代下众多的劳苦大众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反映了时代带给那一代人的命运悲剧。
“军阀割据、秩序大乱,每个人都命贱的很,生来很随意,死也随意。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正面人物或者英雄人物死得特别壮烈,惊天动地,特别有意义。《山本》里死亡特别多,而且死得都特别简单。但是,你想想,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没有谁死得轰轰烈烈,都是偶然就死了,毫无意义就死了”[4]在《山本》中“跑龙套”的小人物有很多,比如天真而又无所事事的杨钟、忠实厚道的杨掌柜、始终守护涡镇的老魏头、聪明可爱的花生等人,这些都是涡镇朴朴实实的居民,勤勤恳恳,本本分分,这也是中华人民的传统的品德,即使在战争的硝烟中,中国人也从未抛弃过这些优良品质。但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这些小人物也不免受到时代和命运悲剧的捉弄,在这涡镇的方寸之间上演一幕幕悲喜剧。
在土匪五雷等人进驻涡镇之后,镇民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涡镇人民渴望出现一个英雄人物,能够赶走土匪,保卫一方。而井宗秀的足智多谋和圆滑顺道,使得他能够妥善的处理匪、官和民之间的关系,最后以全勝的方式使得涡镇人民接受这个救星。就连最后,井宗秀死了之后,预备旅与阮天保开战,大量的炮弹落在涡镇,企图将这个小镇毁于一旦之时,安记卤肉店的掌柜已经疯了的大喊井宗秀是涡镇的英雄,你怎么不来守护涡镇。在战乱中如落叶飘零的芸芸众生,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的自然性和分散性,导致生产资料零散且依靠自然条件,因此个人能力的有限,无法抵挡时代的洪流,个人命运在战争中漂浮不定。生存意识迫使将个人期望寄托在英雄之中,希望能出现一个全能的“神”来解救劳苦大众于战争之中,得到安宁与和平。正如鲁迅在《文化偏执论》中探讨“一独夫”与“千万无赖”的关系,而“不堪命”的百姓希望的是“独夫”的暴虐统治压缩到最低限度。因此,在现实面前,劳苦大众的愿望是破碎了。
涡镇以及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普通人,只是想寻求一个安稳、和平的生存环境,涡镇的人民并不关心此时的统治者是县长还是预备团的井宗秀还是游击队抑或是阮天保。在特殊的时代洪流中,这种设想只能转化为对个人命运的起起伏伏的无奈与悲凉,和中国小农乞求无尽的自保心态中。在预备团与阮天保的保安队第一次交锋之前,涡镇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借镇民骡子去买石灰。不料在路上遇到了保安队的伏击,骡子全被带走了。而此时的涡镇人民并不关心战争的准备,只关心索赔,预备团战备物资本就捉襟见肘,无法赔偿。后周一山将镇民与预备团的利益放在一起,将阮家的地抵给镇民,自然主动支持后来的保卫战。在战争过程中,保安队故意放出镇骡子,而因镇民怕伤了骡子差点让保安队攻破城门。从预备团和保安队的战争来看,涡镇人民具有着典型中国农民的阶级局限性,自私而不顾全大局,战争的失败对涡镇来说就是一场屠杀,也是一场灭顶之灾,而小镇人民却因为几口骡子而动摇了保卫镇子的决心,而选择守护个人财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无法做到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甚至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这种只求安稳自保而放弃团结、封建自给自足的心态的弊端在战争的洪流面前被完全暴露出来,这是当时中国传统的农民普遍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
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芸芸众生在时代的潮流里,苟且偷生,苦苦挣扎,小农性格和阶级局限性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普通百姓的命运悲剧,也彰显了农民阶级是无法完成战争的胜利。生存意识迫使他们乞求一个英雄的出现,而各位“英雄”在获得成功之后,沦为权欲的奴隶,杀戮从未停止过。只要战争还未结束,普通百姓仍将会在这水深火热的生活中谋求生存,苦苦煎熬,祈祷出现下一个能够保卫家园的英雄,渴望得到身心的救赎。
三、苍莽之中大爱的救赎
作者在写完《山本》后记中说道:“英雄随草长,阴谋遍地霾。世道荒唐过,飘零只有爱。”在莽莽秦岭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武装斗争一直在继续,英雄在各个年代都会出现,多少兴亡事,都付诸于秦岭之中,而在秦岭中只有亘古不变的爱能够为这世道的人性带来救赎。这是作者对战争环境下人性异化和受苦的芸芸众生的痛楚解读之后,给予的答案,也是这部秦岭人物志最后想要的传达的主题。
(一)地域文化的救赎
在战争的年代,地域文化如同脆弱的孩子随时都会被摧毁,而在涡镇却有一个特殊的文化人的存在,那就是麻县长。由于时局无力挽回,并且不断的被各方武装势力架空的他,深知在武力征伐的年代中,百无一用最是书生。因此小说在这个人物出场之时便说了这个奇怪的县长,原想造福一方,对时局心灰意冷,无法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便生出了编写一部秦岭植物志和动物志,记录秦岭的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也算造福一方,流传千古的想法。因此,无论在老县城还是在涡镇,对于权欲的斗争,麻县长都选择规避,用考察作志的借口来退隐政坛。虽然对于时局感到绝望,但后在战火轰炸的涡镇中,麻县长也是以宁死不屈的态度与小镇共存亡,将自己写的秦岭植物志与动物志交于蚯蚓保存以流传,后投于涡谭自杀。麻县长的人生态度正好与井宗秀等人相反,从权欲中走出来,以研究和保护秦岭民间文化为己任,这种认识自然,回归自然的态度,正是道家所倡导的道法自然,但作为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还是无法放弃家国天下的夙愿,因此产生了自杀与小镇共存亡的结局。麻县长在儒道思想之间的融合使其自觉选择对战乱时期秦岭文化的保护,回归自然,追求本真。
(二)人性的救赎
《山本》中人性中所有美好的化身都集中于陆菊人身上,她善良淳朴,守身如玉,孝敬长辈,和小镇的其他人一样,渴望英雄来解救所有的人。她深知三分胭脂地的秘密,也得知自己的丈夫杨钟不是成大器之人,阴差阳错之下,胭脂地成为井家的祖坟,便密切关注井宗秀。陆菊人支持镇子里所有的工作,也爱护镇子里每一个人,为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陆菊人身上每一个点都体现了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光辉。而后在预备旅成立之后,受井宗秀的委托,掌管茶庄的各项事务,知人善任,善于交际,以德服人,成为了具有现代管理意识的企业家。铜镜上的:“内清质昭明光辉夫日月心忽而愿忠然而不泄”正是对她真实写照。陆菊人的爱并不仅仅局限于男女之爱,而是儒家所倡导的仁爱之心,小说中描写到她得知看到宽展师父在庙里给亡去的人做牌位,并超度亡魂,便提出自己捐款为死去的人立牌位,而这些死去的人有自己的丈夫、邻居,还有很多叫不出名的陌生人和外乡人,立了一个“近三年来在涡镇死去的众亡灵”的牌位。陆菊人的爱不是仅仅局限于方寸之间,而是一种普世的人间大爱。
作者在小说中塑造这一完美的女性形象,是想在人性异化为兽性之处,照进一束救赎的光芒。但是这道救赎之光并不仅仅只有陆菊人的仁爱之心,还有代表着道家的陈先生和代表着佛家的宽展师父。陈先生是涡镇的郎中,是元虚道人的弟子,在战争中自己将眼睛弄瞎,来到涡镇做一名乡间郎中。涡镇的居民有个头疼脑热或者气不顺的都会去安仁堂找陈先生,而陈先生并不是只是为人治身,更是治心,安抚病人情绪,缓解病人心结。因眼瞎但却洞察世事,因此和陆菊人不同,在陈先生心中,井宗秀和任何普通人都没有区别。陈先生崇尚道法自然,但是却不是不问世事。在三合县凤镇发生霍乱之时,挺身而出,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救治贫苦百姓,半个月后从三合县回到安仁堂之后,头发竟劳累的全白了。宽展师父是地藏王菩萨庙里的一个哑巴尼姑,终日不与人言语,却一直吹着尺八,希望用音乐来普度众生,并在庙里为战争中死去的亡灵超度。无论是曾经在庙中横行的土匪五雷等人,还是小镇里其他的人,宽展师父都以佛家慈悲的关怀对待,双手合十的诵经,她是出世的、精神的。面对精神与现实混乱的困境,她只能用佛家慈悲的关怀去包纳这个世道。对于涡镇的祸端,陈先生和宽展师父都心知肚明,“但陈先生是瞎子,宽展师父是哑巴,一个看不见,一个说不出,于是涡镇居民就有了祸。”[6]陈先生和宽展师父与陆菊人不同,他们洞察世事,为人间提供正能量,在他们眼中,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井宗秀、阮天保和土匪等枭雄也是与普通人无异,都是在这世间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只是他们面对人的生存困境和苦难的态度与其他人不同,也面对这杀人如麻的无道世界,深感悲凉与无奈。
四、秦岭文化精神的继承
《山本》中通过以秦岭为背景,讲述了官、匪、兵混战的历史。作者借写故事,展示了秦岭本土原生态的传统文化,描写了残酷的战争和人民苦难的生活,以及人在面对苦难与人祸的态度和精神状态。人性在暴力和战争中丧失,每个劳苦大众都被困于求自保而不得的困境中,在战火的炮弹中苟且偷生,惶惶不可终日。在这场人祸中的枭雄们和普罗大众皆为受害者,只是面对这些人祸,各类人的态度不同,所做出的行为不同。无论是何种行为,都是对命运的挣扎,乞求安定的生存空间的努力。而在作者的心中,唯有悲悯的情怀和人间的大爱才能解救人类命运和苦难,这种悲悯的情怀来源于民间传统文化的精神之中。陆菊人、陈郎中和宽展师父的大爱在秦岭这块土地上,为在战争泯灭的人性照进一束光。无论是仁者爱人,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还是佛家的大智大慧和慈悲为怀,都在用爱和悲悯去融汇在人世间的苦海之中的人。而这道儒、道、佛交融的人性的光辉,正是秦岭文化精神的中坚所在。
在《山本》中,作者将秦岭文化精神的继承者,也是秦岭战火中存活者设定为陆菊人的儿子剩剩。剩剩的名字来源于陆菊人陪嫁而来的黑猫吃剩的猫食,而這却将剩剩命运与精灵似的老黑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小时候因骑了井宗秀的马而被摔落下了残疾,后陆菊人担心他以后无所事事便将其托付给陈先生学医术,希望陈先生能教其好好做人,习得一个好手艺。因此,剩剩便带着黑猫住进了安仁堂。正如《山本》在最后写道大量炮弹落进涡镇,陆菊人见到剩剩的场景,“他们相见,没有叫喊,也没有哭啼,甚至剩剩也没有跑入她的怀里,他抱着那只猫,猫依旧睁着眼,一动不动。”陆菊人说,这些炮弹打到涡镇,涡镇就成了一堆尘土了,而陈先生说:“一堆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剩剩与陈先生在炮火中默默的站着,既没有跑也没有躲,这是对秦岭文化精神的一种坚守,一种自信,纵使一切归于尘土,而秦岭文化精神却不会因此泯灭,就算是一堆土,也是秦岭上的一堆土。而秦岭文化精神的继承者剩剩作为战争中的幸存者,作为人性美好的继承者,也是作者心中这股文化自信的表现。
《山本》通过民间说野史将战争中人性的善与丑,展示在世人面前。在民间这个藏污纳垢的环境中,既有在迷失的人们,也有洞察世事的贤明,他们用秦岭的博大胸怀和普世的爱,照亮了所有的黑暗,救赎着迷失的人。一切的世道和阴谋都是人之本性,而宽广的胸怀大爱正是秦岭之本。无论历史的进程如何,多少兴亡事付诸于秦岭,飘零只有爱,唯有永恒的爱和秦岭的山峰一样,以尽着黛青。
参考文献:
[1]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77.
[2] 贾平凹.山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404,523.
[3]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1.
[4] 章榕榕.徜徉在历史血脉中的暴力———解读《白鹿原》中的暴力美学,作家作品研究[J],2006:6.
[5] 贾平凹.写那么多死亡是为了诅咒那个时代,新京报书评:http://www.sohu.com/a/229495586_119350.
[6] 陈思和.试论贾平凹《山本》的民间性、传统性和现代性[J].小说评论,2018,(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