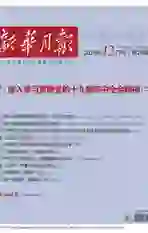马悦然:带着汉语的乡愁离去
2019-09-10艾江涛
艾江涛
在难产的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六天后,据瑞典媒体报道,95岁的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去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马悦然这个来自瑞典的老头,以瑞典学院有资格对诺贝尔文学奖投票的18位终身院士中唯一一位精通汉语的学者身份,为国人所熟悉。在当代作家的圈子中,马悦然则以一位中国文学热心、真性情的推荐者为人们所纪念。
消息传来,诗人芒克发了一条朋友圈:“1996年马悦然老先生和太太在瑞典款待我们,参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大厅,还让我坐在评委会主席的座位上决定让谁获奖。如今老先生走了。”由于平时与马悦然交往不多,芒克并不愿就此谈论更多,但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电话接通的时候,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多年的作家万之,刚刚参加完在哥德堡举办的一个诗歌节,正在等候回斯德哥尔摩的火车,回去后才知道瑞典学院那边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万之告诉我,因为去年诺贝尔文学奖爆出的丑闻,瑞典学院在是否起诉女院士弗罗斯滕松一事上发生内部分歧。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由于马悦然在内的多数院士同意不起诉,结果埃斯普马克、恩格道尔、恩哥伦三位院士愤而退出诺奖投票,当年的诺奖因此延迟到今年颁发。由于万之站在埃斯普马克一方,这使他与私交甚好的马悦然之间有了隔阂。谈及这件事,万之有些感慨:“马悦然这个人,很有点中国人那种,很讲情面。”

然而,留在万之心目中的,仍是三年前中秋节晚上最后一晤的美好记忆:“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很漂亮的雕塑公园,松树林中,月光之下,喝酒赏月。他那会儿已经92岁,还能喝半瓶我带去的五粮液。”
对于多数像我一样并没有见过这位老人的人来说,了解他的更好办法,或许只有读他所留下的文字。在2004年出版的文集《另一种乡愁》中,将近90岁的马悦然追忆过往的学术人生,所写自己青年时期在四川调查方言期间住在一间庙宇中的情景,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怅惘之感:“我永远会记得小和尚们每天晚上用清脆的声音高高兴兴地唱晚上仪式的头一首很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灭。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目。但念无常,慎勿放逸。’”
马悦然与中国的缘分,与林语堂有关。1946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与希腊文的他,人生规划原本是做一名高中老师。无意中读到林语堂的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后,马悦然对其中谈到的老子的《道德经》产生了兴趣。他找了英、法、德几个译本后,发现内容差异很大,于是鼓起勇气给当时已经写出《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打电话求教。初次见面,高本汉便将自己翻译尚未出版的《道德经》,借给了这个好学的年轻人。一周后还书时,高本汉问他:“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学中文呢?”就这样,1946年8月底,马悦然转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高本汉开始了他的汉学研究。
令人惊讶的是,高本汉给他开列的第一本书正是《左传》。对于这本2000多年前的汉语经典,高本汉终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认为它是世界文学中最精彩的著作之一。而且他发现,《左传》古老难懂的文字中,事实上保存了很多当时的口语对话。从高本汉那里所学习的古代音韵学知识,结合自身对语音的高度敏感性,为马悦然后来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在《劳动号子的节奏与诗歌的格律》一文中,他回忆自己用诗人曹辛之的笔名“杭约赫”记录在四川听到拉板车的人哼唱劳动号子的节奏,几年之后,他发现2000多年前荀子《成相篇》的节奏与劳动号子的节奏完全相同。后来,他注意到陕西诗人王老九的叙事长诗也具备相同的节奏,不禁赞叹汉语强大的生命力。
1948年8月,追随高本汉学习两年的马悦然,凭一个美国煤油大王的奖学金,获得去中国调查四川方言的机会。此后两年,他辗转在内战时期的重庆、成都、乐山和峨眉山等地,记录方言数据。初到中国的马悦然,汉语水平还停留在会读不会说的阶段。在重庆和成都待了两个月后,他学会了西南官话,可以独自调研方言。不过,更进一步的學习则来自报国寺一个叫果玲的老和尚。从1949年大年初一到8月,马悦然一直住在峨眉山120座寺庙中最大的寺庙——报国寺中。
在晚年的回忆文字中,马悦然对当年那位曾在大学教过国文的老和尚充满感激:“每天早饭后老和尚到我的房间来给我讲两个小时的课。首先读的是‘四书’,‘四书’读完就念诗,《唐诗三百首》、汉朝的五言诗和乐府、魏晋南北朝的诗,他什么都教我。他也想教我用毛笔写字,但是很快发现我完全缺乏书法的天赋。”
在四川那段时间,马悦然还收获了后来伴随他终生的中文名字。1950年上半年,马悦然跟随华西大学中文系主任闻宥学习宋词,闻教授为他起名“马悦然”。
在回忆文字中,马悦然时不时会冒出几句四川话“莫得事”“莫得办法得”,颇为自得。山西小说家李锐告诉我,马悦然的普通话和四川话都不错,和他在一起时讲普通话,和妻子陈宁祖回四川老家时,便讲四川话。
马悦然刚到成都时,曾在当时担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陈可行的家中租住过一段时间,刚刚高中毕业的陈宁祖正是房东的二女儿。马悦然受命为陈宁祖补习英语,两人渐生情愫。不过当时马悦然已经订婚,直到1950年7月,返回香港得知在美国的未婚妻爱上别人,愿意和他分手后,他才立即给自己的房东发电报求婚。不久,两人如愿走到一起。
此后几十年,陈宁祖成为马悦然的贤内助还有熟悉中国文化的窗口,出现在许多中国作家的回忆中。1996年,陈宁祖去世后,万之所写的纪念文章中,还谈到她在一次闲聊后,为格非收集伯格曼电影的录像、为余华送来某个瑞典音乐家的磁带。
在四川调查方言的两年多时间,马悦然不仅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还更深地体会到传统中国的人情之美。他感慨岳父家那个不但主张放走小偷,还偷偷把对方翻墙用的梯子还回去的厨子。多年之后,他找到那个带他出行遭遇土匪的向导,对方还为弄丢他的一块手表而感到歉意。在一次采访中,他回忆起那时普通中国人对美的感受:“我以前在四川的时候,看见峨眉山的农民总是在农忙之余,翻过一座山去看芍药花……还有一次是我正背靠着一棵大树看书,发现一个老人一边踩着大树周围的落叶,一边说:‘真好听啊!’”
我不知道,这些当年的记忆怎样塑造了马悦然对中国的理解与想象。显然,数年之后,当他再次以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身份返回中国,面对一个气象一新的国家时,发现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东西很多。
经历了驻华文化参赞、国外多所大学讲师等身份变化,1965年,马悦然回国创建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并长期任教于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以实验语言学的方法,从统计学、文字学、语法学等多重角度分析《春秋繁露》《公羊传》和《谷梁传》,发现《公羊传》产生较早,《谷梁传》产生于东汉之后,而《春秋繁露》中的多数章节都是魏晋南北朝之后的人托名撰写。他还将语言统计与比较的方法运用于古汉语写作,写有《论〈左传〉中“其”字的不同功能和意义》等论文。
多年的学术研究,使马悦然成为高本汉之后瑞典汉学界的又一重镇。他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曾比较两代瑞典汉学家的区别:“高本汉的汉学研究注重的是解决知识之谜,马悦然前期继承高氏的汉学研究传统,后期则开始一项可称之为‘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型汉学研究。”
所谓“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型汉学研究,在马悦然那里,集中体现为对中国文学从古至今跨度极广的研究与译介。李锐对此赞叹不已,在一篇题为《心上的秋天》的序言中写道:“他把西汉典籍《春秋繁露》翻译成英文。他让同胞们和他一起分享《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美妙篇章。他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一版再版,到处流传。他的翻译和介绍让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现代、当代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引起世界的注意。我不知道還有哪个外国人像他这样无怨无悔,不辞劳苦,到处传播中国文化,到处传播中国的语言和声音。”
1986年6月的一天,李锐忽然收到一封从瑞典的来信。一个叫马悦然的人,声称自己在订阅的《小说月报》上看到李锐小说集《厚土》的节选,希望获得翻译授权。自此,李锐便开始了与马悦然的交往。1989年,瑞典文的系列小说集《厚土》出版后,1989年、1990年,马悦然连续两次邀请李锐到瑞典访问。1990年,两人终于在瑞典见面。早在一年前,马悦然就告诉李锐,他邀请了瑞典学院的八九位院士,想一起去看看李锐当年插队的村子——吕梁山区邸家河村。结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直到2004年才最终成行。
在邸家河村,马悦然再次感受到来自中国大地的气息。当村长向村里一个年长的老太太介绍这位从遥远的北欧来的客人时,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说:“哈,天下乌鸦一般黑。”马悦然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无论住在什么地方,地球上的人都是一样的”。
马悦然似乎偏爱那些带有泥土气息的中国作家。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说:“我高兴一个乡巴佬得奖,尤其是一个中国的乡巴佬得奖,沈从文、曹乃谦、莫言都是乡巴佬作家。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从1985年,马悦然成为具有诺奖投票权的瑞典学院院士后,他的这种个人偏爱所带来的影响,被难以避免地放大了。一些评论者认为马悦然过于偏爱对中国前现代经验的书写,言下之意是,他也忽略了很多反映当下中国的作品。
李锐对此并不认同。“马悦然喜欢讲‘乡巴佬’,实际上不是在讲那种土得掉渣的东西,而是在讲一种乡土的气息,关键在于,文学是否把乡土变成了文学。如果乡土还是乡土,那有什么可喜欢的?”
“我首先把马悦然定位为一个率性由情的真人,也不拘泥于规范。他的个人喜好多带有偏爱性质。如他对沈从文作品的欣赏,对北岛诗歌的喜爱,对李锐、曹乃谦小说的推崇等,都有偏爱性质。让我以赛马来比喻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虽然这比喻不一定贴切),赛马是很多好马都站到同一起跑线上,发令枪一响,所有马一起跑,哪匹马跑得快就哪匹马胜出。这比较公平。有偏爱的人呢,他只拉出一匹自己喜欢的马来,夸这匹马如何跑得快,但别人(如真正的评委)未必如此看。”万之说。
用万之的话,马悦然翻译了北岛写的每一行诗。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马悦然便通过当时还在外交学院任教的汉学家杜博妮的英文翻译,了解到了“朦胧诗人”们的创作。1983年秋,正是在杜博妮的教师宿舍,北岛、顾城、万之等人第一次见到了马悦然。同年,马悦然还专门给曾批评朦胧诗人的艾青写信,试着为他们辩护。
尽管有所偏爱,但马悦然对自己翻译过的作家也不乏批评。他曾公开说莫言的小说写得太长。文学批评家王元化在关于1991年的回忆文章中便谈道:“他喜欢北岛的诗,但对北岛也不是一味赞扬。有一次,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北岛曾对他说不喜欢中国的古书,表示对传统的厌恶。他说,他不能理解,一个作家倘使把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都当作是要不得的东西,还能写出什么好作品。”
1986年,在旧金山举办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上,不少人提出中国作家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马悦然在发言中试图解释,翻译的质量会影响到评委对作品的理解。没想到这一说法竟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质问他:“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一起参会的王元化看到群情激愤下马悦然发窘的样子,不禁对他有些同情。
回头来看,文学作品必然要通过翻译,才能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本是常识。发生在30多年前的这一幕,无疑反映了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某种焦虑情结。这种焦虑,随着中国作家的得奖,得到了自然的纾解。但围绕在马悦然身上的,依然是无法绕开的诺奖话题。
谈及诺贝尔奖,马悦然最常说的一段话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是北欧几个小国的18个评委评出来的一个奖项,它不是世界冠军,没那么重要。”
在中国作家得奖前,对可能得奖的中国作家,从鲁迅、林语堂到老舍、沈从文,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言。或许是为了一次回答这些问题,马悦然2015年4月在澳门科技馆专门做了一次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1913年选入瑞典学院的斯文·赫定很希望一个中国作家得到诺奖。1924年12月,斯文·赫定给高本汉写信,请他帮忙找到一位合适的中国作家。高本汉的回信说据他看没有中国作家有资格得奖,但他提到一位年轻的中国朋友正在巴黎从事语言学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很熟,也许可以帮忙介绍。这位年轻的朋友正是刘半农。后来刘半农在一次宴会上,趁机单独问鲁迅是否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拒绝了这个好意。很可能刘半农将鲁迅的回答转达给了斯文·赫定。
谈到沈从文,马悦然说:“我是1985年选进瑞典学院成为院士的,要是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的话,他肯定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秘密我不应当说出来,但自从我说出来以后,我的同事们非常理解我的心情。”
熟悉马悦然的人都会说起,他自幼就有创作的兴趣,只是这一兴趣直到他步入耄耋之年后方才展开。除了写作散文集《另一种乡愁》,马悦然还创作了俳句集《俳句一百首》,后来还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台湾前媒体人陈文芬分别以“南坡居士”和“台湾小妖”的笔名,合写了微型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
“马悦然非常喜欢道家。他对儒家不喜欢,比如《论语》,他都不翻译。”万之回忆,他不但重新翻译了《道德经》,大概从85岁之后开始翻译《庄子》。去世前几年,马悦然还将大量精力花在《庄子》的翻译上,据说,他在骨折以后,看到《庄子》,腿就不疼了。
始于《道德经》,终于《庄子》,马悦然带走对汉语的最后一缕乡愁,从此不用再答有关诺奖的各种问题了。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