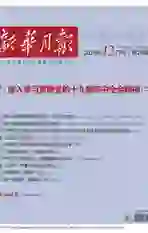从英国到希腊:有暴力,更有仇恨
2019-09-10吴健
吴健
感恩节前,一位试图移民英国的投资家眼看着自己的企业主签证被拒绝,为什么?他在商业计划书里说英国经济和社会是稳定的,而移民局明确表示拒签理由就在这里,因为“正在进行的脱欧进程及暴力示威活动”与这一说法背道而驰。报道如此荒诞的事情时,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弗洛朗坦科隆露出一脸的无奈,广袤的欧洲大地上,反移民、反精英、极端民族主义、富裕地带独立等等诉求引来一场接一场动荡。更致命的是,不知名的小人物一条推文可点燃社会分裂的火药桶,他发推文的时间和内容很难预测,举事者完全根据情绪行事,而公众的行为也变得更加不稳定和出人意料,与此同时,那些民粹主义政客却因此如鱼得水,飞黄腾达,难怪他们把这一切叫作“美丽风景”。
·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将出现硬边界,结果引发抗议活动、道路阻塞及“直接(镇压)行动”。
·港口受到的干扰将持续三个月,然后交通流量将“恢复”到目前水平的50%到70%。
·英国各地爆发抗议活动,“需要调动大量警力”。
……
以上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的约翰逊首相为脱欧极端情况下准备的“黄鹀行动”条款,昭示了极大概率的全国性骚乱风险。这份标记为“官方-敏感”的秘密文件于8月份意外泄露,保守党内阁办公厅大臣迈克尔戈夫紧急灭火,称政府有信心让国家稳妥脱欧,而在野的工党影子内阁“脱欧事务大臣”基尔斯塔默嗤之以鼻,“一个因脱欧导致社会走向部落化对立的国家”是多么害怕“底层怒火”。
赴英采访的西班牙《先锋报》记者拉斐尔拉莫看见,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成了英国政治分水岭,家人、朋友和同事之间因分属不同“部落”而相互仇视,民族主义者奉行民粹保守,不满政府将更多公共支出拨给苏格兰而非英格兰,不满威尔士有自治政府,但约克郡却没有,“感到自己被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排挤了,工作没有技能,福利没有保障,于是想要更多的警察驱逐外来劳工”。欧洲主义者过去是一盘散沙,但其政治激情在反对脱欧运动中被点燃,因为自己有了共同的身份和团结的事业,值得去奋斗至死,他们批评脱欧公投结果是谎言织就的,于是他们用推特相互沟通,策划瘫痪市政,不择手段进行抗议,意图扭转乾坤,沦为别人口中“不接受结果的坏输家”。

英国的情况在欧洲具有共性。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立派”前高官被判重罪引发的骚乱、阴魂不散的法国“黄背心”运动、20万在罗马圣乔瓦尼广场高呼反政府口号“从你们的虚幻世界滚出来”的意大利示威者、针对政府目标和亚非移民实施街头袭击的希腊极右翼金色黎明黨……总之,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充斥着暴力,而法国社会学家阿兰迪阿梅尔更害怕的是,“这一轮政治暴力裹挟着难以遏制的仇恨,这与1968年的欧洲‘五月风暴’完全不同”。这位准确预测欧盟一体化受挫的资深分析家写道:“1968年因经济危机、越南战争等因素引发的西欧各国大罢工甚至‘巷战’,里面有暴力,但没有仇恨,可当前运动的特殊性在于暴力与仇恨混合,那是普遍的仇恨,侵蚀了本就不稳定的政治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
观察这些政治运动,法国巴黎第二大学传播专业教授阿尔诺·梅西耶试图找出他们的动员规律。他以英国“反抗灭绝”和法国“黄背心”运动为标本,这都是个别人在网上发起的倡议,却很快蔓延成全国性动荡。“他们喜欢用脸谱和推特,也包括YouTube和谷歌搜索,就是为了确认活动的地点。这表明,网络成了不可或缺的沟通工具,尤其是涉及自发和没有任何机构组织的活动。”社交网站能快速把民众关注聚集到热门问题上,可以很快就某个主题发起动员,催生出民众偶发性参与的集体性活动。
伴随欧洲社会变化,政治活动逐渐与个人诉求及与别人分享自己遭遇有关,社交媒体提供了互不相识却有共同思想、痛苦之人交流的可能性,在线的抱怨吐槽往往演变成运动。像“黄背心”起初缺乏经社交媒体沟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冲突起始于年轻人雅克利娜·穆朗在2018年10月18日发布的视频,题目叫“对司机的迫害”,以此质问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什么提高燃油税同时却给富裕阶层减税,一下子在网络上获得广泛呼应和请愿,因为这会影响到所有人的家庭开支。之后,社交网站开始接棒,因为它们通过一些讨论群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接下来的互联行动随着新加入的群体而受到普遍认同,滚雪球般得到众多支持。这正是2018—2019年以来在脸谱上可以看到的现象,在该网站上类似群体越来越多。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还有希腊,每周在脸谱网站上都有1500多个组织发出呼吁,无论规模是街区、城镇还是大城市。
要看到,这种动员的奏效与脸谱2018年1月份的改动不无关系。为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其反假新闻不力的批评,脸谱决定减弱媒体内容的上传力度,鼓励社群内的有组织讨论。实际上,此举让“朋友”之间进行直接沟通,这一改变恰逢“黄背心”之类运动发酵,数十万人可在最初没有确定主题的情况下直接互动,产生能量聚集。通过社群串联,运动参与者学会了占据令政府关注的一些地点(加油站、石油库、高速公路收费站等)来扩大影响,这些地方都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环岛通常都位于环城公路的入口,周边的人群很多都是被高昂的房租或交通费撵出城区的人。大型商场的入口也是他们的首选地,因为这里是他们原本可以日常购物却因购买力下降而无法出入的地方。”

面对由网络召来的庞大而复杂的愤怒群体,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埃里克西尔弗斯把视角对准能量最强的年轻人,发现像癌症一样的“就业贫困化”把他们推向悬崖的边缘。
按道理说,2019年算是欧洲失业危机相对缓和的年份。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曾哀叹“800万人无事可干”的法国,在新培训政策支持下,失业率降至就业人口的约9%。300余万完全失业的A类求职者稳中有降,而事务性失业的D类求职者也有小幅回落。西班牙失业人口减到300万,是2013年峰值的一半。意大利25岁以下人口在2019年4月的失业率为惊人的31.4%,可同比却有一定降幅。然而欧洲青年的主要问题是二元就业制度,签订开放式合同的人——通常是年纪较大的劳动者——享有铁定的就业保障和福利,可在经济低迷时期,雇主却偏好使用更多的短期合同,期限一般从一个月到一年不等。在意大利,截至2018年,25岁以下人群有62%签的是短期合同,高于2000年的25%,意大利政府在30年前推出二元合同,本意是帮助年轻人尽快挺过过渡期,最终找到长期工作,而雇主也避免与解雇员工有關的成本和麻烦,2014年和2015年,罗马甚至用减免数十亿欧元税收的方式鼓励雇主签署开放性合同,可毫无起色。
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尔格克雷默称,二元就业造成欧洲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可自由化的“黑暗面”是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只有极不稳定的工作岗位,人称“垃圾工作”,许多新岗位(如旅游业)每周仅提供几个小时的工作,而且工资往往很低,令人难以维持生计。今年4月10日,经合组织报告显示,西班牙的“千禧一代”(出生于1983年到2002年的年轻人),有半数无法进入或不再属于中产阶层,这一比例在出生于1965年到1982年的“X一代”西班牙人中为58%,而在千禧一代中为50%。报告指出,在住房支出方面,高收入人群逐渐吸收中产阶层越来越多的资源,目前,住房开支约占西班牙中产阶层家庭支出的33%。这一比例在2005年时为29%,而在1995年时为24%。事实也证明,震撼西班牙的加区骚乱中,当地“千禧一代”是主要参与者,而且该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应和者。
在法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吉吕眼里,这些以年轻人为主体,各个年龄层、各个职业都参与的运动,体现了过去四十来年欧洲大众阶层在社会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进程。在他们看来,以往构成中产阶级基础的工人、职员、个体户、农民、公务员等等成了全球化经济模式的牺牲品,自己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位置。而他们也不再被政界、媒体和学术界视为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变成精英眼中的“可怜虫”。这种蔑视是引发仇恨的关键,实际上,遍布欧洲的抗议运动凸显了西方综合危机。美国哈得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鲁诺马卡埃斯说,欧洲发生的一切,是对其丧失世界霸权的“报应”,“过去,由于殖民霸权存在,帝国的战利品会流向下层阶级,使之与掌权者和解。可是这一切在“二战”后完全改变了,欧洲精英再向别国发号施令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口袋里也不再有化解矛盾的筹码了”。
根本上,“二战”后,西欧基本形成受政府调控、强调再分配、但仍以市场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经济财富经政府“向赢家课税”和“救助落后者”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新分配,让需要补贴才能活下去的人支持这一基于利害关系的“社会契约”。但它所产生的经济盈余却跟不上政治补贴的胃口。马卡埃斯指出,失去对东方殖民地的剥削后,欧洲国家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中获取盈余,主要靠两项输入的产物:工作时数和每个小时工作的质量。前者是人口统计变量,后者是劳动生产力变量。在欧洲,人口状况和生产力对GDP增长的贡献,过去四十年来都逐渐降为零,有些国家甚至低于零。西方人口老龄化先在日本显现,接着在欧洲蔓延,每年工作时数的增长不像1945年至2000年间那么快,那时五六十年代婴儿潮的新增人口陆续加入劳动力大军。由于GDP增长盈余鲜有增长,社会黏合剂不得不靠债务来融资,举凡出现动乱的欧洲诸国,公共债务都升至GDP的100%以上,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戈夫和卡门莱茵哈特已证明的,一旦政府债务超过GDP的90%左右,经济增长通道就容易堵塞,供重新分配的盈余也就所剩无多了。
恰恰在40多年前,激进的新自由主义从英国发端,然后被兜售到整个欧洲,它承诺提升增长率,可核心是将职场力量平衡倒向资方,把人当成工资的奴隶,确保增长果实为少数人而非多数人占有。全球投资公司格兰瑟姆-梅奥-范奥特洛公司(GMO)分析师詹姆斯蒙捷和菲利普皮尔金顿发现,1979年至今,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欧洲国家有四大特征:放弃充分就业,代之以通货膨胀目标制;加剧人员、资本和贸易流动的全球化;聚焦股东利益最大化而非重新投资和增长;追求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瓦解工会和工人组织,让资方用更多收益投入再生产和技术创新。以这四大支柱中的最后一个为例,其逻辑是“工会与最低工资是有效劳动力市场的障碍”,集体谈判和法定最低工资将导致工人薪水高于市场数字,结果是企业撤离,失业率必然上升,应当尽可能削减最低工资。但蒙捷和皮尔金顿却发现,这种对劳动力市场绝对灵活性的追求,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像过去十年英国个人税额抵免的申请急剧上升,因为公司只愿向员工支付勉强糊口的低薪而让政府兜底,况且既然有低成本劳动力,又何必费劲去投资促进生产力的新设备和新技术呢?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保罗科利尔承认,过去40年,欧洲国家对严重的社会分裂听之任之。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马塞尔戈谢曾对他说:“欧洲的可悲,在于国民没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和归属感,过去‘社会契约’已被烧了。”

戈谢指出,不管有没有欧洲一体化,发生动荡的欧洲各国之“不幸”都是一样的,欧洲不过是“不幸”的放大器和显影剂,“我们面临的最普遍问题是如何在个体自由和集体权力之间平衡,这种平衡可通过维持福利国家来实现,当然福利国家成本很高,要想维持就得改革,使其更有效率”,这是欧洲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他以法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密特朗总统向法国人灌输“法国一切毛病都能通过欧洲解决”的观点,内涵是“法国拥有军事和战略手段,德国拥有经济实力,由此共同打造由法国引领的政治一体化欧洲,抗衡英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按照这种观点,欧洲可帮法国塑造起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新典范。可事实正相反,欧洲加剧了法国向新自由主义转型,“欧盟伙伴们普遍信奉新自由主义政策,欧盟委员会就是这种政策的先锋,布鲁塞尔天天提及的‘恢复秩序’中的‘秩序’一词始终指的是更多的市场,更多的灵活性,而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大众阶层徒劳地抵御着新自由主义浪潮——它在吞没我们”。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指出,欧洲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应当有意识地采取让赢家给输家一些补偿的措施,“如果输家走上末路,它们为何还要支持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呢?支持阻止这种趋势延续下去的政策,才是它们的利益所在”。事实上,如果欧洲缺少渐进政策,尤其缺少对输家进行社会保护和维持就业的管理,民粹主义政客便会玩弄恐惧和沙文主义,结合街头暴力运动,用“敌我势不两立”的思路制造政治僵局,留下一个分裂的欧洲,这是谁都承受不起的灾难。“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人类已互相联系在一起,而且应当一起面对全球变暖、恐怖主义威胁等共同问题,应当加强而不是削弱为解决这些争端进行合作的能力和意愿。欧洲人必须尽快明白,唯一的长久繁荣是分享繁荣,这就是当前政治风波所留下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