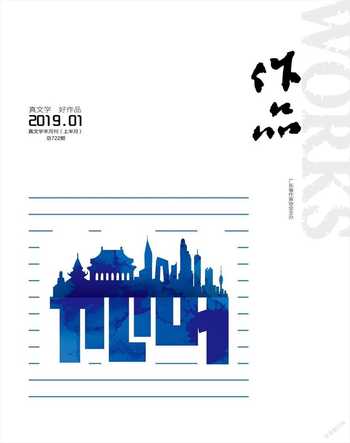啊!
2019-09-10付秀莹
付秀莹
芳村有个风俗,说是正月里不能剪头。出了二月二,才算是出了正月。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正月里剪头,死舅舅。”有舅舅的人家,就格外小心。尤其是做母亲的,早就把孩子们叮嘱过了,说记着啊,千万。也有为这个有了芥蒂的。孩子们一时忘了,被舅舅妗子知道,心里就不痛快。找上门来质问的也有,过后拿这话柄说事的也有。总之是,这地方人都认老理儿。正月里剪头,总是理亏的一方。
这自然是芳村的风俗。城市里却不大讲究这些,比方说,北京。
小见来北京有几年了,先是跟着一个亲戚做。那亲戚是田庄的,跟小见他们家沾着一点老亲。小见他娘教着他,叫宾哥。宾哥性子豪爽,是跟小见他娘拍了胸脯的,说北京城再大,也总得有理发的吧。有他一口饭,就有小见的,放心好了。不料宾嫂却是一个刻薄寡恩的,在人屋檐下,滋味不好受。小见就找了个借口,出来了。
这家店在学院南路上,附近有好几所大学,北师大,北邮电,北影。学生多,生意自然就不错。店面门脸不大,是一幢居民楼的底商,装潢得很有现代感,主调是黑白两色,又时尚,又大气。不像宾哥那店,粉色底子,花花绿绿的,有一种俗丽的乡村气质。店名也有意思,叫作“啊!”。老板是个女的,他们都叫她红姐。红姐喜欢浓妆,年纪嘛,也看不大出来。有说二十大几的,有说三十多的,也有说四十的。红姐好看,却不大爱说话,一张粉脸总是郁郁的。小见他们都有些惧她。
过了正月初十,店里就开业了。学校还没有开学,生意就有点冷清。一大早,小见把店里里里外外都清扫了,还把那棵发财树搬到门口,让它晒晒太阳。发财树很茂盛,养在一个硕大的黑陶盆里。天气不错,难得的是没有霾。天蓝得清澈,叫人心里莫名地喜悦。一只麻雀在地下蹦来蹦去,叽叽喳喳叫着,张狂得很。一只小狗跑过来,穿着小红袄,脖子里的小铃铛叮当叮当乱响,一面跑,一面回头看。主人在后头叫道,慢点,花花,你慢点——人已经到跟前了。小见抬头一看,是一个女人,裹着一件大红长款羽绒服,头发烫了,胡乱在脑后绾成一个髻,乱蓬蓬鸟窝一般。小见不由得皱皱眉头。干这行久了,就格外留心人家的头发。这女人的头发发质干枯,毛糙,发梢分叉,缺乏光泽。这也是职业病吧。小见心里笑了一下。那叫作花花的,却一头闯进店里,差点把门口那个小盆栽给撞翻了。女人惊叫着,直个劲儿说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小见说,没事儿。就蹲下来逗花花玩儿。花花肥胖,小红袄撑得满满当当的。花花?你叫花花?啊?花花?女人环顾一下店里,说今儿个不忙呀。小见说不忙,一般上午活儿不多。那女人想了想说,要不我给你找点活儿吧。
这家店面积不大,被一架屏风隔开来,前面是美发区,后面是洗发区。屏风是黑色,有著坚硬的金属的质感。上面是一些不规则的几何空格,风格硬朗,艺术感十足。小见一面帮客人洗头,一面听她说话。客人跟客人不一样。有的爱说,从头到尾吧啦吧啦吧啦,说个不停。这个时候,你就得认真听着,适时地插话,就像相声里捧哏的那一方,不能说多了,也不能说少了,要捧得恰到好处。也有的客人不爱说,眼睛一闭,自顾养神。或者是戴个耳机听歌,或者是埋头刷微信,这个时候,你就得闭嘴,千万别再跟他东拉西扯说闲篇儿,更不要呱唧呱唧使劲儿推销你家的产品,劝说人家办这个卡吧办那个卡吧。店里小六子就碰上过这事儿。一个客人来染发,他见那客人出手大方,穿戴也不俗,说话的时候,不时蹦出英文单词来,以为遇上金主了。不顾那人一脸的冷笑热笑,皮笑肉不笑,死咬住不放。软的硬的,不软不硬的,吃奶的力气都使尽了。当时正是三八妇女节,被商家美其名曰女神节女王节的。店里趁机推出了各种促销活动。比方说,办一张2018元的贵宾卡,八折优惠。2018年嘛。要发要发,这数字多吉利哪,谁不愿意图个吉利呢您说是不是?那客人从头到尾都一声不吭,结果出门的时候,拒绝结账,说被强势推销了,要么免单,要么就网上曝光去。如今培养个好口碑不易,弄个坏名声可太简单了。别的不说,发个朋友圈,就毁了。新媒体时代,有图有真相,分分钟的事儿。结果那一回不仅给那客人免了单,还赠送了人家一次水疗。小六子被罚了一个月工资,只好借债交房租。红姐说了,不是她狠心,是小六子忒不长眼了。干他们这一行的,就得伶俐懂事儿,有眼力见儿,能看出客人的眉高眼低来,甭老想着推销啊推销啊。偷鸡不成蚀把米,知道不知道?
洗完头,帮着她吹干了,小见引导她坐在一个舒服点的位子上。一番闲话下来,小见知道了,这女的姓旷,他就叫她旷姐。旷姐是河北张家口人,小见惊喜地说,啊,老乡哇,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心里却说,怎么又是老乡?
早先,他刚出来的时候,还是很迷信老乡的。宾哥不就是老乡嘛,不仅是老乡,还是亲戚。宾哥店里人手少,用起人来就格外狠。小见其实是一个勤快的人,出来的时候,他娘嘱咐过来了,在外头,要多干活,少说话,甭怕吃亏,吃亏是福。小见暗暗记下了。宾哥把他带出来,宾哥就是他的恩人。他不过是多出点力气,还说什么吃亏不吃亏的话呢。一天到晚,他手脚不歇。用芳村的话就是,丢了笤帚抓扫帚,做在前头,吃在后头。宾嫂却总不满意,见不得小见歇一下,歇一下就是歇百下,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倒比待旁人还要苛刻几分。他又不能跟宾哥诉说委屈。宾哥大大咧咧,对这些屋里的琐碎闲话也不在意。就算是真的说了,宾哥能怎么样呢?宾嫂到底是他媳妇,要是向着他呢,无非是叫人家夫妻不和睦罢了。他从宾哥那出来,没有说宾嫂半个不字,还给宾嫂买了一瓶香水,是兰蔻。做人嘛,要记着人家的好处。这也是他娘从小教他的。
旷姐的头发被白毛巾包着,身上披着理发用的白单子,坐在椅子上,跟小见商量剪一个什么发型。没有了头发和衣服的修饰,旷姐看起来像换了一个人,有点陌生。旷姐皮肤微黑,却丰满,嘴唇偏厚,口红涂得浓艳。嘴唇上方,有一层细细密密的小绒毛,或者叫作小胡子。这偏于男性化的小胡子,跟那红唇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小见心里笑了一下。旷姐说,弄个直发,怎么样?显年轻。小见犹豫了一下,说,好啊。其实他是想说,她这头发发质不好,就是因为烫染过度。这卷发拉直,又把头发伤一回。像她这样的情况,就焗个营养,适当修一修受损的发梢就行了。还有,直发是显年轻,可那要看谁。只有那些年轻女孩子,又骨感,又灵动,才能剪出那样的效果来。旷姐胖,并且,旷姐也不年轻了。他看着旷姐兴致勃勃的样子,就把想说的话咽下去,说好啊,直发显年轻,旷姐本来就显年轻,留直发就更年轻了呀。旷姐笑得花枝乱颤,那椅子因为承重,也咯吱咯吱一阵乱响。小见说,为了满足客人的不同需求,咱们店里实行分层服务。小见顿了顿,见旷姐没反应,便接着说,美发顾问:38元,美发总监:58元,技术总监:78元,高级发型师:98元……旷姐说,哦,那你是?小见说,我是高级,姐,高级发型师。有点不好意思,又补充道,我干这一行十来年了,姐可以试试我的手艺。又顿了顿,说,当然,姐也可以点别人,全看姐的意思。旷姐就笑了,我就点你了。那么多门道,听着就麻烦。小见忙说,好啊,谢谢姐,包姐满意。手上就更勤快了。其实,店里这些个分层服务,都是老板定的,谁是技术总监,谁是美发总监,谁是助理,谁是高级发型师,红姐说了算。美发师按照收入提成,大家都很在意这个。小见给客人把头发吹了七八分干,俯身对旷姐说,姐要喝点什么,柠檬水,还是苏打水?旷姐说,柠檬水吧。小见就去后面倒柠檬水。心里怦怦地跳着,转过身去,偷偷把胸前的小牌子摘掉,放进口袋里,忽然听见有人扑哧笑了一声,回头一看,却是环环。他抚着胸口说,你猫啊,走路一点动静都没有,吓死人。环环说,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我可都看见啦。小见嘘了一声,许诺道,你叫麦当劳,我请客,随便点。环环打了个“OK”的手势,说这还差不多,说话算数啊。
端了柠檬水过来,旷姐正跟人微信语音。小见不好在那里听人家说话,就去收拾那些兵器,宽齿梳子,细齿梳子,小剪刀,大剪刀,小夹子,大夹子,夹板,顺手还带来一本时尚杂志。旷姐语音完了,就开始做头发,先是剪。剪多少,发中线怎么分,是中分呢,还是偏分。偏分的话,是三七分呢,还是四六分,这些细节,小见都得跟客人商量。女客人在乎的就是这些细节。有一回,一个女客人来,长发及腰,说是要剪短,剪到齐耳。小见心里说,可惜了,这么长的头发,可也不好劝说。那客人头发真好啊,又浓又密,黑压压的,像瀑布一样。一面剪,那客人一面默默流泪,从头到尾,一直在流泪。小见偷偷从镜子里看一眼,剪一下,看一眼,再剪一下,心里忐忑得不行,也不好问。谁知道呢,说不定,这一头长发是有故事的。
旷姐倒爽快,说剪一段就行了,你看着剪吧。小见赶紧说,得嘞。到底是河北人啊,痛快。就趁机推荐一些拉直技术,不伤头发,效果好。就是价格高了一点,可头发是大事呀,头发是女人的第二张脸。旷姐就嘎嘎笑,不是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吗?小老乡你真会忽悠。小见也笑,头发离脸更近嘛。就说好了,用一种离子烫,算是中档。然后焗一点颜色,黑的不好,太傻太愣。焗一点颜色更自然,也更时尚。比方说,浅栗色,姐的皮肤白,浅栗色显洋气。不信你拍个照片让朋友们看看,肯定都点赞。姐你先喝点柠檬水,我帮姐按一按。
镜子很大,几乎占了墙的一面,跟对面墙上的镜子相互映照着,显得店里格外敞亮。从镜子里,可以看见街上,来往的行人,汽车,一辆摩托车呼啸着,像闪电一样飞过,留下激烈的摇滚乐。花花在门口溜达,百无聊赖的样子。环环正在给一个男客人理发。那客人半闭着眼睛,听环环一张小嘴吧啦吧啦说个不停。忽然,环环在镜子里瞥见小见往这边看,就冲着那客人做了一个掐脖子的手势,龇牙瞪眼,嘴里却还在呱唧呱唧说着,一口一个哥,亲热极了。小见心里一笑。这环环是东北妞,五大三粗的,一开口就是东北话,带着浓浓的大碴子味儿。环环来的时候,红姐其实是不愿留的。红姐的意思,现在店里都是男孩子,她一个女孩子,孤单不说,也不方便。环环却说有啥不方便的,大家就把我当男的好了。见红姐犹豫,环环就跟红姐悄悄说了她的事儿,好像是上一个东家在三里屯那边,底下的那些话,他们没有听清。环环的眼圈红红的,眼泪到底是忍住了。红姐就叹口气说,作孽啊。去吧,帮那个客人洗头去。就留下了。
旷姐闭着眼睛,小见捏一下,她哎呀一声,再捏一下,再哎呀一声。小见心里烦恼,这女的真是,知道的是在按摩,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做什么呢。旷姐的肩宽,肩膀上的肉很厚,脊背好像是小案板子一样,一把抓不透。小见瘦长的手就有点力不从心。环环朝这边看,吐着舌头,一脸暧昧,小见心里的小火苗噌一下就着了,还麦当劳呢,我呸。
当初,他出来的时候,他爹其实是不大赞成的。一个大男人,天天摸人家头发,看人家脸色,算怎么回事呢。觉得这一行是低贱行当,说出来,还不如在工地上卖苦力名声响亮。他们在芳村,虽说是庄稼主子,可也是正经庄稼主子,种地吃饭,天经地义。小见不说话。他不能反驳爹,却也不能顺着他的意思。私心里,他是想出来闯一闯,碰一碰运气。挣不上钱,就算是见一见世面也好。村子里像他这么大的,有几个是闲人呢。小见从小就身子单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像乡下的庄稼人,倒像是那戏台上的书生。他爹就恨他这一点。他娘就说,蛇有蛇道,鼠有鼠道。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雀儿。芳村人把雀儿不叫雀儿,叫巧儿。(巧儿就是麻雀的意思。)正乱想呢,曠姐哎呀叫了一声。她说坏了坏了,哎呀,坏了。小见起初还以为捏疼了她,后来看着不像,忙问怎么了。旷姐说,花花,花花呢?扬起嗓子喊道,花花,花花。花花丁零当啷跑过来,在主人脚边撒着娇,蹭来蹭去的。旷姐嗔怪道,吓死妈妈了你,甭乱跑啊,街上坏人多,小心拐跑你。花花湿漉漉的眼睛看着主人,又幽怨,又谄媚。旷姐一口一个妈妈,好像那花花就是她孩子似的。看样子,旷姐总有四十多了吧。这个年纪,肯定成家了。当然了,也不能那么肯定,这里不是芳村,这是北京。在北京,好几十了不成家的多着呢。比方说,红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红姐的先生。据说,红姐是安徽人,早年来北京打拼,做过家政,做过保险,做过服务员,还有的说,做过那种行业。这种话,都是以前的老员工说的,压低了嗓子,语调暧昧。小见不大相信。红姐个子娇小,称得上清秀,眉眼干净,无一丝风尘味。眉尖微微蹙着,眉心里藏着一颗美人痣,好像还藏着一段哀愁。这样的一个红姐,怎么会呢。自然了,红姐肯定吃过很多苦头。她从来没有说起过从前。不像有的老板,喜欢在员工面前追忆,想当年如何如何。红姐不大来店里,偶尔来了,也是坐在前台那里,看着店里人来人往,眼神飘忽,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红姐在牡丹园住,也不见有男人接送她上下班。在他们眼里,红姐是神秘的,有那么一点深不可测。听环环说,红姐的车里挂着一只金色的卷毛狗,十分漂亮,由此猜想,红姐可能属狗。属狗是多大呢?他们掰着指头算了半天,好像都对,好像又都不对。议论一阵子,也就罢了。旷姐就不同了。旷姐爱说,什么都说。说起北京的雾霾来,恨得不行。她说老家的空气多好啊,老家的天蓝,云彩白,水都是甜的,能直接捧嘴里喝,哪像北京啊,简直了。还有这交通,乌泱乌泱的,哪来的这么多人啊。节假日我宁肯在家里呆着,出去干嘛呀,看人去?小见嗯嗯啊啊地应着,说可不是,没错。是不是。嗯呐。敷衍得她滴水不漏。心里却说,北京这么多不好,干嘛在这里呆着呢。真是。一口一个外地人,好像自己就是土生土长老北京似的。旷姐聊得高兴,被按得也舒服了,就说要试试那种最好的,哪国的技术来着。小见忙说,韩国。哎呀,姐真是太有眼光了。我这就给姐准备去啊。
环环那客人已经理好了,在镜子里左顾右盼。环环拿了一面小镜子,踮着脚尖,帮他照后头,说,哇,好帅啊哥,太帅了。那客人皱眉道,还是有点短了,这边,喏,就这边。环环说多精神哪,一点也不短,酷!那客人半信半疑,说是不是?
小见见环环翻着白眼过来,笑道,你那哥打发走了?环环说,谁哥呀。白叫了我。铁公鸡,一毛不拔。小见说,下回再叫甜点儿。环环说,我呸,那家伙还不老实,脑袋一个劲儿往我胸脯上蹭,靠。环环说要不是怕丢饭碗,我早大耳刮子上去了我。小见说,厉害了我的姐。环环叹口气,厉害不起来喽。一上午,白费了唾沫。我得查查,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出师不利啊。瞥见小见在预备东西,又高兴起来,说不错啊今天,别忘了呀,请客。
阳光透过玻璃门照进来,把一大片光泼在地下,有几片反射在大镜子上,亮闪闪的,刺得人睁不开眼。大街上,汽车飞快地驶过,扬起淡淡的飞尘。有人在人行道上走着,一面走,一面低头看手机,不一小心,撞在另一个看手机的身上,很尴尬了。天气晴好,是那种北方冬日的明朗澄澈。店里暖气很足,弥漫着一股洗发水的香气,吹风机嗡嗡响着,升腾起一种醉人的暖香,叫人头昏脑涨。小见穿黑色小脚裤,又瘦又紧,露着脚踝的那种,上身只穿了一件衬衣,下摆扎进皮带里面,外面套一件马甲,显得干净利落。干这一行,讲究的就是干净利落,没有多余动作。就算是有,也不能让客人看出来。比方说,现在,他一面给旷姐做烫头,一面跟她聊天,夹板把头发一点一点拉直,大约离开根部一寸多远,一直到发梢,缓慢的,但是果断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有时候,偶尔不大流畅,话就得跟上,解释受损发质对夹板形成阻力的原因。转身的时候,或者从马甲口袋里拿工具的时候,动作格外洒脱,屁股底下那凳子是带滑轮的,忽左忽右,忽前忽后,滑出花哨的弧线,简直像变魔术一样。旷姐在镜子里看着他,满脸赞赏,满脸信任。小见越发来了兴致,动作繁复,却准确有力,带着一种富有感染力的专业气质,又热烈,又冷漠,又专注,又倦怠。小见都被自己给迷惑了。旷姐说,哇,好棒,哇。少女一般。小见的脸唰的就红了。
这种头发费时间,总有三个多小时吧。店里的客人来了一波,走了,又来了一波,又走了。环环一时无事,闲着无聊,过去看小六子给一个小孩子剪头。小孩子顽皮,那妈妈左右按不住,急得一脸热汗。小六子却不急不躁的,拿一个玩具逗那孩子,趁他不注意,三下五除二就给他剪好了。环环说,牛,太牛。小六子说,别夸我啊,我会骄傲。环环说,德性。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妈妈了。小六子说,少胡说。你这思想,得改造了。
烫完头,旷姐看着镜子里,哎呀一声,说这是我吗?小见说,漂亮吧姐。像二十岁。旷姐说,真会聊天。小见说,真心话。旷姐就笑了。出门的时候,说你叫什么啊,下回还找你。
环环走过来说,今天你这个姐土豪啊。小见说,还行吧。环环切的一声,还装,你还装。小见说,不就是办了张卡吗,又不是金卡。小六子也凑过来,你们猜,这姐是干什么的?环环说,看穿着嘛,倒不大像有钱的。小六子说,废话,有钱的来咱们这儿呀。小见说,不一定,这可是四环以内,能买得起这一片的房子的,还不算富人?小六子说,对啊,也有可能是老北京,吃房租就养住了。小见说,不是老北京,我老乡。环环说,一口一个外地人,自己不也是外地的吗,势利眼,还不如那花花呢。忽然高兴起来,花花那小红袄,真逗。
中午果真就请了客,连着小六子,三个人叫的必胜客外卖,花了两百多。小见心疼得不行,暗暗怨环环心狠手辣,宰了这么一大刀。脸上又不好露出来,心想下午得想办法把这点钱赚回来。二月二还不到,好像是,北京这边也有剪龙须的说法。二月二,龙抬头。店里早就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了。
中午没客人,他们也不敢眯一会儿,店里的规矩是,没有午休。况且,也没有午休的地方。店里空间小,他们在通州那边住,几个人合租,房租分摊。有厨房,也不怎么开火。白天店里站一天了,谁还愿意钻厨房弄饭呢。天通苑那一片住的,大都是白天出去一整天,晚上回来睡,因此,被人们叫作“睡城”。有好几回,小见忙得晚了,就索性在店里凑合一夜。后来就慢慢动了心思,想跟红姐提出来,他夜里看店。省了房租不说,还省挤地铁了。无论高峰还是平时,五号线永远人满为患。还有一点, 他说不出口,合租麻烦,男女合租,更麻烦。环环大咧咧的,平时穿衣服也不严谨。小六子他不知道,反正他头一个就受不了。二十来岁,血气正盛,实在是活受罪。他真怕哪天闹出什么乱子来。自然了,这后一条,他不能跟红姐说。红姐虽然看上去挺文静,却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意思,他們到底是有些惧她。
下午客人不多。零零落落的,叫人打不起精神来。正放着一首流行歌,一个男人,痛楚地反复吟唱着,北京,北京——小六子埋头刷微信。环环在玩自拍。小见把地扫了,又把用过的毛巾收起来,扔洗衣机里,把干净毛巾叠好。客人用过的一次性杯子,也都收拾了。又跑到屏风后面,把洗发间的水渍碎发都清理干净。环环说,哎,别瞎忙啦,红姐又不在。小见不理她,拿着喷壶给那些绿植浇水。环环说,你先别浇,看看我这自拍水平。非逼着小见看照片,那些照片都修过图了,上面的女孩子,个个美若天仙。小见说,这谁呀,不认识。环环打了他一下,说你就说漂亮不?小见说,修图技术不错。环环气得不行,你这人,还能不能愉快地聊天了。
正说着话,门口一暗,来客人了。环环捅了他一下,小见抬头一看,叫道,姐过来了?
旷姐坐在椅子上,眼睛红肿,好像是刚哭过。黄着一张脸,没有化妆,跟上午比起来,仿佛换了一个人。小见给她倒了一杯水,也不敢多问。又给小六子使眼色,叫他把音乐调低一点。小六子却关了。店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安静得有一点尴尬。小见拉过一张凳子,半个屁股坐上头。旷姐慢慢喝水,喝了一杯,又喝了一杯。然后,她跟小见说,没事,我就是有点难受。小见说,怎么了姐?旷姐说,我怎么忘了呢,我怎么就忘了呢?小见心想,都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看来这二月二的讲究,旷姐老家也有。莫不是,她是想起老家的风俗了?不出二月二,不能剪头发。旷姐说,我怎么就忘了呢,不能剪。小见说,没事啊姐,如今都不讲这个啦。旷姐说,啊?小见说,就是在咱们老家,都不大讲这个啦,何况这是北京啊。不是——不是——旷姐的泪就又下来了,抽抽搭搭的,一时说不出囫囵话来。小见看她伤心,心里倒也酸酸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看来,旷姐是个有情义的。她宽宽的肩膀颤动着,那一头直发随着肩头一耸一耸,好像是无数个叹号,发出琐琐碎碎的摩擦声。真不该劝她办卡。也不该劝她烫这么贵的头发。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那个小牌子,脸上烧起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这是怎么了?北京这地方,真是厉害,把人变得,自己都不敢认自己了。他趁着倒水,把那小牌子又偷偷摘下来,藏进口袋里。心里咚咚地跳着,做贼一样。旷姐抽了一张面巾纸,大声地擤鼻涕,发狠似的,把湿漉漉的纸巾扔进垃圾桶里。小见看她渐渐平静下来,就慢慢拿言语劝慰她。旷姐看着镜子,说,王八蛋!就是个王八蛋!混蛋。狗日的。剪了。剪短。剃了。干脆剃了。剃了我当姑子去。我算是够了,受够了。像是跟小见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小见说姐?你说什么?姐?
镜子里,是冬天午后的大街。车马辚辚,像潮水一样汹涌着,在寒冬的阳光下,梦幻一般,显得又虚假,又游离。一个女孩子,一面走,一面对着手机说话,忽然间就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的,索性就蹲在马路牙子上。一个路过的男人,走老远了,还回头看她,是又惊又疑的意思。花花忽然跑过来,跑进镜子的正中间,一脸惊惶,穿着小红袄,小铃铛在脖子底下叮当乱响。一辆车嘎吱一声,在店门前停下来。
花花——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