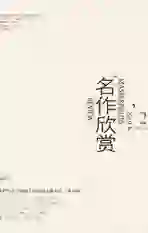不止是乡愁
2019-09-10易晓明
郑山明,文学硕士,研究员,现为湖南科技学院副院长。讷于言,拙于行。教过书,从过政,搞过管理。籍贯湖南永州,喝潇水长大,在潇湘流域学习、成长和工作。留恋乡土,痴迷乡情,关切乡亲,是一生不变的情怀。
易晓明(以下简称易):郑教授,非常高兴获得您惠赠的散文集《乡愁的滋味:那年·那事·那人》,我一口气将之读完,感觉它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熟悉的生活以及我们这代人所亲历的历史演变。在现代性语境下,回望散文里呈现的静态的乡村传统生活,以及它在逐渐融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遗失的美好,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我想就这本书,跟您做些交谈。
郑山明(以下简称郑):好的。
易:您的散文集《乡愁的滋味:那年·那事·那人》去年年底由东方出版社隆重出版,深得读者喜爱。您是什么时候产生写这样一本散文集想法的?开始着手写又是什么时候?
郑: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没有创作、出版散文集的想法。缘由和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我大学毕业后在高校教了几年书,然后转到地方党政机关工作,经常撰写各种领导讲话、调查报告,起草各类文件。这种“命题作文”,缺少自我表达,时间长了,难免产生疲惫和厌倦之感。为了调节心情,我在公文材料不多的时候,也会写一点其他文章。这类文章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时事杂谈,写了大约有二十余篇;另一种就是写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回味那并不遥远的青春岁月,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改革开放后,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一些美好的事物也在悄悄地、快速地消失,每次回到家乡,面对这种消失,心里总是隐隐作痛,并引发对孩童时期生活的频繁回忆。后来,觉得个人的回忆总是会淡忘的,于是就把这些陈年旧事付诸笔端,形成文字。记得最早写的一篇就是《过年》,是20世纪90年代末写的。在我个人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年节总是很热闹,很有人情味,虽然菜肴并不是很丰盛,但年味浓郁,大人小孩都特别开心。相比之下,现在的年节虽然隆重,也不乏热闹,却人人显得心事重重,笑容都是浮在脸上,而不是发自内心。所以在《过年》这篇文章里,我着重把童年时代过年的印象和感觉写了出来,把那种发自内心的热闹写了出来。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写了《挑煤》《烧窑》《娱乐》《成亲》等散文。
无论时事雜谈还是这类怀旧文章,写出来之后并没有往正式刊物投稿,偶尔在市内的一些内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如《过年》就在当时市委的机关刊物《永州通讯》上刊载过,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肯定。当时写这些文章,主要是想作为个人资料保存起来,没有其他想法。写着写着,有关乡村生活的散文在不知不觉中便有了三十多篇,十几万字。在亲人和朋友的劝导下,加之后来离开党政机关回到高校工作,有了寒暑假,能集中时间做一些个人的事情,便对这类散文重新归类整理、打磨,有了成册出版的想法。先是将稿子交给一家非文学出版社,该社一位资深编辑读了觉得不错,便推荐给了东方出版社,编辑部的专业人员审阅后给予认可,经过他们的精心指导和用心编辑,便产生了这样一本散文集子。我非常感念这些朋友,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的这些文章也许现在还存放在电脑里。
易:您书中有关于父母的篇幅。您提到一方面是表达对他们的感念,另一方面也是了却自己的心事,获得一份内心平静。事实上,这本散文集超出了家庭关系的范围。除了您提到的与父母情感这个动因之外,还有什么动因吗?
郑:对父母的情感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割裂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家庭伦理文化的国度,父母总是个人情感生活中最重要的存在。于我而言,父母亲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绝对是最重要的,对父母的情感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小时候,父母留存于我心中的是敬畏和抱怨;成年后,与父母的情感距离拉近,对他们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等到父母进入垂暮之年,存于心中的主要是感恩和牵挂;到父母过世后,与他们唯一的情感联系就是感念与追思。父母离我们越久,他们的音容笑貌、行为细节、个性特点却越发鲜活清晰。回到老家,行走在山野田畴,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劳作的身姿;看到家中积满灰尘的桌椅,便能在脑海里闪现母亲忙碌的身影;在路上看到一个与父母亲相似的背影,便能勾起对父母的绵绵思绪。这种对父母日渐浓郁的情感不停地在内心缠绕,逐渐化为斩不断、理还乱的个人情结。近些年,一直想找出一个头绪,把这份魂牵梦萦的情感疏导出来,却一直找不到切入点。意想不到的是,在回望和描写家乡那些年的人和事的过程中,对父母的感念和追思却自然而然地宣泄出来了。我想,父母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而是与家乡的山水、人事紧密相连的,他们是乡愁的组成,是乡愁的核心。我所描写的故园生活、农事,都有他们的影子。我写这本散文集子,虽然主要不是为了写对父母的感念,但这份情感确实给作品融人了灵魂与灵感。没有这份历久弥新的情感,作品会缺少最起码的感染力。
如果要寻找这本书主要的创作动因的话,可能是我个人对过去一些美好事物的留恋和不舍以及由此产生的失落。这在散文集的《序·遥望乡愁》中已有表达。我并不是厚古薄今的人,但老家农村的变化很多方面都背离了乡亲们的期望。大量的土地荒芜,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环境也遭到破坏,过去常见的老鹰、喜鹊、白鹭、狐狸、小松鼠等动物踪迹难觅。田园里热闹的劳动场面不复存在,很多青壮劳力走上了进城打工的道路,多数人在陌生的城市失去了尊严、人格、健康甚至生命。像散文集中“麻生”这样的人生悲剧绝非个例。我感叹世界发展变化之快,也悲悯那些美好事物消失之速。我就有了尽自己之所能把那些已经或即将消逝的美好东西记录下来的想法,不让它们这么快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忘。书出版之后,一些阅读过的同龄人跟我说,书中的描绘,让他们想起了过去的岁月,有一位已退休的朋友还特意找我多要了两本书,说一本送给老家村里的图书室,另一本送给读小学的孙女。一些年轻的朋友也说,看了此书之后,他们更多地了解了父辈的生活,理解了长辈故土难离的执拗,两代人之间也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一本小书,能发挥这么一些作用,我已心满意足。
易:二十四节气在2017年“申遗”成功,这是中国农民处理农事而获得的经验总结,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您的散文中,特别多地出现与节气、時令相关的生产、生活场景。您注意到了中国乡村文化与节气、时令的密切关系,它不只是生产指南,同时也成了浑融的生活形态,您能延伸性地谈谈这个话题吗?
郑:二十四节气确实非常神奇,在湘南农村被奉若神明,人们安排农事、摆布生活都离不开对节气的认知与应用,这些情况我在作品中也有涉及。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二十四节气在湘南农村的作用。
首先,二十四节气是安排农业生产的时间坐标。中国传统农业强调不违农时,中国传统农民强调顺应自然。顺应自然、不违农时,最重要的就是按照节气来安排农事。对于城里人而言,知道一年有春夏秋冬就行了,而对于农人来说,须将四季细化为节气。每季有三个月,每月有两个节气,一季便有了六个时间节点,每个节气做什么事,便有了明确的规定性。农人都会严格遵循规定,什么时候育秧,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投放鱼苗,什么时候施放肥料,都有严格的讲究。时至今日,科学技术发展神速,二十四节气的气候与物候特征依然准确,对农事的约束依然严谨。可以说,中国的农业生产始终与二十四节气相生相伴,没有二十四节气,就没有中国的农业文明!
其次,二十四节气衍生了规范乡民行为的伦理文化,农村生活出现了许多与节气相关的禁忌。湘南农耕文化中的禁忌比较繁杂,主要体现为不求发达、只求平安的生活态度,与“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互为表里。其中与节气相关的禁忌占了大多数,什么节气不能做什么事,都有口耳相传的民俗约定。以“立春”为例,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节气。这一天,大人不出远门,小孩不走亲戚;不准说不吉利的话,不准做不道德的事,特别是交节的那个时辰,约束更加严格。在传统中,对犯忌的事,可通过礼敬的方式来禳除,所以每到立春时节,很多农户都有给祖宗和各类神灵献祭的习惯。还有一些重要节气如惊蛰、夏至、立秋、冬至等,也都有相应的忌讳和祭祀活动。这些看上去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实质上是以二十四节气为依归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伦理文化,对乡民们的约束力至今还难以解除。
再次,二十四节气还包含生活智慧,体现了我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划分二十四节气的根本依据是阴阳的消长变化,乡民们根据二十四节气来判断么时候阳气最旺,什么时候阴气最重,并以此来打理生活,确定什么节气吃什么菜、穿什么衣,什么时候熏腊肉、烘板鸭、晒冬衣等,以此达到身体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互动,保障身体内部气息充沛、运转流畅,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正是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丰富经验和生活智慧,使它上升为世界文化遗产。
易:童年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华兹华斯写有很多赞颂儿童的诗歌,还有“儿童是成人的父亲”这样的经典句子,而且华兹华斯写的也是他在自己的乡村——湖区的童年时光。我感觉,您散文集的辑一“那些年”,大部分写的是您儿时记忆中村子的外形地貌、生活场景与趣闻趣事。能否谈谈您童年阶段的生活在您的人生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您觉得童年之于您的一生有怎样的意义?
郑:我在读研时就非常喜欢华兹华斯的作品,几乎阅读了当时国内能找到的他的全部诗歌。作为湖畔诗人的代表,华兹华斯厌恶悖离人性的工业文明,他把眼光转向了自然和童年。在他看来,自然和儿童都是最纯粹、最美好的,一旦走人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功利的污染,出现不同程度的天性扭曲。我国道教创始人老子,也十分称颂童年,认为人的童年时期最接近于“道”,希望人类社会返璞归真、绝智去圣,像儿童一样单纯。我们可以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深远则是不争的事实。
我的童年时代影响了我的一生。那时的湘南农村,生产工艺还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比如稻谷脱粒用的是最古老的扮禾桶,乡民们双手紧握稻梗用力将谷穗敲向上宽下窄的方形禾桶,效率十分低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人力打稻机。施撒田间的都是农家肥或草木灰,施肥方式可称作“定点施肥”:乡民们佝偻着腰行走在水稻的行距间,双手不停地从木桶里撮起草木灰插进一棵棵禾蔸里,既是节省肥料,也是精耕细作。乡民们敬畏自然、惜土如金的生活理念,他们知足常乐、注重亲情、与各类生物和谐共处的人生态度,都在我心中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多年的城市生活,都没能改变我小时候形成于农村的基本价值观。淡泊名利,不生贪念妄念,不占小便宜,勤勉工作等,是我最简单的座右铭;珍视缘分,以诚待人,重视耕读传家,追求内心的自由宁静,是我最朴素的价值取向;倾心自然,尊重生命,悠游山水,安恬岁月,则是我持久的生活习惯。可以这样说,我写这本散文集,除了回忆与怀念,也有展示我个人内心追求和审美情趣的意图。我的童年确立了我一生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影响了我为人处事的方式。也许这种带有小农经济色彩的观念有些消极,也或多或少影响了我的事业,但我从不为此而后悔,因为我保持了自己的本心和快乐。
易:您高中毕业到考上大学,中间在家务农时间也只有五年,而且那时是五年制小学、两年制初中和高中,高中毕业后也才十五六岁,那么年少的你,就能对整个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各种流程熟悉到如数家珍的程度。一个干几十年农活的人也不一定能总结得这么透彻,这说明您敏于学。这些是早已存于您的心中,还是您为了写书专门去做了阅读准备呢?这些活计,包括打石灰、烧窑等,您干过吗?
郑:是的。我1974年高中毕业后便回乡务农,到1979年秋去县城复读,在家乡扎扎实实当了五年拿“全劳力”工分的农民,加上初中毕业后休学一年在家劳动,总共做了约六年的农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熟悉农事也是很自然的事。我小时候算得上体弱多病,并由此导致一定程度的多愁善感,因而比一般的儿童有更强的好奇心,更善于和乐于观察一些生活和生产的细节,更愿意去做一些思考,自然对一些农事的流程和工艺的细节会更清楚一些。
与同龄伙伴相比,我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社队企业干过三年多,接触的劳作突破了传统农业的范畴。最初是创建水泥厂,后来又去当养路工,再后来又根据公社的安排去烧砖瓦,对这方面的工艺都相当熟悉。此外,我对其他手艺也很感兴趣,包括木工、织布、弹棉花、竹编、补锅等,只要农事不忙,都会站在旁边观看揣摩。至于普通的稼穑之作,可能身上流的是农民的血,都是一学就会。很多农活,只要你去做,就很容易掌握;只要你用心,就能把农事做得很精致。当然也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到什么年龄做什么农活,在大集体里还是有一定章法的。因为我年纪较小,犁田、耙田、打石灰之类带有一定危险性的农活没有去尝试,说起来算不上真正的庄稼汉。
这些以农村农业为题材的散文创作,只要静下心去回忆,就能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清晰起来,所以没有必要回老家去重新温习。再者,当下的农村已与往昔大不相同,很多生产工艺和流程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踪迹难寻,想去再度熟悉也没有条件了。于我而言,如果湘南农村的耕作和生活依然保留了当年的模样,我也许不会产生撰写这些散文的冲动。因为逝去,它们才显得珍贵;因为逝去,创作才多少有些价值。
易: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的国度。中国的政治文化结构,被称为“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而不是“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这在您的散文中也有体现。您觉得那个时期的湘南乡村,制度文化与民俗文化,各自有哪些形态?影响是怎样的呢?情感、心理、态度到价值观与民众认同感,民俗与人情,就不止于民俗文化,而包含有政治文化了。散文中对“四类分子”的批斗等,是不是涉及民俗中的政治倾向与认同问题?
郑:这个问题很有新意。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大集体时期湘南农民的动因,应当很有研究价值。据我了解,改革开放前,我们老家的乡民们世世代代都按照传统的规矩去做人做事,基本没有什么制度意识,更谈不上制度文化。大集体时期的湘南农村,一直是民俗文化占主流,主导乡民生产生活的始终是传统的道德文化和农耕文化。乡规民约从表面上看是制度文化,具有一定的約束力,但它们更多的是以民俗方式出现的,这些约定都是经过民众认可的、由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外化而成的契约,与其说是一种来自外部的规定,不如说是发自内部的自觉。在乡民们的生活中,自律是常态,他律是异态。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们都以自律为荣。来自外部的制度规定,只有与当地的民俗民风相契合,才能得到乡民们的认可和遵守。从负面看这是保守;从正面理解,这是坚守,是对内心信念的坚守。政府出台交公粮的制度,与乡民们认为皇粮国税、天经地义的民俗文化相契合,所以得到自觉执行。但凡与民风民俗相矛盾的东西,哪怕来头再大,也很难在这里推行。1966 1976年,工厂里的工人、学校里的学生,都纷纷离开自己的岗位去串联、武斗甚至打砸抢,历朝历代最具造反精神的农民却依旧在田里劳作。因为他们深信,不种粮食就会饿肚子。这就是他们简朴而正确的价值观,也是最本质的民俗文化基因。我在散文《开会》里描述的早请示、晚汇报,可以说是一种制度规定,但不久之后就不了了之,因为这种制度不能与民俗契合。我觉得,当年的湘南农村,浸润乡民生活的主要是民俗文化,制度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
易:这个散文集是您的第一本文学创作成果,您推崇什么样的文学?您的文学观是怎样的呢?您最喜欢的作家作品是什么?创作过程中您秉承什么样的文学思想?
郑:说起来,我看了不少文学作品,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观。年轻的时候,喜欢看故事生动、情节复杂的作品,一度痴迷金庸的武侠小说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后来更倾心于一些史诗般的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作品,近来还重新细读了《红楼梦》《飘》等名著。反思起来,我喜欢的作品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历史厚重感,二是有扎实的生活基础。我认为,任何缺乏生活根基的应景之作、任何缺乏文字打磨的赶时之作,都是注定没有生命力的。
这种文学倾向也无意识地体现在我自己的写作中。这本散文集虽然由多篇短文组成,但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我力求通过多个生活场景、生产活动和多个人物的刻画,展现一幅意蕴深厚的湘南农村大集体时期的历史画卷,引起读者的联想和深思,特别在人物群体的描写上,我努力揭示那个年代特有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追求。麻生随遇而安,其简单的梦想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瞬间破灭;秀秀经历了情感的幻灭,却始终对人生和社会抱有坚定的信心,还有理发的驼子、头脑简单的木鱼脑壳等,他们都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那一个”,他们身上既有中国传统农民的底色,又充满了湘南农村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中施与他们的冲突、恐慌、纠结和痛苦。当然,作品的最后效果还需要读者和时间的印证。
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您非常关切农村,您对城镇化进程带给乡村的影响怎么看,它在永州老家有什么体现?
郑:我个人认为,城镇化对乡村施与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毋庸置疑,城镇化的进程丰富了农民的物质生活,基本上使他们摆脱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但就我老家的情况看,城镇化带来的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一是农业和农村的凋敝。由于青壮年都奔赴城市,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农业生产力大幅下滑,曾经热闹的村落和田野人烟稀少,缺乏生气。先是大量的旱地荒芜,曾经种植黄豆、红薯和小麦的山坡长满荒草,外出务工的农民将自己的责任田租给别人耕种,每亩收取两三百斤稻谷抵作租金。后来随着农业生产资料的大幅涨价,粮食生产变成亏损的活儿,再没有人愿意承租他人的稻田,大量良田闲置抛荒。那些外出打工赚了钱的乡民们,带着钱和图纸在老家的责任田上建起了一栋又一栋小洋楼,那些被祖祖辈辈视为命根子的良田,从此不可逆转地消失了。二是环境的污染。大量新的农业技术和生产资料进入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业生产的劳动难度,但它们对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破坏是空前的。除了地块板结地力下降之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很多鱼类和鸟类绝迹,生物多样性不复存在。地表上的污染更是触目惊心,空农药瓶、废塑料袋无处不在;原来甘甜的泉水、清澈的河流踪迹难寻,人畜饮水受到污染,粮食和蔬菜的农药残留严重,患癌和疑难杂症的村民日益增加。住房建设缺乏规划,废水废物得不到科学有效的处理,村中富有地域特色的建筑不断颓败,成了臭气熏天和繁殖“四害”的垃圾场。三是教育的隐患。有人说,中国城镇化进程是以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这话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不是没有道理。很多青壮年去沿海打工,把小孩留在老家交给老人抚养。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一些劳务输出集中的地区,留守儿童占学生比例高达六成以上,隔代的亲人对他们要么过分溺爱,要么严酷打骂,相当一部分孩子性格孤僻,行为乖张,厌学逃学辍学,成为教学管理最头痛的一个群体。学校再努力也无法替代父母亲的影响和亲情的浸润。这些学生慢慢走向社会,他们能否适应社会并为社会所接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四是人性的沦落。城市发展与市场化相生相伴,市场经济的利己观念不断地冲击和蚕食着温情脉脉的小农经济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老家乡民传统朴素的利他思想不可逆转地败退于强大的市场法则。进到大城市打工的他们,对市场经济和市场法则陌生而隔阂,一些怀揣美好理想的年轻人来到大城市就迷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的流浪于街头,有的走上犯罪道路。在古老的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物化”,亲情友情让位于物质利益,良知和天性得不到尊重,传统的忠孝廉耻不再有约束力,一些农村女孩到城市里以出卖肉体和色相谋生,一些子女双全的老人得不到应有的赡养和照顾,冷漠成为乡村人际关系的基本底色。散文集中“麻生”的人生际遇从很多方面反映出城镇化带给乡村和乡民的影响,让人在牧歌式的悲悯中感叹城市化带来的失落和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