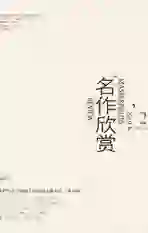“接力”还是“拒迎”:关于章太炎对“五四’’运动态度新探
2019-09-10张吕坤
张吕坤
若从“五四”精神内涵的承传迎拒,以及新旧之辨来说,“章太炎和‘五四”颇具言说价值。不仅因为后来“五四”健将多为其学生,有思想、做派的纠缠,更因为章太炎学术实践所处时代的关键位置。晚清学人,或者说“戊戌学人”,因其求强运动和维新变法,和“五四”多少有“接力”关系。这里的“接力”涵盖多方面因素:思想启蒙、学术代际、政治风气、语言文章、融通中西等,且接力姿态可顺承,可递增,亦可扭拒。这也是近年来学界强调“五四中的晚清”和“晚清中的五四”的原因所在。
但回到历史现场,章太炎对于这场被迅速经典化的“五四”运动持何种态度?至今著文并不见多。
近观:一个旁观者?
在《自定年谱》中,章太炎有对“五四”这一天发生事情的描述:“五月四日,京师学生群聚击章宗祥,欲尽诛宗祥及陆宗舆、曹汝霖辈,三人皆伪廷心膂,介以通款日本者也。事起,上海学生亦开国民大会,群指和议为附贼。”
这段仅有的对“五四”正面描写的文字,章太炎给予学生的笔墨寥寥可数,或许他仅仅认为这也是他经历众多运动、革命事件中的一个罢了。但是,敏锐的章太炎应该是嗅到了一些不同的氛围,从他的前后行动来看,他对“五四”运动的主要缘由和议题有切实了解,并且时刻关注着事态发展,尤其是其对于国家政事的影响。
但在“五四”运动的思想方面,章太炎似乎并没有过多反应。和章太炎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截然不同,另外一拨人迅速做出了反应。5月9日,北大教授兼教务长顾兆熊的文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活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发在(《晨报》上,这是迄今关于“五四”运动最早的评论。稍后的5月26日,学生领袖罗家伦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5月27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另一位学生头目康白情则在北大校长的指示下,率北京学生代表南下请愿,风头一时无两。他们对于“五四”运动迅速做了定性:爱国思想、顺应潮流、国民之精神,之准确之全面,让人惊诧。
也并非所有的“辛亥派人物”都对这起运动漠然处之。在辛亥智识群体中,朱执信便在信中表露过:“弟现在视察中国情形,以为非从思想上谋改革不可,故决心以此后力量全从事与思想上之革新,不欲更涉足军事界。”不得不说这位曾和章太炎于《民报》共事的革命宣传者聪慧敏锐且思想力极强。
另一位辛亥派理论家戴季陶则写下《“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学潮与革命》一系列讨论革命、工人学生运动、启蒙的文章。他说:“五年五月四日,是新文化对于旧势力,平民主义对于官僚主义,民族自决主义对于侵略主义举行大示威的日子。由这一个大运动,才能唤醒许许多多青年鼓起对于旧势力宣战的决心。”“驱逐恶魔,撤废障蔽,这就是我们中国青年唯一任务。”
虽然有朱、戴等少部分的敏感者,但大部分辛亥派要员对“五四”并不感冒。辛亥一派内部对于“五四”运动的看法并不统一,或者说重视程度很不一致。孙中山在1920年1月《与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一文中指出:“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但孙中山此种主张随着他的去世,亦在北洋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中失势。可以说,在1919年前后,辛亥一派心志和关注的焦点全然不在“五四”运动上。
和辛亥一派大部分人员一样,章太炎匆匆记录“五四”青年群聚之事后,笔锋一转,回到了其时他最为关心的南北问题上。章太炎自辛亥革命后,便极其热心介入实际的政治事务。当年转投袁世凯,谋得东三省筹边使一职,后因并无实际决策权而放弃,转而把希望寄予黎元洪。章太炎毕生对黎元洪保有好感,对黎元洪的政治投靠和信任,很大程度上遮掩了他对时局、文化走向的判断,这次“五四”运动也不例外。如要完全勾勒章太炎对“五四”的态度,必须从他的政治实践和学术取向两处着手。
袁世凯倒台之后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对章太炎政治观点影响最大的莫外乎19121918年出使西南诸省,以特使身份斡旋广州军政府与西南军阀间的关系。章太炎表露过此次行走之心迹:“仆此行自广东过交趾,如昆明。北出毕节,至于重庆。沿江抵万县,陆行至施南。南抵永顺、辰州,沿沅水至常德,渡洞庭入夏口以归。环绕南方各省一币,凡万四千二百余里,山行居三分一。”虽然西行斡旋艰苦,劳心耗神、呕心沥血,但收效甚微,唐继尧、岑春煊、陆荣廷等军阀对其阳奉阴违,让章太炎愤恨不已。11月底,写下(《章太炎对于西南之言论》,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言和不过希恩泽,言战不过谋吓炸,里巷讼棍之所为,而可以欺大敌欤?要之,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这次西南之行,让章太炎对南北议和失去信心。就在章太炎看清西南军阀的面目,寄希望黎元洪复位总统重开国会之时,传来徐世昌就任中央政府大总统的消息,这让章太炎难以忍受,现实政治企图(联合西南)和个人政治抱负(攀附黎元洪)双双受阻。此刻章太炎身心俱疲,全然没有意识到一场异于往常的政治、文化大变革悄然而至。
在经历了三年软禁、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西南政阀的首鼠两端之后,章太炎似乎大致明白了其时下政局的混乱与不堪。但同时,章太炎身上不谙世故、意气用事的一面又依旧强烈,其间还混杂着个人强烈的理想抱负。章太炎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长于计划,而短于任事,这是他们作为学者的底色,并不为过。但运筹帷幄与决胜千里毕竟不能混为一谈,政治便是如此。在写给吴承仕的信中,章太炎说:“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学人痕迹之顽固可见一斑。”
中观:依然致力于“增进国民道德”与“增进爱国的热肠”
“五四”运动前,章太炎的政治、学术活动显得相当纠缠,反反复复出入“政治”和“学术”之间,显得挣扎和困顿。他对“五四”运动有意无意的忽略,无疑也受到这种情感因素和潜意识判断的影响。
1917年3月,章太炎在上海发起亚洲古学会,并召开了第一次大会。这并不是章太炎第一次参加亚洲范围的学术、政治活动。1906年章太炎甫到日本便参加了社会主义讲习所和东亚联合协会,不久,章氏又加入亚洲人道主义兄弟会,和一群来自中国、日本、缅甸、菲律宾、越南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印度中心”(India House)谈论、交换意见。慕唯仁认为,章太炎很有可能从这些活动中将他身上原有的反帝主義、民族主义、联亚主义和社会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相融合并置。上海亚洲古学会,可以说是章太炎《民报》时期“联亚主义”的延续,表明了章氏身上独特的“民族主义”思想。章太炎在学会成立大会上演讲:“予在日本时即拟发起亚洲古学会,以与全洲人士提倡旧日之文明,旋以他事牵绊,未克实行。今日此会初设,而各国人士均联袂偕来,斯则昔年筹画,或可成为事实矣。”确认了这一点。
“迩来西势东渐,我亚人群,有菲薄旧日文明,皮傅欧风,以炫时俗者。亚洲古学,益虑沦亡。”这是亚洲古学会的目标,这里并不能认为章太炎是反对西学的,不管是之前的“国粹”运动还是现如今的古学会,章太炎对待古学、传统文化的态度、立场只有两个:革命和文化保存。前者在他那场震撼人心的东京演讲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動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而文化保存主义,则是章氏作为一个学者的一贯主张,只不过在他晚年表现得愈来愈清晰。
但章太炎的文化保存主义和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五四”运动的确存在鸿沟,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其中涉及两种知识谱系强烈碰撞的问题。就在“五四”发生的前些日,《国故月刊》出版,章太炎就其中学术问题给吴承仕写过信,信中说:“大抵远西学者,思想精微,而证验者绝少,康德、肖宾开尔之流,所论不为不精至。至于心之本体何如?我与物质之有何如?须冥绝心行,默证而后可得,彼无其术,故不能决言也。陆、王一流,证验为多,而思想粗率,观其所至,有绝不能逮西人者,亦有远过西人者,而于佛法终未到也。”可见他对于中西之学有过深入思考,他对传统学术的固守坚持同时是其选择后的结果。有些学者认为,在“订孔”和反对设立孔教这个问题上,章太炎和“五四”一派拥有相同的反对立场,由此章太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这实则是混淆了这两者间最基本的批判立场和价值取向。章太炎之“订孔”并非反对儒家学说,而是其背后的维新派保皇思想。“五四”运动之后,章太炎在回复柳诒徵“诋诃孔子”辩难时,称年轻“订孔”实乃“狂妄逆诈之论”,这表明章太炎强烈的民粹思想,和“五四”一派是决然不同的。
远观:“欲迎还拒”的复杂态度
《时报》在报道3月4日亚洲古学会成立状况的时候说:“日昨章太炎先生假江苏教育会发起亚洲古学会,其宗旨以研究学术、联络群谊为前提,绝不含有政治上之臭味,斯亦近日不可多得之学会也。”《时报》只说对了一半,亚洲古学会虽行学术之名,但不能排除政治的因素。早在章太炎初涉时局时,他便写过《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文章,提倡联合日本、兴办学会以达到排满和资产阶级维新的目的。到达日本后的联合印度,至当下学会联合,都可视为一脉相承的章氏民族革命思想,虽然期间含义多有变迁,但都暗含政治目的。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学会,是近现代传播思想、团结帮派力量进行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三件法宝。长期浸淫其中的章太炎不可能不知道其中之利害。“五四”前的这次学会事件,虽然前后召开了四次会议,但随着章太炎同孙中山南下,学会和《大亚洲》杂志都不了了之。它不是一次纯粹的学术活动,而应把其放置在章氏民国政治实践和个人野心上来思考。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一派迅速、积极地做出反应,且回应之准确、全面同样让人诧异,这也许表明“五四”运动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学生运动,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时代的潮流趋势。在新文化运动酝酿、行进这么多年后,人们已经隐约感觉到一场大变革的来临。
章太炎对“五四”运动的忽视,首要原因在于其时他更关心南北的政局走势和个人的抱负野心。参见1919年他的(《自定年谱》,“五四”爆发时,他更在意、着墨更多的是朱启钤和唐绍仪的和谈问题,因为这确乎和他这几年的辛苦工作更为相关。新文化运动的文言、白话,或者大众文化、文学观念兴起的争吵熙熙攘攘,的确没有勾起章太炎的兴趣和注意。在为被捕学生做了通电声明后,章太炎旋即卷入更为复杂的“联省自治”政治旋涡中。其次,在学术层面,“五四”运动及其背后新文化的激进思想也不对章太炎胃口。此时章太炎更为看重史学之于民族和民众的长久安身立命的价值,看重汉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而“五四”一派恰恰要拿语言文字、传统礼教开刀,这让章太炎对其并无特别好感。
在章太炎看来,“五四”运动只是当时政局形势的一部分,准确地说,是南北斗争的一部分。而从章氏的学术出发,“五四”一派学人甚至没有立论的基础。于章太炎,“五四”运动既不是某种开始,也不是某种结束,而是“戊戌学人”在1898到1928这三十年间一个尴尬境遇的缩影。